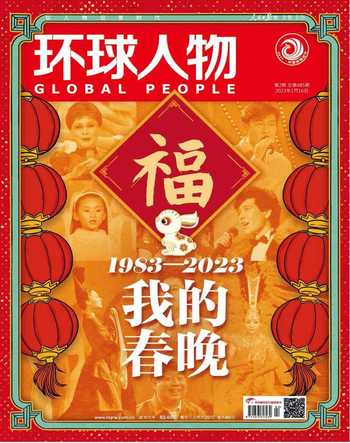馬伯庸的歷史狂想
陳娟

馬伯庸
這段時間,作家馬伯庸正處于休整期。他最近變得有些嗜睡,每天保證睡夠8小時。之所以說“嗜睡”,是因為此前他經常整夜失眠,“能清晰地聽到自己的腦神經如生銹齒輪一樣咯吱咯吱轉圈”。后來去睡眠門診看病,醫生告訴他這屬于大腦皮層興奮過度。
興奮過度,是因為他的大腦時刻處于高速運轉當中。出門時,他習慣背一個黑色的雙肩包,里面裝著電腦,一有空閑就打開碼字,不論是在人聲嘈雜的咖啡館,還是人來人往的候機廳、候車室,他都可以奮筆疾書,心無旁騖。哪怕有空閑,不寫作、不閱讀,他也停不下來,甚至有一種焦慮感。眼睛一刻也不能閑著,等地鐵等紅燈或者坐電梯的時候也必須看點什么,否則便會陷入嚴重的無聊和驚慌。有時上廁所沒帶手機,他都要順手拿過旁邊的牙膏、洗發水,一字一句讀完上面的說明。

2022年9月,馬伯庸在杭州參加最新長篇小說《大醫》的新書發布活動。

正是在這種長期的高速運轉中,馬伯庸成了一位高產的作家——幾乎一年一本,且本本暢銷。2022年,他連續出版兩部小說《大醫》和《長安的荔枝》,前者聚焦清末民初的醫療與公共衛生事件,后者書寫唐代小吏運送荔枝的故事。“其實,每一部我都希望寫一個以前沒碰過的題材。如果一定要找共同點的話,他們都是一種‘歷史可能性寫作’,在真實歷史的夾縫中去尋找空間,在不改變歷史的前提下,以一個全新的現代視角去詮釋。”馬伯庸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馬伯庸信奉法國19世紀小說家大仲馬說的那句話:歷史是我掛衣服的釘子。從事寫作的20多年,他一直在做的,正是“把小說掛在歷史的釘子上”。
《大醫》的寫作,緣起于 2017年。
當時,馬伯庸受邀到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參加一個講座。因為到得早,便去參觀了院史館。華山醫院前身為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中國人自建的第一家現代醫院。院史館是一棟西式二層小樓,又名哈佛樓,里面的展廳不大,大部分是紅十字會與華山醫院的歷史文獻、照片、文物等。他邊看邊拍照,發現幾乎每一件展品都能勾連到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最終串聯成一條隱線,與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如影隨形。
“我有一種直覺,這絕對是一個上好的題材。從一家醫院或一個醫生的視角,去審視那個時代,想想都興奮。”講座結束,馬伯庸回到酒店,把拍下來的照片傳進電腦,一一檢視后,創作的念頭冷卻了下來:一是醫療很專業,是他不曾碰觸過的領域;二是如果寫作,不光要熟知近現代史,還要熟知上海城市發展史,以及附著其上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軍事、交通、教育、飲食……思前想后,他將所有照片存檔,留待日后再說。
“但我一向喜新厭舊,好不容易碰到一個新鮮的、陌生的題材,心里還是有一種創作的沖動,一直揮之不去。”100年前的中國醫學是什么樣的?當時的醫生是如何對患者進行治療的?這些問題一直撩撥著馬伯庸。之后,他有空就到哈佛樓轉一圈,也有意識地去買一些與民國醫學相關的書。如清末的《藥學大全》、上世紀60年代的《赤腳醫生手冊》《農村常見病防治》,還有《吳淞衛生示范區檔案》《紅十字會歷年征信錄》,等等,越積越多,堆滿了一個大書架。
到了2018年,馬伯庸決心要寫下這個故事。他四處查找資料,翻遍學術文庫、二手書市場、各地圖書館,走訪一些老醫生和老專家,甚至考慮過找個醫科大學報一門基礎課,學上一兩個學期——當然后來沒成行。2019年底,他敲下“華山醫院,第一章”幾個字,開始寫作,整整兩年后,完成80萬字的《大醫》。
《大醫》的時間跨度從1904年至1950年,聚焦中國第一代公共慈善醫生。有三位命運、性格、出身截然不同的主人公:日俄戰爭中死里逃生的東北少年方三響,倫敦公使館里跑腿的廣東仔孫希,不甘于安享富貴的上海富家女姚英子。3人一開始都是天真懵懂的少年,后來在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相識,開啟了醫海生涯,最終都成長為出色的醫生。
如今再回憶整個寫作過程,馬伯庸覺得最難的是細節。“我給自己設定一個原則:一個故事只能發生在一個時代,也就是說這個故事必須是遵循著特定的時代背景、特定的邏輯才發生,換個時代就不成立。”寫《大醫》時,他堅持每天看20份影印版《申報》,看當時的人怎么說話、怎么發廣告、怎么寫社論,研究當時的流行語,了解當時的人對歷史大事件有什么樣的反應……將自己徹底放逐到民國時的大上海。
在各種細節中,最麻煩的要數醫療細節。一開始,馬伯庸請了幾個醫生朋友做學術顧問,但后來發現這樣行不通。他們都是接受了現代醫學培訓的精英,熟知正確的治療方式,而他需要的是符合當時年代的、可能是“錯誤的治療方式或理念”。
“比如盤尼西林,也就是被視為‘抗感染神藥’的青霉素,1928年才發現,真正出現在實驗室是1938年,最后投入量產,市場上能夠買到差不多要到1945年。如果我寫一個人在一九二幾年就接受了抗生素的治療,信息就不對了。”馬伯庸說。最終,他通過查找資料,發現當時的人們用的主要是磺胺。此外,還有一些醫學冷知識:1904年還沒有“血型”概念;1910年已經有了點滴,但還沒有調速管……
遵循“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馬伯庸寫下那段百年前被遺忘的醫療史。在他的筆下,方三響、孫希、姚英子、沈敦和、張竹君等人一一登場,歷經上海租界鼠疫、淮北水災、青幫食物中毒等公共衛生事件,投身到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中去,并以他們的人生經歷回答:學醫有什么用,能不能救中國。

馬伯庸的作品《風起隴西》《長安十二時辰》《長安的荔枝》。
“我寫《大醫》,就是想讓大家記住那批最早的醫務工作者——他們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下,能夠不計私利,忘我地、奮不顧身地去為中國四萬萬同胞尋找、提供健康支持,我覺得有必要為他們樹碑立傳。”馬伯庸說。
對馬伯庸來說,《大醫》的寫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常常會因考證一個小細節而花費大量精力。“就像長跑一樣,跑得久了累了,就需要休息。”但他的休息不是完全“躺平”,而是“寫一個短篇來調節一下”。
2020年5月31日,有朋友在微博上說:“楊貴妃要是馬嵬坡沒死真逃到日本,是不是再也吃不到荔枝了?”馬伯庸看到后,靈感迸發:人們在談論“一騎紅塵妃子笑”時,大都關注“妃子笑”,卻很少有人關注“一騎”。那個時代,在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沒有先進的保鮮技術的情況下,荔枝是如何運到長安的?
為解決這個疑問,馬伯庸寫下了《長安的荔枝》,講述司農寺上林署令李善德突然接到命令,從嶺南運送新鮮荔枝到長安為貴妃祝壽。其間,李善德經歷官場博弈、同僚算計、路線設計、保鮮試驗等,最終把兩壇荔枝運到長安,實現了“妃子笑”。小說中,李善德花費11天運送荔枝,馬伯庸的寫作也僅用了11天,“是一次酣暢淋漓的寫作,整個人進入忘我的狀態,腦海里的東西噴薄而出”。
《長安的荔枝》完成后,最先刊載于《收獲》長篇2021春卷上,2022年底出版單行本。不少讀者從書中看到自己的生活,與疲于奔命的李善德產生共鳴,“大城市買房落腳、職場情商博弈、不得已的違規逾矩等,‘社畜’的生活是那么相似”。
甚至有讀者和馬伯庸說,故事看到一半便不忍看下去了:“我每天上班就夠苦的了,為什么休息時看篇小說還要再遭一次同樣的罪?”馬伯庸就想,小人物的窘境與煩惱,真是不分古今的,“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從最本質上來說,我們去書寫古人,去演繹過往,其實是在尋找舊日與當下可以共鳴的點”。
無論是《長安的荔枝》,還是《大醫》,都延續了馬伯庸之前的寫作。他最為人所知和稱道的歷史小說,大都是“在歷史縫隙中尋找其他可能性”:在《風起隴西》里,他寫不被亂世聚焦的陳恭、荀詡等人,在蜀漢和曹魏的秘密情報線上“暗戰”;在《三國機密》里,他為漢獻帝虛構了一個孿生弟弟劉平,寫他與一干人等斡旋于各方勢力之間,平亂世、安天下;在《長安十二時辰》里,他寫沒能在史書上留下痕跡的死囚張小敬,化解突厥狼衛企圖摧毀長安的危機;到了《長安的荔枝》,他又寫一個不起眼的長安小吏……在真實歷史背景下加入懸疑、推理等元素,講述史書背后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
“我喜歡去追逐小人物身上那一瞬間的光輝。這光輝很短暫,但足夠耀眼,那一瞬間他就是天下的焦點、是時代風云的源頭,能夠讓歷史進程微微改變一下方向。”馬伯庸說。其實年少時讀書,他也喜歡帝王將相的故事,看他們馳騁沙場、縱橫天下,“滿滿的英雄氣概”。但慢慢地,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多、閱讀的加深,他開始看到“更多的人”。
“大時代就是由小人物、普通人聚合起來的,千千萬萬個他們產生了同一個訴求,這訴求就形成了歷史的浪潮,英雄則是被潮流推上浪頭的人。”馬伯庸說。
他至今還記得,2021年曾去看了一個三國志特展,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兩塊磚:一塊磚上的文字,大約寫于黃巾起義的前14年,是一個砌墻修墓工人寫的,大意是“你們快把我逼死了,我現在就等著‘倉天乃死’的那一天和你們算總賬”;還有一塊磚,造于晉滅吳的那一年,上寫“晉平吳天下太平”,是一位已過耄耋之年的老人寫的——也就是說,這個老人從出生開始,等了80多年才等來一次和平。而這樣的老人,并不只有一個。
“這兩塊磚正好代表了三國亂世的開始和結束。從兩塊磚就能看出,是小人物的心聲匯聚到一塊,才形成了歷史的潮流。”馬伯庸說,正是這些小人物決定了歷史的走向,真正創造歷史的是人民。
在馬伯庸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都有一種相似的氣質——充滿理想主義的固執:《風起隴西》里的荀詡,頂著官僚系統的內部掣肘,孤獨而堅定地追查著真相;《長安十二時辰》里的張小敬,受盡誤解仍要拯救整個長安城;《長安的荔枝》里的李善德,拼盡全力尋找破局的辦法,“就算失敗,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離終點多遠的地方”……
但現實中的馬伯庸,并不固執。“我不軸,我的座右銘就四個字:隨遇而安。”馬伯庸說。這與他的童年經歷有關,父母從事機場建設工作,少時的他只能跟著父母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不斷搬家,從小到大一共轉了13次學。“對小孩來說,面對不斷出現的陌生環境,你的生存哲學就是好好適應它。”
馬伯庸走上寫作之路,也是順其自然。那是1999年,他在上海讀大學,混跡在一個名叫“黃金獅子旗”的文學論壇。當時為了省錢,他常常拿著軟盤到網吧上網,先把論壇上的文章拷貝下來,再拿到學校的機房看。有一次,軟盤壞了,打開后里面有一半文件是亂碼。他心里著急,不斷地搗騰軟盤,不小心碰到鍵盤,眼看著屏幕上打出兩三個字,忽然想到自己好像也可以寫,“于是我就試著往下寫了幾句,發現還挺通順的,就開始了我的寫作生涯”。之后,他的生活就從每周下載變成每周上傳——將自己寫的文章發表在論壇上。

根據馬伯庸的作品改編的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根據馬伯庸的作品改編的電視劇《古董局中局》劇照。
“那時愛寫一些自嗨的東西。”馬伯庸回憶說,完全不管別人怎么看,也沒有什么遠大的抱負。2003年,他到新西蘭留學,學習之余,依然混跡在各大貼吧、網站,惡搞式地改編一些武俠、科幻、靈異故事。當時,他天馬行空,模仿古龍筆調,寫下一個無聊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故事《留學生七種武器之泡面》;他還以中國古典白話小說的風格,講述一段西方人耳熟能詳的英雄傳奇《歐羅巴英雄傳》。那些文字,很多都是和網友閑扯或討論的結果,他自稱那是一段“嘻笑怒罵的寫作時期”。
回國之后,馬伯庸在外企當白領,朝九晚五,閑暇時間寫作。2005年,他寫《風起隴西》,將現代諜戰情節嫁接到三國背景下,演繹出一段精彩的三國諜戰傳奇;2010年,他考證曹植、曹丕、甄宓之間的八卦關系,寫成散文《風雨〈洛神賦〉》,獲得人民文學獎。頒獎辭中寫道,馬伯庸“抽絲剝繭,咄咄逼人,對歷史可能性的探究具有一種童言無忌的機敏和快樂”,網友則評價他是“一本正經胡說八道”。也是從那時起,他開始有意識地往歷史小說上靠,在歷史的縫隙中閃轉騰挪、恣意狂想,“歷史上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內幕,如果沒有,那么就制造一個出來”。
2012年《古董局中局》的誕生,則是馬伯庸真正邁向暢銷的轉折點:“之前是小打小鬧,之后進入了大眾視野,很多人陪我一起玩。”第一部上市,一下子就賣了50多萬冊。2015年,全系列4部完成,銷量過百萬。在之后影視市場的IP熱潮中,《古董局中局》和《三國機密》又成了馬伯庸最先被改編的作品。
也是這一年,馬伯庸算了筆賬,發現寫作的收入已遠遠超過工資,于是下定決心遞交了辭呈,希望奪回自己人生的節奏,嘗試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之后的他,的確實現了部分“自由”,但并沒有真的“散漫”起來。他依然筆耕不輟,書一本一本地出,不少作品被影視公司看中,改編成影視劇。最火的莫過于《長安十二時辰》,2019年播出時,熱搜不斷,整個夏天大家都在討論劇情、長安城布局、大唐妝容與服飾等,連劇中張小敬吃的水盆羊肉也賣斷了貨。

2019年8月,馬伯庸在西安講座。
面對不斷攀升的作品銷量和紛至沓來的影視資本,馬伯庸保持冷靜。他會有意識地調節自己的創作,以避免“被熱度沖昏頭腦或者被流行裹挾”。同時,他也坦然于商業成功和市場擁抱:“寫作就是一個暴露的過程,暴露給更多的人是好事。”
馬伯庸每天8點多到工作室寫作。他將工作室特意選在一所學校附近,下課鈴響,便起身活動10分鐘,上課鈴響,繼續伏案寫作,一直寫到下午5點,“下課”回家。不動筆的時候,他喜歡做史料研究,經常四處淘書,大都是冷門書,每每讀到好玩的,他都記下來——可能會成為未來作品的素材,偶爾也分享在微博上。他電腦里有一個文件夾,取名“坑”,一旦有創作的念頭,他就打開一個新文檔寫下來,等待時機成熟,再拿出來寫。
對于自己的創作和身份,馬伯庸一直有著明確的自我定位——一個有趣的歷史小說作家。《長安的荔枝》之后,他想寫一系列“歷史技術類小說”——從技術的角度講歷史故事,繼續歷史狂想:比如詹天佑如何在晚清混亂的時局中修京張鐵路,海瑞如何在幾個月內花很少的錢疏通了吳淞江,一個修長城的小工如何驗證“是孟姜女把長城哭倒了”……
“我不考慮太多,只要寫得過癮就行。寫作,對我來說僅僅是對舒適感的一種追求,既不是多么神圣的使命,也沒有一定要寫出宏篇巨著。歸根到底,就是一種率性而為,若算計太多就失去意義了。”馬伯庸說。
1980年生于內蒙古赤峰,作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風起隴西》《古董局中局》《長安十二時辰》等,人民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茅盾新人獎得主。新書《大醫》《長安的荔枝》于近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