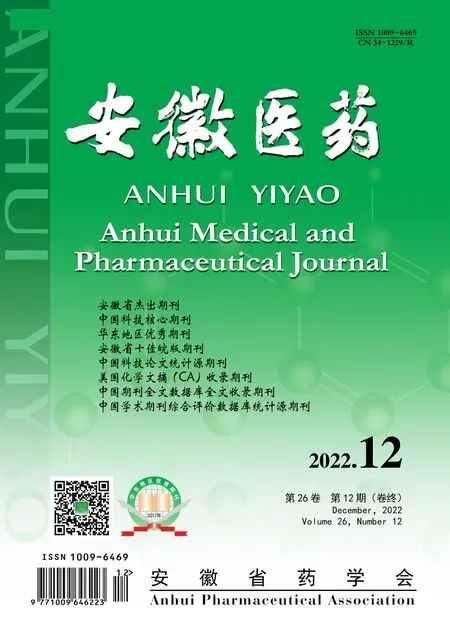淺談運用補益法辨治消化道惡性腫瘤化療后的不良反應
閔希瑞,潘楊
作者單位:南京醫科大學附屬腦科醫院中醫科,江蘇,南京 210000
惡性腫瘤是提高人類預期壽命最主要的障礙[1]。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統計,全球172個國家中,70歲前人群主要死因是惡性腫瘤的占一半以上。在我國,惡性腫瘤病發率顯著增長,惡性程度及難治性不斷增加[2]。2018年全球惡性腫瘤新發病例1 810萬中,中國占380萬,發病人數居全球第一[3]。國際癌癥研究組織2018年發布的全球癌癥統計報告顯示:消化道惡性腫瘤涵蓋世界十大惡性腫瘤之五——腸癌,胃癌,肝癌,胰腺癌和食道癌。排除性別差異,消化道惡性腫瘤發病率占所有癌癥類型的30.47%,死亡率占41.01%[4]。21世紀消化道惡性腫瘤現已成為導致我國國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和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5]。
化療是內科治療惡性腫瘤最主要的方法[6-7]。隨著多學科綜合治療不斷發展,新輔助化療和同期放化療等多種化療方案廣泛應用于臨床,在拓寬化療施展邊界的同時,也放大了化療副作用的影響[8]。如今,惡性腫瘤化療后的諸多不良反應正成為臨床亟待攻關的新難點[9]。
化療后不良反應涉及人體多系統多器官。表現于外癥狀各異,個體差異大,西醫極難進行綜合的診斷與治療[10]。傳統中醫在辨證與辨病方面獨具特色,善于根據腫瘤及化療損傷共同致病的內在原因和整體狀況綜合審度,整體觀念設計多維治療方案,密切觀察個體病情進退及時調整用藥方向,對于化療后不良反應的治療臨床療效顯著[11-12]。
1 治病求本,病證結合
中醫使用“有毒藥物”治療惡性腫瘤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周禮·天官·醫師》記載:“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中醫認為天下無不偏之藥,無不偏之病,藥的偏性謂之毒,唐代王冰注解《黃帝內經·素問·藏氣法時論》:“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謂之‘毒藥’也”。化療應用于臨床雖然僅半個世紀,但其藥物特點、作用療效與中醫“攻邪毒藥”卻無二致。相對于分科明確,專病專科專治的現代西醫學,更重視人體的統一性和完整性的中醫療法,能更好地兼顧處理有毒副作用藥物施用所導致的多種不良反應。遵循“治病必求于本”,化療用藥后癌毒雖減,但機體正氣更虧,因此補益先天之本與后天之精尤為重要[13]。
臨床辨治中絕不囿于中醫對癌病的定義,而是充分考慮西醫診斷及檢查結果,在掌握病人病情發展和治療經過的基礎上,從當下癥狀入手,四診合參,辨病與辨證相結合,重視氣血陰陽、寒熱虛實的綜合分析,據病據證組方用藥,回歸中醫手段解決化療的遺留問題[14-15]。
2 填精益髓,厚先天之本
化療的毒性作用機制復雜,除了影響機體的一般狀況外,主要損傷骨髓細胞、黏膜細胞、毛囊細胞等增殖較快的細胞。而在中醫系統中,這些機體受影響較大的功能部門都與中醫概念“血”的化生密不可分。腎藏先天之精,精能生髓,精髓是血液化生的源泉和動力。因而欲解其苦,必先填精益髓,以厚先天之本。
2.1 疲乏無力腎為人體陰陽之根。《諸病源候論》論虛勞羸瘦時提出:“精髓萎竭”則“血氣虛弱”。“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髓傷元氣虧耗,水火陰陽失調,命門火衰,表現在外為面色黧黑,畏寒肢冷(下肢為甚),精神萎靡。治以溫補腎陽,藥用肉桂、巴戟肉、肉蓯蓉。
2.2 骨髓抑制骨髓抑制導致白細胞減少、血小板減少和貧血[16-17]。《靈樞·經脈》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干,脈為營……血氣乃行”。腎為先天之本,主骨生髓,藏精化血。化療后三系減少,是為氣血不足,腎精虧虛,治以益氣養血,填精益髓,補血與破血兼施。藥用炙黃芪、炒黨參、炒當歸、淮山藥、白芍、熟地、枸杞子、女貞子、三棱、莪術。
2.3 皮膚、黏膜毒性(面色晦暗、口干口潰、皮膚瘙癢)腎是元氣之根,元氣發生,推動一切組織器官的生理活動,借三焦之道布達全身,為生命動力之源泉。腎精不足,氣血運行無力,瘀血留滯,面色晦暗無華。治以補益氣血,化瘀解毒,藥用紫丹參、炒白術、當歸;血虛生熱,熱蒸津液,陰血虧耗,發為口干、口潰。治以滋陰降火,養血潤燥,口干藥用南北沙參、麥冬、玉竹、川石斛、天花粉、百合、大生地;口潰藥用黃柏、丹皮、生石膏、知母;血虛生風,血行而后風自滅,故治以補氣養血,涼血祛風,藥用當歸、紫丹參、白鮮皮、地膚子。
2.4 周圍神經毒性(手足麻木不溫)肝藏血,腎藏精,精血同源。肝不生血,則氣血不足,血脈不暢,氣虛則麻血虛則木,治以益氣和血,化瘀解毒,藥用黃芪、桂枝、白芍、拔葜;腎陽為人體陽氣之本,溫煦肢體、臟腑的,若陽虛則推動無力,機體功能減退,導致畏寒怕冷,四肢不溫。治以健脾益氣,溫補腎陽,藥用黃芪、黨參、桂枝、白芍、干姜、巴戟肉、肉蓯蓉。
2.5 肝毒性腎中精氣充盛,則肝有所養,血有所充。肝血失養,疏泄無力,血不能藏,氣滯血瘀,濕熱蘊蒸,發為肝功能異常,治以補益肝脾,利濕退黃,清熱解毒,藥用當歸、白芍、炒黨參、炒白術、茯苓、山藥、丹皮、澤瀉、淡茱萸、夏枯草、垂盆草。肝氣不舒,發為脅痛,治以破血行氣,和中止痛,藥用三棱、莪術、木香、烏藥、青陳皮,白芍、延胡索。
3 益氣健脾,開后天之源
脾為后天之本,運化水谷精微,供應機體正常功能活動需要。化療藥物刺激性強,多直接干擾細胞DNA、RNA及各種大分子功能物質的合成,因此在殺傷腫瘤細胞的同時,也對正常細胞功能及免疫系統構成巨大打擊[18]。最明顯表現在脾胃運化功能障礙,水濕飲食內停,出現疲乏、納呆、腹脹腹瀉、惡心嘔吐等癥狀;此時若機體本身正氣不足,無力抵抗化療藥物毒力,癌病纏綿、日久不愈,機體更無以充養,故病人出現疲乏、氣短、中氣下陷等癥狀。
此時加入中醫輔助抗癌,應根據病人的具體情況辨證,病證結合,實現精準醫療。經方為主,時方為佐,重視脾胃,扶正為主,隨癥加減,主要通過中藥減輕化療不良反應、增加飲食、提高生活質量、提升免疫等,實現減毒增效的目的,使病人能平穩度過艱難的化療階段,提高化療耐受性,增加療效。
3.1 不思飲食化療損傷胃腸黏膜,使腸道功能失調,打破消化系統微環境平衡,癥狀表現為病人化療后食欲不振、口干口中無味,納少納差,體下降。此時中醫治療宜配合補益胃氣,健脾助運,安脾和胃以開后天之源。食欲不振,胃氣不和,治以運脾開胃,方用香砂六君、參苓白術散加減。藥用砂仁、陳皮、炙雞金、焦山楂、六神曲。
3.2 嘔惡痞悶,食入即吐中醫言化療藥性味苦寒,易傷脾胃陽氣。惡性腫瘤其病本身代謝活動旺盛,消耗機體能量物質多,虧虛正氣,虛弱脾胃。此二者互結,致使水谷精微運化失調,脾胃失養,胃氣上逆,常表現為心下痞滿、惡心嘔吐[19];脾胃失職,氣機升降不利,水濕無力運化,應治以和胃降逆,化濕醒脾。方用理中湯、小半夏湯加減。藥用木香、砂仁、黨參、茯苓、白術、炙甘草、陳皮、半夏等。
3.3 大便不調正常人體中,腸道微環境維持著微妙的平衡,10萬億腸道菌互相制衡共同維護腸的消化吸收。化療作用下,大量有益菌被清除,菌群平衡被打破,胃腸免疫屏障薄弱,防御功能下降。中醫此時宜攻補兼施,理氣健脾,化瘀解毒,既幫助腸道功能恢復,又幫助清除有害菌,止瀉與通便共行。方用參苓白術散為基礎,健脾止瀉湯、麻子仁丸加減。藥用炒訶子、炒白芍、炮姜、肉豆蔻、赤石脂、五倍子、柏子仁。
4 醫案舉隅
男,66歲,主訴:口干、手足不溫數月。
2019-09-09 初診,左下肺癌術后5月余,ⅢA期,已行化療3周期,刻下手足不溫,口干,大便干燥,干咳無痰。舌紅中裂,脈細。脾胃陰傷,滋陰潤燥,扶正祛邪。用藥:南北沙參各15 g,天麥冬各15 g,玉竹15 g,川石斛15 g,天花粉15 g,百合15 g,大生地15 g,太子參15 g,五味子5 g,枳實10 g,陳皮6 g,瓜蔞皮15 g,半枝蓮15 g,石打穿15 g。14付。
2019-09-23 二診,大便已軟,咳嗽痰粘,口干,頭暈,舌紅細裂,脈細,養陰潤燥,化痰止咳。用藥:初診方,去太子參、半枝蓮,加川貝10 g,枇杷葉10 g,白蒺藜10 g。14付。
2019-10-08 三診,藥后諸癥改善,口干雖減仍存。氣陰兩虛,前方化裁。用藥:前方去瓜蔞皮,加冬瓜子30 g,炒薏米30 g。21付。
2019-10-29 四診,諸癥均緩,病情平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