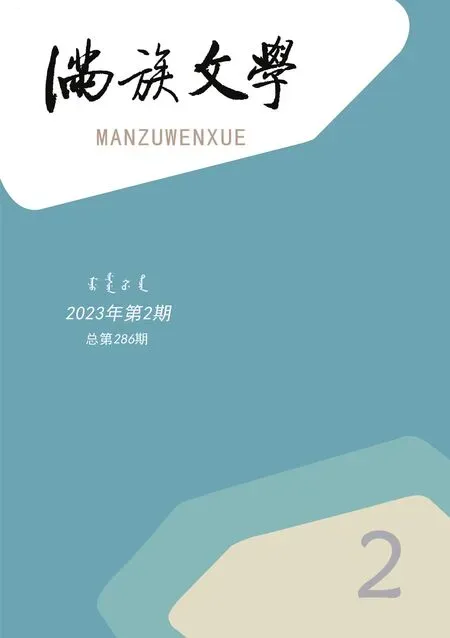主持人語:于曉威
2023-02-01 21:17:24
滿族文學 2023年2期
黃風的短篇小說《馬燈,馬燈》在隱約的年代背景下,敘寫了兩個農村少年渴望了解外面訊息和通向外面世界的故事。這篇小說的線索極其單純,甚至單調,然而,作家的真實用意并不在于“所敘之事”,而在于“如何敘事”以及“敘事為何”。這種跟文學上的“成長”或“反叛”有關的命題,作家賦予了新的敘述寓言和策略。對于主人公——兩個農村少年來說,“成長”究竟是意味著成功,還是經歷?又究竟,怎樣的成功才叫成功?相信在今天,每個人都會有屬于自己的判斷。
王曉燕的中篇小說《創作者》,關注的是婚姻、家庭和女性心理領域。作家在作品中插入了類乎“元敘事”的功能,以及“莊周夢蝶”式的心理與現實的互嵌結構,反映了關于個體的“疾病的隱喻”,折射出的是現代女性在生活、家庭、情感以及社會上潛在的心理危機。
付桂秋的中篇小說《收梢》,目光聚焦的是一個中年男人與他彌留之際的繼父之間的故事。相同的題材似乎并不多見,付桂秋采用了極其日常和現實的角度,游刃有余而波瀾不驚地打撈出一個普通男人可感的親情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
許冬林的短篇小說《看姑娘去》是本期欄目又一篇可稱優秀的作品。這篇小說值得再三味讀之處在于,作家以極其詩意和適宜的筆法,營造了一個大家都熟悉、或者似曾相識的人生環境與圖景,這種環境和生活細節看似抒情,但是詭詐之處在于,作家以草蛇灰線的鋪墊,漫不經心的對話和場景,極具反差地埋設了一個人不同的人生狀態和命運。它令人感慨。不僅是故事令人感慨,連帶的是作家的寫法。好的小說,以及它敘述語言的玄機妙用,一般而言,就是這么自然出脫的。
衣水的短篇小說《第十三只白鸛》,具有文本的實驗性。作品融現代科技、自然物種領域和發生在人的意識結構深層的演繹,探討的是性別、角色和愛情的命題。這種新穎的嘗試值得贊許。
猜你喜歡
光明少年(2024年5期)2024-05-31 10:25:59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當代陜西(2022年4期)2022-04-19 12:08:5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s(2022年1期)2022-02-08 03:23:58
娃娃畫報(2019年11期)2019-12-20 08:39:45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百花洲(2014年4期)2014-04-16 05:5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