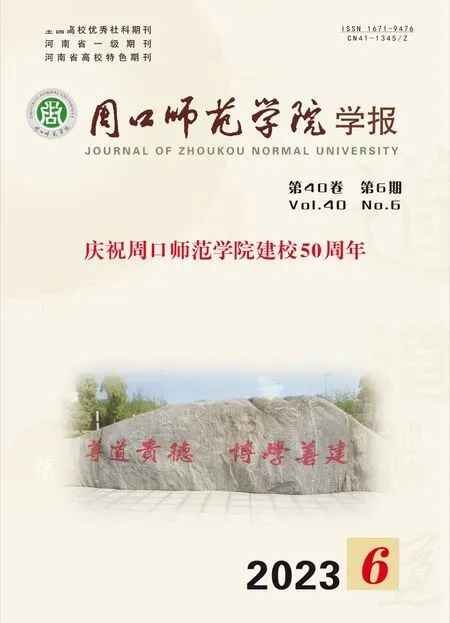作為中華民族認同的貴州石門坎體育文化闡釋
苑青松,胡艷玲
(1.韓山師范學院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廣東 潮州 521041;2.韓山師范學院 政法學院,廣東 潮州 521041)
貴州石門坎是我國西南邊疆的一個多民族(苗、彝、回)小山村,地處滇黔川三省交界處,地形封閉,跋涉艱難,氣候惡劣,面積142平方公里。至新中國成立前還是土司制度,1.6萬口苗族(大花苗)集體淪為彝族土司的奴隸,數千年來處在自然和人為的雙重封閉之中,正如石門坎苗族溯源碑所言:天荒未破,疇咨冒棘披荊。古徑云封,遑恤殘山剩水。訪桃源于世外,四千年莫與問津[1]233。 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里發生了一場苗族文化復興運動,使石門坎由一個荒蕪之地變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2]4。正因為它在“三零”(政治、經濟、文化資本皆為零)平臺上取得的突出文化成就,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石門坎研究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
縱觀石門坎研究成果,主要體現為歷史事實考證和石門坎文化成就描述兩個方面,作為歷史回歸性研究,時間過去了100多年,石門坎資料的遺失以及親歷者的相繼離世,使得許多史實逐漸模糊起來,對其進行認真考證并呈現其真實面貌理所當然。研究者在學校體系、苗文創制、三語教學、個體研究、全民閱讀、社會改良等方面形成了豐富的成果。然而,“石門坎苗族文化復興運動為什么會發生”這一根本問題并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結論,如果把外國傳教士的“偶遇式”發動作為根本動因的話,那最初“四個苗族人”找到傳教士柏格理要求讀書而不是信教以及石門坎出現的狂歡式讀書現象就無法解釋。從何入手才能準確揭示石門坎文化現象的根本動因呢?石門坎苗族體育文化賡續于苗族整個發展史中,以石門坎體育文化為對象,弄清其背后的文化動因,一方面可以形成對石門坎現象的文化解釋,另一方面也可發現少數民族興衰的文化決定。
一、場域理論分析框架
場域理論是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提出來的經典理論,其創新之處在于提出者以概念束(場域、資本、慣習)的形式來定義場域,突破了“就事論事”式的下定義方式。之所以如此,在于他認識到社會文化學是一個主客觀互動的復雜系統,任何單一的概念都難以完整反映主客觀要素的真實面相及二者之間的互動規律,為此,他創造性地運用復合概念來對應研究對象的復雜性,進而實現對研究對象的準確闡釋。
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強加于占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之上的決定性因素之中,這些位置得到了客觀的界定,其根據是這些位置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占有這些權力就意味著把持了在這一場域中利害攸關的專門利潤(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權——的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situs),以及它們與其他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支配關系、屈從關系、結構上的對應關系,等等)[3]134。布迪厄把場域看作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用場域來觀照某種文化現象就能使行動者的位置得到客觀的界定,不同行動者所處位置關系也能得到清晰的呈現。
布迪厄在場域描述中提出了資本概念并對資本進行分類:資本表現為三種基本的類型,這就是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文化資本還可叫作信息資本(informational capital),它本身存在三種形式:身體化的、客觀化的和制度化的。社會資本,則是指某個個人或是群體,憑借擁有一個比較穩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識的關系網,從而積累起來的資源總和,不管這種資源是實際存在的還是虛有其表的[3]162。有什么樣的資本就有什么樣的行動,就有可能占據相應的位置,資本使行動者與位置的互動關系得到生動的表達。
布迪厄在資本概念基礎上又提出了慣習概念,慣習,就是知覺、評價和行動的分類圖式構成的系統,它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又可以置換,它來自于社會制度,又寄居在身體之中(或者說生物性的個體里)[3]171。從定義中可以看出,慣習形成了對傳統主客觀二元對立的超越,它使行為與結構走向一種新的鏈接。慣習是一套持續的、可轉換的性情傾向系統,具有持續性和可轉換性,同時也具有歷史性和生成性。
場域的價值在于把貌似蕪雜的文化體放置在特定構型中,運用資本和慣習概念來呈現位置及行動者的性情傾向,最終得出行動者的行動是什么和為什么的判斷,三者內在地形成場域理論的分析框架。為此,我們運用場域分析框架把石門坎體育文化放置其中,通過梳理其基本構型、資本類型和慣習特征等,為發現這一文化現象背后的根本動因提供理據。
二、石門坎苗族三階段體育文化描述
我們把石門坎體育文化的階段特征描述作為對其整體面相呈現的手段,把體育文化與歷史發展統整起來,為此,把石門坎體育文化的發展分為歷史記憶、復興嘗試和現實實現三個階段。
(一)歷史記憶:“耍山梁子”上的游戲
威寧為古苗獠之地,位于黔省西鄙,跨南嶺,左右烏江、盤江兩大徑流導源于此,萬山重疊,山高氣寒,火耕水耨,一貧壤也[4]3。在威寧縣城西北約170公里處,有一個叫“卯嶺南”(苗語)的地方,它處在烏蒙大山深處,這里山高壑險,濃霧不散,跋涉艱難,據此,它還有著“涼山”“屙屎不生蛆的地方”“云的那一邊”“未知的中國”等稱呼,這充分彰顯著它地處偏遠、氣候惡劣的自然屬性。要去“卯嶺南”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先從云南昭通去70公里以外的威寧縣中水鎮,中水鎮是進入“卯嶺南”的門戶,二者相距40公里,這110公里的行走難度絕不是數字可以體現的,可以稱其為路,也可以不稱其為路,所謂路只是環繞在群山之間的一條灰白色印痕,即使到21世紀通了微型面包車,也需要7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威寧古縣志上記載:岡阜盤旋,山崖險扼,羊腸小路,十倍蜀道[4]5。縣志生動地描述了烏蒙山層層隔絕的地理形態和跋涉艱難的生存條件。
在烏蒙群山之中,“卯嶺南”只是一片相對開闊的地方,它的東面橫臥著野鷹梁子,北面坐落著陡峭的猴子巖,西面聳立著3000米的薄刀嶺,南面是一道東西走向深不可測的石門坎溝,“卯嶺南”就處在這個封閉的“四邊形”之中,這個“四邊形”算起來總共也不過4平方公里大小,但它卻統轄周邊142 平方公里的廣闊區域。進入的路原名叫“獅子洞”,只能先爬上由亂石形成的細線般的坡道,再由坡道頂端的洞口進入,酷似《桃花源記》中陶潛筆下桃花源的入口,因此,封閉是其地形的最準確概括。從“卯嶺南”往東,翻過野鷹梁子的北口,在崎嶇危險、荊棘密布的天然小道行走約2公里的路程,有一座酷似圓柱體的山體聳立著,其頂端被自然之刀橫向削平,形成一個橢圓形且相對平整的橫截面,酷似樂器小鈸,東西長約200米,南北長約100米,地表長著一層茸茸的青草,青草低矮整齊,沒有一根雜草抬頭,不得不讓人贊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橢圓形小鈸”整體上由四周向中心傾斜,傾斜的坡度不大,底部稀松地長滿了不知名的低矮雜樹,這就是被“卯嶺南”人稱為花場的耍山梁子。耍山梁子四周雖有些山巒,但相對較矮,在重巒疊嶂的烏蒙山中,呈現出一種難得的空曠。由于海拔的原因,云霧不時從腳下飄過,耍山梁子酷似一個空中舞臺——空曠、縹緲而潔凈。
古歷每年5月5日,“卯嶺南”142 平方公里區域里的1.6萬口“大花苗”(苗族的分支之一)從四面八方來到耍山梁子,他們身上的“花衣服”十分醒目,衣服以白底為主,男裝酷似古代將士的戰袍,肩上披有肩甲,胸前掛有胸甲,女式比較艷麗、柔和,花邊圓領的上衣,下邊是白底并繪有圖案的百褶裙,舞動起來楚楚動人[5]45。大花苗聚集后,一些男性拿著叫“蘆笙”的樂器,蘆笙是苗族最早的樂器,葫蘆笙亦瓠笙……列管六,明清以后都記作蘆笙了[6]294。蘆笙曲調也是苗族最早的音樂之一,它的聲音低沉哀怨、曲折悠揚。特定時辰一到,耍山梁子上蘆笙驟然響起,穿著盛裝(苗族人叫花衣服)的男子吹奏著蘆笙,他們的隊形時而縱橫交錯,時而前后變換,在此起彼伏的節奏中,個體的夸張與群體的整齊完美融合,他們以大號笙為軸心,其余以此靠右排列,由最小的一支開頭領奏,然后全部齊奏。蘆笙樂曲逐步點燃了人群的熱情,龐大的人群開始舞動起來,男人們圍繞著大蘆笙旋轉起舞,姑娘們則排列環繞于蘆笙隊外,踏著蘆笙的拍節而舞,熱烈而有序。宏大有序的舞蹈之后,一壇壇燒酒被抬上來,人們拿著牛角互相挑逗著痛飲起來,酒的烈性助推了人們的狂熱,耍山梁子頓時變成了粗獷、狂躁、無序的狂歡場。在酒精刺激下,一些男女開始有了不潔凈的行為,直至爛醉如泥、不省人事地沉睡過去,此時的耍山梁子又歸于死一般的寂靜。
耍山梁子上神秘粗獷的狂歡游戲卻沒有一個他族觀眾,成為延續千年的“獨角戲”。
(二)復興嘗試:運動場上的運動會
1888年,基督教新教循道公會的英國傳教士塞繆爾·柏格理(Samuel Pollard)來到云南昭通,雖然他意志堅定、充滿智慧、待人友善,但在昭通近20年的時間里也只有幾個阿婆信仰了基督教,絕望之際,山里四個苗族漢子的到來為他迎來了轉機。然而,四個苗族漢子的第一個要求竟然是讀書,傳教士們從來沒有遇到這樣的情形。他們好奇地記述了當時的情形:
他們對于柏格理的第一項要求,是請他教他們讀書。它似乎一直為這些人頭腦中的一個明確想法[7]527。
處于絕望之中的柏格理絕不可能放棄一絲一毫的機會,他善意地接待了四個苗族漢子,當時他也只能為苗族漢子提供開水之類的東西,這微薄的善意卻引起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轟動。他們把柏格理的耶穌理解為“愛穌”,把“愛穌”的到來稱為“蚩尤佬”又活了,他們因此爭相傳頌并成群到來。這微不足道的關心所引起的巨大震動是傳教士們沒有想到的,這足以說明關心對他們來說有多稀少,絕望已成了這一民族的特性,苗族對待壓迫的唯一武器是麻木、忍受和逃跑[8]139。
苗族的貧窮、道路的艱難、學習的熱情和土司的恐慌等因素促使柏格理決定到山里傳教辦學,面對苗族人讀書的訴求柏格理只能順勢而為。在石門坎辦學過程中,他發現失去文化幾個世紀的苗族人學習起來十分困難,苗族沒有文化已有4000余年,讀漢語書比什么都困難,要有銅鑄的身體,鐵鑄的肺,橡木腦袋,蒼鷹的眼,要有圣徒的心靈,天使的記憶,麥修拉的長壽[9]19。這種困難帶來的是自我懷疑甚至可能招致學習熱情的消退,如何增強苗族人學習的信心成為首要問題。人類學上說:人生游戲[10]352。游戲是人的本質,因此,游戲是一種令人愉快的、自我獎賞的活動[10]351。同時,它也是跨國界、跨民族的共通性文化活動。西方發達的現代體育、柏格理個人的體育天賦、石門坎苗族的現實閾限等因素,促使柏格理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突破閾限的切入點——體育,他以現代的視野完成了由石門坎游戲到體育的改造,這種改造不是強硬的阻斷而是靈活的置換。
“耍山梁子”變成了運動場,由沉醉的花山節“花場”變成了振奮的端午節運動會。端午節運動會屬于苗族社會公共場域的運動會,是具有全員性質的綜合性運動會,從其項目設置上可見一斑。
石門坎運動會共設置四類項目:一是由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現代田徑、球類等體育項目,如足球、排球、單雙杠、短跑、鉛球、鐵餅等。二是石門坎傳統游戲項目,如爬山、拔河、賽馬、斗牛、獨輪車賽、蛙跳賽等。三是生活習俗項目,如穿裙、割亮篙、績麻、穿針等。四是學習識字項目[5]94。從項目設置上看,石門坎體育呈現出本土與外來的統整性,尤其是把識字設置為運動會項目十分特殊,也十分罕見。
端午節運動會開展得也十分熱烈。親歷者(張國輝)的描述:
學生方隊中男生一身黑色(黑衣、黑褲、黑帽)的學生服,女生穿著苗族傳統的花色盛裝,男女生分列站定,顯得既華麗又威風凜凜。鑼鼓聲、銅號聲一響,他們喊著響亮的口號,邁著整齊的步伐,變換著各式隊列,令群眾耳目一新,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
一頭黃建牛獲得了斗牛的第一名,獲勝者和牛都披掛著大紅花繞場一周,觀眾熱烈地鼓掌,獲勝者十分的驕傲和自豪,仿佛獲得了世界冠軍一樣。
運動會的重頭戲是足球,大家都很喜歡足球,開展得也最普遍,水平也很高。最后的決賽是在光華小學與大關小學之間進行,光華小學獲得了最后的勝利,獎勵也很特殊,拿紅旗繞場一周。大關小學輸了還不服氣,把紅旗搶走了,我們也不跟他計較,反正大家高興就行了。
石門坎光華小學修建了具有現代性質的運動設施——大球場和游泳池,其性質屬于學校教育的一部分。
游泳池是用青石砌成的兩個相連的、東西走向的池子,女池在上,男池在下。女池長5.7米,寬8.3米,深1.12米;男池長10.9米,寬8.3米,深1.41米。現在它外面的墻體雖已倒掉,但這足以顯示它是一個室內游泳池。
大球場是一個東西走向、腰子形狀的場地,東西長度約97米,兩端都是懸崖已經沒法再延伸了。兩端的寬度分別為19米和15.6米,中間的寬度約為20米,它的北邊是一個斜坡,南邊是深不見底的石門坎溝。從數字信息上看,它與西方標準的足球場比起來是一個極不規則的大球場。
這兩個修建于19世紀末的體育場所,以1904年中國施行現代教育的時間節點來判斷,應該是最早的足球場和游泳池了。足球運動的開展更令人驚訝。親歷者(楊明光)的聲音:
苗族人精神萎靡不振是一個大問題,足球可以提振精神。大家都愛踢足球,20世紀30年代,貴州省主席楊森帶隊伍路過石門坎,他也喜歡足球,軍隊足球隊和石門坎光華學校隊踢了一場球賽,結果輸了,還把我們的隊員帶走了幾個呢!
農民也打足球,小孩在地里踢,沒有真正的足球,他們就用草或線繞成“草球”。
苗族人在體育上的突出表現,使他們確信了自我,有了自信,并把體育上的勝利和自信遷移到勞動和學習上,充分表達著無所不能的自我。
建校盛況:
苗家的男女老少不分晝夜地往返于石門坎和冷杉林之間,人們與時間賽跑,一天往返路程最多的居然達一百六七十公里,我們總說自己很忙但不累。人們在勞動中拼耐力、拼力量、拼貢獻,比誰流的汗水多、砍的樹多、拉的物多、往返的次數多![王文憲口述]
讀書盛況:
遠近的苗民都各自背自己的包谷——食糧,及行李,來參加一年一次的神圣的讀書會,讀書的人數不一,有的頭痛齒落,有的龍鐘潦倒,有的血氣方剛,這期間有多少是父子共讀,但集合在一塊兒讀書絕沒有父子老少之分[2]253。
以上資料表明,石門坎上形成一種難得一見的奇觀,這種以讀書為訴求的狂歡游戲在體育史上十分罕見。狂歡形成了兩個令苗族人自豪的結果:一是石門坎由沉醉千年的蠻荒之地一舉成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二是苗族人的活動不再是“獨角戲”,而是引起了族群外他者的強烈關注。一位富裕的土司已經把兒子送到石門坎,于是就發生了一位年輕土目與一個苗族孩子坐在同一條長板凳上的事。在幾年之前,此類事情是不敢想象的[7]161。
(三)現實實現:現代規范的體育課程
新中國成立后,石門坎場域得以被重塑。在共產黨領導下,石門坎成為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的一個鄉鎮,代表舊有政治力量的土司、傳教士、國民政府已不復存在,石門坎苗族成為各民族中平等的一員,他們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土地、房屋、牲畜等。在此背景下,石門坎體育文化又一次發生轉變,即由基督救贖為特征的體育活動變成了社會主義體育課程。但由于受地理條件、經濟水平和發展觀念的影響,學校的體育課程仍然在傳統游戲場所和傳教士遺留的舊址上開展。
習近平說,新中國成立后一些“一步跨千年”進入社會主義的“直過民族”,又實現了從貧窮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歷史性跨越。所有深度貧困地區的最后堡壘被全部攻克。脫貧地區處處呈現山鄉巨變[11]129。習近平的話準確概括了少數民族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兩次跨越,石門坎苗族就是典型的“直過民族”,新中國成立意味著他們從奴隸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新時代到來,石門坎苗族又實現了整體脫貧的第二次歷史性跨越。石門坎的教育、醫療、通訊、交通、村寨、環境等設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石門坎教育也真正進入了新時代,全鄉共有1所初級中學和10所小學(5個完全小學,5個教學點),這11所基礎教育學校在“山鄉巨變”背景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石門坎民族中學從傳教士辦學舊址上進行了整體性搬遷,10所小學也都進行了現代化改造,體育設施按照國家標準進行了改造,徹底告別了隨機、零星、不規范的原始狀態。見表1:

表1 石門坎體育場地信息
新時代石門坎體育文化呈現出兩個特征:一是學校的體育課程完全按照國家課程標準來開設;二是石門坎區域內各民族(苗族、彝族、回族)傳統體育項目都平等地作為地方(或校本)課程來開展。這兩個特征一方面充分保障了少數民族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苗族的民族平等從制度上得到的保障。石門坎體育按照國家課程標準有計劃地實施,其面相少了神秘、狂歡的性質,形成了規范有序的常態課程。
三、石門坎體育文化內涵闡釋
石門坎三個階段的體育呈現出不同的文化面相,形成特定的發展軌跡,具體如下:
神秘游戲→讀書狂歡→常態課程
石門坎體育在不同階段為什么會呈現出不同的面相,促使其面相變換的不變因素才是石門坎體育文化的本質內涵,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
行動者的行動是由其擁有的資本決定的,傳說中的涿鹿大戰決定了古老苗族悲慘的遷徙歷史,被稱為蚩尤御林軍的石門坎花苗,屢戰屢敗,從黃河邊一路南逃,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失去了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本,最后集體淪為土司的奴隸,從此失去了做人的資格。
唯一殘存的資本可能是自己作為古老民族的歷史記憶,石門坎溯源碑信息:我們好像未開化的人一樣……別人看不起,盡笑話我們……我們確是北方古老的民族啊……[2]16
如果我們把古老民族的存在作為資本,那他們的這種資本業已現實性的失去,但他們仍把古老民族存在的歷史記憶當作資本。特殊的資本必然促使行動者采取特殊的行動方式,爛飲、放縱、狂歡成為行動者行動的主要特征,這種極端表現被他者視為動物性存在并遠離他們,耍山梁子上的狂歡游戲逐步淪落為沒有他族觀眾的“獨角戲”。石門坎土司擁有全部資本,苗族擁有零資本,資本擁有上的絕對化形成了超穩定的二元政治結構,超穩定的二元政治結構又決定著超穩定的社會位置關系,超穩定的位置關系決定著無人關注的“獨角戲”延續千年而不變。苗族就靠著這種以沉醉為特征并被人歧視的游戲頑強地保持著自我的存在,儀式并不只是一套認知性分類體系。它們同樣也是一套喚起性的工具體[12]41。千年重復形成慣習,反過來慣習又無形地推動著游戲的延續,只要二者之間的資本變量沒有出現,耍山梁子上游戲的面相就不會改變。
資本性質和數量的改變必然引起游戲者游戲方式的改變,20世紀初傳教士的到來使資本的比例發生了改變。千年以來,由于歷史和地理的原因,石門坎政治上施行的是土司制度,中央政府只擁有名義上的主權,土司則是石門坎苗族的真正統治者。傳教士是一個特殊的符號,它是一種外來的政治力量,這種政治力量是因受清政府的保護而形成的,此時的石門坎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生態,即苗族怕土司,土司怕政府,政府怕洋人,洋人傳教的對象是石門坎苗族。洋人為了在石門坎傳教辦學需要與土司打交道,石門坎花苗成為土司和傳教士之間的連接點,傳教士是帝國主義政府與清政府條約下的產物,它不是權利的直接擁有者,而是權利的間接擁有者,土司不怕傳教士,但也礙于政府的保護而有所忌憚,這樣傳教士為苗族爭取一些權利成為可能,石門坎資本形態開始出現變化。
資本擁有上的任何變化必然引起行動者用與資本相匹配的行動展開對社會位置關系的爭奪。石門坎苗族正是抓住這微弱的資本變化迅速地行動起來,形成以讀書為內涵的體育活動,他們想用讀書來證明自己歷史記憶中的位置并回到那里去,歷史背景動因和資本變化誘因雙雙決定了石門坎第二階段以讀書狂歡為特征的體育文化面相。
中國在以上兩個階段發生了由封建王朝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轉變,然而,這種轉變對于石門坎苗族來說并沒有實質性改變,無論是土司還是民國政府所塑造的社會構型都是為少數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石門坎苗族依然是被壓榨剝削的對象,即使是苗族人做出了狂歡式的努力,也無法改變苗族資本占有和社會位置上的絕對劣勢,那他們作為中國古老民族的歷史記憶就無法實現。
新中國成立后,各民族擁有平等權利,全體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這意味著各民族擁有的資本無論是性質還是數量上都是相同的,在相同資本擁有下,場域中行動者的行動在性質上應該是無差別的。因此,石門坎第三階段的體育活動變成了現代規范的國家課程,與前兩個階段相比,少了狂歡神秘的性質,呈現出平等規范的特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石門坎苗族回歸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后,體育設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前面石門坎體育設施的統計信息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體育設施也只是石門坎社會巨大變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變化的力度和廣度是傳教士們所不可比擬的,國家是推動石門坎苗族實現歷史巨變的決定因素。
四、結論
通過石門坎三個階段體育文化的描述和分析可知,石門坎體育的面相是不斷變化的,體育價值也是包括習俗、進取、團結、振奮、獎賞等在內的多維存在。那么,看似復雜的石門坎體育文化背后不變的決定性力量是什么呢?這種決定性力量才是石門坎體育文化本質性內涵。第一階段狂歡游戲的決定性力量來自于石門坎苗族的歷史記憶,第二階段讀書狂歡的決定性力量來自于對歷史記憶的復興嘗試,第三階段國家課程的決定性力量來自于民族平等的國家確認。歷史記憶、復興嘗試和國家確認都指向一個東西——中華民族認同。
“中華民族”是近代出現的一個新詞,20世紀初隨著民族國家意識在中國的傳播,中華民族逐漸成為一種政治文化符號下的民族觀念,費孝通對此作出明確界定:中華民族這個詞用來指現在中國疆域里具有民族認同的全體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元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13]。中華民族認同就是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承認、認可與歸屬。中華民族身份的確認始終是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的核心,石門坎苗族體育文化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
這就回答了為什么會有延續千年的神秘游戲、找傳教士要求的不是信教而是讀書、為什么新時代會發生根本性巨變等讓人費解的問題,由此可以得出:中華民族認同是石門坎體育文化的根本內涵。從三個階段體育文化面相的考察可知,一個族群失去了中華民族認同就有失去族群身份的危險,對中華民族的堅韌融入是獲得解放的根本性要素。國家政治制度保障是少數民族能否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決定性因素。同時,中華民族認同是一種無形的文化觀念,需要通過具體的載體去表現它,從人的本質、個體喜愛、習俗傳統來看,體育游戲都是一個最具匹配度的賦形載體。
一言以蔽之,中華民族認同是石門坎苗族體育文化的根本內涵,它清晰地表明中華民族認同決定著民族的生死興衰,是民族發展振興的根本動因和文化保障。同時,石門坎苗族的中華民族認同意識是通過體育游戲表現出來的,這提示我們——對體育游戲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在一般性的體育活動上,而應從更豐富的文化層面上去體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