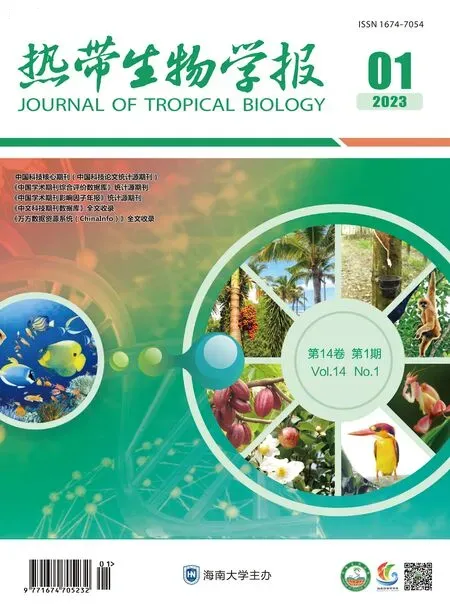廣州管圓線蟲免疫調控機制及診斷技術研究進展
許靖云,周宇晨,黃 碩,韓 謙
(1.海南大學 生命科學學院病媒生物學實驗室,海口 570228;2.海南大學 全健康研究院,海口 570228)
廣州管圓線蟲(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是一種人獸共患食源性寄生蟲病——廣州管圓線蟲病(Angiostrongyliasis cantonensis)的病原,隸屬于線蟲目,后圓線蟲科,后圓線蟲亞科,管圓線蟲屬[1],廣泛分布于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引起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1-2]。由于其適宜在25~30 ℃的潮濕環境中發育,因此在我國主要分布于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海南、云南、廣西和廣東等地[2]。A.cantonensis生活史較復雜,鼠類是A. cantonensis的終末宿主,中間宿主包括陸生和水生軟體動物。保蟲宿主可以是淡水魚、蝦、蟹、蟾蜍、青蛙,也可以是包括人、貓、犬在內的幾十種哺乳動物[3-5]。人作為其非適宜宿主,主要通過攝入感染性幼蟲污染的食物而發生感染,引起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腦膜炎(eosinophilic meningitis,EM)。廣州管圓線蟲病相對罕見,但隨著人們生活方式與飲食習
慣的改變,廣州管圓線蟲病患者越來越多,如今世界累計報告病例已超過3 000例。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將廣州管圓線蟲病列為21世紀新出現的全球威脅性傳染病之一。在醫療上通常根據食用軟體動物史、臨床特征及實驗室檢查做出推定診斷,但目前已開發出的針對廣州管圓線蟲病的血清學檢測的多種診斷方法的靈敏度及特異性仍有待提高。增加對廣州管圓線蟲病的認識將有助于快速診斷并改善臨床結果,為此,筆者重點對廣州管圓線蟲的病原生物學、流行病學、發病機理、免疫機制及診斷技術的研究進展進行了概述。
1 生物學形態
1.1 卵A. cantonensis蟲卵卵殼較薄、無色透明、形狀不一,多為橢圓形,且新鮮的蟲卵多處于單細胞期,因此常難以檢獲[6]。Uga S等人[7]證實超過50%的A. cantonensis蟲卵在-30 ℃的溫度條件下存活,且隨著溫度下降,蟲卵的存活率顯著降低,在-50 ℃時存活率低于10%。
1.2 幼蟲A. cantonensis幼蟲可分為5期,第Ⅰ期幼蟲:體表無色透明;尾端細尖,近尾端背側有一明顯刀切樣凹陷。第Ⅱ期幼蟲:體表具鞘;體內尤其是食管與腸管交界處含有大量折光顆粒[8]。第Ⅲ期幼蟲:蟲體明顯膨大增粗,呈細桿狀;體表由外層鞘膜和內層皮層組織構成;頭部頂端圓鈍,尾部尖,聚集實質細胞。第Ⅳ期幼蟲:蟲體雌雄區分明顯,長度約為Ⅲ期幼蟲的2倍;雄蟲尾部膨大,出現交合刺和交合刺囊;雌蟲前端可見雙管形子宮,陰道和肛孔位于蟲體末端。第V期幼蟲:蟲體體積較IV期增大;雄蟲已形成交合傘;雌蟲卵巢膨大,陰門明顯。張超威等[9]發現中間宿主福壽螺體內的部分Ⅲ期幼蟲已褪去鞘膜,僅腹部留有痕跡,但仍有部分Ⅲ期幼蟲在繼續脫鞘發育,其特征為尾部末端有一段短小纖細圓柱體。另有少數蟲體體內已出現IV期幼蟲才有的亞腹腺和雙管子宮結構,但其是否能在中間宿主體內繼續發育至IV期幼蟲仍有待探索。
1.3 成蟲A. cantonensis成蟲呈兩端略細的線狀,角皮透明、光滑,體表有清晰可見的微細環狀橫紋。雄蟲尾部略向腹部彎曲,多呈“腎”形,有一個對稱的交合傘;雌蟲通常比雄蟲大,尾部多呈斜錐型,體內子宮與腸管相互纏繞,在顯微鏡下可以清晰看到紅(或黑褐)白相間的結構[10]。
2 生活史
A. cantonensis生活史較復雜,可以在保蟲宿主、中間宿主和終末宿主體內移行或發育。保蟲宿主可以是淡水魚、蝦、蟹、蟾蜍、青蛙,也可以是包括人、貓、犬在內的幾十種哺乳動物[3-5]。中間宿主多為軟體動物,如螺類(福壽螺、皺疤堅螺、中國圓田螺、褐云瑪瑙螺、東風螺、明線瓶螺、銅銹環棱螺等)、蛞蝓類(足襞蛞蝓、雙線嗜粘液蛞蝓等)和蝸牛類(同型巴蝸牛、短梨巴蝸牛等)[3]。終末宿主為嚙齒動物,如褐家鼠、黑家鼠、黃胸鼠和黑線姬鼠等鼠類。A. cantonensis成蟲在終末宿主的肺動脈內雌雄交配產卵,蟲卵孵化后,I期幼蟲穿破肺毛細血管進入肺泡,延支氣管上行至咽喉,并隨著呼吸道分泌物進入消化道,最后隨糞便排出體外。I期幼蟲進入中間宿主體內后可移行至肺、肝臟、肌肉等處寄生;幼蟲經2次蛻皮發育為Ⅲ期幼蟲。終末宿主吞食含有III期幼蟲的中間宿主或被III期幼蟲污染的蔬菜或水源時而發生感染[11-12]。另一方面,保蟲宿主同樣會因為誤食了感染性III期幼蟲而發生感染。在保蟲宿主體內,蟲體雖然可以繼續發育為IV期、V期幼蟲或童蟲,但不能發育為性成熟的成蟲[13]。楊發柱等[5]發現,犬和貓作為保蟲宿主經口感染III期幼蟲后未出現異常表現,體內也檢測不到蟲體;而貓經皮下注射III期幼蟲后雖可導致感染,但只有在表現出明顯癥狀時,才能在腦及脊髓中檢測到幼蟲,癥狀消失之后,亦檢測不到蟲體,因此,貓可以成為研究廣州管圓線蟲病治療方案及機體清除A.cantonensis機制的動物模型。
3 廣州管圓線蟲病的流行、發病特點及防控策略
3.1 我國廣州管圓線蟲病流行情況1984—1996年我國廣州管圓線蟲病確診病例僅有4例,之后十余年,在浙江、福建、江西、北京、遼寧、云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和臺灣等地區均出現過因生食、半生食福壽螺導致的廣州管圓線蟲病暴發流行[14-19]。2010—2012年流行病學調查[20]證實海南全省各地居民普遍存在A. cantonensis感染情況,血清學檢測平均陽性率達20.04%,個別縣高達49.45%。截至2017年,全國各地累計報道病例高達521例[21],其中廣西和福建的感染率最高,其次是云南。
人主要通過生食或半生食A. cantonensis的中間宿主而發生感染,因此對中間宿主感染率及流行情況進行調查具有重要的意義。2008年對廣東省深圳西南部褐云瑪瑙螺體內A. cantonensis感染率進行調查,數據顯示其陽性感染率高達31%,同時,檢出陽性螺的區域內A. cantonensis終末宿主褐家鼠和黃胸鼠也存在感染現象,感染率平均為12%[22]。2009年對浙江省A. cantonensis的不同中間宿主的感染情況進行調查,調查數據顯示溫州市福壽螺感染率達到69.4%[23],麗水市蛞蝓感染率更是高達80.65%[24]。2012年在福建省福州、廈門的菜市場和餐飲店銷售的福壽螺和銅銹環棱螺中[25]以及2015年在龍海市居民居住環境中采集的褐云瑪瑙螺中均檢出A. cantonensis幼蟲[26]。2021年,鄭丹等[27]對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在福建省多市縣的農貿市場、超市、早市以及路邊攤上未發現福壽螺和褐云瑪瑙螺售賣,這可能是政府宣傳教育及加大管理力度的結果,但在野外及居民居住環境中采集的福壽螺和褐云瑪瑙螺中仍存在A. cantonensis感染。2022年最新流行病學數據顯示,廣州市不同地區城市公園中的不同種類中間宿主的感染率存在明顯差異,其中,褐云瑪瑙螺和蛞蝓的感染率較高,分別為16.5%和14.9%[28]。
除上述重要疫源地以外,2020年3月首次在四川省自貢市貢井區確認2例A. cantonensis本地感染病例,且這2名患者均有生食淡水螺史。在患者食用淡水螺的水田周圍采集福壽螺,螺體感染率為10.69%[29]。在患者家周圍菜地、房屋前后和魚塘邊捕捉到的雙線嗜粘液蛞蝓體內也檢測到了A. cantonensisⅢ期幼蟲[30]。隨著經濟的發展,不同地區人們的飲食習慣日益融合,因此,除了加強重要疫源地調查外,還應掌握全國各省市螺類分布情況以及螺類和鼠類A. cantonensis感染情況。
3.2 廣州管圓線蟲病發病特點廣州管圓線蟲病潛伏期一般為3~30 d,少數患者當天即可發病,出現惡心、腹痛、腹瀉和嘔吐等非特異性癥狀和體征,小部分患者會出現斑丘疹或蕁麻疹等皮膚性癥狀。早期癥狀持續數日后便可自行消散,隨后出現持續數天至數周的無癥狀期。在病程后期,患者會產生以發熱、頭痛、頸部僵直為主要臨床表現的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腦膜炎(eosinophilic meningitis,EM)[31]。嚴重者還會出現面部、肢體麻痹、單側視力下降、失明、昏迷,甚至死亡[32]。
由于寄生蟲感染數量及寄生部位的不同,廣州管圓線蟲病患者體內的病變通常是多灶性的[33]。例如,遭受免疫系統攻擊的移行期幼蟲的遺骸很可能在中樞神經系統中持續存在數月至數年,誘導周圍組織出現慢性炎癥反應,同時,膠質細胞的增生會導致永久性疤痕組織沉積。另一方面,逃避宿主免疫系統攻擊的幼蟲會通過腦靜脈和脊髓靜脈離開中樞神經系統,到達肺部。當大量幼蟲在肺動脈中寄生時,會導致患者出現嚴重的肺部疾病[34]。因此,盡管進行了及時的診斷和治療,感染A. cantonensis也會使許多患者出現長期甚至是永久性的后遺癥。
3.3 廣州管圓線蟲病的防治策略
3.3.1 治療迄今為止,針對廣州管圓線蟲病的治療主要采用對癥和支持療法。苯并咪唑類藥物(阿苯達唑、甲苯達唑、噻苯達唑和芬苯達唑)、伊維菌素和左旋咪唑已被廣泛用于治療廣州管圓線蟲病。Jacob等[35]通過體外研究分析多種驅蟲藥對A. cantonensisⅢ期幼蟲的藥效,結果表明阿苯達唑和伊維菌素/莫西菌素可用于廣州管圓線蟲病的治療,而雙羥萘酸噻嘧啶則可作為預防廣州管圓線蟲病的候選藥物。Jhan等[36]發現阿苯達唑和地塞米松等藥物聯合治療EM的效果更佳。Lin等[37]研究發現生姜的部分成分也可用于抗A.cantonensis感染,但受病情嚴重程度、治療方案、治療時機、年齡體質等多因素的影響,治療效果及治療周期會存在些許個體差異。
3.3.2 預 防 措 施(1)改變飲食習慣。A.cantonensis主要感染途徑是經口感染,所以要注意飲食衛生,改變生食或者半生食食物的習慣,特別是醉蟹、醉蝦及爆炒田螺等。(2)淡水螺類和鼠類分別是A. cantonensis主要中間宿主和終末宿主,應加強魚塘、稻田、居住地垃圾堆等周圍環境的清理整治,切斷該病原體的傳播途徑。
4 A. cantonensis與宿主免疫系統的互作機制
A. cantonensis感染是引起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性腦膜炎(EM)的典型原因,可導致中樞神經系統嚴重損傷。寄生蟲和宿主因素都有助于EM的發生,但相關的免疫-炎癥發病機制仍不明確。
4.1 A. cantonensis感染對T細胞分化的影響A. cantonensis感染的免疫應答與宿主的自我保護和線蟲的發病機制密切相關。T細胞和B細胞免疫在抵抗感染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A. cantonensis感染導致小鼠免疫功能明顯減弱,表現為進行性脾、胸腺萎縮,且這種萎縮與脾細胞增殖減少及凋亡增加而導致細胞總數減少有關,其中T細胞亞群結構也會發生改變,如CD4+T/CD8+T細胞比值和B/T細胞比值降低,CD4+CD25+Foxp3+Treg、CD8+CD28-T和CD38+T淋巴細胞比例增加[38]。但Chen等[39]則認為脾臟和胸腺細胞的急劇減少不是由于細胞凋亡,而是由于B細胞生成的停止和胸腺細胞發育的受損而引起的。
Lee等[40]發現C57BL/6小鼠感染A. cantonensis后,外周血中CD4+T和CD8+T細胞的百分比顯著增加,且T細胞耗竭小鼠體內的蟲荷數明顯多于未耗竭小鼠,將感染小鼠體內CD4+T細胞過繼轉移至同系感染小鼠可以介導保護作用,但過繼轉移CD8+T細胞群則無保護作用。Aoki等[41]的研究結果同樣證實,抗CD4抗體處理會增加感染A. cantonensis的BALB/c小鼠的發病率,而抗CD8處理則不會提高其發病率。Liu等[42]通過流式細胞術檢測感染A. cantonensis小鼠脾細胞中T細胞亞型分化情況,實驗結果表明,感染小鼠脾細胞中CD4+和CD4+IL-4+T細胞百分率明顯增加,而CD4+IL-17+和CD4+IFN-γ+T細胞的百分率則顯著降低;此外,感染組小鼠脾細胞培養上清中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4濃度明顯升高,但IL-17顯著降低;說明A. cantonensis感染誘導小鼠體內CD4+T細胞向Th2表型分化,而Th17細胞分化受到抑制;由于Th2細胞主要發揮抑制免疫反應的作用,Th17細胞參與介導炎癥反應的發生與發展,所以推測A. cantonensis可能通過誘導Th2細胞為主的T細胞應答,從而有利于其在宿主體內的長期存活。
A. cantonensis感染宿主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存在種系依賴性差異,那么不同種系之間的免疫應答機制是否同樣存在差異呢?劉珍等[43]檢測了A.cantonensis感染對大鼠胸腺及脾臟中T細胞各亞群的影響,結果發現大鼠胸腺中CD4+、CD8+、CD4+CD8+和CD4-CD8-T細胞比例和數量在感染21 d后與對照組相比無顯著性差異,而脾臟中CD4+/CD8+T細胞比值顯著增加,且大鼠胸腺、脾臟及腦組織中單個核細胞各亞群變化同樣不明顯。胸腺作為中樞神經系統,是T細胞發育分化的場所,在感染后期,胸腺中T細胞各亞群無顯著變化,說明此時大鼠體內的炎癥反應已經得到緩解,無需更多的免疫細胞發揮調控作用,同時,腦組織中單個核細胞變化不明顯也進一步證實腦組織中炎癥反應得到緩解,而脾臟中CD4+/CD8+T細胞比例增高,說明CD4+T細胞主要發揮清除和控制感染的作用。簡而言之,在大鼠體內CD4+T細胞通過清除和控制感染可使腦部炎癥反應在感染后期逐漸得到緩解,這與以小鼠為研究對象獲得的實驗結果相一致。
4.2 A. cantonensis感染對嗜酸性粒細胞功能的影響當機體發生感染時,活化的嗜酸性粒細胞(eosinophil,EOS)可遷移至外周血中,隨后被募集到組織中并分泌高水平細胞因子、趨化因子、脂質調節物和細胞毒性顆粒蛋白等,從而迅速引發并維持局部炎癥反應[44]。研究結果表明,在A. cantonensis感染過程中,一方面EOS能通過分泌顆粒對A. cantonensis幼蟲發揮殺滅作用;另一方面其釋放的EOS陽離子蛋白(eosinophil cationic protein,ECP)和EOS蛋白X(eosinophil protein X)也會造成神經系統損傷[45-46]。EOS(以及其他免疫細胞,如T細胞)也被證明可以產生、儲存和釋放神經營養因子,如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47,48]。有研究結果表明,在中樞神經系統中局部產生的BDNF可以減輕炎癥依賴的神經元損傷[49]。
4.3 A. cantonensis感染對膠質細胞的影響在中樞神經系統病變中常觀察到小膠質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的激活,以及各種炎癥反應信號通路的活化[50]。小膠質細胞正常情況下處于靜息狀態,當小膠質細胞被激活后可發揮“雙刃劍”作用,一方面活化的小膠質細胞可通過分泌細胞因子和神經生長因子促進神經組織修復;另一方面小膠質細胞又可通過釋放細胞毒素、炎癥介質及細胞因子加重腦組織損傷[51],活化的小膠質細胞可以產生IL-4、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等促炎因子,高水平表達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釋放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和一氧化氮(NO)等毒性介質也具有殺死寄生蟲作用[52]。Wei等[53]發現在A. cantonensis感染過程中,膠質細胞的激活以及神經毒性炎性因子的釋放破壞了神經系統生理平衡,導致中樞神經損傷。因此,小膠質細胞活化與A. cantonensis感染后EOS浸潤所引起的腦炎和腦膜腦炎具有一定相關性。
4.4 A. cantonensis感染對細胞因子表達的影響Sugaya等[54]發現小鼠的腦脊液、血清和脾細胞或頸淋巴細胞培養上清液中IL-5和IL-4的產生水平顯著增加,這說明全身和局部Th2細胞因子反應,特別是涉及IL-5的反應,在A. cantonensis感染的小鼠中占主導作用。IL-5在A. cantonensis感染小鼠的EOS反應中同樣是必不可少的[55]。通過檢測30例嗜酸性粒細胞性腦膜炎伴廣州管圓線蟲病(EOMA)患者腦脊液中細胞因子的表達情況,同樣證實在EOMA患者腦脊液中局部Th2細胞因子應答占據主導地位,同時,IL-5、IL-10和TNFα產生水平與EOS浸潤水平相關。因此,腦脊液中Th1/Th2細胞因子的測定對寄生蟲相關腦膜炎的診斷也具有一定的潛力[56-57]。
Chuang等[58]研究發現,在ST2單抗治療A.cantonensis感染小鼠后,血清中IL-5水平明顯降低,嗜酸性粒細胞在腦膜的浸潤也明顯減少,因此推測IL-33/ST2軸可能在廣州管圓線蟲病的發病機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Peng和Du等[59-60]也通過一系列實驗證實,在A. cantonensis感染過程中,大腦中的IL-33和ST2L mRNA轉錄水平顯著上調,同時,IL-33誘導脾細胞和大腦單個核細胞產生IL-5和IL-13。此外,給予A. cantonensis感染小鼠IL-33后,ST2L的表達和細胞因子的產生均有所增強。因此,大腦中產生的IL-33可能在A. cantonensis誘導的EM中發揮炎癥介質的作用。
4.5 A. cantonensis感染對趨化因子表達的影響伴隨著A. cantonensis的感染,宿主免疫應答會同時啟動趨化因子和趨化因子受體來阻止寄生蟲的入侵、移行等行動。幼蟲在感染后第2天即遷移到宿主腦組織,隨著感染時間的延長,在幼蟲刺激下神經元和星形膠質細胞釋放趨化因子。Li等[61]發現Cys-Cys(CC)型趨化因子CCL2、CCL8、CCL1、CCL24、CCL11、CCL7、CCL12、CCL5在感染晚期顯著升高;同時,腦脊液中EOS增加趨勢與趨化因子水平變化趨勢基本相關,因此說明趨化因子在招募EOS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Ym1作為一種嗜酸性趨化因子,對T淋巴細胞和骨髓細胞同樣具有趨化活性。有報道稱,在寄生蟲感染過程中,Ym1是由活化的巨噬細胞合成和分泌的[62]。在大腦中,小膠質細胞是交替激活的巨噬細胞源性細胞,是參與中樞神經系統炎癥的關鍵免疫細胞。Zhao等[63]的研究結果表明,Ym1在感染A. cantonensis的小鼠的大腦和腦脊液中隨著炎癥的發生而大量表達,且Ym1比IL-5和IL-13的變化更明顯。通過抗體定位實驗也證實Ym1由大腦小膠質細胞合成并分泌。因此,Ym1可能作為一種替代的潛在病理標記物。
Chang等[64]發現A. cantonensis感染小鼠腦脊液中嗜酸性粒細胞活化趨化因子(eotaxin)和巨噬細胞炎癥蛋白(MIP)-1α同樣具有EOS趨化活性,且eotaxin的釋放具有時間依賴性和蠕蟲負荷依賴性[65]。Intapan等[66]通過檢測30例患者的腦脊液中eotaxin和eotaxin-2的濃度,進一步證實腦脊液中eotaxin-2水平與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相關。這些結果提示患者EOS聚集到大腦和脊髓可能與eotaxin-2水平升高有關。
4.6 A. cantonensis 的排泄-分泌產物具有發揮免疫調控的作用寄生蟲的排泄-分泌產物(ESP)作為生物活性分子可直接與宿主的免疫系統相互作用。A. cantonensisIV期幼蟲的ESP具有誘導巨噬細胞選擇性激活的能力[67]。V期幼蟲的ESP可以通過激活NF-κB和Shh信號通路刺激星形膠質細胞活化和細胞因子生成[68]。同時,V期幼蟲的ESP還可以通過激活抗氧化劑導致氧化應激水平的降低,進而激活星形膠質細胞內Shh信號通路,發揮抗凋亡作用。Shh(sonic hedgehog,音猬因子)信號通路主要在發育過程中發揮控制神經祖細胞、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細胞的形成的作用[69]。對于EOS而言,A. cantonensis成蟲的ESP不顯示出趨化活性,而其體蛋白則具有一定的趨化活性,且呈蛋白濃度依賴性。Wang等[70]進一步通過ELISA檢測發現,體蛋白中半乳糖凝集素-9樣(galectin-9-like)蛋白在趨化EOS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在中樞神經系統中,殼多糖酶3樣蛋白3(chitinase 3-like protein 3,CHI3L3)具有誘導少突膠質細胞形成髓鞘的能力。Wan等[71]研究發現,A. cantonensis可溶性抗原可以通過增強IL-13與CHI3L3之間的正反饋環路誘導EM的發生與發展。但無論是ESP還是體蛋白都是多種蛋白組成的混合物,其成分復雜,下一步的研究重點應放在分析其中某一具體的抗原成分在A. cantonensis與宿主免疫互作的過程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Sun等[72]研究發現在IV期幼蟲和成蟲體內高表達的半乳糖凝集素-1(Galectin-1,Gal-1)可以通過減少脂肪沉積,對氧化應激引起的損傷發揮防御作用,這可能提示了A. cantonensis在人類中樞神經系統EOS的免疫攻擊下存活的機制。另外,Gal-1可通過與膜聯蛋白(Annexin)A2結合,激活JNK下游凋亡信號通路誘導巨噬細胞凋亡[73]。因此,Gal-1可能在A.cantonensis免疫逃避機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4.7 miRNA參與A. cantonensis感染期間宿主的免疫反應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miRNA在A.cantonensis感染引起的EOS增多性腦炎和腦膜腦炎發生與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顯示,在被A. cantonensis感染后的不同時長中小鼠腦內miRNA表達存在明顯差異,大多數差異表達的miRNAs參與了免疫反應,特別是EOS分化的調節,且隨著感染時間的延長而發生動態變化[74]。另一方面,不同發育階段的A. cantonensis本身miRNA表達亦存在較大差異[75]。
綜上所述,A. cantonensis與宿主之間的免疫互作機制需要固有免疫細胞、外周免疫細胞以及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等共同參與,因此,免疫細胞及相關因子的炎癥調節機制與miRNA的轉錄調節機制在A. cantonensis的研究中有著重要的地位。
5 廣州管圓線蟲病診斷技術
廣州管圓線蟲病的診斷首先需要考慮近期流行病學資料,如患者近2個月是否有意或無意地攝入螺類(中間宿主)、食用未煮熟、未洗過或洗得不充分的受污染的蔬菜水果[76],然后結合臨床表現(有無發熱、頭痛等神經系統癥狀)及實驗室輔助檢查(如腦脊液檢查、血清抗體檢查等)進一步確定。目前還沒有明確作為首選的診斷方法,且由于廣州管圓線蟲病臨床癥狀與其他多種疾病癥狀相似,缺乏明顯的典型性,導致該病往往不能及時確診,容易出現誤診和漏診現象。
5.1 實驗室檢查早年廣州管圓線蟲病的診斷,主要依賴于病原學檢查,只有在腦脊液等標本中檢測到蟲體才能作為確診依據。但A. cantonensis幼蟲侵入人體的中樞神經系統后,絕大部分幼蟲不再繼續發育而停留在腦部,或被宿主免疫系統及藥物及時清除,因此患者腦脊液中幼蟲的檢出率極低。但A. cantonensis的感染會導致患者腦脊液中蛋白含量升高,其外觀表現為渾濁或乳白樣狀態。磁共振影像學特征顯示,五分之四的患者腦實質病變呈彌漫性或散在分布,少數患者出現腦室擴增的現象[77]。同時,血常規檢測結果顯示白細胞及嗜酸性粒細胞數量會隨患者病程延長而逐漸升高[78]。
5.2 免疫學診斷盡管早期使用的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間接血凝試驗(IHA)、間接免疫熒光抗體試驗(IFAT)、反免疫電泳(CIE)等方法進行檢測并未得到預期的效果,但隨著技術的發展和改進,免疫學診斷方法因簡單、廉價和快速的特點而被認為是目前最適當的診斷方法。
5.2.1 抗體檢測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主要利用A. cantonensis成蟲粗提抗原或部分純化抗原、腦期幼蟲的排泄-分泌產物等進行免疫學檢測[79]。Maleewong等[80]對A. cantonensis雌蟲體蛋白提取物(adult female worm somatic extract,FSE)的抗原成分進行了檢測,并通過免疫印跡分析廣州管圓線蟲病患者血清及腦脊液對FSE的反應性,結果發現29 kDa抗原帶可作為可靠的診斷指標。
Eamsobhana等[81-83]通過電洗脫方法從A.cantonensis成蟲體蛋白粗提物中得到了高純度的31kDa糖蛋白,并利用dot-blot ELISA檢測方法對廣州管圓線蟲病患者血清樣本進行檢測,檢測結果表明,該診斷方法靈敏度和特異性均高達100%。2018年,Eamsobhana等[84]開發了一種快速橫向流動免疫層析法(AcQuickDx試驗)來檢測人血清中的抗A. cantonensis抗體,該方法具有檢測速度快,靈敏度和特異性高等特點。最近,Eamsobhana等[85]又新建立一種雙夾心斑點免疫金滲濾法(sandwich dot-immunogold filtration assay,DIGFA),該方法能夠在臨床樣本中快速定性檢測A. cantonensis特異性31 kDa抗原。
除上述檢測方法之外,免疫印跡也是一種常用的,較為簡單的免疫學檢測方法。Vitta等[86]建立的81 kDa重組蛋白免疫印跡檢測方法的特異性及靈敏度均大于90%,但與多種寄生蟲病患者血清存在交叉反應。16 kDa重組蛋白免疫印記診斷方法的特異性高達100%[87],更為重要的是,16 kDa重組蛋白免疫印記診斷方法與感染了棘顎口線蟲(Gnathostoma spinigerum)和豬囊尾蚴(Cysticercus cellulosae)的患者血清中的抗體無交叉反應,這兩種感染在臨床上表現出類似于廣州管圓線蟲病的神經癥狀;這些數據表明,16 kDa重組蛋白是一種具有高潛力的廣州管圓線蟲病血清診斷候選抗原。
由于A. cantonensis幼蟲可以寄生于腦室,因此,血清抗體濃度可能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從而影響了血清學診斷的準確性。Chye等[88]用特異性單克隆抗體通過免疫親和層析法純化了來自A.cantonensisV期幼蟲(AcL5)的抗原,SDS-PAGE分析顯示純化的抗原為204 kDa的單條帶,將純化的抗原作為包被抗原建立ELISA檢測方法,與其他幾種寄生蟲誘導的抗體無交叉反應;同時,使用該ELISA方法檢測血清和腦脊液標本時,血清中抗體水平略高于腦脊液中抗體水平,因此該方法檢測血清抗體的可靠性略高于檢測腦脊液標本抗體的可靠性。
5.2.2 抗原檢測感染后抗體延遲出現及治愈后抗體持續存在等情況限制了血清抗體檢測診斷的可靠性。抗體檢測的另一種替代方法是抗原檢測。抗原檢測證明宿主中存在蟲體,同時,也可更迅速地確認急性或活動性感染。將A. cantonensis特異性單克隆抗體(AW-3C2)作為夾心ELISA捕獲試劑,檢測廣州管圓線蟲病患者血清中特異性循環抗原,其特異性為100%,但敏感性僅為50%[89]。在廣州管圓線蟲病患者的血清和腦脊液中,使用雙單克隆抗體(AcJ1和AcJ20)進行檢測,其特異性為100%[90]。Chye等[91]使用AcJ1單抗作為捕獲抗體,通過免疫PCR(Immuno-PCR,Im-PCR)檢測廣州管圓線蟲病患者血清中循環的204 kDa抗原,檢測特異性為100%。同時,Im-PCR方法對已知感染A. cantonensis的患者的腦脊液標本的檢測靈敏度為100%,對僅表現出臨床癥狀的患者的腦脊液標本的檢測靈敏度為96.7%。Liang及Tan等[92-93]利用成蟲的3個特異性單克隆抗體(2A2、3F1、4H2)進行血清學檢測,其陽性檢出率為86.4%。
5.2.3 宏基因二代測序檢測腦脊液收集和患者血清中低抗原濃度帶來的診斷挑戰促使人們開發更敏感的替代檢測方法。近年新興的宏基因二代測序病原檢測方法具有精準、快速、陽性率高、覆蓋度廣等優勢。羅智強等[94-95]采用宏基因二代測序技術在患兒外周血和腦脊液中均檢測到A.cantonensis,因此該方法可以無創、快速且精準地診斷廣州管圓線蟲病。
6 結 語
雖然已經有許多針對A. cantonensis生物學方面(包括其生活史方面的試驗數據)的研究資料,但目前對于該蠕蟲與宿主之間的免疫互作機制仍知之甚少,因此,闡明A. cantonensis與宿主之間的互作機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同時,基因組學、蛋白組學、轉錄組學和生物信息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也為探究寄生蟲-宿主互作模式的研究提供支持。了解A. cantonensis免疫調控及免疫逃避機制,不僅可以為患者的早期快速診斷提供依據,也會為研發抗寄生蟲藥物,防治寄生蟲感染提供新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