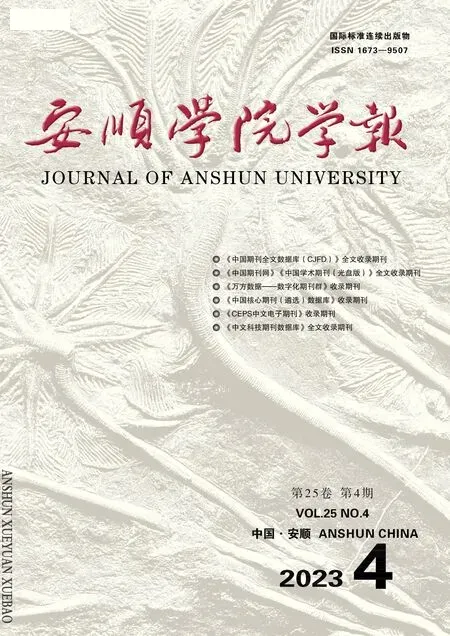21世紀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的鄉土敘事
龍 潛 李益茜
(貴州民族大學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一、性別意識與鄉土敘事
地理位置的僻遠與自然條件的惡劣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貴州的發展,但從另一方面看,位置的閉塞讓其地域文化得以保存。貴州各民族文化爭奇斗艷,呈現出一片繁華的盛況。21世紀以來,貴州少數民族文學取得可喜成績。在貴州少數民族文學發展歷程中,鄭欣、王華、肖勤、楊打鐵和崔曉琳、聶潔、幺京等一批女性作家前后出現,她們以女性獨到的眼光聚焦于時代生活,用女性細膩的筆調窺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厘清世俗生活與文學世界相糾纏的脈絡,使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作品呈現一片光亮。
20世紀90年代,一批年輕女作家以身體敘事進行寫作,創作出一些具有女性意識的作品,推動了女性文學的發展,但這種私人寫作最終走入封閉的圈子,消失于文學視野。21世紀,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謀求新的寫作道路,關注現實生活。她們把筆觸伸向鄉土,從女性的視角去描摹底層人物的日常生活、鄉村風俗和世態人情。女性視角的介入使21世紀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對鄉村歷史與現實的敘述呈現新的美學特質。鄉土敘事在中國文學史中有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從狹義講,指以故鄉生活、鄉村面貌等為題材創作出的具有泥土氣息的文學作品;從廣義說,指一切書寫鄉村生活世界的文學形態。鄉土文學作為主流文學延續了近百年,每個時期都有自己的特質。從20世紀30年代的蹇先艾到20世紀80年代的何士光,貴州的鄉土文學以男性話語為主,經驗主體和表達主體的性別身份單一,文本中呈現出的人物形象以男性為主,作家主要從男性的視角建構小說話語體系。由于性別和社會環境的差異,男女作家建構的文本有很大不同。女性性別意識與鄉土敘事的融合,打破了貴州鄉土小說以男作家為主導的創作局面,使鄉土小說在性別上具有雙重視角。女性鄉土敘事成為新的創作潮流,豐富鄉土文學創作內涵與形式。性別意識不獨屬女性群體,男性同樣具有性別意識。但更多時候它是與“女性”同時出現的。這既體現出將女性視作“第二性”的傳統思維邏輯,又反映出女性自身反抗男性話語霸權的強烈訴求。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鄉土小說中展現出來的性別意識有:一是女性成為“主角”。雖然以往鄉土小說中不乏鄉土女性形象,但這些女性只是男性構建小說故事內容的一個“配角”。21世紀貴州少數民族女作家開始關注鄉土社會中女性的生存狀態,重塑女性在歷史中的地位,女性真正意義上成為小說“主角”。二是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塑造女性形象時帶有自我審視的眼光,她們更加關注女性心理狀態的變化以及對日常生活細節的描摹。三是不回避女性性別意識覺醒的艱難。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敘述了女性生存的困境,深刻剖析女性群體內部存在的弊端,直指女性性別意識覺醒的困難,表達出作家對女性前途命運的探索與思考。“新世紀女性鄉土敘事的崛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將性別意識帶入了有男性壟斷的鄉土敘事領域,呈現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鄉土經驗,提示鄉土經驗的復數形態;另一方面,又將鄉土/底層經驗帶入女性文學中,提示女性經驗的復數形態。”[1]女性文學與鄉土敘事兩個因素在21世紀貴州小說創作潮流中同時顯現,二者并非是簡單相加,從更深層次來講,二者之間的內部聯系密切,在相互融合中構建了女性鄉土敘事的獨特話語體系。
21世紀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用性別書寫卻又超越性別意識,著眼于人性之本質的探尋與追問。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的加入讓貴州鄉土敘事文學進入更廣闊的視野。性別意識與鄉土敘事交織形成的關系展現出作家的書寫立場、寫作姿態和審美追求。
二、多重文學主題的呈現
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把握主流文學的同時又融入自身地域體驗,從時代主旋律、城鄉關系、民族民俗角度書寫文學主題。從文字中感知時代面貌,傳遞時代精神。
一是主旋律下的家國史。鄭欣的長篇小說《百川東到海》獲“貴州省優秀文藝作品獎”“貴州省首屆文學獎”、貴州省第十六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文藝報》發表系列評論展開討論。《百川東到海》[2]是一個史詩性的作品,講述北洋軍閥覆滅之際,第一批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年輕人對革命道路的摸索和人生的愛恨糾葛。作者以唐氏家族的興衰折射一個時代的滄桑變化,詮釋中國共產黨是歷史和人民正確選擇的偉大主題。大浪淘沙后,每個人都必須面對抉擇后的人生,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只能百川歸海,滾滾向前。這是時代摧枯拉朽的過程。小說中三條線索齊頭并進,塑造眾多具有生命溫度的人物,還原歷史真相。在虛構與真實中剪裁故事,凸顯小說的張力。第一條線索由大兒子唐淳衷完成,他貪圖享樂,不諳世事,沒有理想信念與偉大抱負,最后被社會吞噬。第二條線索以二兒子唐淳祐為主,因家族被卷入政治風波致使父親遇害,決心為父報仇,放棄留學,進入黃埔軍校,隨后加入國民黨,在解放戰爭時期,重新審視個人與革命,明辨歷史發展趨勢,最終走向中國共產黨,為天津解放做出重要貢獻。第三條線索以三兒子唐淳袏的成長經歷鋪展開,作為首批翻譯《共產黨宣言》的年輕人,他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從一開始就堅定革命信念,最終迎來勝利的曙光。小說將諸多歷史事件與唐氏三兄弟的人生相交織,呈現出一幅震撼人心的歷史畫廊。作品敘述了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國共合作、抗日戰爭等眾多歷史事件,把歷史的深沉厚重寫進小說,蕩氣回腸、感人肺腑,令人肅然起敬。
《百川東到海》不僅有其鮮明的政治色彩和社會價值,還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古典傳統的融入讓小說厚重且綿實,小說深受《紅樓夢》的影響,小說前部分寫唐氏家族的生活,這與賈府由繁榮走向衰落極其相似。作者在小說中也直接引入《紅樓夢》中的一些手法技巧。曹雪芹在塑造王熙鳳這一人物時,采用了“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手法,成就了王熙鳳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鄭欣巧妙的借鑒這種手法,精心設計了方大總統公子方可為的出場。如果說王熙鳳的出場代表的是封建制度下女性間的一場較量,那么方可為的出場就是以男性為主導的各種政治勢力間的暗潮涌動。小說文字細膩、富有古典韻味,以書香門第孟家兩個女兒的出場開篇,環境、玩物、語言都帶有一種書香氣息。小說并非只是書寫宏大的革命歷史主題,性格各異的女性形象讓小說更加具有生命力。孟敏之溫柔、睿智,挑起家庭的重擔,成為唐淳祐的堅強后盾;顧蕙茗卻在歷史中迷失自我,最終結局悲慘;翠仙有著傳統文學中青樓女子不羈的個性,也有現代莎菲女性的自覺。文學是人的藝術,《百川東到海》呈現出的女性形象系列既有深度又有溫度,這些人物的生死悲歡牽絆著讀者的情思。小說的空間轉換與故事情節的推進相得益彰,早期人物主要活動于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國共合作破裂后,革命者們遭到逮捕,被迫轉移陣地。小說中的人物活動空間也由城市轉到農村,這也預示著農民階層走向革命的可能,跟隨小說中個體的行動軌跡與革命形勢的走向,小說的空間涉及北京、天津、聊城、遵義、重慶、延安等各地區,輻射出各階層對歷史的參與和認識。作品奏響時代和個體相交織的生命旋律,凸顯豐富意蘊,傳達家國情懷。
二是城鄉關系的沖突與和解。“鄉土世界不再作為自然村舍和自然群落獨立于世外,古老的、靜態的、凝滯的‘傳統社群’在現代化的逼迫下,處于不斷的變動和重組中”[3]。在現代化浪潮的裹挾下,農民帶著對美好生活的憧憬涌入城里,不幸的是,城市不是伊甸園,處于城市底層的打工人慢慢失去對美好生活的憧憬。20世紀60年代,美籍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發表《寂靜的春天》[4],這部小說用生動而嚴肅的筆觸描寫生態環境被污染后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災難,向人類提出嚴重警告,這部作品也是生態文學誕生的標志。仡佬族女作家王華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她始終關注鄉村人物和他們的命運,關注生態環境變化。作品不斷見諸于《人民文學》《當代》《中國作家》《民族文學》《小說選刊》《山花》等,曾兩次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
王華在《回家》中敘述了一群由城市返鄉的打工人故事[5]337。管社會無論如何也要買一張臥鋪,前兩次回家他都向母親謊稱自己是坐臥鋪回家,他想讓父母知道自己在外面混得不錯,讓他們心安。第三年回家他買上了臥鋪,但由于手中沒有錢,只能買到婁底的臥票,輾轉回到村里,大家聚在一起討論的是生存的艱難。王華借這篇小說談論了經濟危機下,打工人難以在城市立足,被生活蹂躪后無奈回到農村的現實問題。隨后,她發表長篇小說《雪豆》,這是一部與生態危機緊密相關的作品,揭示經濟迅速發展后留下的弊病,啟發人們對未來命運的思考。《雪豆》講述幾十戶村民為謀生搬到橋溪莊,但這個地方環境污染嚴重,巨大煙囪噴出的灰籠罩整個村莊,由于長期生活在污染嚴重的環境里,村民患上各種怪病;橋溪莊自從最后一個健全的孩子雪豆出生后就沒有新的生命到來;在無數次的掙扎后,一批橋溪莊村民無奈離開,尋找生命的住所。[6]作品描述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帶給人類的滅絕性災難,表現人們渴望救贖,渴望重生。王華的《在天上種玉米》講述一個村莊向城市整體遷移的故事,這群農民有著向往城市的夢想,房東看到自家房頂一片片玉米林時的妥協則體現了城市人的田園夢。[5]127王華在女性的人文關懷下展現出一幅和諧的圖景,那一片片生機勃勃的玉米林是“城鄉融合”的象征。
三是對隕落的民俗文化的復活。鐘敬文提出:“民俗學研究對象是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人民所創造、享用、傳承的生活文化。”[7]民俗隨著民族的歷史演變而不斷發生變化,以一種流動的姿態而存在。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將民俗文化帶到文學創作中,彰顯民俗文化的價值與意義。肖勤先后在《當代》《十月》《小說選刊》《民族文學》等刊物上發表《棉絮堆里的心事》《霜晨月》《丹砂的味道》《云上》《暖》等幾十部作品,曾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其作品有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厚重的民族文化意蘊。
肖勤作為仡佬族,對本民族文化無比崇敬,她渴望在文學作品里尋找到民族歷史的記憶,挖掘本民族的精神信仰。她穿梭于歷史的幽徑,解讀民族代碼,追憶一代代仡佬族人的生活。《丹砂》中的“我”出生時,奶奶剛好離開人世,這讓“我”的身份更加神秘;而“我”的行為也是非常怪異,晚上清醒,白天睡覺,總是重復做著一個相同的夢,夢里有一片紅色海洋,堂祖公給“我”沖儺時,“我”一進門就要屋里藏著的“紅色東西”;對“我”而言,丹砂是身體不可或缺的元素“鋅”,我在丹砂的滋養下走出大山,奔向外面的世界;對于堂祖公老一輩的人,丹砂是他們的“命”,是一種身份象征,堂祖公在死時都因沒有借丹砂給奶奶而愧疚自責,尋找丹砂也是在尋找遠去的仡佬族文化。[8]235貴州各少數民族文化奇特而神秘,但在現代化進程中,民族文化不斷流失,語言、建筑、服飾、節日等元素逐漸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以肖勤為代表的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懷著對民族的信仰與崇拜進行文學創作,期望重拾民族文化的碎片。肖勤在《你的名字》,通過塑造馮愉快、滾月光、袁百里三個性格身份迥異的人物,連接起底層社會、村寨、基層權力機關三個不同場域,寫出社會的不公、生活的沉重、欲望的膨脹和權力間的較量[9]。肖勤用真摯的情感和執著的姿態,用質樸堅實的語言敘述鄉土中的人們邁向現代文明時遇到的種種困惑和抗爭,書寫對民族精神的堅守傳承和對精神信仰的追求。
三、多種藝術手法的探索
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植根現實土壤,用文字記錄時代變化,同時,她們借鑒吸收多樣的藝術手法,豐富小說內容,增強小說藝術感染力量。
一是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注重小說真實性、典型性,關注現實人生。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的鄉土小說,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一直貫穿其中,她們關注地域文化、苦難敘事、底層書寫。王華的《儺賜》、肖勤的《暖》、崔曉琳的《東一街》、幺京的《彩蝶飛舞》和聶潔的《我在老鴰林》都是取材于黔地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展現貴州獨特的地域特點,一方面關注環境中人的生存狀況。這些少數民族女性作家親眼見證貴州鄉村近幾十年的滄桑變化。貴州的鄉土雜糅了新與舊、苦難與溫情,在走向現代化時有著不為人知的辛酸歷程。作家們用女性溫柔情懷細數鄉土點滴,她們的創作有意識地對本民族文化、風俗、語言進行展示,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民族文化認同感。一部好的作品往往隱含著作家獨特的思想內涵,表達出對人的關懷。王華的《儺賜》表達作者對底層人物命運的關注與對陋俗的鞭撻[10];崔曉琳的《東一街》講述小城市民的日常生活,揭示現代化浪潮帶來的時代變化和精神困惑,是對當下生活的真實寫照[11];幺京的《彩蝶飛舞》講述黔東地區普通人的生活,反映當地獨特的風俗文化[12];聶潔的《我在老鴰林》以非虛構的寫作方式記錄老鴰林的發展變化[13]。女作家們展現出在新的審美觀念下對鄉村書寫的新探索,挖掘現實主義美學特征,探尋貴州鄉土精神中生生不息的文化要素。
二是借鑒吸收魔幻現實主義。20世紀50年代前后,拉丁美洲掀起了魔幻現實主義浪潮,該創作方法在拉美地區產生巨大影響并傳入國內。一些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也受其影響,少數民族身份更為她們的創作添上一種神秘文化色彩。王華的《雪豆》、肖勤的《丹砂》創作手法都是對魔幻現實主義的借鑒。《雪豆》的“魔幻”主要體現在故事背景的神秘與故事情節的荒誕上。《雪豆》中的橋溪莊充滿“魔幻”色彩,作者在文中用大量筆墨寫村莊的怪異。橋溪莊多年不下雪,村莊周圍都在飄雪,但橋溪莊的上空依舊不見雪的影子。作者筆下的橋溪莊永遠死氣沉沉,整個村莊充滿異樣。在情節上,“雪豆”是橋溪莊最后一個健康出生的嬰兒,這個人物帶有一種神秘性,剛出生時她就會喊“完了”,在母親咳嗽嚴重時開口會說“媽,不死。媽,不死”。“雪豆”身上被賦予某種象征意味。橋溪莊“雪”字輩的人命運不同,但都蒙上了一種神秘而悲慘的色彩。雪山為雪豆偷貓不幸被砸傻,雪果因雪朵的離去、田妮的逃跑而變得非常怪異,最后對母親和雪豆犯下亂倫之罪,被李作民砍掉一只腳板,后來雪果悄悄地離開了橋溪莊,而橋溪莊的人都瘋瘋癲癲,得了各種怪病,“魔幻”的色彩始終籠罩橋溪莊。肖勤的《丹砂》中同樣有一種“魔幻”的氣息。“我”在奶奶剛死之時毫無預兆地來到世上,只在白天睡覺,經常做相同的夢,而夢中的紅色海洋讓我如癡如醉,“我”的堂祖公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他說“我”身上附有“我”奶奶的魂,他對著我喊“崽他奶”。作者在真假變幻中顯示出現實、希望與幻想之間的緊張沖突,使文本呈現荒誕性。作者直面荒誕、用節制陌生化的語言將魔幻現實主義滲透于文本中。
三是后現代主義小說創作手法的運用。在后現代主義作品中,傳統的小說觀念和形式被棄如敝履,他們用游戲化的姿態對待小說語言的使用和文本呈現,在敘事上以元敘述和碎片化的策略打破傳統小說的封閉性和完整性,用各種體裁、話語的雜糅和拼湊打破小說的體裁界限。后現代主義作家認為,小說本身是虛構的,在講故事的過程中不局限情節的邏輯順序,虛構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中融為一體,力圖從內部對傳統敘事方式進行解構,建立新的敘事模式。后現代主義主張世界并非是一個整體,而是由零散的碎片拼湊而成,這種認識下后現代主義小說故事的完整性也被破壞,這些小說家呈現的作品是由混亂的故事碎片構成,這與傳統小說敘事主張故事情節的完整性、邏輯性截然不同。布依族女作家楊打鐵的小說突出特點就是后現代主義的運用,獲“駿馬獎”的作品《碎麥草》[14]就是最好的體現。“在《寫作的零度》中,巴特認為零度寫作是一種直陳式寫作,敘述者以一種冷靜、客觀的方式講述筆下的故事,給讀者一種沒有溫度的情感體驗,讓人難以把握寫作者的立場。”[15]楊打鐵用后現代主義構建了另類的文學磁場,她的小說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情節破碎。《碎麥草》中情節跳躍,每個故事都可以獨立存在,作品像無數個故事拼湊在一起。從楊打鐵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后現代主義對她文學創作的影響,這也為貴州少數民族文學提供了新的范本。
四、體悟日常生活中的文學價值
崔曉琳、聶潔、幺京三位女性作家著眼于對日常生活的書寫,在平淡悠長的日子中講述時代變遷,展現人與命運的漫長對決。她們的作品呈現一種綿密、細致、內斂的敘述氣質,善于把日常生活陌生化。像亞當·扎加耶夫斯基、雷蒙德·卡佛等藝術家都擅長將日常生活的書寫作為創作的重要內容,對生活進行文學性關照,構建一個日常生活間隙中的詩意世界。日常生活,是與眾生最貼近的生存之地,卻也是最容易被忽略與忘卻的現實。作為生存空間,日常生活展現出一種瑣碎、真實、新奇的狀態,最能反映時代生活的變化和人的精神困境,是當下現實的真實寫照。在眾多文學經典作品中,作家們更傾向于把日常生活作為敘事背景呈現。崔曉琳、聶潔、幺京充分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把生活細節納入話語體系,找回生活本體的意義。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社會面貌煥然一新,鄉村在衰敗、在改造、在重生,鄉村日常生活的變化演示著中國時代文化形態的變化。書寫鄉村日常生活是中國鄉土文學的一個重要使命,通過對鄉村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描寫,彰顯鄉村在變與不變中始終保持著的蓬勃生命力。文學不應該只寫那些宏大主題,更應該致力于挖掘日常生活的細節,抓住日常生活也就抓住了敘事的重要內容。
崔曉琳的短篇小說集《東一街》把故事定格在一條充滿人間煙火的小街巷,小說中沒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只有平淡日子里普通人的生生死死。崔曉琳把普通人請上舞臺,上演了一個個瑣碎而又真實的故事。《金鐲子》講述婆婆與新媳婦的暗自較量,如何才能讓毫無血緣關系的兩代人消除對彼此的顧慮,讓兩顆陌生的心真正靠近。《如果就此老去》寫一個家庭破碎后,彼此之間的牽掛。“我”的父親是神一樣的存在,是有知識、有氣質的男人,母親其貌不揚,整天嘮嘮叨叨,但任勞任怨。“我”的父親選擇離婚,母親從此獨自生活,但是母親一直默默守護著他,任何節日都要“我”去陪父親說話、吃飯,關心他生活的點點滴滴。他們是普普通通的人,有著庸常、平凡、孤獨的生活處境,也有著自尊、固執、善良的性格。母親身上的溫暖讓整篇小說散發人性的光輝。他們終將在愛與被愛中釋懷。
聶潔《我在老鴰林》講述一個真實存在的貴州少數民族村寨,也是她用心建構的文學世界。她用“村落志”的文字記錄鄉村的地理空間與日常生活,在前進的歷史潮流中留下自己的生命體驗。聶潔用女性獨特的視角去看待處在社會轉型期的鄉村社會,借助大量真實存在的人物講述“老鴰林”這片土地的滄桑變化,為讀者呈現一個過去、現在與未來相互勾連的鄉村。聶潔用一個中立者的姿態記錄,盡可能還原現實真相,揭示現實背后的社會歷史意義。聶潔用文字記錄老鴰林人們生活的種種景象,關注這群生活在城市與鄉村中間地帶的普通人如何尋找生活的出路。
幺京的《彩蝶飛舞》取材于黔東少數民族生活,讀她的文字如沐春風,她筆下的生活明亮,作品中傳達出生活的溫度。她用銳利的眼睛挖掘時代變遷下的日常生活,作品中跳躍的是她熾熱的青春以及體察生活后的感悟。《貓眼》中,李衛國和妻子在偏遠的地方當駐村干部,幫扶村里的老人和孩子,而把年幼的貝貝交給行動不便的母親照看,貝貝意外受傷,夫妻倆無比自責,為時刻關注家里的情況,特地安裝攝像頭,父母和孩子之間通過那小小的貓眼傳遞著對彼此的掛念。近些年,文學作品中出現大量有關鄉村扶貧題材的作品,一方面,這是時代現實的寫照,另一方面,也表現出這些作家的時代自覺。
五、“土地”意象及其內涵
21世紀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小說中意象繁多,烘托出濃厚的地域色彩與多姿的風俗民情,有獨特的審美意義和藝術價值。意象是中國古代文論的一個審美范疇,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16],這里“意象”即表意之象,指用來表達某種觀念或具有哲理的藝術形象。龐德認為意象是在瞬間呈現的理智與感情的復雜經驗,意象承載著作家獨特的生命體驗與情感意蘊。在眾多的鄉土小說中,土地始終作為核心意象被闡釋。
在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上,農耕文明占據主導地位,中國的鄉村植根于土地,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中,人們為土地而生,為土地而斗爭,中國的歷史也是一部土地文化史。作為一種物質生產資料,土地是人類生存的載體,真實存在于客觀世界中。土地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自然地理概念,也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原點。在人類長期發展形成的話語系統中,土地的含義又遠遠超過其自然屬性,承載著內蘊豐厚的文化原型。在現代化語境中,土地衍生出諸多的聯想物,代表生命、故土、母親、原鄉等文化命題。“土地”意象具有象征意義和文化含義,是人類精神的符碼,在社會現實意義、審美特質、價值立場上有重要作用。從文學表現看,“土地”作為重要的審美對象存在于中外文學視野中,由于國別、地域、種族的差異,作家們賦予土地的內涵也有所不同。艾略特筆下生成的是遼闊的荒原,而在中國作家筆下呈現的是“麥地”“商州”“東北高密”等精神原鄉。中國作為一個以農業為主導的國家,土地的文學書寫更具表現性、意義更加豐富。21世紀以來,中國的鄉村受到城市化、商業化的沖擊,城市的價值觀念體系日漸侵蝕鄉村的倫理價值,現代生產方式改變傳統的農耕方式和土地的自然屬性,土地的重要性遭到質疑。新一代農民放棄土地,奔向城市尋求新的生存方式。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把土地作為文本內容的核心意象,進一步探討人和土地的關系。王華《儺賜》《在天上種玉米》《回家》和肖勤的《暖》《霜晨月》等作品中反復出現“土地”這個意象。她們以現實主義精神直面鄉村巨變的現實,反映21世紀的農民關于土地觀念的變化,描寫在歷史變遷中農民對土地情感變化的軌跡。
21世紀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鄉土小說中土地意象主要表現為農民對土地的依賴和人與土地的疏離兩種狀態。第一是農民對土地的依賴。在傳統觀念中,土地是農民生存的根本,土地是衣食住行的重要載體,是漂泊者的精神原鄉,對土地的眷戀與依賴是人的天性,特別是在農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中華民族,對土地的熱愛早已烙印于心。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在文本中就表達了農民對土地的崇拜與依賴。《儺賜》中的村莊地理環境惡劣,土地貧瘠,但是儺賜莊的村民辛苦耕耘于那片土地,從未埋怨、從未想過逃離。《在天上種玉米》中,年輕一代帶領整個村莊搬離農村,實現了從土地謀生到打工謀生的過渡,但以王紅旗為首的老一輩卻放不下“土地”,于是他們在異地開辟了屬于自己的一片“土地”。第二是人與土地的疏離。隨著社會轉型,世代在土地上掙扎的農民選擇逃離家園,尋找更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在鄉村和城市相互流動的過程中,作家們關注到土地意識弱化、農民身份缺失等問題。王華《回家》中,一批農民工涌入城市,經濟危機的到來讓他們難以在城市立腳,無奈之下又回到鄉村,由于土地轉租與撂荒,他們很難回到土地,于是這批人就在城市與鄉村的夾縫中艱難尋找出路。究竟何去何從是小說中這批人所面臨的困境,也是作者的發問。肖勤的《暖》以商業化沖擊農村,一批農民流向城市為寫作背景。他們對土地價值持懷疑態度,于是失去了耕種的熱情。事實上,人們對土地的疏遠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由于經濟發展,人們不再需要將土地視作唯一出路,人與土地的感情也隨之破裂。貴州少數民族女性作家沒有一味地去營造鄉村詩意化的田園生活,也沒有去揭露鄉村愚昧與落后的精神狀態,她們只是把故事的背景建構在自己熟悉的地域,將土地作為自己靈魂的棲息地,去闡發自己對土地乃至人類命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