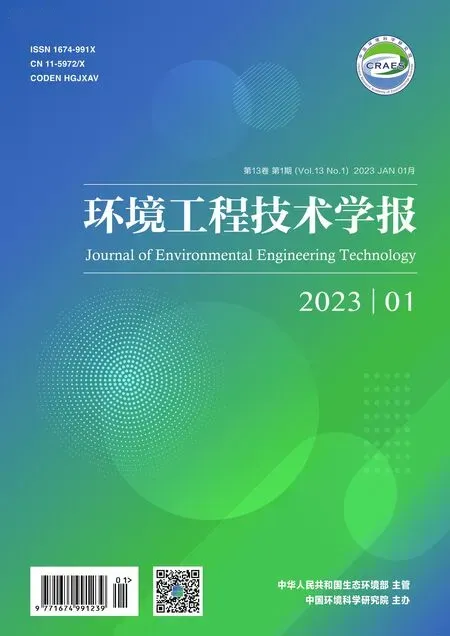燕山礦區苜蓿恢復過程中土壤養分與微生物的演變特征
馬建軍,姚虹,劉輝,田美榮,3*
1.廊坊師范學院生命科學學院
2.廊坊澤通林業工程設計有限公司
3.環境基準與風險評估國家重點實驗室,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礦區是在人為因素嚴重干擾下形成的一種極度退化的生態系統,礦產資源開采時會因原有的表土及植被剝離而導致水土流失加劇、生態系統功能降低。植被恢復是控制水土流失和恢復生態系統功能的唯一策略,是礦區土壤生態系統重新發育和演替的基礎。自然恢復通常需要較長時間,生態威脅將可能長期存在。因此,在礦區建立一個高效、可持續的人工植被恢復系統已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和廣泛關注[1-2]。
植被恢復對土壤生態系統具有深遠影響,而土壤對植被恢復的響應存在滯后效應[3]。因此,有必要評估植被恢復對土壤養分及微生物的長期影響[4]。苜蓿(Medicago sativa)是京津冀地區分布廣泛的人工植被類型,其抗堿能力強、生態適應性強,具有增加生態系統氮輸入的潛力,同時可促進植被和土壤中碳、氮的積累[5-6]。苜蓿的土壤改良效果尤其明顯,在加速植被恢復[7]、防止水土流失[8]、修復退化土壤等方面效果顯著[9]。然而,種植年限直接影響著苜蓿的生長情況,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區,苜蓿生長盛期持續時間一般為5~6年,6~7年產量迅速下降,10年后逐漸退化演變為自然植物群落[10],苜蓿的這種階段性生長對土壤水分、理化性質、養分變化和土壤酶等方面造成影響。
目前,苜蓿對土壤的影響研究多集中在土壤理化性質[11-12]、修復重金屬污染[13]、土壤微生物[14-15]等方面,而對于在極端惡劣礦區環境中,苜蓿地土壤養分與微生物演變規律及其土壤改良的時效性和持續性仍缺乏足夠的研究[16],但這方面的研究對于持續恢復礦區脆弱的生態系統有著積極的指導作用。
燕山山脈是中國北部著名山脈之一,是首都北京的綠色屏障和水源地,是環首都生態建設的重點地區,也是我國重要的礦產基地。河北省三河市東部礦區是廊坊市唯一的山區,系燕山余脈南麓,盛產白云巖。自20世紀70年代至2015年作為京、津建筑原料的供應基地,長期石材的開采破壞了山體的外貌和植被,導致土地資源和環境資源喪失,使土地失去原有的利用價值。本礦區在開采的同時進行了植被恢復工程,其中以種植豆科牧草苜蓿為主,在礦區形成了不同種植年限的苜蓿地恢復序列。
筆者以該礦區采石場平臺不同種植年限的苜蓿地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苜蓿地土壤養分和土壤微生物的動態變化,探索苜蓿地恢復過程中土壤養分和微生物的演變規律,旨在闡明以引種苜蓿作為土壤改良的措施在燕山礦區生態恢復中是否是高效和可持續的,即與未恢復對照樣地相比,苜蓿對土壤的改良效果是否是高效的;與原生境對照樣地相比,苜蓿對土壤的改良效果是否是可持續的,是否有明顯的時效性。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為三河市東部白云石露天礦區(117°05′13″E~117°11′10″E,40°00′23″N~40°02′34″N)(圖1),行政區劃屬三河市黃土莊鎮和段甲嶺鎮。三河市東部礦區地處燕山山脈東段南緣與華北平原接壤部位的低山丘陵區。三河市屬典型暖溫帶大陸性氣候,年均氣溫11.1 ℃,年均降水量617.4 mm,年蒸發量1 681.9 mm。礦區土壤類型以石灰性鹽堿褐土為主,土質疏松,抗蝕抗沖性差,水土流失嚴重,有機質濃度低。礦區采石場原生表土已經全無,現多為缺乏養分與水分的新生石礫土和沙質土。

圖1 研究區及樣地設置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tudy area and sample plots
1.2 樣地設置與采樣
2020年8 月,在坡位、坡向、海拔等立地條件基本一致的采石場平臺上選擇恢復年限分別為3年(Me3)、6 年(Me6)、10 年(Me10)和 15 年(Me15)的4個苜蓿恢復樣地,苜蓿地種植后僅在前2年進行澆灌和2次刈割,以后未進行人工干預,處于自然演替狀態。在礦區內選擇已經開采但未進行恢復的區域(CK1)和有代表性且未經開采的自然區域(CK2)設置2個對照樣地(圖1)。樣地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樣地基本情況Table 1 Basic properties of the sample plots
4個苜蓿恢復樣地和對照樣地CK1的表層覆蓋客土,來源于研究區附近建筑工程地基開挖過程中所產生的開槽土和工程棄土。恢復期間所有樣地均未施肥。
在每個樣地中,設置3個10 m×10 m取樣小區,小區之間及其與樣地邊界之間的距離均大于10 m。在每個采樣小區中,按照S型多點采樣法,沿S形路線均勻設置12個取樣點(取樣點距離植株基部3~5 cm左右),去除土壤表面凋落物層后,用土鉆采集0~20 cm土壤樣品,并進行混合,用無菌塑封袋密封后,用冰盒冷藏并迅速帶回實驗室。采集的土壤樣品分為2份:一份過2 mm篩后室內自然風干,用于測定土壤養分;一份于-20 ℃冷凍保存,用于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測定。
1.3 土壤養分的測定
速效氮(AN)濃度采用堿解擴散法測定;速效磷(AP)濃度采用鹽酸和硫酸溶液浸提法測定;速效鉀(AK)濃度用乙酸銨浸提-火焰光度法測定[17];土壤有機質(OM)濃度采用重鉻酸鉀容量法-外加熱法測定。每個樣品做7個重復。
1.4 土壤微生物群落分析
采用CTAB法對不同樣品的總DNA進行提取,經1%瓊脂糖凝膠電泳測定抽提的基因組DNA。擴增細菌16S rRNA基因的V3+V4_b高變區段,引物為 338F(5'-ACTCCTACGGGAGCAGCA-3')和 806R(5'GGAC TACHVGGGTWTCTAAT-3')。真菌多樣性對18S rRNA的ITS1_f區段進行測序,引物為ITS1F(5'-CTTGGTC ATTTAGAGGAAGTA A-3')和2043R(5'-GCTGCGTTCTTCATCGATGC-3')。擴增條件為 98 ℃ 預變形 1 min,98 ℃ 變形 10 s,50 ℃ 退火 30 s,72 ℃ 延伸 60 s,30 個循環,72 ℃ 延伸形5 min[18]。土壤樣品完成DNA提取后,送北京百邁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進行Illumina高通量測序。每個樣品做7個重復。
1.5 數據處理與分析
所有數據采用Excel及R-3.6.3中的Vegan分析包進行統計分析。根據方差分析和Tukey檢驗分析樣品間的顯著性差異。分析土壤細菌、真菌群落的Beta多樣性時,首先對操作分類單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s)表進行Hellinger標準化,采用R-3.6.3的Vegan包計算Bray-Curtis差異性距離(Bray-Curtis dissimilarity,dBCD),并進行相似性分析(analysis of similarities, ANOSIM)及置換多元方差分析(permutation-based multivariate ANOVA,PerMANOVA),分析各分組之間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并進一步通過主坐標分析(principal co-ordinates analysis, PCoA)進行可視化組間差異分析[19-20]。其中,dBCD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SA,i和SB,i為第i個OTU分別在A群落和B群落中的計數。dBCD為0~1時,數值越大,則2個樣本之間的相似性就越低;如果2個樣本相同,則dBCD=0。
2 結果與討論
2.1 土壤養分演變特征
種植苜蓿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養分[21-22]。由圖2可見,苜蓿對于土壤AN濃度、AP濃度、AK濃度和OM濃度的改良效果有一定差異。

圖2 不同樣地土壤AN、AP、AK及OM濃度Fig.2 Concentrations of soil AN, AP, AK and OM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由圖2(a)可知,隨著恢復年限的增加,土壤AN濃度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變化規律。種植苜蓿的初期,樣地Me3與未恢復對照樣地CK1間土壤AN濃度無顯著差異;隨著恢復年限的增加,樣地Me6中土壤AN濃度達到峰值,其濃度顯著高于除原生境對照樣地CK2外的所有樣地。這是由于苜蓿根部形成了大量根瘤菌,其具有固氮作用;另外一部分根系和地上莖葉腐爛進入土壤,增加了土壤養分濃度。隨著恢復年限的進一步增加,在恢復的第10年和第15年,土壤AN濃度持續降低。研究發現,本礦區苜蓿的生長盛期為6年,之后苜蓿進入衰退期,且隨著種植年限的繼續增加,根系活力下降,生物量減少,對氮素利用強度減弱,而導致的氮素歸還減少,苜蓿地土壤肥力并不會繼續保持增長[23-24]。
由圖2(b)可知,隨著恢復年限的增加,土壤AP濃度呈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的變化規律。盡管在樣地Me6中土壤AP濃度達到峰值,但是所有樣地間土壤AP濃度均無顯著性差異,表明種植苜蓿對土壤AP濃度的影響并不明顯。研究區各樣地土壤AP濃度整體偏低(均在10 mg/kg以下),苜蓿對土壤AP的消耗甚微,甚至可以積累AP。隨著種植苜蓿年限的延長,土壤AP濃度呈下降趨勢[25]。
由圖2(c)可知,隨著恢復年限的增加,土壤AK濃度呈現與土壤AN濃度相同的變化規律。苜蓿對于土壤AK濃度的影響較為明顯,樣地Me6中土壤AK濃度達到峰值,其濃度顯著高于所有樣地。苜蓿在生長過程中對鉀元素的需求量也很高,在本研究中樣地Me3和Me6土壤AK濃度顯著增加,這是由于在研究區鹽堿性土壤中鉀元素濃度較低,且主要以礦物態鉀和非交換態鉀形式存在,交換態鉀和水溶態鉀濃度較低[26]。不同形態間的鉀存在著動態的平衡,苜蓿生長過程中需要大量的AK,而各苜蓿地中AK濃度依然高于對照樣地CK1和CK2,說明長勢旺盛的苜蓿(Me3和Me6)可以大大促進土壤AK的轉化[27]。隨著苜蓿生長的衰退(Me10和Me15),苜蓿對鉀的轉化能力逐漸減弱,同時大量本土植物在樣地中出現,植物在生長過程中的吸收及淋溶作用會造成土壤AK的減少,因此隨著種植年限的延長,土壤AK濃度降低[14]。由圖2(d)可知,隨著恢復年限的增加,土壤OM濃度總體呈增加趨勢,且均高于對照樣地CK1,但均顯著低于對照樣地CK2,這與樣地中枯落物的淋溶腐解、腐殖質含量增加有關[28-29]。
有研究顯示,苜蓿在不同地區有著7年[10]、10年[30]、11年[31]等不同的生長盛期,本研究區苜蓿的生長盛期為6年,這與采石場土壤現狀(開槽土和工程棄土)、利用方式(保土固沙、2次刈割)和管理措施(未施肥、長期自然演替狀態)等有關。因此,應加強苜蓿地的科學管理和合理利用以延長苜蓿的生長時間[32]。
2.2 土壤細菌群落結構演變特征
不同樣地優勢細菌的相對豐度如圖3所示。本研究區細菌類群中相對豐度水平前5的優勢門依次為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酸桿菌門(Acidobacteria)、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厚壁菌門(Firmicutes)、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圖3(a1)~圖3(a5)〕;優勢科依次為鞘氨醇單胞菌科(Sphingomonadaceae)、梭菌科(Pyrinomonadaceae)、伯克氏菌科(Burkholderiaceae)、根瘤菌科(Rhizobiaceae)、芽孢桿菌科(Bacillaceae)〔圖3(b1)~圖3(b5)〕。
由圖3(a1)可知,變形菌門的相對豐度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變化規律,樣地Me10中變形菌門的相對豐度顯著高于所有樣地;其他樣地間,該門的相對豐度無顯著差異;該門中的鞘氨醇單胞菌科〔圖3(b1)〕和伯克氏菌科〔圖3(b3)〕呈現與該門一致的變化規律,而根瘤菌科〔圖3(b4)〕則呈現較復雜的變化規律:峰值出現在樣地Me10,而Me6、Me15及CK2樣地中根瘤菌科的相對豐度均較低且無顯著差異。變形菌門細菌在不同環境中廣泛分布,適應能力強[33],是堿性土壤中的主要優勢群落,廣泛存在于以鹽堿土壤為主的礦區土壤中[34]。與CK1相比,富營養型細菌類群變形菌門的相對豐度在所有苜蓿樣地中有所增加,這與黃土高原草地植被自然演替過程中的細菌群落組成的變化規律表現出相同的趨勢[35]。其中樣地Me3、Me6和Me10中變形菌門的相對豐度均顯著高于CK1和CK2。變形菌門在土壤中所占比例越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土壤越肥沃,在一些黑土地及半濕潤地區的土壤中變形菌門往往是優勢菌群[36]。本研究也證實,在種植苜蓿初期,可以改善土壤變形菌門分布狀況。
酸桿菌門〔圖3(a2)〕的相對豐度呈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的變化規律,第6年其相對豐度顯著高于其他苜蓿樣地及對照樣地CK1,而顯著低于樣地CK2;其中,隸屬于該門的梭菌科〔圖3(b2)〕的相對豐度隨著苜蓿種植年限的增加而增加。酸桿菌門在自然環境中亦十分常見,可以降解植物纖維素等大分子聚合物[37]。本研究發現酸桿菌門主要存在于原生境樣地CK2中,可能與樣地中有大量的荊條、沙棗等灌木植物有關。
放線菌門〔圖3(a3)〕和厚壁菌門〔圖3(a4)〕呈現相同的變化規律,即二者的相對豐度先降低后增加。樣地Me3、Me6中,放線菌門的相對豐度高于樣地CK1(但無顯著差異),表明種植初期苜蓿雖能夠改善放線菌狀況,但效果不明顯。樣地CK1中厚壁菌門的相對豐度最高,而該門的相對豐度在樣地Me6、Me10及CK2間無顯著性差異;隸屬于厚壁菌門的芽孢桿菌科〔圖3(b5)〕的相對豐度的變化規律與厚壁菌門的變化規律一致。在干旱和寡營養的土壤中放線菌門和厚壁菌門的相對豐度較高[38]。厚壁菌門細菌細胞壁厚,結構簡單,可以產生芽孢,它可以抵抗脫水和極端環境,因而能較好地適應礦區惡劣環境[39]。樣地CK1幾乎無植被覆蓋,土壤水分含量低,故其厚壁菌門的相對豐度最高,在樣地Me3和Me6中,植被覆蓋顯著增加,土壤水分含量有所增加,故厚壁菌門的相對豐度呈下降趨勢。樣地Me10(苜蓿呈現衰退跡象)和Me15(苜蓿基本消失)的土壤含水量減少,此時相對豐度出現增加的趨勢,原生境樣地CK2中厚壁菌門的相對豐度較低,這些差異說明厚壁菌門的相對豐度與植被恢復的不同階段土壤含水量有關[40]。

圖3 不同樣地優勢細菌的相對豐度Fig.3 Relative abundance of dominant bacteria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擬桿菌門〔圖3(a5)〕的相對豐度則隨著恢復時間的增加而增加,樣地CK1、Me15的擬桿菌門的相對豐度顯著最高,而其他樣地間,該門的相對豐度則無顯著差異。擬桿菌門在水體、土壤及沉積物中也是廣泛分布的一個類群,在研究區該門也有較高的平均相對豐度。樣地Me3、Me6、Me10和Me15中擬桿菌門的相對豐度逐漸增加,但是均低于樣地CK1,這與變形菌門、酸桿菌門、放線菌門等優勢菌群在上述樣地中競爭性增強有關[41-42]。
2.3 土壤真菌群落結構演變特征
不同樣地優勢真菌相對豐度如圖4所示。本研究區真菌類群中相對豐度水平前5的優勢門依次為子囊菌門(Ascomycota)、擔子菌門(Basidiomycota)、毛 霉 門 (Mucoromycota) 、 隱 真 菌 門(Rozellomycota) 、 被 孢 霉 門 (Mortierellomycota)〔圖4(a1)~圖4(a5)〕;優勢科及其平均相對豐度依次為曲霉科(Aspergillaceae)、毛殼菌科(Chaetomiaceae)、被孢霉科(Mortierellaceae)、粉褶菌科(Entolomataceae)、枝孢霉科(Cladosporiaceae)〔圖4(b1)~圖4(b5)〕。
在真菌群落中,子囊菌門和擔子菌門是自然界中分布最廣、豐度最高的2個真菌類群,這與其代謝特性及在多種生境中較強的生存能力有關[43]。本研究區子囊菌門〔圖4(a1)〕和擔子菌門〔圖4(a2)〕的相對豐度均較高,這與Yang等[44-45]在黃土高原半干旱區退耕草地中研究的結果相似。子囊菌門和擔子菌門大多數為腐生菌,本研究中各樣地土壤pH為7.5~8.5,堿性土壤最適合腐生真菌的生長,這可能是子囊菌門和擔子菌門為優勢菌門的一個原因[46]。
由圖4(a1)可知,隨著恢復年限的增加,子囊菌門的相對豐度呈先降低后增加趨勢。子囊菌門是土壤腐生真菌,易受到植物種類和植物殘茬的強烈影響,其功能是分解木質化植被碎屑[47]。本研究中各苜蓿樣地中植被覆蓋度及植被殘茬均顯著增加,使子囊菌門真菌能夠更好地利用可降解的植被殘茬,促進菌群的快速增長與繁殖[48],故各苜蓿地子囊菌門的相對豐度均顯著高于CK1。本研究中,隸屬于子囊菌門的優勢科為曲霉科、毛殼菌科和枝孢霉科。曲霉科〔圖4(b1)〕的相對豐度隨著恢復年限增加而增加,而毛殼菌科〔圖4(b2)〕與枝孢霉科〔圖4(b5)〕呈現完全相反的變化規律,即隨著恢復年限增加,毛殼菌科的相對豐度是先降后增,而枝孢霉科的相對豐度是先增后降。

圖4 不同樣地優勢真菌相對豐度Fig.4 Relative abundance of dominant fungi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擔子菌門〔圖4(a2)〕呈現與子囊菌門相反的變化規律,這與子囊菌門真菌優勢度增加有關[49-50]。自然界中超過98%的陸生真菌屬于子囊菌門和擔子菌門,而且前者的物種多樣性明顯多于后者,子囊菌門的物種數量是擔子菌門的2倍多[51]。本研究中,隸屬于擔子菌門的粉褶菌科〔圖4(b4)〕的相對豐度隨著恢復年限增加而增加。
毛霉門〔圖4(a3)〕和隱真菌門〔圖4(a4)〕的變化規律較為一致,即二者的相對豐度隨恢復年限的增加而呈現降低的趨勢。毛霉門真菌能夠吸收糖和簡單的多糖以及N、P、K等營養物質,其孢子萌發快,菌絲生長速度快。因此,在植被恢復的初期最先形成優勢菌,然而毛霉門真菌對自身代謝副產物的積累較為敏感,尤其是環境中CO2的積累,使其停止生長,產生休眠結構,進入休眠狀態。毛霉門真菌的相對豐度在苜蓿種植初期(3~6年)之后逐漸較低,這一演替階段隨著毛霉門真菌自身可利用的營養物質的消耗和土壤中CO2的積累而消失,樣地Me15中毛霉門真菌幾乎消失。隱真菌門是在水體及極端環境中廣泛分布的真菌,在土壤中相對較少[52-53]。本研究顯示,各樣地的隱真菌門無論從相對豐度(均較低),還是從變化規律(逐年遞減)呈現出非常一致的變化規律。
隨著苜蓿種植年限的增加,被孢霉門〔圖4(a5)〕的相對豐度在樣地Me6中達到峰值(與Me10間無差異);在樣地Me3、Me15和CK2中,其相對豐度均極低;在樣地CK1、Me6、Me10中,其相對豐度均顯著高于樣地CK2。被孢霉門是土壤養分豐富的標志類群,與土壤養分有密切聯系[54]。本研究顯示,盡管各樣地中被孢霉門的相對豐度較低,但是呈現了一定的規律性,即隨苜蓿種植年限的增加呈先升后降趨勢,最高值出現在第6年,這與土壤AN和AK變化規律相一致。本研究中,隨著恢復年限的增加,隸屬于被孢霉門的被孢霉科〔圖4(b3)〕的相對豐度呈現與該門較為一致的變化規律。
2.4 細菌/真菌群落Beta多樣性演變特征
為了進一步闡明不同恢復年限苜蓿地間微生物群落組成上的差異性,本研究基于Bray-Cutis距離矩陣采用PCoA分析了6個樣地土壤細菌及真菌群落物種組成的相似度,結果見圖5、表2。

表2 基于Bray-Curtis距離算法的樣地間土壤細菌/真菌的距離(dBCD)矩陣Table 2 Distance matrix of soil bacteria / fungi between sample plots based on Bray-Curtis distance(dBCD) algorithm
由圖5可見,土壤細菌和真菌的7個重復樣本聚在一起,這說明樣本的重復性較好,組內變異相對較小。在細菌PCoA分析中PCoA第1軸和PCoA第2軸分別解釋了變異信息的32.59%、16.36%,二者累計貢獻率達48.95%。結果表明,在第1軸方向上,樣地Me3與樣地CK1的細菌群落組成較為相似,樣地Me6和Me10相似,樣地Me15與樣地CK2相似性較低。在真菌PCoA分析中PCoA第1軸和PCoA第2軸分別解釋變量方差的24.97%、14.69%,二者累計貢獻率達39.66%。結果表明在第1軸方向上,隨著苜蓿種植年限的增加,土壤真菌群落組成發生明顯的階段性變化,樣地Me3和Me6與樣地CK1相似,而樣地Me15與CK2相似。

圖5 土壤微生物PCoA分析圖Fig.5 PCoA analysis of soil microorganisms
土壤細菌和真菌隨著恢復時間的增加呈現逐漸本土化的演變趨勢,但二者的演變進度存在差異。由Bray-Curtis距離矩陣(表2)可知,與未恢復樣地CK1相比,在種植苜蓿的第10年,樣地Me10與樣地CK1的細菌群落的Bray-Curtis距離就達到了0.524 4,而此時兩樣地的真菌群落的Bray-Curtis距離為0.245 2;在種植苜蓿的第15年,樣地Me15與樣地CK1的真菌群落的Bray-Curtis距離為0.572 2。各樣地與樣地CK2的真菌群落的Bray-Curtis距離也明顯大于與細菌群落的Bray-Curtis距離。顯然,苜蓿地土壤細菌群落演變較快,而真菌群落的演變相對緩慢。
Dangi等[55]研究了美國懷俄明州東北部露天煤礦復墾地經過14年的土地復墾,土壤真菌群落結構基本達到正常水平。本研究與Dangi等[55]研究結果存在差異的原因在于苜蓿對土壤細菌群落的碳源供應更充足,恢復能力很強[56],所以本研究中細菌的恢復進程更快,而真菌在競爭中處于劣勢,恢復較為緩慢[57]。另有研究顯示,隨著生態系統的成熟,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主導地位將由細菌向真菌轉變[58]。
3 結論
(1)與未恢復對照樣地相比,苜蓿可以高效地提高土壤AN、OM、AK等養分的濃度以及變形菌門、酸桿菌門、子囊菌門、擔子菌門、鞘氨醇單胞菌科、伯克氏菌科、根瘤菌科、芽孢桿菌科、毛殼菌科、粉褶菌科等優勢微生物類群的相對豐度。
(2)與原生境對照樣地相比,苜蓿的土壤改良效果有明顯的時效性。苜蓿對土壤養分的恢復以第6年為最佳,之后隨著恢復年限的延長,土壤AN濃度及AK濃度呈下降趨勢;在第6年或第10年,土壤優勢微生物類群的相對豐度顯著升高;苜蓿對細菌的恢復進度較快,而對真菌的恢復較慢。苜蓿地恢復中應充分考慮氣象、土壤等環境因素,根據不同區域特點對苜蓿地進行科學的管理與利用,以延長其土壤改良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