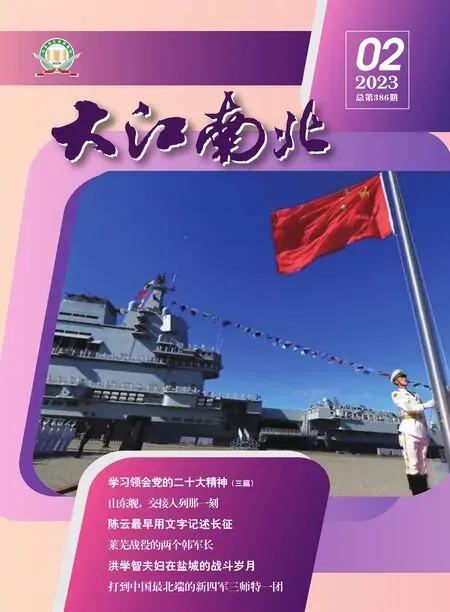劇壇“將星”劉保羅的傳奇人生
□ 石慶華
在我國現代新文化運動中,有一支“輕騎兵”,那就是進步話劇。這支隊伍有一位領軍人物,名叫劉保羅。
劉保羅,1907年出生于湖南長沙,出生時,家中窮得請不起接生婆,他的臍帶還是姐姐給咬斷的。為了記住這困苦,母親給他取名臍生。他父親早逝,靠著姐姐紡紗織布供讀書。1925年考入長沙師范,開始接受進步思想,后在長沙大東書店當雇員。1927年他離鄉赴上海,在南華書店當雇員期間,閱讀了大量進步書籍,視野更加開闊。1928年秋天他路過南京,觀看了南國劇社演出的話劇《湖上的悲劇》,從此愛上了話劇。他認為“戲劇能夠陶冶人的精神,還可以用來宣傳發動群眾”。在書店當伙計的他,每天起早摸黑干活,每月到手也就二三元工資,仍省出零錢來買話劇票。有一次,他聽說田漢率團在南京演出,就專程趕到南京。兩位老鄉一見如故,很快成了莫逆之交。在田漢的引領下,他如愿走進了話劇圈。在以后的日子里,劉保羅逐步參加到田漢旗下的好幾個劇團,開始在上海舞臺上嶄露頭角。
1929年,他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上海藝術劇社。次年春,他在《西線無戰事》中飾演了—位從軍的青年戰士保羅,由于富于激情、演得逼真,受到觀眾贊賞,從此易名劉保羅。藝術劇社在逆流中勇進,也激勵和團結了不少戲劇人。隨著劇社的影響不斷擴大,當局對之也加緊了“圍剿”。1930年4月的一天,年少氣盛的劉保羅因抗議查封藝術劇社,與外國巡警發生沖突,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參加了監獄里黨組織領導的絕食斗爭。1931年,被關了一年的他獲釋,出獄后任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黨團書記。此后一段時期,他組織領導大道劇社的演出活動,積極推進左翼戲劇運動,無奈因年輕又無名氣,難以打開局面。他帶了幾位年輕同行去了杭州。
1932年4月,他在杭州組織五月花劇社,并在《浙江日報》上和龍倬合編《五月花周刊》,還多次組織會演,推動了浙江的戲劇救亡運動。他們排戲、出刊物、招募新成員,搞得紅紅火火,吸引了許多青年。五月花劇社在上海、杭州等地演出,積極開展學生和工人演劇活動,擴大影響。這時的劉保羅參加了《馬特迦》《阿萊城的姑娘》《洪水》《亂鐘》《生的意志》等劇的演出,并創作了話劇《血衣》《炮口移動》《關廠》,集編、導、演于一身,在抗敵戲劇的舞臺上相當有名氣。
1932年7月,五月花劇社在杭州演進步戲劇時,被一群軍警封在大門內,前后臺所有人員均遭逮捕。經上海戲劇界團體的交涉、疏通,幾位較有名的上海女演員和杭州的一些中學生被釋放了,但劉保羅和另兩位“領頭者”卻被判刑,關進陸軍監獄。1935年冬,剛出獄不久的劉保羅,又繼續投入進步戲劇運動,組織浙江兒童劇場,創作兒童劇《報仇》《小姐哭黑貓》等。
二
抗日戰爭爆發后,剛成立的“浙江流動劇團”請他去當導演。他與邵荃麟等人組織流動劇團在浙東、浙西城鄉各地巡回演出,宣傳抗日救亡。劉保羅集編劇、導演、演員于一身,編演了許多反映中國人民抗日愛國的劇目。流動劇團是掛靠“浙江省抗敵后援會”這個民間組織的,沒有固定經費,所謂“導演”自然沒薪水,其他人也沒有。全體團員不發一分錢生活費,伙食是就地“募化”,“募化”不到錢時就賣幾分錢一張門票,住宿地是戲臺或祠堂,運輸工具是兩條裝載行李道具的小船,人員則全是開步走。有時由于觀眾踴躍,門票款收入除開銷外有剩余,他就拿去資助當地民眾的抗日費用。那時的劇團不僅每天晚上演出,白天還上街挨門挨戶作抗日宣傳,刷漫畫標語,協助當地青年成立抗日宣傳團體……開始時劇團二三十個人,最后達到四五十人。劇團里許多成員都是杭州師范、高中的學生,他們大都慕保羅之名而來,相處融洽,精神愉快。劉保羅對這群“學生娃”很友善、耐心,排戲時一遍遍地教,從不厭煩。能寫會導又會演的他,過硬的本領讓青年人由衷敬佩!

劉保羅
這樣忙碌又快樂的生活持續了幾個月,后因為劉保羅他們在紹興柯橋鎮散發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引起當局不滿,遂把劇團人員關在諸暨城一小學內,不許有任何活動。幸虧諸暨一位慕劉保羅之名的世家子弟周抗知道此事后,托關系去縣政府說情,才解除了封鎖。隨后,周抗帶著自己創辦的小劇團投奔劉保羅而來。然而,危機之根已埋下。劇團剛回到金華,即被當局責令去麗水集訓。這一集訓,劇團就被弄散了,一部分年紀較大、水平較高的成員去龍泉縣參加地方工作了;劉保羅則帶另一部分年紀較小的人繼續堅持著流動演出。
劉保羅的隊伍輾轉由麗水經過縉云、永康,沿著懸崖峭壁的桃花嶺,再次來到金華。當趕到凌鶴的劇團駐地時,他碰巧看到作曲家麥新正站在一條板凳上指揮大家唱新作《大刀進行曲》。劉保羅跟他們都是熟人,很快就融合在一起,大唱特唱氣勢雄壯的《大刀進行曲》。后來這支歌一直伴隨著劇團從金華唱到安徽大別山,再唱到江蘇鹽城。
當劇團接到去建德勞軍任務時,情況突然發生變化。劉保羅在這里碰到了他30年代初在上海“左劇聯”的老朋友何某,后者當時在一支廣西部隊政治部當秘書,正想建立一支政治工作隊,三言兩語,就把劉保羅的隊伍給拉了過去。劉保羅也來不及跟大伙兒商量,就決定立即出發,奔赴安徽大別山。他們步行、乘卡車,又改乘火車,終于在1938年初冬在九江附近渡江北上,后經黃梅、宿松到達太湖(當時安徽省第一行政督察專署所在地)。這時,保羅劇團的其他人員才知道自己已成了國民革命軍陸軍(桂系)第21集團軍戰地服務隊第3政工大隊的隊員,劉保羅任隊長。劇團雖不列入第21集團軍正式編制,但發國軍服裝,實行供給制,每人每月有15元津貼,基本生活總算有了著落。
太湖民眾總動員委員會在圣公會掛出牌子,劉保羅領導的第21集團軍戰地服務團也在太湖城鄉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一時,農民抗敵協會、工人抗敵協會、商民抗敵協會、抗日兒童團紛紛成立。劉保羅領導的戰地服務團尤為活躍,不僅在縣城,而且經常深入到畈區、山區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演出抗日話劇,喚起民眾抗日熱情。那時,縣城的群眾集會常在公共體育場或西門外大河沙灘上舉行。人們常可看到一位中等身材、瘦削臉蛋,扎著皮帶、布綁腿,深陷的眼睛炯炯發光、講話很有吸引力、英姿勃勃的年輕人活躍在臺上,即席發表抗日救亡演說,或演出抗日內容的話劇。他慷慨激昂的言辭、精湛的表演,不時贏得觀眾雷鳴般的掌聲。這位出色的演講者和表演者,就是給太湖人留下難忘印象的劉保羅。
這時城關的學校尚未復學,由劉保羅領導的戰地服務團與抗日工作動委會在圣公會共同籌辦了兒童補習班,招收學生40多名,教材是《民眾識字課本》,教員由戰地服務團、抗日工作動委會的干部兼任。該補習班與戰地服務團、動委會駐地近在咫尺,劉保羅也曾給孩子們講課。一次劉保羅問學生什么是全民總動員?學生們一時答不上來。他含笑伸開五指說:“這五個指頭就是工、農、商、學、兵。他們分開沒有力量,要握成一個拳頭,打在鬼子身上才堅實有力。這就是全民總動員……”形象生動的比喻,平易近人的音容,數十年后,當時的學生回想起來仍覺得歷歷在目。
在農村進行抗日宣傳時,由于受演出條件和觀眾文化水平的限制,多幕、情節比較復雜的話劇往往不具備演出的客觀條件,故演出的劇目往往是一些情節較為簡單直白、獨幕劇式的活報劇,最常演出的就是《放下你的鞭子》和《盧溝橋》等。然而,由于當時各劇團都演出這些劇目,觀眾看多了,失去了新鮮感。為此,劉保羅及時創作推出了《保衛華北煤礦》的戲劇,描寫煤礦職員對日本入侵毫無思想準備,直到日本人用武力來“劫收”,才臨時抱佛腳保衛賴以生存的礦山,處處被動、捉襟見肘,鬧出許多笑話。在演出中,他不忘與觀眾互動,如專門安排角色在觀眾席中與舞臺角色對話,調動現場氣氛,引導群眾的愛國、護廠之情。這種形式既貼民眾日常生活,又達到了宣傳的目的,獲得很大的成功。此后,劉保羅開始思考“應景劇”的創作,不久又著手嘗試創作了《各界抗日鋤奸大游行》等,利用巧妙的手法把觀眾拉進戲劇當中。
劉保羅所帶的戰地服務團在太湖活動不到一年時間,由于不用顛沛流離,生活相對安定,演員們每天清晨跑步、出操、練形體,上下午排戲或上街下鄉進行抗戰宣傳,晚上演出。劉保羅在太湖期間,積極進行戲劇實驗活動,在創作和演出的過程中探索,提出和完善了“應景劇”這種新的藝術形式。為使戲劇起到總動員的效果,能從劇場戲劇走向廣場戲劇,他們的演出形式多用街頭劇、茶館劇、游行劇、活報劇等,打破了舞臺和觀眾之間的隔閡,使得觀眾參與到戲劇中來,更有利于政治教化和宣傳功能的統一。
三
抗戰戲劇是戲劇形態中號召力很強的一種,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有著特殊作用和意義。它又受戰爭條件限制,在實際功能上不得不注重特定負載,以便直接作用于現實的人,又因地域條件的限制,在生存關系上要更富于機動性,以便適應戰時環境的變化。這兩方面所造成的歷史局限,正好體現出抗戰劇單一又多棱的復雜性。“應景劇”的出現正是這種矛盾的體現。劉保羅提出:“以抗戰的政治斗爭中當前緊要的問題做內容,采取適合當時當地客觀環境的諸般形式而及時即興‘編演戲劇’。作為抗戰戲劇來說,只有兼顧宣傳性和娛樂性才能保持其影響力。”可以看到,正是這兩點促成了“應景劇”的出現。
劉保羅在創作和演出的實踐中總結出:“抗敵戲劇必須活用自己的舞臺,把戲劇當作真,分不清演員和觀眾,運用天時、地利、人和巧妙結合,表達自己正確的主題。”他十分反對只喊打倒和擁護的標語口號式東西,主張演出要有吸引人的人物、故事和戲劇性。
1939年前后,劉保羅先后創作了《滿城風雨》《盤查哨》《劉永貴放哨》《廟會》《良緣惡計》《誤會》《新鞋子》《新年小景》《二十五個》《自殺》和《奪回廣武尉》等劇本,較有影響的有諷刺民族敗類的喜劇《滿城風雨》。他創作、導演,還親自登臺表演,并且表演熱烈、真摯,極富藝術感染力。
1940年初,劉保羅到新四軍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工作。在劉少奇和鄧子恢的關心下,抗敵劇團成立,劉保羅任戲劇教員(即指導員)。同年6月,劉保羅改編的《苦難中出生的孩子》在蘇皖邊區文化委員會成立大會上演出。劉少奇看后贊賞地說:“你們很快搞出這些節目,很不錯,有戰斗作風。”1941年1月,劉保羅任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戲劇系主任,編導了《一個打十個》《王玉鳳》《月上柳梢頭》等劇目。他創作的劇本還有《寶山中秋月》《采菱船》《保險箱》《在鐵蹄下》《棗莊大捷》《臺兒莊大捷》《光榮之家》《約會》等,大多為小型話劇,反映抗日軍民生活,深受觀眾喜愛。
1941年3月15日,他率領魯藝實驗劇團去龍岡參加新兵團成立大會的慰問演出。午后,他在南寺正殿前指導排練獨幕話劇《一個打十個》,當排到劇中新四軍戰士舉槍擊斃汪偽軍時,不料演員用的道具是一支膛內有子彈的執勤步槍,使扮演汪偽軍的演員當場中彈。同時,子彈又從青石板上彈起,擊中劉保羅的腦部,造成他殉職。劉保羅就這樣結束了他傳奇英勇的一生,時年34歲。他的遺體被送回鹽城,安葬于魯藝校園西墻邊。
像他這樣活生生倒在排演場上的戲劇人,全世界都少見,也是中國戲劇史上的“唯一”。劉保羅為祖國和話劇而生,也為這二者而死。34歲,多么年輕呀!但他火一般熱情、崇高的精神品質永遠不會死。2015年8月,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名錄上,就有劉保羅的名字。
21世紀初,太湖尤其是城關及縣城附近的老年人,在談及抗日戰爭初期的太湖情況時,無不想起劉保羅。當年戰地服務團的演員經常在圣公會禮拜堂內接受劉保羅的導演,他那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和熱情開朗的音容笑貌,讓見過的人終生不忘。
歷經歲月滄桑,圣公會禮拜堂尚在,但斯人已逝。凡是在那風雨如磐的歲月里接受過劉保羅教誨的太湖人,特別當年的青少年學生,是終生都不會忘記這位杰出忠誠的愛國戰士、劇壇“將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