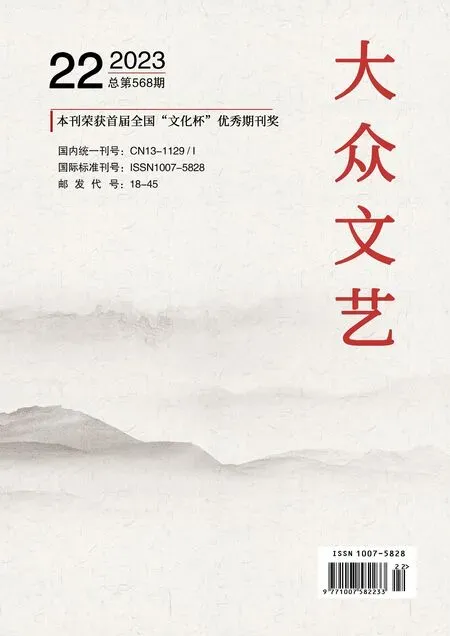論《寵兒》中塞絲從獨體到共同體的身份轉變*
王金美 袁慶鋒
(華南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廣東廣州 510642)
托尼·莫里森是非裔美國女作家,于20世紀60年代末登上文壇,其代表作《寵兒》等,“富于洞察力和詩情畫意的小說把美國現實的一個重要方面寫活了”,先后獲得普利策獎和諾貝爾文學獎。《寵兒》取材真實的歷史,以魔幻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講述了女黑奴塞絲在攜女逃亡途中遭到追捕,因不愿看到孩子再次淪為奴隸,毅然殺死幼女,而十八年后奴隸制早已廢除,被她殺死的女嬰還魂歸來的故事。小說聚焦美國奴隸制晚期和南方重建時期的歷史問題,迫使讀者再度反思種族主義造成的文化記憶與身份的傷痛和割裂。正如卡爾·雅斯貝爾斯所說:“人就是精神,而人之為人的處境就是一種精神的處境”[1],精神生態,和自然生態一樣,也會遭遇危機,而美國種族主義正是通過精神上的侮辱對少數族裔及個體進行摧殘、貶低,破壞其精神生態,使其扭曲或異化,最終陷入文化和身份危機。本文以《寵兒》中塞絲為研究對象,基于精神生態的緯度關注其精神世界,探討種族主義精神侮辱帶給少數族裔的文化創傷與精神分裂。
一、物化:白人對黑人群體的精神侮辱
白人中心主義的排他性注定奴隸主絞殺黑人族群利益以維護其自身利益,對黑人文化及其價值觀進行審判、貶低和否定,并通過白人凝視維系其權力運作。薩特認為凝視表明“我是一個為他的存在,我在他人凝視中發現自己,我即是他人,是為他人而存在的。”[2]奴隸主通過權力“凝視”把被看者置于被動位置,對其進行監視與審判,以控制黑人族群。黑人族群長期在“看”的監視下,內化了白人價值觀,自主地鞭笞、監控自己,如塞絲所說,“(白人)玷污得如此徹底,讓你不可能再喜歡你自己。玷污得如此徹底,讓你忘了自己是誰,而且再也想不起來”①[3],所以黑人社區得到奴隸主前來追捕的消息卻不告知塞絲,最終導致塞絲弒嬰慘案的發生。
馬克思認為勞動產品一旦采取了商品形式,生產者之間交換勞動的社會關系就表現為商品之間的物物關系,通過商品化衡量勞動和人導向的結果是以商品價值來衡量人的價值,最終導致人的物性,能力成為可以占有和出賣的“物”,人的權利和價值被忽視被剝奪[4]。
“學校老師”在追捕黑奴時算的一筆賬可以淺窺物化的特質:他把塞絲和她的孩子們用只來計量,用公母論其性別,把孩子稱作崽子,并用塞絲的“價格”與2個幼年“崽子”相論,甚至思考塞絲的生育能力所“下的崽子”可能帶來的利潤。黑奴被奴隸主視作家畜、個人財產和商品,被貼上價格標簽,他們的價值從一個人主觀能動的價值變為機械單一的商品價值。黑人的價值被限制在這樣的框架下變得狹隘、低廉,被剝奪人的價值,黑奴也最終喪失對自己生而為人的基本價值追求的權利意識,對自我價值產生懷疑,陷入自我認同危機。盧卡奇指出,物化把人的勞動變成商品中對象化的抽象勞動,被商品化的勞動便理所應當按照商品生產的規律進行,將生產過程合理化。黑人作為商品而言,一切苦難被視作理所應當,這是種族主義的“原罪論”[4]。
當保羅D問一個黑鬼到底該受多少罪時,斯坦普說該受多少受多少,能受多少受多少。前者把受苦作為必然前提,后者則認為黑人應該毫無怨言接受種族命運,苦難潛移默化成了黑人的命,具有種族合理性。如塞絲背上的那棵“苦櫻桃樹”,明明是“一堆令人作嘔的傷疤”,卻和塞絲融為一體,仿佛與生俱來。黑人族群在白人物化下對自我價值和命運產生懷疑與悲觀,甚至把不幸當作種族命運,無知無覺中接受白人對黑人族群劣等化的文化灌輸,變得麻木,內耗,忘記抗爭。
二、獨體:精神創傷與人格分裂
種族主義精神侮辱導致黑人族群難以愈合的精神創傷與人格分裂,使黑人個體、家庭共同體和族群共同體分崩離析,精神創傷往往伴隨黑人一生,沿著代際橫向蔓延。“創傷”的核心內涵是人們對自然災害、種族滅絕等暴行的心理反應,它對受創者的思想和行為造成巨大影響,導致遺忘、恐怖、麻木、抑郁等情緒,使受創者無法構建正常的個人和集體文化認同[5]。種族主義造成的精神創傷寄居于被奴役黑人心中,無從和解,變成一座不斷醞釀悲傷的墳冢深埋內心,而逃避痛苦過往,選擇不去面對苦痛的經歷,只會被動陷入身份迷失,每個人變成一個被圍困的、沒有出口和入口封閉的孤島式的“獨體”。
1.行尸走肉的獨體
后弗洛伊德心理創傷理論認為,愛的客體的缺失和外在世界的詭秘變異會產生內并心理創傷,[6]在自我的心理空間形成了一個秘密墳冢,用以隔離和埋葬所失去的愛的客體,使自我處于一種對創傷麻木或無意識的狀態,內化并拒絕思考,因此被剝奪了直面自我、社會和歷史的力量。
《寵兒》中黑奴被白人視為財產物品,被徹底剝奪了權利和價值。塞絲意識到黑奴身份導致她無法保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格也在奴隸主的蹂躪中遭到摧毀,她從學校老師的非人待遇中逃脫以便與這種奴隸制永遠地決裂,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免受生為黑奴的命運,無奈但決絕地選擇將孩子殺死。應激式的弒嬰使塞絲連為人的精神都徹底喪失,“眼白消失了,她的眼睛有如她皮膚一般黑,她像個瞎子。”②[3]塞絲的愧疚和痛苦隨著時間的推移像鬼魂般悄然折磨著她,這種心理創傷一直被她埋在心里不敢面對。“至于其余的一切,她盡量不去記憶,因為只有這樣才是安全的。”③[3]她鴕鳥式地把遭遇的苦難和失去的親人深埋心中,而被埋藏的創傷在她心里成了內心創傷沉默的墳冢。內并心理創傷使塞絲拒絕思考和回憶過去,拒絕與痛苦的過往重逢,拒絕直面自身。塞絲所經受的是廣大黑人經歷的縮影,黑人族群的內并心理創傷對過往歷史、世界、自我的逃避導致了黑人群體的文化身份認同危機。
2.名存實亡的家庭共同體
代際間幽靈是“無意識的產物。它以尚待確定的方式從父母的無意識轉入孩子的無意識……在主體自己的心理空間中,它像腹語者、像陌生人那樣活動。”[7]代際間幽靈把上一代內心埋藏的創傷在無意識間傳遞給下一代,如幽靈般如影隨形。塞絲的觀念對塞絲的兒女皆產生了巨大影響。塞絲在意識到奴隸制對黑人的摧殘后選擇殺死幼女以示反抗,而弒嬰的記憶使她極度抗拒回歸社區和面對白人,由此創造出以124號為基礎的對外封閉的名存實亡的家庭共同體。而她的兒女,在此情境下被動地、潛移默化地接受塞絲的觀念,承受塞絲傳遞下來的創傷,對外界與白人產生敵意與畏懼。124號的壓抑氛圍正是塞絲內心沉默墳冢的體現,她對于寵兒揮之不去的愧疚就像124號的鬼魂,藏匿于黑暗處,日夜不停地折磨著塞絲和她的家人,導致家庭紐帶的斷裂,沒有溫暖的關懷,而是塞絲和丈夫黑爾、塞絲和情人保羅D、塞絲和小女兒丹芙之間的疏離與漠視,以及兒子們由于無法忍受壓抑家庭氣氛而出走遠離。塞絲的家庭共同體名存實亡,家庭成員缺乏自我認同、獨立性,也沒有任何的溝通與共情,而變得形同虛設。
3.鄉鄰/精神共同體的消亡
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基于現實的有機的一種結合關系,是一種“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8]。塞絲弒嬰引起周圍黑人群體的不滿與排斥,他們無法理解,更不能團結起來共同面對白人種族主義帶來的群體悲劇與苦痛,在孤立塞絲一家的同時,也形成自我孤立,黑人共同體分崩離析,也反過來鞏固了白人的宰制地位,同時也加劇了美國白人與黑人之間的文化隔閡、對立與沖突,即便存在著友善開明反對種族主義的白人如納爾森、鮑德溫。丹芙作為代際間幽靈的承受者,她也與社區和白人有著巨大的隔閡和恐懼:“在外面,有的是罪孽深重的地方,當你走近時那一切惡事還會重演……時間在那里停滯,像她媽媽講的那樣,不幸同樣也在那里等著她。”④[3]她站在124號與外界的通道時,所感到的源于未知與混亂的恐懼和警惕一次次阻撓著124號與外界的連接。
黑人家庭與社區本應是黑人的精神家園,但種族主義宰制下缺乏自主權的黑人難以建立起緊密的紐帶。黑人族群在同病相憐的同時沒能主動打破白人價值觀的禁錮,反而內化白人價值觀,接受“被劣等化”的命運并互相傷害、孤立。
三、從獨體走向共同體身份的辯證統一
除了反映黑人的慘痛歷史,莫里森在《寵兒》中更加關注黑人族群如何走出創傷,如何構建一個美好、健全的黑人族群的未來。落腳于現在的敘事、寵兒的消失和塞絲與黑人社區關系的緩和、丹芙走出黑人社區做出融合于美國主流社會的努力都體現出莫里森對此問題的思考。
1.正視創傷本質
對于承受創傷的個人和共同體來說,如果不理解過去,就難以走出迷惘和徘徊,只有正視了過去才能面對現在和未來[9]。種族主義精神侮辱導致黑人群體無法承受的心理、文化、歷史創傷,使其難以建立自己的文化歷史與身份認同。小說中塞絲多次拒絕前往“林間空地”,對于她來說,那里就是她埋葬痛苦回憶的地方。因為曾經所受過的苦難,致使她不敢再度面對,也不愿再接觸外界,因為她害怕再次為之付出代價。由于無法正視創傷,她便一直無法了解自己恐懼的根源,以至于被囚禁在過去,內疚、自責而無法做出改變、邁向未來。
而寵兒的再度出現,讓黑人社區都回憶起了曾經的苦難。如果不回望過去,就不能明確自己為何走到這里,怎么走到這里。只有對過去的清晰認識,才能構建更加完善的自我身份認同。當黑人社區都回到124號前時,他們再度記起了在這片土地的共同經歷,進而變得更加團結,幫助塞絲和每一個黑人拋棄獨體的自閉,同時打開彼此之間共同體的大門。正視歷史現實使塞絲和其他黑人最終走出種族主義的陰影,找到自我,重新構建自我身份,并最終實現個體身份與共同體身份的辯證統一。
2.打破獨體禁錮,構建共同體身份
“凝視不但要求黑人成為被看的對象,更確切地說是要求黑人放棄對自己的主權。”⑤[9]凝視使得黑人內化白人的審判,成為被監視被操控被鞭策的客體和他者。接受凝視的黑人為了迎合白人而行動,像黑人社區在學校老師趕來時的默不作聲,便是一種對白人迫害的潛在認同,喪失了維護族群權利的意識,從而導致白人對黑人更加牢固的操控。對于這種強加給黑人族群的價值限制、“框架”,黑人族群需要主動跳出這種價值評判,認識真正的自我,獲得真正的自我認同。當丹芙主動叩開瓊斯女士的家門,主動看向外部世界時,就找回了部分的主動權。用“看”來建立對自己的正確認知和與世界關系的認知,才能使人們撥開心中來自種族主義的迷霧,以更堅定平等正確的眼光審視來自外界的惡意,使得這些曾經可怕的審判露出其虛無本質,才能使得黑人面對種族主義精神侮辱的價值貶低和低人化時堅定不動搖。
此外,一個人的身份離不開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殷企平在闡述威廉斯“情感結構”概念(“某一特定時代人們對現實生活的普遍感受,這種感受飽含著人們共享的價值觀和社會心理”)時認為他提出了一種“深度共同體”[10]。這種共同體的連接不是僅憑血緣或地緣所聯系,而是基于情感上的共鳴和生活的共同體驗而形成的深度共同體[11]。當社區成員來到124號時,”她們第一眼看見的不是坐在臺階上的丹芙,而是她們自己。”⑥[3]寵兒的存在揭開了社區成員記憶深處的創傷,使得黑人族群與塞絲再度聯結、共情。情感的連接使得塞絲能夠與社區成員共同面對寵兒,給予塞絲勇氣正視過去傷痛,重新認識自我價值,并尋求出路。在塞絲與社區再度聯接時寵兒的悄然消失,象征著住在124號和塞絲心里的鬼魂,塞絲內心沉默的、創傷的墳冢里埋葬的愧疚與傷痛正在為塞絲所接納所正視,并且化解。共同體的構建幫助黑人愈合過去的傷痛,勇敢面對過往并且與之抗衡。共同體成員彼此之間的互相扶持互相關愛幫助黑人個體找回自我身份,形成自己的、種族的文化傳統與聯結。比起用一個人的力量去與奴隸制度所帶來的創傷抗衡,在共同體的支撐下找回自我身份的認識和對本民族文化的正確認識,增強個人價值觀和自信,更有利于對抗歷史的、現世的以及未來的、原形畢露的抑或隱匿的精神侮辱。
四、結語
綜上所述,《寵兒》作為一部黑人遭受精神侮辱的記錄史,深刻地揭示了白人精神侮辱的本質、手段及其對黑人群體造成的種種困境。白人奴隸主通過凝視與物化擊潰黑人的價值觀與自我認同,白人的審判滲透進黑人族群的觀念使其自我監禁,白人的迫害留下的創傷使黑人族群一代一代麻木逃避,始終阻礙著黑人共同體的構建。正因如此,莫里森借助塞絲從獨體到共同體身份的轉變,指出受歧視、排斥的少數族群應該積極勇敢面對種族主義精神侮辱與創傷,主動找回自主權。通過族群共同體的構建,時刻以共同的遭遇為警醒團結起來,建立起族群自身的文化體系和價值觀,樹立起自己的話語體系,積極謀取族群發展,以給予白人長久以來的價值審判以反擊。但少數族裔共同體不是拒斥、遠離主流社會孤立封閉自己,而是打破血統論膚色論,以情感共鳴的精神共同體為核心導向。雖然,少數族裔對于個體和族群主權的重新構建與發展的道路依舊曲折多阻,但莫里森對共同體(“最重要的屬性是文化實踐,意在改造世界”)的倡導與文學實踐,為其指明了前進方向[12]。
注釋
①②③④⑥托妮·莫里森.寵兒[M].潘岳,雷格,譯.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第291頁,第139頁,第6頁,第244頁,第299頁.
⑤陳后亮.“被注視是一種危險”:論《看不見的人》中的白人凝視和種族身份建構[J].外國文學評論,2018(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