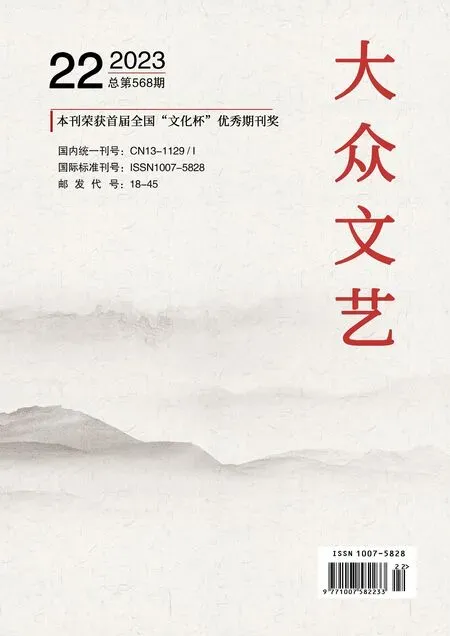傅抱石客蜀時期人物畫的家國情懷*
郭 原 陳晶晶
(鹽城師范學院美術與設計學院,江蘇鹽城 224007)
重慶作為抗日戰爭時期的重要陣地,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舞臺,是抗戰大后方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一批批優秀的中國藝術家在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緊要時刻來到重慶。傅抱石的“客蜀時期”以客居重慶的七年半時間為主,從1939年4月至1946年10月這段在重慶寓居的生涯,于國、于家、于己,傅抱石本人和家人的心境,都與世事密切相關,盡管創作環境較為窘迫惡劣,但卻迎來了他創作內容的豐厚與藝術風格的成熟。
在重慶時期,傅抱石的作品主要有山水畫和人物畫,其中人物畫主要取材于歷史典故及歷史人物。作為愛國主義學者,他描繪的人物對象大多是歷史上有品德與抱負的人,如屈原、蘇武、竹林七賢等。他們對世事的不滿與感懷以及自我心靈的憂傷與苦痛,在傅抱石的作品中得以呈現。
一、歷史人物繪畫
(一)屈原情節
屈原可以說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愛國文人主要的人格品質、心理沖突、精神內涵,都匯集在了屈原身上。郭沫若就曾說道:“由楚所產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產生出的楚辭,無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國統一著的。”郭沫若對屈原生平及其作品進行研究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關于屈原》《革命詩人屈原》《屈原考》等文章都是20世紀40年代初所撰寫。傅抱石本就十分仰慕欽佩屈原的人格品質,抗戰客蜀時期創作了為數不少的屈原與《楚辭》的主題故事畫,時常以屈原的詩詞歌賦作為刻印的邊款。在抗戰的歷史背景下,屈原更是成為繪畫推廣的賢士典范,他盡忠愛國的民族精神被寄予了抗辱圖強的主題思想。
皖南事變爆發一年之后,郭沫若創作的歷史劇《屈原》于1942年4月在重慶公演。屈原寧死不屈的錚錚鐵骨以及憤世嫉俗的孤傲品格,在傅抱石看完此劇后更加深刻地激勵著他,給予他創作的靈感和激情。傅抱石激動萬分,心潮澎湃地揮毫繪制了人物畫作品《屈原行吟圖》,其間四易其稿,最終完成此作。畫幅縱62.2厘米,橫109.3厘米,寫就屈原在江濱行吟即將投江的情景,畫面中江水浩渺、波濤洶涌,疾風吹拂著蘆葦和水草,描繪出江畔的蕭瑟荒蕪,將氣氛渲染得極為悲壯。一位身形瘦削的老人披散著長發,眼窩深陷、面龐清瘦、神色黯然、憂心忡忡地行走在瑟瑟涼風拂過的叢林之中,畫家將屈原深厚的愛國情懷、濃烈的憂患意識、簡淡的詩人氣質刻畫得形神兼備、栩栩如生、耐人尋味。形象鮮明、倔強剛直的頭發與胡須,深沉偉岸、飄蕩風中的身體與袖籠,都在強烈體現出屈原滿身的凜然正氣,顯現出他從容自若的淡然神情,似乎在訴說著滿腔的忠貞與心愿,仿佛他驚天地泣鬼神的吟誦就縈繞在我們的耳畔。
出于文人與藝術家的視角,傅抱石體察愛國詩人屈原的家國情懷,并以自己的體悟吟味詩人的內心,又以此感情為出發點,贊頌其不忍家國飄搖、抗擊強秦的民族大義。傅抱石對屈原的情感質樸且真摯,這種贊頌更是一種愛國文人的感同身受。
1943年11月21日,傅抱石與羅時慧夫婦二人在金剛坡下詠讀《楚辭》,在讀到《湘夫人》中“裊裊兮秋風”一句的時候,兩人相視無語。因為這個時期,日本軍隊的鐵蹄正肆意踐踏著沅水、澧水間的大好河山,傅抱石將心中痛恨外敵、思念國土、心系百姓的感情匯聚在一起,全身心投入、構思創作了《湘夫人圖》,畫作縱105.2厘米,橫60.8厘米,描繪了落葉飄飄、秋風蕭瑟、煙波浩渺的洞庭湖畔,湘夫人亭亭玉立于樹下,儀態萬方、端莊淑靜、怡然自若。“湘夫人”是傅抱石經常描繪的題材之一,他常以此作畫,立軸、冊頁、扇面的形式多種多樣。“二湘”題材是傅抱石最為喜愛的《楚辭》詩意系列繪畫題材。20世紀40年代以來,傅抱石一直沒有中斷這一繪畫主題的創作,其中尤以客蜀時期創作的《湘夫人圖》《湘君圖》《二湘圖》最具代表,此中寄寓自己的精神情感追求、文化價值思想和繪畫創作理念。
(二)蘇武氣節
蘇武留居匈奴19年,始終威武不屈,至始元年(公元前81年),得以獲釋回漢。1944年1月,傅抱石依此立意,創作《蘇武牧羊》,縱61.6厘米,橫84.2厘米。蘇武去世后才被漢宣帝列為麒麟閣十一功臣之一,被世人所敬仰。作品描繪漢朝將領前來迎接蘇武歸來的場景:蘇武手執漢節、須眉白發、傲然而立于羊群之中,他深沉堅毅的性格躍然紙上。漢將彎腰鞠躬表示對使節的敬重,匈奴官員有的注目凝視,有的交頭接耳,油然欽佩蘇武不屈不撓的精神。陰沉沉的天空、蒼茫茫的雪地,都為畫面渲染了肅穆莊嚴的氣氛,充分體現了文人高士放蕩不羈、恬靜淡雅的內心狀態。當時國統區文藝活動的特點就是運用歷史題材宣傳抗戰,開展抗戰文化運動。那時候的金剛坡下,很多文化藝術界人士都在此落過腳,而傅抱石到這里生活創作了七年有余。“金剛坡下抱石山齋”成了傅抱石許多經典繪畫作品的誕生地。從這期間創作的一批批人物畫代表作看,傅抱石始終追求一種自在瀟灑、古典雅致的人物畫風格。《蘇武牧羊》創作于《開羅宣言》簽署一個多月之后,蘇武是為國家為民族守大義守節操,更是偉大人格力量的象征。《蘇武牧羊》頌揚蘇武忠心忠誠、不畏強權、威武不屈的民族氣節,表達了畫家堅信抗戰到底必定勝利的決心和信念。
(三)六朝風度
傅抱石可以說是中國畫史上創作魏晉南北朝名士作品最多的畫家了。六朝精神既有隱逸蒼涼、又有悲憤感懷。畫家的心性正與六朝人物的追求相似,于是古賢志士的言行風度就常被置于筆端。六朝人物的詩性與神韻都體現在傅抱石的人物畫作品中,寄予了他豐富的情感,也浸潤著他對六朝歷史、人物風情的理解。“傅抱石的繪畫創作與高人逸士息息相關,從而達到民族文化精神一脈相承。”[1]作品自然呈現出的六朝文化品格與傳統文化精神,代表著民族文化的“超然”。
長達三米有余的手卷《蘭亭修禊圖》,可謂傅抱石金剛坡時期的杰作,畫面描繪東晉時期的士大夫及侍者,雅集于崇山流水之間,總共繪制了五十三個人物。這些人物神態各異而又形象生動。卷首以行筆爽利圓潤的篆書題寫“蘭亭修禊”四個大字,氣息渾厚、暢然一氣,卷尾以雋秀清逸的金石小楷抄錄《蘭亭序》的全文,畫面完整、遙相呼應。在傅抱石的作品中,如此多形式內容集于一體的巨制并不多見。
《東山圖》描寫了謝東山在山陰道上迎接王羲之等群賢的情景。畫中背景有一株“六朝松”,據說為梁武帝親手栽種,是位于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園西北角的一株檜柏,相傳為1500多年前的遺物。隋軍滅陳之后將宮苑城邑盡數毀滅,而此樹卻不懼兵火幸存下來。傅抱石筆下的謝安既儒雅清秀又剛毅不屈,此樹與謝安的品格一樣,都被畫家用筆墨化為歷經喪亂而不息不滅的生命象征。
畫家筆下的眾人性格鮮明、線條流暢、古意盎然。屈原正襟危坐、執著倔強、心性孤僻,而竹林七賢衣衫而闊、縱情灑脫、狂放豪邁,他們不盡相同、對比強烈。正面向畫的高士腰間衿帶結系的一絲不茍,能夠感受到賢人志士的禮節風度及相互尊重賞識的中國文人面貌。傅抱石對人物與其社會背景有著深刻的鉆研及獨到的理解,描寫各類人物的衣著裝束、表情神態,從中自然流露出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
二、古典女性繪畫
傅抱石畫仕女畫基本是在抗戰入蜀之后。在這樣的歷史時期,人民受到困苦磨難,經歷生死離別考驗,美好的事物能夠給人帶來信念與希望,燃起熱情與理想。
1944年,傅抱石在重慶沙坪壩金剛坡創作《眉鎖章臺》,似乎是在抒寫兒女之情,但畫中的深深幽怨,實則是畫家的借古喻今。正如畫家亞明的跋文所說:“抱石寫人物獨一無雙。”作品追求高尚的品位和意境,有別于傳統技法,把水、墨、色融為一體,同時把山水的畫法運用到人物畫中,改變了清代以來的人物畫畫風,顯現出畫家獨特的風格。
1945年所作的《柳蔭仕女圖》描寫仕女漫步于柳蔭溪邊的景象。人物形象的樸素無華、嫻雅高貴、風姿綽約、優美動人無異于畫家心中的夫人模樣。傅抱石抗戰入蜀后的仕女畫,成為在兵荒馬亂年代繪畫創作的精神寄托。
日寇侵略不斷、國民流離失所,傅抱石夫婦對侵略者的惡劣行徑深惡痛絕,也激發起他們強烈濃厚的愛國思鄉之情。作品承載家國仇恨,使人不忘悲傷痛苦。在那個戰爭的年代里,傅抱石用灑脫自如的筆觸,創造出理想的美人,把形象描繪得精致唯美。人物的精神和畫家的思想碰撞,使畫面充滿生命力。
傅抱石的仕女畫以中國畫筆墨及古典美的詮釋方式和風格呈現,也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體現。對他而言,這或許正是從文化上戰勝敵人的一種方式。
三、古典詩意繪畫
《杜甫詩意——佳人》創作于1943年,杜甫作此詩時,正值落魄,浪跡于秦州附近,天寒地凍、條件惡劣。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杜甫辭官西行,帶著家人躲避戰亂,暫住秦州(今甘肅天水)之時,在山里度過打柴、撿橡栗為生的日子,偶遇一位隱居此處慘遭喪亂的女子。有別于《麗人行》,這時候的杜甫并沒有耗費筆墨去描寫美人的容貌與身形,也沒有描寫她的發型與服飾,而是通過她的不幸遭遇以及對待艱苦生活的態度,塑造了一位佳人的鮮明形象。
依據杜甫詩意創作的作品中,最為人們熟悉的屬《麗人行》,作于1944年的該作被徐悲鴻譽為“乃聲色靈肉之大交響”,張大千題此畫“開千年來未有奇”。《麗人行》一詩是杜甫天寶十二載(公元753年)于長安所作,此時距安史之亂尚有兩年,杜甫在詩中描繪了楊氏姐妹們春日游玩的情境。畫面共安排了5組37名人物,每組人物各有差異,并以不同的樹木分隔,畫家用潑墨法寫就濃密樹蔭作為背景,獨具匠心。“長安水邊多麗人”反映時政的腐敗不堪和君王的昏庸無能。而此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不顧人民的困苦,紙醉金迷驕奢無度。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日益不滿,民眾的呼聲日益強烈。傅抱石曾目睹國民黨高官及家人在重慶南溫泉浩浩蕩蕩的出游隊伍以及盛氣凌人的驕橫之氣,他對深惡痛絕這樣的奢華現象,用借古諷今的創作手法對國民黨的腐敗予以揭露和抨擊。
《琵琶行》是傅抱石客蜀時期頗為喜愛的題材之一。1944至1945年間所作的《琵琶行》存世居多,整個四十年代都延續著《琵琶行》詩意入畫的創作。畫面中間遮天壓地的大樹挺立,顯得空間緊迫。詩人與行客止于畫中,傾聽著琵琶女的彈奏,似乎在感嘆境遇相似的處境。傅抱石用悲涼的氣氛渲染整幅畫面,但并不讓人感到凄涼,他用撫慰心靈的繪畫之美詮釋一種人文關懷,消釋人們靈魂的痛苦,治愈人們內心的創傷。
1944年3月3日,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了中國文藝社主辦的“傅抱石畫展”。“他的人物畫,那時候比山水畫更獲觀眾欣賞,人們傾囊爭購”。[2]之后《時事新報》上發表了《傅抱石畫展觀感》,作者是美國的艾惟廉博士,文中提到“傅先生的畫里面,最顯然的特性就是富于歷史性。”[3]
1945年11月9日,在重慶江蘇同鄉會舉辦了“傅抱石畫展”。之后張道藩《論抱石之畫》文中說“山水畫占五分之三,人物畫占五分之二”,這一論述雖然是對于本次畫展而言,但可以知曉傅抱石于20世紀40年代所創作的人物畫比重,以《麗人行》《湘夫人》《琵琶行》《東山絲竹》等作品為例,評論傅抱石人物畫,做出了較早對其人物畫品格極具深刻認識的評述:“抱石先生寫人物絕不拘泥于其表面之華麗服飾而旨在刻畫畫中人之情緒生命”。[4]
四、畫家的家國情
生活于重慶西郊賴家橋金剛坡的七年半時間,是傅抱石藝術生命至關重要的時期,極具個性的藝術創造在他的抗戰客蜀時期得以大展身手。既充斥在敵機的轟炸和刺耳的警報中,又在相對自由與單純的藝術創作中,金剛坡下的日常生活是復雜的,既有平淡純真又包裹著彷徨恐懼。傅抱石在這一情境下的人物畫創作不只局限于“東晉六朝”系列,有描寫韓愈被貶途經藍關遇風雪困路的《雪擁藍關圖》,也有展現蘇軾遭遇“烏臺詩案”遷至黃州后面對無際長江的《赤壁舟游》,還有圖繪白居易被權貴陷害左遷江州后偶逢琵琶女的《琵琶行》等。雖然,傅抱石沒有直接描繪沖鋒陷陣的斗爭場面,沒有表現現實生活百姓流離的凄涼景象,但是他一直都在以他獨到的方式傳遞著堅定的抗戰救國的精神使命。
“凡一件成功的作品,其唯一條件是時代精神最豐富的作品。”[5]抗戰客蜀時期,傅抱石創作的六朝題材故事畫以及其他人物畫,不僅是特殊時期將時代背景與思想情感的交織,還使得這些人物畫作品成為特殊年代的精神寄托。這時期的人物畫以形寫神,重在表現人物的內在氣質,雖形象簡練,有些甚至亂頭粗服,卻恬靜矜持、引人深思,烙印著時代的印跡,蘊含著畫家豐富的個人心態和情結。
傅抱石的民族精神在客蜀時期的畫作及著述中還以遺民情懷呈現出來,他呼吁保存中國繪畫“民族性”之“線”的相對平靜態度[6],以圖畫描繪明清遺民,以文字歌頌民族藝人。傅抱石以自己的方式投入中國的抗日大業,通過人物畫的形式宣傳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這些作品的內容題材都充滿著對國家命運的關注。
傅抱石創作講究“大膽落墨,小心收拾”,他對人物對象神情與服飾衣著等刻畫深刻,細致入微地體現人物的精神面貌,在大氣象之外善用微妙的細部刻畫。他將黑白、疏密、虛實等對比關系運用自如,烘托畫面氣氛,營造畫面意境。大氣磅礴的畫面因這些人物形象而活躍起來,流露著魏晉氣息。顧愷之的高古、石濤的淋漓以及傅抱石的激情,完美結合實現了筆墨與圖式現代性轉化的突破。
“美術是民族文化最大的表白。”這是傅抱石作為藝術家的愛國情懷。傅抱石是具有強烈愛國意識和時代精神的畫家,其創作的靈魂就是對民族文化的歌頌。抗戰的時代,傅抱石通過中國畫創作,讓人們形成深刻的民族記憶,鑄造不移的民族精神,建起深厚的民族情結。傅抱石的藝術作品由內而外滲透著愛國忠貞,藝術思想蘊含著自強不息的民族自豪,體現著他深沉的人文精神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