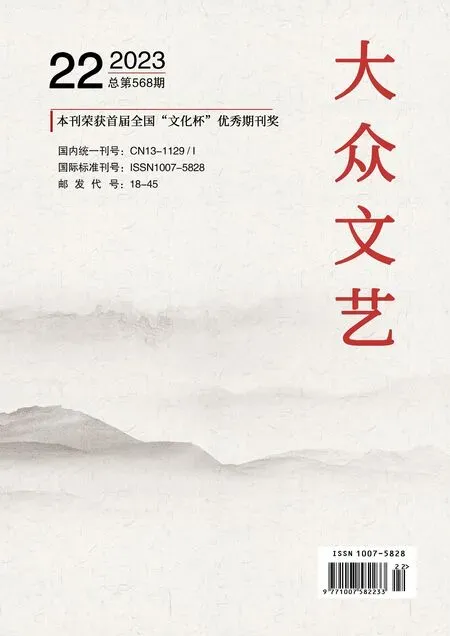雙排鍵樂曲《北京喜訊到邊寨》的音樂與演奏分析
張蓓蓓
(西安音樂學院,陜西西安 710060)
《北京喜訊到邊寨》由著名作曲家鄭路與馬洪業共同創作。鄭路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深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和啟發,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激情,創作出了一首充滿激情的舞曲,將我國西南少數民族人民的歡樂情緒,使用音樂的形象展現得淋漓盡致。這是一支苗族、彝族的舞蹈,充滿了歡快的旋律,充滿了濃郁的民族氣息。在這首樂曲中,舞蹈的銜接非常突出,充滿了喜悅。音樂很簡單,但節奏卻很靈活,給人一種強烈的反差感。
一、雙排鍵樂曲《北京喜訊到邊寨》的創作背景分析
(一)創作背景簡介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共中央把“四人幫”一網打盡。作家鄭路在兩次集會后深受鼓舞。他想起了很多次去過祖國南部的少數民族聚居地,看著人們在篝火前載歌載舞的情景,想起了“粉碎四人幫”的巨大好消息,全國人民都在慶祝。鄭路在創作熱情的驅動下,不久便創作出了一首管樂合奏《北京喜訊到邊寨》,并于一九七六年與馬洪業合作,把它改編成一支交響樂合奏[1]。
(二)創作作者簡介
鄭路一九三三年生于北京市順義區板橋村。一九四八年,加入了解放區的兒童劇團,并在一九五〇年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音樂學院。一九五二年后,曾任中國軍樂隊單簧管演奏員、作曲室副主任。他長期從事軍事音樂藝術,經過多年實踐探索,逐步掌握了軍事音樂的基本技法。他創作的中外音樂作品超過三百多部。他的代表作品有:《民歌主題組曲》《北京喜訊到邊寨》《漓江音畫》《檢閱進行曲》《紅太陽瑤寨》《喜送豐收糧》《風雷頌》等等,還有其他歌曲。馬洪業,黑管手,作曲家,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曾擔任宣傳組成員,并參與創作。一九五四年以后,先后在東北、上海、中央廣播公司擔任單簧管演奏。除了與鄭路合作的交響樂《北京喜訊到邊寨》,他還創作了《愉快的勞動》,《春曉》和《圓舞曲》。
二、雙排鍵樂曲特點
雙排鍵與管風琴的淵源:它的名字是因為它的彈奏風格類似于管風琴。雙排鍵,擁有上千種不同的聲音,聲音質量與真正的樂器非常相似。而且可以按照音樂的要求來修改音色,比如音調的強度,比如弦樂的速度和力度。每個鍵盤可以重疊幾種不同的聲音。能演奏出一支管弦樂隊,聲勢宏大。早期的風琴演奏一般要求兩個人一起演奏,再后來,風琴發展到一定程度,單靠人工吹風是不夠的,于是就有了更加精密的機械鍵盤。但是它在鍵盤上的彈奏方式與其他鍵盤樂器相似,一種雙排鍵,需要身體多個部分的協調,一般是用手來演奏,用來控制音量,用左腳來控制鍵盤,用來演奏低音,調整音色。彈奏一首曲子,要求全身上下都要有一個協調的動作,這對于演奏者的要求是極高的。
三、雙排鍵樂曲《北京喜訊到邊寨》的音樂本體分析
(一)內容介紹
《北京喜訊到邊寨》以激越的旋律,將邊塞人民歡樂的情景展現得淋漓盡致,而且樂曲中還吸收了民間的藝術形式,形成了獨特的樂曲形象,展現了邊塞人民的歡樂心情。樂曲分為七個部分,展現了多種不同的氛圍。作品的音樂素材選用苗族和彝族的民謠。樂曲以圓號為前奏,模仿中音區的號角,演奏出一種雄渾、宏偉的曲調。就好像北京的喜訊一樣,它穿越了千山萬水,來到了每個家庭,展現了邊塞地區的家庭在聽見了喜訊之后載歌載舞的情形。隨后,是兩個有力的舞蹈動作,這也是樂曲的第一個主題。接著就是一連串的、像“牛角”一樣的聲音,與之前的音樂完全相反。樂章中有一段過渡樂句,用弦樂彈奏,木魚、鐘鼓的清脆悅耳,熱情不斷高漲。樂曲的曲調不斷變化,情緒逐漸高漲。
由于《北京喜訊到邊塞》的旋律比較生動,所以,一聽這支樂曲,就會深深地被它所感染,展現了青年在聽到喜訊之后的欣喜若狂。曲中由多個樂器演奏組成,有圓號、小提琴、雙簧管、小號、鑼鼓;終于,在一片鑼鼓聲中,氣氛高漲,號角吹響,表達了人們向美好的明天前進的想法。
(二)旋律特點
整個作品的和聲、節奏、技巧都很簡潔。樂曲的前半部是降E大調,主旋律也是以主三和弦的分解音型為主,非常有規律,這種表演形式意味著整體樂曲的節奏很強。整個樂曲的旋律都是以少數民族為主,而第一個主題則是以苗族舞蹈中的西洋樂器來表現。第二個主題更多地運用了裝飾性的倚音。在彈奏時要掌握彝族樂曲的級進,盡量使音色的輕巧靈活,突出民族音樂的特色。雙簧管吹出了一種類似于蘆笙舞蹈的伴奏。后面的木琴和鼓聲更加活躍,給人一種群策群力的感覺。第三個主題是用木魚和鼓聲,輕松地將觀眾帶入一個充滿激情的場景,無論男女老幼,大家都徜徉在喜悅的氛圍之中。主題曲轉為C大調,但增加了具有民族風格的降級三級,這是苗族民謠中常見的顏色音色,使整個樂曲具有西南民族歌舞的聲韻與風格。
《北京喜訊到邊寨》是一首以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為基本要素的樂曲,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山區的苗族居民,以他們的熱情、慷慨的飛歌著稱;彝族民間的民謠大都是抒情、富有想象力的,其內容主要集中在勞動情景上,故而措辭較為簡單。將這兩種民族音樂特色融合、提煉,形成了以上作品的主題。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感受到,當他們得知這個好消息的時候,心中的喜悅。不論何時何地,聽著這首曲子,就像是在火把節,圍坐在火堆邊,沉浸在歡快的歌聲和歡樂的氣氛中。
(三)曲式結構
《北京喜訊到邊寨》采用了主題并列的形式,每個段落都是統一的,具有一定的趣味。樂曲的主體部分為4/4的降E大調,其結構較為寬松,樂曲為多樂段、單樂章,其曲型可以看作是“變化性”的復三部曲。這首曲子共分三段。第一節:引子部分(1—5節)描述了一組舞蹈場面,并用圓號吹奏出美妙的樂曲。“牛角號”作為當地的一種傳統樂器,以圓號為代表,伴隨著民族的音樂,能將觀眾帶入特殊的氛圍環境之中,來到了西南少數民族的邊疆,青年們興奮的吹響了號角,將好消息傳達給了千家萬戶。用圓號模擬了當地少數民族的號角,不但聲音相似,而且還帶有地方特色。與此同時,小提琴發出了輕微的顫音,就像是一條帶著好消息的電波,在三個音節的震動中,力量符號變成了強烈的ff,與之前的鼓聲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就是主題曲的開始。第二部分:呈現部,主題I,以降E大調主音為主。主題曲激情奔放,呈現出一副激情澎湃的舞蹈場面,高亢而又矯健。高音部門的木管樂器、弦樂器,銅管樂器,低音部分木管樂器,弦樂器,敲擊樂器,演奏出鏗鏘有力的節拍。音樂的主題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一種歡快的感覺一浪高過一浪。在單簧管和小提琴兩個小節的輕快的旋律之后,音樂自然而然地從低音E大調的B大調降到了中段。
中間部分,主題曲反復播放,由領奏樂器和管弦樂配合,苗族舞曲的旋律栩栩如生,主題曲II樂曲詼諧幽默,號角取代“牛角號”,繼續拉長音。隨著力量的增強,長笛和小提琴的主旋律又回到了E大調,“主奏”和“伴奏”也在不停地變換,或強或弱。俏皮的調子,鼓聲就像是少女的輕快舞步,鈴聲清脆。隨后,音樂進入了下一個主題。
主題III的主旋律是用小提琴和中提琴來完成的,而小號則是在句子的末尾呼喚著主題。敲擊樂器用的是一種很有節奏感的木魚和鐘鼓。當主調再次響起的時候,一號小提琴以高八度的方式彈奏,加上了大提琴,歡快的氣氛變得更加強烈了。這一段反復的彈奏和力量得到了強化,配樂的聲音變得更加強烈,氣氛也變得更加熱烈。
該題材運用了大量彝族民族的音樂材料,形成了這一段主題的抑揚頓挫的曲調。當過渡樂句再次出現的時候,樂曲的力量就會變得微弱,整個樂章都進入了(主題Ⅳ),C大調中加入了苗族的降3,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民族風格。隨著這些元素的改變,音樂逐漸呈現出一個人領一群人,一起表達自己的愿望,以及對黨領導下的國家的無限向往,表達出了各民族的美好愿望。主題Ⅳ的曲調也是反復的,不過彈奏的強度和配樂不同。第一遍是mf,第二遍是f,在彈奏的時候,要掌握好這兩種樂器的區別,才能讓人聽得出來。上一次,他的力量是mf(中),到了最后,他的聲音變得微弱,以強音結束。以這樣的結尾,可以總結、概括,并引導下文,很自然地引出了熱烈、歡快的重演[2]。
《北京喜訊到邊塞》以宏大的樂隊聲效變換為“歡騰主題”。音樂中的小號發出了粗獷的旋律,像是一個健壯的年輕人在跳舞,他的小提琴聲中充滿了活力和生命力。同時,利用號子吹響了帶有民族特色的號角。在這個題材里,音樂把少年的粗壯舞步和女子的優美舞步分別描述,使配樂和力度、速度都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豐富了層次,并能使聽者產生不同的聽覺體驗。當樂曲的強度越來越大,整個樂曲就變成了E,第二次演奏的時候,小號的曲調上升了三度,樂曲進入了高潮,主題曲也隨之響起。這首樂曲由全體樂隊演奏,鼓樂齊鳴,恢宏地重現了一號的主題,光彩奪目,將人民的歡樂氣氛發揮到了最大程度,形成了一個盛大的節日。最后,號角聲再次響起,這是一種對祖國的美好祝愿,也是一種堅定的信念[3]。
四、雙排鍵樂曲《北京喜訊到邊寨》的民族元素
雙排鍵樂曲《北京喜訊到邊寨》雖然以西洋樂器為主,但其聲學效果與民樂基本相同,屬于典型的西洋樂器改編民樂。它在運用西洋樂器的同時,也突出了其民族特征。無論是樂器的布局、意境還是創作手法,都是一部相當成功的作品。中西方音樂的結合,不但推動了民族音樂的發展,而且將西方的樂器也融入了它的創作之中。
進入新世紀,音樂理論走向規范化,特定音樂氛圍逐漸形成,音樂環境日趨成熟,這也給音樂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隨著時代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各國之間的音樂交流越來越多,音樂的國際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在當今的音樂發展過程中,民族民間音樂的傳承和發展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新世紀音樂家們怎樣承擔起時代的責任與使命,創造性地傳承和發展中國民族音樂的藝術形式與風格,從而在世界文化舞臺上占據一席之地,就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首先,新世紀音樂工作者要樹立民族自信,這是繼承和發展民族音樂的先決條件。其實,我們的民族音樂有很多優點,但我們的音樂人卻往往忽略了中華民族的音樂,盲目的模仿和否定自己的民族音樂,導致他們的作品幾乎沒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制約了民族音樂的傳承以及發展。所以,對傳統與民間音樂的傳承,必須建立起牢固的民族自信心;其次,要以開放的心態發揚和繼承民族民間音樂,不但要深入地鉆研、深入地練習,更要了解和借鑒國外的先進技術,以達到我們在傳承中發揚民族民樂的奮斗目標,就如《北京喜訊到邊寨》,雖然它在樂器的編排上采用了西洋樂器,但它的聲效與民樂有異曲同工之妙,屬于一種典型的西洋樂器改編民樂。它在運用西洋樂器的同時,也突出了其民族特征,這種突出民族特色的方式是十分可取的[4]。
《北京喜訊到邊寨》是一部民間樂曲,但它的配樂主要是西洋樂器,音效與民樂相似,是西洋民族音樂的典型代表。在使用西洋樂器的同時,也突出了民族的特點。《北京喜訊到邊寨》是一部優秀的交響樂作品,它的創作手法、藝術構思、配樂等方面都非常成功,讓中西文化在音樂上碰撞,迸發出動人的火花。在音樂上的中西融合,不僅使我國的傳統民族音樂得到了發揚,而且把西方的樂器也運用到了樂曲之中,使之成了中西方民族音樂合作的一個典型。
《北京喜訊到邊寨》旋律清新,技巧明快,歡快的伴奏充滿了歡快的旋律,整個樂曲的歡愉氣氛濃重。我國是一個有著5000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在幾千年的時間里,各種藝術和民族的聲調在民間廣泛地傳播著。《北京喜訊到邊寨》是從西南少數民族中吸收過來的,運用主題分割、和聲、節奏、配器等技巧,層層鋪陳,營造出一種情景交融的氛圍。在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它的音樂形象鮮明,情感豐富,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正如吳祖強在《曲式與曲式分析》一書中所寫的那樣:“末樂章代表著音樂發展的結果的形象和情緒”一樣,很好地闡述了《北京喜訊到邊塞》所渲染的情緒。
五、樂曲演奏分析
弦樂組的樂器有大提琴、小提琴等,通常以連聲奏法來演奏。連音也可分成兩類,即大連音線與小連音線,而弦樂組則多采用大連音線。連音,顧名思義,就是要把音節連在一起。比如結尾的UK是弦樂,所以我們在彈奏時要模擬氣息的發聲方式。在彈奏的時候,指尖要稍微平緩,在彈奏之前,要為下一個音符做好準備,兩個音符間的空隙盡可能地減小[5]。
長笛、雙簧管等是木管樂隊的樂器,通常以連音的形式演奏。比如,四號的UK是雙簧管,所以我們要學著雙簧管的發音。雙簧管是吹奏樂器,應注意其氣口的呼吸與樂句的歌唱。彈奏時要有觸感,音頭不能過大,聲音要干凈、清晰、均勻。在演奏過程中,小連音的最后一個音節要收、要跳,以展現苗族姑娘們的歡樂與活潑。
銅管組樂器包括長號和大號,通常采用保持音奏法。比如,過渡樂句LK是圓號音色,所以大家演奏時,要仿照圓號發聲,就是利用按鍵,吹氣等方式發出聲音,所以每一個音間都被切斷了。演奏這一部分,每一個音都應該是豐滿的,將所有的力全部用到指尖。音間的空隙與弦樂器的奏法有所不同,音間應有空隙,表現為演奏時是把手指提起,然后下落,演奏下一音。
打擊樂組主要以定音鼓和木琴為樂器,樂曲中打擊樂的音色主要是木琴,常采用跳音奏法。如主題五中跳音的部分,就是木琴音色,所以我們演奏時,要仿照木琴靠敲擊來發出聲音。演奏這一部分,用我們手腕控制,把雙手設想為敲木琴用的小錘,跳音時,也要使每一個聲音都具有顆粒性。
六、結語
綜上所述,《北京喜訊到邊塞》取自我國少數民族中苗族以及彝族調子。以中國民族調式譜寫管弦樂,帶有明顯的中國民族風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軟實力,給中華民族發展注入了巨大精神力量,只有更好地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之中,才有可能為實現中國夢創造出巨大的文化力量。所以作為一個中國人,要認識與研究中華民族的文化,并傳播中華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