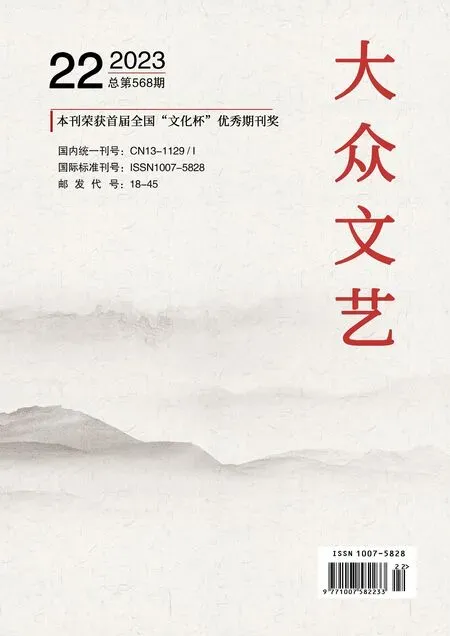河北青年導演的創作與區域電影研究
——以郝杰、蔡成杰、徐磊的電影作品為例
周 逍
(河北科技大學影視學院,河北石家莊 050000)
近年來,一批河北籍80后青年導演異軍突起,頻頻攜本土影片現身各大電影節。在2022年第16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上,80后河北籍青年導演蔡成杰的長片《四十四個澀柿子》作為閉幕影片特別放映,而早在2018年由其執導的劇情電影《北方一片蒼茫》就已經獲得了第11屆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劇情片獎。來自河北張家口的郝杰導演在第2012年和2013年分別憑借《光棍兒》和《美姐》蟬聯兩年FIRST最佳導演獎,同時兩部影片都入圍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2019年徐磊憑借處女作《平原上的夏洛克》引起對農村懸疑推理喜劇的廣泛討論。
以郝杰為開端,這些背景各異的河北電影人在新世紀10年代之后,創作出多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河北電影。他們在作品中充分表達鮮明的個人風格以及嶄新的河北鄉土面貌,將燕趙大地上的民俗文化帶入觀眾視野,注重傳統民俗文化與現代電影鏡語的結合,關注華北農村中人際關系的復雜性,跳出宏觀的時代視閾轉向個人生命體驗,對敘事方法與影像方面都展現出了強大的革新力量。
一、視覺手段:民俗文化新想象
(一)鄉土空間
河北是中國唯一兼備高原、平原、草原、沙漠和海洋等各種地貌的省份,而這復雜多樣的地理特征賦予了河北千姿百態的自然風景。如果說本土文化需要以視覺手段得以外化,那么河北省獨特的鄉土空間在這幾位導演的作品中呈現出獨具華北風情的地理景觀,以外部的視覺風景召喚出內部的情感歸屬體驗。
蔡成杰導演的《北方一片蒼茫》(2018)用河北承德平原縣——蒙冀遼三省交界處的充滿悲愴的遼闊之美,描摹了北方風景冷清地域景觀的蒼茫質感,這種蒼茫又因王二好對貪婪的村民報以幻想,反襯出現實情況的人心的冰冷。電影開頭,王二好與男人行走被大雪覆蓋的樹林中,大量留白的風景充滿了影像的詩意。同時,整部電影將一個個大雪滿地的村落作為故事發生的天然背景,不僅將荒誕的事件合理化,還以強大的力量擎起屬于這片土地的悲涼。蔡成杰導演說:“雪景的好處尤其在北方農村里,從攝影的角度來說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功能就是遮丑,那些房屋莊稼爛葉子凌亂不堪,而且灰突突的,但一場雪下過之后,所有的基調都特別統一。”[1]電影中因大雪而變得潔凈畫面,卻以內容和形式的反差凸顯了骯臟的現實沖突。蒼茫雪景里種種凝結傳統詩意的符號元素在導演鏡頭中極具諷刺意味。
具有公路片元素的徐磊導演的《平原上的夏洛克》(2019)一路呈現出河北農村的田園視覺圖譜:碧綠的西瓜地、金色的麥田、高大的楊樹……在城市圖景的橋段中,也對真實的高樓大廈予以客觀旁視。農村和城市不同景觀的對比,暗含了農村終會被城市全盤接收,古老的土地與樸實的農民以最后的熱情捍衛屬于自己的空間。在郝杰導演的《光棍兒》(2010)、《美姐》(2012)中,一脈相承的河北張家口農村卻被賦予永不消亡的生命力。在黃土和陽光中,能若有若無地捕捉到第五代導演張藝謀《紅高粱》關乎人物生存的原始野性與欲望本能。這兩部作品都借用真實的農村不發達的風景毫不掩飾地展現農村地區的貧窮落后,卻分別透露了不同創作者對土地以涇渭分明的情感視角。
復雜多樣的華北農村地貌與風情給中國電影增添了“有意味的形式”①,有助于強化中國地域電影中富有辨識度的、直觀的外化標識,并構建民族的獨特景觀儀式。
(二)民俗文化
電影從喬治·梅里愛時期便與戲劇藝術結為血親,當電影傳到中國,就不可避免地將古老的戲曲藝術加入其中,公認的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中,電影與戲曲的親密關系昭然若揭。
無論是借用戲劇性敘事結構電影情節,還是在影片中植入京劇《過昭關》(2018)、越劇《柳浪聞鶯》(2021)、河北梆子《人·鬼·情》(1987),還是戲劇后臺伶人生活的敘述《霸王別姬》(1993),都在這門年輕的藝術——電影中,試圖表達戲劇藝術的在場。《美姐》中的幾位主要角色都是二人臺劇團中的演出人員,流行于張家口農村地區的獨特劇種——二人臺②,是表達人物生命變遷的重點場景。將民間通俗文化與古老民族的生存與欲望相結合,以二人臺的喜樂悲歡和人性中的不屈與堅韌為基底,糅合出對華北大地新的情感想象與文化想象。影片主人公狗蛋的童年、青年、中年時期的愛情、家庭和事業,分別與現實中的“文革”前、“文革”十年,以及80、90年代的社會轉型相連接。大眾文化與商品經濟以大刀闊斧之勢進駐華北農村,劇團藝人的生存、人們的心理變化都不可避免被波及。屬于張家口農村的二人臺的傳統演出劇目被時下的流行歌曲替代,連體現民俗風情的戲劇服裝都換成了城市的服裝。改革浪潮下,除了代表傳統文化的演出受到沖擊以外,人們的情感也因此被迫異化。郝杰導演用《美姐》《光棍兒》展示了承載著厚重的地方文化的二人臺,是他對那片土地上存在的傳統文化記憶。
蔡成杰《北方一片蒼茫》中對中國北方的另一民間奇談——“出馬仙”③進行了尖銳描繪,在民間,“出馬仙”某種意義上是盛行蒙古地區的“薩滿教”的延續。影片借用三任丈夫意外離世的寡婦王二好偶然間被村民奉為擁有法力的“大仙”為出發點,王二好成為能溝通萬物神靈的“大仙”后因她所謂借助鬼神力量實現村民私欲,繼而引起對河北農村經濟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泯滅人性的批判。“……薩滿文化只是作為故事的外殼,或者說只是一個可以辨識王二好身份的編碼。如果說薩滿文化的出現是對抗自然受挫后集體焦慮的體現,而王二好成為薩滿則是集體無意識的惡果。”[2]王二好成仙、成為薩滿,滿足村民關于求子、求生、求錢財等等的欲望,惡果與受挫相輔相成。影片原名為《小寡婦成仙記》,主人公王二好“成仙”之后,迎來村民的熱情相待,不僅與成仙前的冷遇形成對比,還極大諷刺了后半部分為了追求錢財而喪心病狂的、扭曲了人性的村民對所謂“信仰”的冷酷無情。蔡成杰導演借用民間傳說式的外殼講述了一個荒誕的現代農村故事。
二、影片風格:超現實
(一)超越現實
三位青年導演的作品不約而同使用了超現實的手法設計出荒誕、魔幻的農村現實。蔡成杰《北方一片蒼茫》的開場部分隨著樹林場景結束,影片以王二好的主觀鏡頭和她的畫外音來表達屋內的人們聽不到她說話的非真實情境,她的肉身無法動彈,只有意識清醒。而主觀視角的運用讓王二好、攝影機、觀眾三者合一,面對“老豆腐”的性騷擾,觀眾與王二好并列,無法反抗。片中出現的幾次彩色片段也將超現實荒誕感一次次拋出并加深。王二好被村民恭維成“神仙”的夜晚,以她為彩色中心構圖,向周邊逐漸呈黑白色調,同一幅場景中彩色與黑白共存的不合理讓王二好是“大仙真身”這一事件更加荒謬。此外,不明所以的翅膀、小裁縫女兒的鬼魂、民間舞扇隊,以及早就死去多日的四爺等等。這些基于薩滿神仙的“通靈能力”而構建的超現實設計與殘酷的農村現實情節組合起來,突出了她作為影片中唯一心存善意的有人性的象征,與麻木不仁的村民形成對比。她拯救人間的愿望淪為幻想。
郝杰《我的青春期》結尾,隨著與畫面內容無關的鐘聲音響越來越加速,并忽然暫停,屋內的兩位男女主角消失不見,木門被塞滿大雪封死。接下來的轉場是一個非真實空間,整個世界被大雪覆蓋,兒時的男女主角從地底破土而出。而這部青春片整體都是依托現實建構的,片尾的超現實色彩將青春的回憶涂抹了深深的一層虛假。
徐磊《平原上的夏洛克》片名以神探夏洛克的故事揭示出這是一部探案元素的影片,卻以華北平原淳樸的兩位農民去替代夏洛克、華生組合,便使之雜糅推理探案與戲劇性的類型。圍繞尋找肇事兇手展開一段啼笑皆非的拼貼式喜劇,而喜的另一面,則是一出農村荒誕景象。徐磊給予農民這一階層以詩意的溫情與浪漫的堅守,以超越現實強化現實,在現實中又失衡于現實。
(二)人際關系的復雜多樣
中國傳統的社會關系被費孝通比喻為“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3]意味著波紋不斷向外推出一圈又一圈,個體與他人的聯系逐漸向外生發出由近到遠的圓圈,遠近構成了以血緣為中心、以人們與他人繼續發生交往產生親疏程度的地緣關系。《光棍兒》中的二丫與同村的老楊、梁大頭、顧林等多人維系地下的性來往,而俏三又花錢娶來了老楊買的四川妞。整個村莊中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彼此共享身體與金錢甚至勞動力的資源,各有所圖的前提下相互連結交織,貧苦農村的性開放狀態與農民生存法則被郝杰的鏡頭毫不遮掩地推到鏡頭前,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概念成為后景,在悖于綱常的氣氛中也而“波紋”模式也喬裝成另一種樣貌,以二丫為中心,勾連了幾個光棍兒并再次向外擴散的圓圈邏輯式的人際關系網絡。在《美姐》中以狗蛋為“波紋”中心向外擴散聯絡出美姐母女四人等。
隨著社會的發展,在不斷的變遷中個體的獨立意識會逐漸增強,掩蓋傳統的農村社會人際交往中因為血緣和地緣而緊密的感情。《平原上的夏洛克》的超英除了情義之外,同時也為自己的房屋建造考慮,而與正義結伴為遭遇車禍的樹合尋找肇事兇手。農村人際交往中賴以生存的情感因素與利益的驅動共同構成了混合的特點,“農村人際關系的復雜性與時代性,是時代變遷以及人們思想觀念變化在人際關系上的客觀顯現”。[4]
三、銀幕內外:作者與區域電影
(一)作者與故鄉
三位導演一致在影片中呈現出個人成長的經驗,展現鮮明的創作特色以及地域特色。一方面由于21世紀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加速前進,一方面農村遭遇城市發展入侵,城鄉差距越來越大,而不斷凋敝的鄉土文化促使導演將電影中的故事場域與文化場域轉向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2010年,郝杰首部作品開始對準家鄉張家口顧家溝村,片中的演員都來自這個村落里的村民,此后《美姐》《我的青春期》《馮海的夢》,都沒有脫離導演的家鄉,甚至文化心理。郝杰在訪談中說過:“我從不避諱說我是土生土長的農村孩子,因為這就是我的根。”[5]他在影片中表達自己對人生經驗中體驗到的真實感受,不僅表達了他對家鄉故土上人們的情欲、人際關系、生存狀態,還是真實的年代細節,毫無渲染的原始風味刻畫承襲了現實主義題材的特點。
《平原上的夏洛克》靈感來源于徐磊的家鄉深州發生過的真實車禍事件,肇事逃逸之后被撞者的親戚因報警需要自費住院的醫藥花銷,而謊稱是意外自己摔傷則能報銷“新農合”(新型合作醫療)。本片的拍攝地點也選在距離徐磊的家鄉五六公里的深州。導演將來自故鄉的真實故事搬上銀幕,演員是自己的親人和鄉里鄰居們,把家鄉的地理風貌呈現出來,用鏡頭留下自己的鄉愁,傳達出歷史進程中不斷后退的家鄉記憶。
同樣,蔡成杰出于描摹家鄉中人們的精神與情感面貌的意圖,在《北方一片蒼茫》中放入作者本人對現實的感觸與體認,勾勒出冰天雪地的承德農村中畸形化的人性。
(二)區域電影
隨著重寫電影史的呼聲越來越高,圍繞某個區域電影作品進行的研究也逐漸有了不少成果:藏地、杭州、重慶、貴州、東北……來自同一個省份或同一種文化背景的導演,在個人的作品中會不約而同地融合了具備相似性并各有特征的區域面貌,書寫了遼闊的中國大地上自成一家、各有千秋的精神氣質。
郝杰、蔡成杰、徐磊三位導演無一例外在選用家鄉河北的非職業演員、河北方言、河北農村的人物與故事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性。他們都選擇對家鄉故土的風光實景拍攝,張家口、承德、衡水,黃土、冰雪、雨季,將河北省的不同地貌風情刻入自己的創作;喜劇、懸疑、推理、愛情的混合運用也體現了青年導演對類型片的革新性運用;在城市化、經濟化的背景下表達農村生長滯后的亂象與落寞。
同時,在不同的創作個性中也獨具各異的創作色彩。徐磊傾注了溫情的俠義熱腸與蔡成杰作品中王二好、弟弟石頭之外自私、險惡的眾生相形成鮮明對比,并探討了男女不平等、猥褻未成年人等嚴肅的社會話題,而郝杰又在貧窮的北方農村里側重兩性關系、買賣婦女的刻畫。
2021年郝杰參加《開拍吧》創作的短片《馮海的夢》《橘子》,進一步拓展其作品譜系中的兩性關系與男女愛情;蔡成杰的長片作品《四十四個澀柿子》作為2022年第16屆first青年電影展的閉幕影片特別放映;徐磊為bilibili視頻網站“大世界扭蛋機”創作科幻短片《地球最后的導演》。三位導演都在電影業內紛紛拿出表達個人話語的作品,耕耘著屬于河北電影創作群體的土地。河北導演突破性的新創作,表明了河北電影的創作正在繼續,而針對區域電影研究,河北的電影樣本日益豐碩。
四、結語
通過對三位導演主要作品的探究,梳理出“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的河北農村面貌,呈現全新的創作表征與美學氣質。不僅讓觀眾看到與各自地域風情緊密擁抱的獨特的民俗文化,還對農村傳統人際社會的變化與不變進行了細膩傳達。
青年導演們對作品堅持自我表達,以作者性與多樣性連接了銀幕內外的情感張力。然而郝杰在堅持個性、對作品進行創新——《桔子》的地理空間轉到城市,話語機制卻變得晦澀難懂,院線電影《我的青春期》中對女性的過度意淫等問題,遭遇票房和口碑的雙重危機。在藝術創作、張揚個體的背后,創作者仍要考慮與市場的關系。
三位導演各自的作品使話語主體為農村的電影文化進一步得到塑造,為河北電影的現代化發展錦上添花,有力推動了華北民族文化與電影美學相互促進的步伐,并為區域電影研究拓展出一條新的路徑。
注釋:
①出自克萊夫·貝爾《藝術》,指有別于日常情感體驗的一種獨特的、崇高的、抵觸相關日常生活的諸多考慮到的“審美觀情感”,是區別藝術品與非藝術品的“最基本的性質”。
②二人臺:二人臺俗稱雙玩意兒,二人班。起源于山西,成長于內蒙古,是流行于內蒙古自治區中西部及山西、陜西、河北三省北部地區的傳統戲曲劇種。
③“出馬”,據說是指一些動物,例如狐貍、蛇、黃鼠狼等,修煉成精而附體人身,進而讓人有了為他人斷事治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