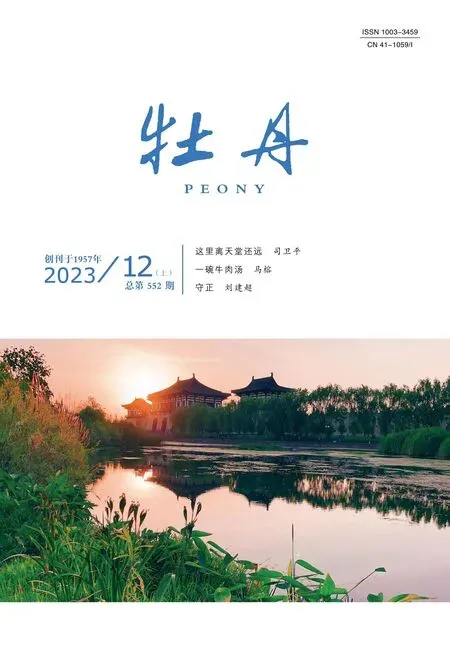在創作中感悟傳統與創新
董 菲
推陳出新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文藝發展的必然要求。作為一名美術工作者,既要在傳承中華優秀文化中汲取養分,又要在互學互鑒中著力創新。就自身創作而言,不能脫離時代氣息,也不能做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新”是花鳥畫創作的目的,古人反映了自己的時代,我們也可以反映我們的時代。在深入生活的基礎上,走出畫譜和畫室,走向更豐富而神秘的大自然,會獲得更廣闊的創作題材。北方茂密的灌木叢林題材的花鳥畫,則成為新時代花鳥畫獲得真正解放和生命力的重要途徑,花鳥畫因為新題材的開發與新形式的表現,從而思想感情和題材內容上產生了新的變化。藝術標準和審美觀點也是日常生活中最熟悉、最常見的題材——北方茂密的灌木叢林。筆者結合自己的近作《幽溪漾碧煙》,分析創作動因與藝術思路,來探討工筆兼小寫意花鳥畫的筆墨之美、造型之美、意境之美。
作為一個花鳥畫家,自我繪畫風格的形成是許多成熟藝術家追尋的目標,同時凝聚著艱辛而漫長的藝術探索過程。當代花鳥畫家一直在追求如何去塑造個人符號的語言圖式,探索對物象抒發的情感轉變成現實畫面。當代創作者們探索的勇氣和可貴的品質,一直在影響著筆者的花鳥畫創作。一直以來,筆者在創作中,以小寫意和工筆的筆墨語言來表現內在的精神世界,通過對物象寫實性的敘事表現,來展示對詩意、靜謐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
《幽溪漾碧煙》取材于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最常見的題材——北方茂密的灌木叢林和荒僻山嶺中的古木蒼柏。筆者認為對自然的如實寫生是藝術創作的源泉,不同的表現內容需要營造不同的畫面形式語言,從而達到豐富與完善自己的創作實踐的目的,這正是筆者作品想要呈現的視覺思考。
前期通過大量寫生訓練去提高自己,表達自己,為今后的創作積累資源、指明方向。將方案計劃做得詳細,先選擇一些較為常見的樹木、灌木叢、石頭構圖入畫。接下來重點到名山大川寫生搜集題材,像懸崖峭壁、參天古木、飛瀑流泉,碩大的古榕樹,茂密繁復的原始森林,茂盛挺拔的樹木群。畫大場景古樹溪流題材,高聳的參天大樹,樹葉茂密不見底,林中小溪旁幾只白鷺嬉戲飲水,河畔斗舞,構成一幅生態文明的美麗畫卷。這種大場景寫生在眾多植物和禽鳥中提煉物象結構,抓住大結構,捕捉大動勢,始終以營造動靜對比為主題。
通過一定的寫生積累,也慢慢地總結了一些規律,在復雜的場景面前,首先要選擇一個適合入畫的角度,確定整個畫面的結構動勢,用前面幾根主線條去定住畫面的走勢,把畫面分成幾個大塊面,選取比較集中離自己最近的一個點,按照物象的結構慢慢開始畫,逐漸向四周擴散,從而布滿整個畫面。然后再回到這個點圍繞對象,深入刻畫,畫出它的結構、層次、疏密關系,層層深入到整個畫面。在大場景對景寫生面前,學會移花接木,在不違背其生長規律的情況下,作一些主觀處理。因為自然界的植物,無論是桿、枝、葉本身都有自身的規律,我們要在雜亂中找出規律,用自己的感受畫出對事物的理解,使之繁而不塞,密而不亂,給人意境深遠的畫面意味。在這個藝術再創造過程中,靠的不是寫生的技巧,而是對自然生命的理解,對物象題材的歸納,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去創造自然界最真實的自然之美。
在《幽溪漾碧煙》的寫生稿進行筆墨轉換的創作環節中,針對幾種題材的搭配穿插、相互呼應、取舍關系,筆者選擇傳統的表現手法,擬宋元筆意,以小寫意的筆法勾線、皴擦出樹木的結構層次,再以工筆細膩的手法勾畫,層層分染出白鷺的動態結構。整體擬宋元畫風的墨花墨禽,畫面以水墨為主,追求幽遠靜謐的無我之境。此幅作品的細節處理工作量相當的大,每一棵樹木和枝干都要皴擦出結構,每一片葉子都要積出水墨效果,顯現出豐富的層次。白鷺的身體結構和羽毛鱗片要染出厚度,染出虛實。由開始對幽溪古木題材瞬間萌發的一種“意象”,到最后的層層相映,交錯復雜。筆者認為創作是一個由形象到意象的完美蛻變與升華,在這個蛻變與升華的過程中,真正實現了情和人、情和景的自然融合,體現書卷幽境、古意雅致的格調與品味。
《幽溪漾碧煙》將總結寫生經驗,反復思考繪畫作品可讀性與耐讀性,如何傳達物象之生命意義將是筆者創作下一步思考的問題。以往的寫生,過于注重物象本身的形,直到創作《幽溪漾碧煙》時,才慢慢地去嘗試,忽略物象本身的形,去尋找形之外的東西。當時只是一種朦朧的意識,寫生的意義不在于描繪其形象本身,而在于傳達形象之外的一種精神氣質。
寫意精神不同于西方的傳統寫實主義,它不是客觀對象的完全模仿再現,而是建立于客觀、真實的物象基礎之上,融入了畫家的情感,強調對物象自然形態的改造、超越與提煉,最終是為了表現事物的本質和抒寫人的自然本性。《幽溪漾碧煙》是一種以自然題材為主的藝術門類,是從自然中獲得素材、吸取養料、總結繪畫的觀察理論和方法,寫生創作了大量精湛絕倫的花鳥作品。仔細觀察分析歷代花鳥畫作品,會發現他們在構圖上講究
含蓄巧妙,達到了生動自然,反對加工造作,意境上更是追求情景交融,天人合一。從而形成了中國花鳥畫形神兼備的特征,直到今天,仍是我們追求的最高目標和現實意義。
《幽溪漾碧煙》展現花鳥畫之寫意精神,創作靈感來源于對大自然靜謐幽深、素以為絢的詩學意境為追求。不拘泥于一景一物的細致描刻,而是主張超越有限形質,以物抒情,構建幽遠靜謐的無我之境。
《幽溪漾碧煙》作為小寫意花鳥畫,在造型上以寫實為主,有主體形象的生動塑造,又有畫面的前后呼應虛實關系,整體色調古樸淡雅,耐人回味。筆墨關系是運用傳統的表現手法,表達不同的現代人思想。花鳥畫創作不同于人物畫,無法直觀突出主題,表達思想。但一幅好的作品,應該是通過畫面能夠傳達一種人文精神,表達作者的美好祝愿,也就是所謂的借物抒情。《幽溪漾碧煙》正是抓住了這一點,以幽溪古木的質樸無私、靜謐幽深來傳達一幅書卷幽境、和諧盛世下的幸福家園。
如何衡量一幅優秀的藝術作品,也是藝術創作的關鍵。筆者認為首先要新,新就是有新意,有現代氣息,不守舊。都說藝術要反映時代,這是對的。我們可以學習傳統,但一定要在傳統基礎上有所創新。現代人畫花鳥,畫面就是要有現代花鳥畫的氣息。其次是美,美就是形式之美、筆墨之美、造型之美、色彩之美、意境之美的完美統一,畫面有了這些新和美,就能衡量出一幅作品的質量高低。
總的來說,筆者創作《幽溪漾碧煙》時,立足于中國本土美術傳統,從藝術本體角度出發探討花鳥畫的用筆、結構、寫真、傳神等問題,融入了新的思考和個體化陳述方式,也獲得了許多感悟。文藝創作不能是“一個人的風花雪月”,學術研究也不能是“象牙塔里的枯燥文章”,一切有價值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該是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的。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創作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也只有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創作精品上,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才能成就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