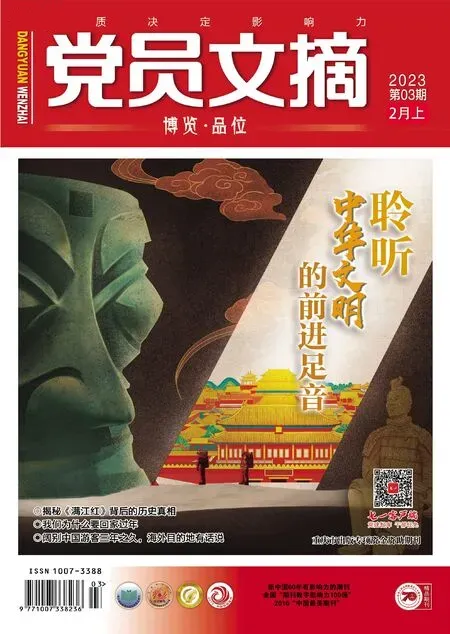走進中國書房,感悟文明的力量
□劉小草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一篇人人耳熟能詳的《陋室銘》,將對書房的想象刻入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從劉禹錫的“陋室”到蒲松齡的“聊齋”,從杜甫的“草堂”到陸游的“老學庵”,從梁啟超的“飲冰室”到魯迅的“老虎尾巴”……讀書人的書齋從來都不僅是存放書籍、查閱資料、方便書寫的場所,而是著書立說、寄托情感、賡續文脈的精神空間。
隨著網絡、電子閱讀的普及,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擁有一間實體書房已非必需。但在讀書人的精神角落,總有一片天地,是屬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
書房的意與象
書房,古稱書齋。書籍與房舍,構成了書房的實體存在。從僅可容膝的陋室草堂,到四庫充棟的皇家庭院,書齋可藏于市井,可隱于郊野,并無一定之規。
書房既是有形的,有藏書,有陳設;也是無形的,安住著讀書人豐富的精神世界。讀書人在書房中讀書、寫書、藏書,思考自我、社會和自然的關系。他們既可以“入世”,將個體命運與家國天下聯系在一起;也可以“出世”,走向審美的、廣闊的精神世界,與人、與天地相交流,與萬物化為一氣。
講書房,其實是為了講人。書房是如何被塑造的?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王子林認為:“書房應當是古人的生活方式和哲學思想的體現。孟子說過‘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如果讀書人有了這種豁達的胸襟,就可以實現‘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理想。”
《大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古代讀書人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將個體命運與家國天下聯系在一起。
尋找“書房的根”
“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晉書·天文志》記載,在古代的星象構圖中,東壁是藏書的地方,是天上的圖書府。
回顧書房的物質和精神史,可以見證這條文脈逐漸成型和發展的歷程。現存文物中,與書房相關的早期畫面,出現在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上,如《讀經圖》《拜謁圖》《講經圖》,畫中文士席地而坐,手捧簡牘,向高臺上尊者拜謁求教。在后世傳說中,也有不少關于私人讀書場所的記載。河南淮陽縣西南的“弦歌臺”,傳為孔子讀書處。山東鄄城的“陳臺”,相傳是曹植被貶出京后,讀書飲酒打發時光的地方。這些讀書場所一般選在僻靜清幽之地,避免外界紛擾。
唐代許多文獻中,都出現了文人在書齋中讀書、作畫、籌謀、著述的記載。有劉禹錫在陋室“調素琴,閱金經”;也有悲涼如杜甫者,“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有研究統計,《全唐詩》中收錄反映書齋理趣的詩共計兩百余首,作者近百人,以書齋為中心的繪畫更是延續到后世。
書房:一種生活方式
“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幾案。”
作為讀書人精神空間存在的書房,承載著主人的心性與志趣,文人也多將文集以書房命名,如陸游的《老學庵筆記》、趙孟頫的《松雪齋集》等。
文人的書房生活并非只有埋首書海,而是相當富有情趣的。東漢時期的文學家王粲,博聞強識,卻有一個怪癖,喜歡聽驢叫。他去世時,曹丕參加葬禮,還令前往吊唁之人集體學驢叫。傳說王粲在家中專門建了一個“吟驢亭”,一邊讀書一邊聽驢叫。
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他在解釋其緣由時說:“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把詩書、金石鑒藏與下棋喝酒等日常娛樂并列。
周密的父親周晉在《清平樂·圖書一室》中記錄過自己的書齋生活:“圖書一室,香暖垂簾密。花滿翠壺熏研席。睡覺滿窗晴日。手寒不了殘棋。篝香細勘唐碑。無酒無詩情緒,欲梅欲雪天時。”在滿室圖書中考據金石、品香插花,又可飲酒作詩、觀梅賞雪,自成一方天地,何樂而不為?
書房的革命
“十年飲冰,難涼熱血”,提起近代中國書房,繞不開梁啟超的“飲冰室”書齋。“飲冰”語出《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梁啟超自謂“內熱”,始終滿懷報國的赤子之心,以“飲冰”自解。在飲冰室,他以筆為槌,敲響了振聾發聵的時代戰鼓。
也正是在這里,晚年的梁啟超潛心思考中國社會走向,專注著書立說和講學。在這里,他完成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重要學術著作。直到病逝前,他的案頭還擺放著未完成的《辛稼軒先生年譜》。
魯迅曾向人介紹:“在房子的后面搭出一間平頂的灰棚,北京叫作老虎尾巴。這是房子中最便宜的一種。”這個小屋,可謂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書房。在這里,為了喚醒沉睡在舊時代的同胞們,魯迅斗志昂揚,筆耕不輟,寫下了《野草》《彷徨》《華蓋集》《朝花夕拾》中的大部分作品。
1920年,一位身著長衫的中年人,帶著行李搬入上海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一幢磚木結構的老式兩層石庫門住宅。
這位中年人就是陳獨秀,隨他一同遷入的還有《新青年》編輯部。這里是他的住所、書房,也是工作地。同年6月,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此成立。
在風云激蕩的20世紀20年代,這里曾是許多重要歷史人物的聚合點: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翻譯《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的李漢俊、年輕的毛澤東……
這一間間書房,無疑是近現代中國思想最為活躍的地方。它們承載著新青年的朝氣與夢想,見證著覺醒年代的先行者如何披荊斬棘,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條屬于中國的道路。
百年風云際會。隨著科技發展,紙質出版物日漸式微,閱讀、寫作、傳播的形式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書房甚至“白紙黑字”都不再是必需品時,我們的精神生活又將安放于何處?
在一篇題為《移動的書房》的文章中,作家馮驥才迎來了又一次書房“革命”:這一次,iPad(平板電腦)是他“流動的書桌”,汽車和飛機是他“移動的書房”。
馮驥才捫心自問:“我的書房書桌,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的書房書桌了吧?”
“不不,應該說,它們僅僅是我的書房和書桌的一種延伸,也是一種開創。我的‘心居’,仍是我心之所居。一切往日情景,今日依然都在。或曰:今日之枝,乃出于往日之木也。”馮驥才自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