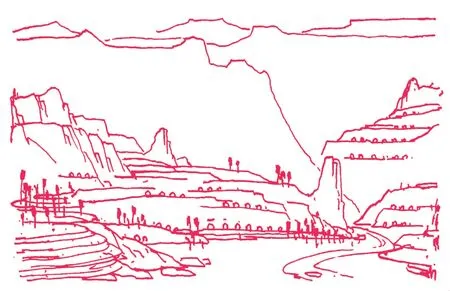柏骨香
山西/郭淑紅
齊總對那件事一直耿耿于懷。
此刻,他撳亮燈,在書房里轉了幾圈兒,走到書櫥與窗臺夾角的崖柏茶桌前,把蓋在桌上的布揭起一抖,動作有些猛,塵灰揚起,嗆得他咳了兩聲。
茶桌取自太行山高海拔地區的某處崖壁,生不知幾百年,風扭雪催;死不知幾百載,雨咬霜噬。缺土少水、朔風烈陽的嚴酷,鍛造了它異常堅硬細膩的質地,更雕鑿了它甚為奇崛的外形。
數月前,齊總應同學老吳之邀去故鄉某地考察,途經一個莊子時,老吳忽然笑問:“齊總,還記不記得小俞?他就是這個莊的。”一個黑瘦的少年,在齊總的記憶中突然浮現。讀初中時,小俞瘦小,老穿他哥的一件舊褂子,人像根火柴棍晃蕩在衣服里。因他說話結巴得厲害,沒少遭同學們的嘲笑與欺負。那時金庸小說風靡校園,受俠義精神影響,齊總故意與小俞同桌,護著他,還用白面饅頭換小俞長毛的窩頭吃。
“要不,見見?”老吳開著車,隨口一問。“彈指間,三十多年沒見了!不知道小俞好不好?”齊總感嘆道。老吳撥了電話,不過十多分鐘光景,一個精瘦的中年人遠遠地揮舞著胳膊,向村口跑來。小俞成了老俞,山風吹皺了面龐,眼睛卻異常明亮。看得出,為迎貴客,他還特意穿了身挺括的新衣服。
齊總就是在老俞家遇到這張崖柏茶桌的。幾個人喝著茶,老俞侃起了他與這張茶桌的傳奇經歷:“這塊崖柏老料,是我從北山的老鷹崖采下來的。這家伙嵌在離地三十幾米高的石縫里,弄下來費老鼻子勁了,腰里系的鋤把粗的繩都差點兒磨斷,得虧我這身板兒輕,才安全著陸!”老俞夾煙的手忽高忽低地比劃著,這番驚險描述,引得老吳一陣唏噓。
齊總輕輕觸摸桌面,暗暗吃驚:好一塊千載難逢的柏料,清香撲鼻,面如浸過紅油,光潔照人。這桌子似與他有緣,他不停地摸著,奇香就不停地散發出來。
他久久不愿放下手!
老吳窺他此態,便笑說:“老俞,明兒也給齊總踅摸塊好料,聽說柏香有助睡眠,還能驅蚊蟲哩!”老俞一捶大腿,震得煙灰掉了一截兒,慌忙抹著新褲子笑:“嘿呀,踅摸個啥呀,待會兒直接把這個拉去!這柴疙瘩能進城,也算它的造化了!”齊總放下杯子,忙擺手笑道:“那可不成,你甭聽老吳胡咧咧!”
把茶言歡,不覺時近中午,齊總和老吳要趕路,老俞苦留不住,執意要把茶桌裝上車,老吳也在一旁煽風點火。齊總雖力拒,兩百多斤的木頭還是被兩人抬出,硬塞進了老吳大越野的后備箱里。老同學盛意難卻,齊總動容,回身把三千塊現金悄悄壓在了茶壺下。
回來沒幾天,尚未給茶桌配齊茶具,老俞的電話就來了,結結巴巴的:“村、村里需、需要修個路,老鄉進城賣山貨、娃上學,都、都難著嘞!可是、可是、可是……”老俞掛斷了電話。
齊總這才醒過味兒來,久違的那份兒同學情,頓時凋零。
這世道,沒有免費的午餐哪!連多年的老同學,都變成了這樣!
幾天后,老吳突然來了個電話:老家下了一場暴雨,平時的干河灘突遭洪水襲擊,老俞出事了!
齊總一驚,忙問怎么了?老吳在電話那邊哭了:當時老俞和三個玩耍的孩子被困在河里的一塊石頭上,幸好不遠處有臺施工的裝載機,司機在洪水的咆哮中聽到他們的呼救,趕來搭救。老俞把三個孩子連舉帶推,弄進了鏟斗內,自己還沒來得及爬上去,腳下的碎石被兇猛的洪水沖走,一瞬間,人就卷進了滾滾濁浪里。鄉親們沿河找到百里之外,也不見人影。幾天后洪水退卻,人們找到老俞時,他夾在兩塊大石頭間,已經被卵石擊得面目全非……
齊總回村看到了一切。他下了決心:路,一定要修。為了老同學,更為了全村的鄉親們!
點評:
小說最顯著特點是行文的曲折。開頭寫齊總得到了一塊千年不遇的好柏木。這塊柏木很特別,得之不易,同時有奇香。柏木桌只是一個引子,更深刻的內容在后面。
齊總很順利地得到了柏木桌子,卻沒想到這是老同學設的局,為的是以此引來他的資金。小說到這里,情節發生了陡轉,這不禁引起了齊總的警覺:社會上的許多腐敗就是在迎來送往中產生的,用小恩小惠把意志不堅強的官員拉下了水。同時也引起讀者的關注:看事態怎么發展。
小說再次轉折,把這個事按下不表,宕開一筆,寫了老俞的犧牲。他的犧牲,引起了齊總的高度關注,決心回村察看實情,并決定出資修路。
小說寫得千曲百折,不僅使得情節引人入勝,也延展了小說的內涵。同時,作者刻畫人物的手法也比較高明:齊總是正面寫,為的是襯托側面寫的老俞。老俞不是一個心懷叵測、油滑的“釣魚者”,他想的、為的是全村的百姓。最后,他為救人付出了鮮血和生命,他的高尚品德令人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