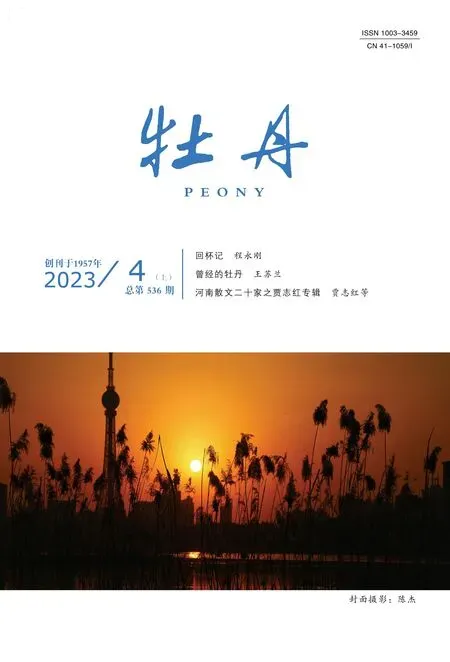證書丟了
王 剛
一
這一次,學校有三個高級指標,卻有四個老師符合要求:我,老張,黃婷婷,龍偉。換句話說,我們四人得展開PK,干掉一位老師。為了順利出線,我花錢發表了論文,升級了普通話證,評了市級優秀教師,完成了規定的繼續教育,通過了計算機考試……總之,徹底掃除了通往高級的地雷。教育局下發文件后,我抓緊時間準備評聘材料,包括各種表格、計劃、總結、家訪記錄、輔導記錄、作業批改記錄、述職報告等,腦殼都被搞大了。
簡單點兒說吧,我這一次拼盡全力,只為拿下夢寐以求的高級。老師嘛,當不了官,發不了財,只能靠職稱吃飯,職稱上去了,工資才能上去,養家糊口才有著落。不過,評職稱可不像爬梯子,說上去就能上去。為了保證不被干掉,我絞盡腦汁,深挖文件精神,按照材料目錄,將申報資料裝訂成冊,可謂文圖并茂,要內容有內容,要顏值有顏值。
下午四點,我忙完手中的活兒,打算去一趟學校,一是打印材料,二是復印證書。想到這個艱巨的工程終于即將完工,我頓覺一身輕松,吹著口哨向學校走去。保衛胡師傅拿著對講機站在校門邊,露出滿嘴漆黑的齙牙,問我大周末的不休息,來學校干嗎?我心情好,甩一支煙給他,揮揮手說,我要評中高,來學校搞資料。胡師傅滿臉堆笑,按了一下鑰匙,打開伸縮門,讓我進去。我吹響口哨,在他驚異的目光中,大步向教學樓走去。可是,當我爬上教學樓,走進辦公室,拉開抽屜時,不由愣住了。
抽屜里空空如也!
證書呢?我的證書呢?長腿跑了?插翅飛了?我有點兒發蒙,大腦一片混沌。長期以來,我的畢業證、教師資格證、普通話證、聘任證、獲獎證、課時證等一直放在抽屜里,就像寶劍躺在劍鞘里一樣。可現在,滿滿一袋證書,怎么說沒就沒了?
我定了定神,彎腰查看桌子下面,水洗一般干凈。翻檢桌上書本,什么也沒發現。見鬼了?早知如此,應該把證書帶回家,可誰知道會這樣?學校三天兩頭讓填表,為了省麻煩,我把證書放在辦公室。這樣做的不止我一個,幾乎所有老師都是如此。誰能想到呢,這個古怪的日子,我的證書竟然不翼而飛。
直起身子,掃視遠遠近近橫七豎八的辦公桌。學校辦公條件差,十幾人在一個辦公室,顯得擁擠窄逼。桌子上胡亂放著資料書,作業本,試卷。坐在我對面的,是滿臉絡腮胡的老張。老張教歷史,上課用方言,土得掉渣。經常穿一套皺巴巴的西服,戴著厚厚的眼鏡,頭發花白如雪,像個老學究。學生們當面稱他張老師,暗地里叫他古董。老張的辦公桌與我的辦公桌緊挨在一起,桌上擺滿小山一般的試卷,還有一些大部頭。我扒拉了半天,沒發現任何蛛絲馬跡。拉了拉抽屜,紋絲不動;看了看,原來上了鎖。
動手檢查黃婷婷的桌子時,我遲疑了一下。這女人心細,如果動她的東西,她肯定會察覺。我仿佛看見她瞪著金魚眼,皺著眉頭,嘴唇翕動,吐出一串嘰里呱啦的聲音。黃婷婷是全校最洋氣的英語老師,大波浪頭,眉毛細長,嘴唇像花朵。這女人仗著有幾分姿色,總以為自己是塊兒肥肉,男人全是餓狗。我翻了半天,左看上看下看右看,沒發現什么。
龍偉教數學,人高馬大,喜歡健身,像個籃球運動員。這小子不太講究,辦公桌擺滿書籍資料,還有兩桶方便面,幾個一次性杯子。我費了差不多半小時,才把桌上的東西清理完畢,卻什么也沒發現。我有點兒累,靠著桌子,看著緊鎖的抽屜發呆,腦海里冒出一個念頭,證書會不會鎖在抽屜里?
我真想找把扳手,把抽屜一一撬開。不過,我馬上打消了這個念頭。不管怎樣說,我還得在這里待下去,最好別干這種惹眾怒的事情。
二
天色暗下來,窗欞上仿佛爬滿了成群結隊的烏鴉。我累了,嘆了口氣,坐在椅子上,茫然地仰起頭,看著灰黑的天花板。這時,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拉開門,原來是胡師傅。他拎著電棍,盯著我說,王老師,你在干嗎?
我沒好氣地說,搞資料,你也要管?
胡師傅咧開嘴,露出滿嘴齙牙,歪著身子擠進來,啪地按下開關,眼前立刻光明一片。他瞟了瞟辦公室,用警棍扒拉著亂糟糟的書本,啞著嗓子說,這是怎么回事?
我看了看他的齙牙,說,我的證書丟了。
你不能這樣干啊,如果上面追查下來,我該如何交差?
我的證書丟了,那你說,該怎么辦?
胡師傅咧嘴笑起來,王老師,別生氣,生氣有什么用?
我一下子泄了氣。不錯,生氣有什么用?我看著他的黑制服,手里的黑警棍,發亮的黑齙牙,油亮的光額頭,笑笑說,胡師傅,我的證書丟了,請你幫個忙。
你這話什么意思?我又不是警察。
放心吧,我只是想看看監控錄像。
胡師傅松了口氣,走吧,去監控室。
胡師傅打開監控視頻,叫我自己看。真倒霉,辦公室沒裝攝像頭。當初,按學校領導的要求,所有辦公室全裝上了攝像頭。這事引起了老師們的激烈反應,認為這種做法太過分,不把老師當人。想想也是,只要走進辦公室,背脊上總有一只眼睛盯著,那滋味真不好受。由于反對的老師太多,學校領導做出讓步,撤掉了辦公室里的攝像頭。不過,走廊過道裝了攝像頭,只要偷證書的人從辦公室走出來,就會被攝像頭拍下來。
胡師傅扔下我,出門巡邏去了。我坐在椅子上,用鼠標拖動畫面,尋找該死的犯罪嫌疑人。我盯著大門,看高矮胖瘦的老師們陸續走出,再走過長長的過道。平時倒不覺得,一旦通過視頻觀看他們,竟發現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說,老張把擦了鼻涕的衛生紙揉成一團,偷偷扔到地上;黃婷婷的裙子后擺提了起來,露出半邊屁股;龍偉跟在一個女老師后面,盯著她扭來扭去的腰肢;某位豐碩的女老師邊走邊理衣服,乳房忽隱忽現。
手機響了幾次,是謝芬打來的,我懶得理睬,直接掛了電話。
看了半天,眼睛發酸作痛,畫面逐漸模糊。我仰面躺在椅子上,點燃一支煙,使勁吸了幾口。胡師傅走進來,沖我笑了笑,又露出門板一樣的齙牙。
我丟了一支煙給他,他接過煙說,找到了嗎?
找個鏟鏟。我摘下煙頭,丟在地上。
我扔下胡師傅,起身走出監控室。城市燈火輝煌,看看手機,竟然已近十點。我把手揣進褲兜,縮著脖子往前走,只覺天地一片茫然。證書丟了,高級咋辦?這不是要人命嗎?是誰暗里對我捅刀子?我拿出手機,打開教師微信群,往里面扔了一條信息:我的證書丟了,誰看見?若有知情者,請及時跟我聯系。
等了幾分鐘,沒有人吭聲。我又砸下一條信息:到底是誰拿了我的證書?
不知不覺中,我已經走到派出所大門外。看看微信,沒人放一個屁。我打開手機相機,對著派出所拍了幾張照片,將照片丟進群里,補上一條信息:看來,我只能報警了。
僅僅過了一分鐘,手機鈴聲大作。按下接聽鍵,傳來了馬校長的怒吼聲,你瘋了?你想毀了學校?我告訴你,不要亂來,趕快給我滾回來。
我愣了愣,掛掉電話,在心中罵了他一句。
三
謝芬歪在沙發里,見了我不理不睬。虎子坐在地板上,抱著一輛玩具車,扯著嗓子嚎。我頗感詫異,這是怎么回事?謝芬平時對虎子可疼了,含著怕化了,捧著怕飛了。可現在,虎子哭得那么兇,她卻置若罔聞。我抱起虎子說,兒子,乖,別哭?
謝芬瞪了我一眼,一句話也不說。
怎么?臭小子闖禍了?我沖她笑了笑。
謝芬哼了一聲,扭過頭去,盯著地板。
餓壞了,有吃的嗎?我訕笑說。
想吃?自己弄。
你怎么回事?吃錯藥了?
我就是吃錯藥了,你要咋的?
我想了想,忍住了。記得某哲學家說過,一個女人等于500只鴨子,我可不想跟500只鴨子干仗。再說呢,一想起那些證書,心如貓抓一般,哪有吵架的興致?虎子掙扎著,哼哼唧唧的,我拍拍他的屁股,抱著他跳來跳去。不一會兒,他靠著我的肩膀睡著了。我把他抱進臥室,放在床上,蓋上被子,走回客廳。謝芬仍保持著固定的姿勢,臉色烏云翻滾。
別生氣了,有話好好說。我在她的身邊坐下,摟住她說。
她甩開我的手,眼睛瞪著我,看得我心里發毛。
我避開她的眼光,說,你到底怎么了?
她哼了一聲,你咋不接電話?耳朵聾了?
我去學校搞申報材料,你又不是不知道?
搞材料?怕是搞女人吧。
別吵了,我的證書丟了。我提高聲音說。
什么?證書丟了?她有點兒轉不過彎來。
沒有證書,我沒辦法評高級。
不能評高級?那你快找啊。謝芬失聲喊起來。
到處都找過了,連影子也沒看見。我低下頭說。
謝芬一下子站起來,看著我說,你怎么搞的?是不是忘記放哪兒了?是不是被人偷了?誰會拿你的證書?你是不是得罪了哪個?證書沒腳沒翅膀,怎么會突然飛了?
我能說什么呢?沉默了一會兒,低聲說,時間不早了,睡吧。
躺在床上,滿腦子是證書。謝芬已經進入夢鄉,說著含糊不清的夢話。月光從窗戶灑進來,斑斑點點,飄忽不定。謝芬說得對,證書沒腳沒翅膀,怎么會飛了?一定是誰故意整我。老張、黃婷婷、龍偉、小馬,小王……誰是犯罪嫌疑人呢?誰都像,誰都不像。我是威嚴的法官,用各種問題盤問他們,試圖把真正的盜賊挖出來。這些家伙很狡猾,誰也不肯亮出底牌。我跟他們吵了大半夜,搞得頭昏腦漲,卻沒挖出一點兒有用的線索。
不知過了多久,他們全消失了。我看見自己站起來,踩著鋪滿月光的大街,走到了學校門口。胡師傅提著警棍,筆直地站在值班室外,如一尊泥菩薩。我走進去,他仿佛沒看見我,連招呼也沒打。我懶得管他,徑直飄進教學樓,飄進辦公室。
風拍打窗戶,嗚嗚直叫。辦公室空空蕩蕩,一個人也沒有。我撿起鐵棍,走到一張桌子前,三下兩下撬開了抽屜。我赫然看見,抽屜里放著一疊鮮紅奪目的證書。我趕緊伸出手,要把證書抓住。證書卻動起來,噼啪作響,仿佛鳥兒拍打翅膀。一陣冷風破窗而入,嗖嗖有聲。一張張證書隨風起舞,長出了嘴巴,尖牙,翅膀,變成一只只大鳥,呼啦啦張開翅膀,撞開窗戶,飛向遼闊的天空,眨眼間已蹤影全無。
我一下子醒了,聽見心臟撲通亂跳。
四
穿衣,漱口,洗臉,刮胡子,匆匆出門。周一要搞升旗儀式,七點前必須趕到,晚一秒都不行。學校安排了值班人員打考勤,晚到者扣分扣錢,作為推優評模的重要依據,與目標考核獎掛鉤。老師們如裝了發條,哪怕睡得比狗晚,也要起得比雞早。
天空灰暗,飄著毛毛細雨。我沖出小區大門,看看手機,已經六點五十。我站在路邊,使勁招手,打算攔一輛的士。附近站著幾個面目模糊的人,伸長手臂,伸長脖子,像一只只鵝。幾輛的士爬過來,我晚了一步,被搶走了。沒辦法,我只得給辦公室主任打電話,說我遇到點兒事,晚一點兒才能到校。主任說,算事假,盡快趕來。
等了好一會兒,終于搶到一輛的士。趕往校門口,耳邊傳來高亢的國歌聲。灰色的天幕下,學生們齊整整地站在煙雨中,像一片濕淋淋的樹。胡師傅提著電棍,帶著幾個保安站在伸縮門外,攔截遲到的學生。我快步走過去,悄聲說,胡師傅,請開一下門。
胡師傅看了看,低聲說,王老師,你怎么才來?剛才馬校找你,臉色很不好呢。我的心咯噔一下,問,找我干嗎?胡師傅說,不知道。我看了一眼黑壓壓的學生,說,胡師傅,讓我進去。胡師傅低聲說,王老師,以后來早點,我們挺為難的。
胡師傅按開門,我趕緊溜進去,跑到教師隊伍的尾巴上。
升旗結束,我擠開亂哄哄的人群,快步往辦公室趕。我恍惚覺得,只要像往常一樣拉開抽屜,就能看見那些紅紅綠綠的證書。我第一個沖進辦公室,拉開了抽屜。我失望了,奇跡并未出現,抽屜空空如也。
老師們陸續走進來。我像一根木頭杵在桌邊,看著一覽無遺的抽屜。幾個老師看了看我,什么話也沒說,低頭收拾辦公桌。老張走到他的桌邊,敲了敲桌子,對我說,兄弟,怎么了?魂魄丟了?我嚇了一跳,把抽屜推回去,連聲說,沒什么,沒什么。老張問,證書丟了?我說是啊,丟了。老張笑笑,會不會把證書落在其他地方了?我說,怎么可能?證書一直放在抽屜里,從來沒有動過。老張說,你的意思,這辦公室有賊?
其他老師紛紛湊過來,七嘴八舌議論起來。龍偉撇撇嘴,大家都是知識分子,誰會干這種事?龍偉的話引起了大家的附和,他們一致認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應該不會發生這種事。有人提醒我請個假,回家找一找。有人說我睡眠不好,會不會患了神經衰弱癥。有個小女生甚至提到了老年癡呆癥,說這種病很可怕,患這種病的人,會忘記所有的事情。為了驗證她的觀點,她跟我做了一個實驗,我說說最近一個周做了什么事,讓我一一列舉出來。我努力想了又想,怎么也說不清楚。小女生笑了,說這就是最好的證明,最好去醫院查一查。我拍桌子吼道,胡說,瞎扯,亂彈琴。
鬧哄哄的聲音沉寂下去。老師們你看我,我看你,氣氛詭異而尷尬。有的縮回座位,裝模作樣做事。有的打著哈哈,說不扯了不扯了,上課去。有的轉過身,盯著手機,聚精會神玩游戲。我努力笑了笑,大聲說,看來,我只得報警了。
此話一出,引起了大家的熱烈反應。有的問出多少酬金,有的建議成立一個專案組,還有的搬出福爾摩斯、柯南、狄仁杰。黃婷婷抱著手,哼了一聲說,你們不累啊,為這無聊的事情扯上半天?老張咳了幾聲,說,黃老師說得對,該干啥干啥。說著,拍拍我的肩膀,兄弟,幾張破紙,誰會感興趣?我憤怒地看著他,大聲說,那不是破紙,是證書。
老張說,證書不就是廢紙嗎?別人拿去干什么?不能吃,也不能用。
有個男教師說,話不能這樣說,證書對別人沒用,但對王老師有用啊。
對啊對啊,王老師,你仔細想想,跟誰有仇?有人附和。
黃婷婷冷笑一聲,殺父之仇?還是奪妻之恨?
上課鈴聲響了,大家如釋重負,談笑著走出辦公室。
五
上了兩節課,我拖著沙袋似的身體回到辦公室,手機催命般叫起來。
幾分鐘后,我坐在了馬校的面前。馬校四十出頭,比我小幾歲,可他早就是高級了。他拿著一支鉛筆,坐在寬大的辦公桌后,像一尊彌勒佛。我縮了縮肩,笑著問,馬校,你找我有事?馬校端起水杯啜了一口,輕輕放下,看著我說,證書丟了?我說,丟了。馬校說,聽說你要報警?我豎起身子說,沒,沒這回事。馬校哼了一聲,是嗎?可有人對我說,你要報警?我趕緊說,沒有的事,沒有的事。馬校笑起來,是啊,我想王老師也不會這么幼稚啊,學校是文明的地方,老師們都是有素質的,誰會拿你的證書呢?
我抬頭看了看校長的笑臉,竟然無話可說。馬校走到我的面前,語重心長地說,你是老教師了,遇事要多想想,這樣吧,抓緊時間找找。我答應一聲,退出了辦公室。
走過狹長的樓道,轉角處冒出一個人。定睛一看,原來是同一辦公室的小王。小王是90 后,下巴光溜溜的,像個高中生。我說,小王,有事嗎?小王左看右看,低聲說,王老師,你想過沒有,你的證書丟了,對誰最有利?我愣了愣,問,什么意思?小王說,對誰最有利,誰就最有可能拿走證書。說完,不等我回答,忽然轉身走了。
大老遠,看見龍偉抱著手,站在辦公室門外。我走過去,他把手指放到嘴唇邊,噓了一聲,走,跟我走。我說,干啥?他以一種不容反駁的口氣說,走,去足球場。
學生們正在上課,足球場上空無一人,顯得格外空曠。龍偉不回頭,甩著手往前走。剛下過雨,山巒格外碧青,就連足球場上的毯子,也格外青蔥,仿佛是真的草地。
喂,可以了吧。我對著他的后腦勺喊道。
龍偉不說話,繼續往前走,我只得跟著走。龍偉走到足球門邊,停住腳步,抱著手,靠在門框上,陰沉沉地說,你懷疑我拿了你的證書?
我愣了一下,說,沒,怎么會?
可是,你翻過我的桌子。龍偉盯住我說。
我沒別的意思,只是想找到證書。
你翻過我的桌子,你這是懷疑我。
別這樣,評中高的不只你一個。
龍偉笑笑,明人不做暗事,我如果對你不爽,根本不用偷偷摸摸,我會跟你真刀真槍干一仗。我跟你說了這些,如果你還懷疑我,那就別怪我不客氣。
龍偉抬起手,指著球場說,來這兒,單挑。
別這樣,何必呢?我們是同事,是兄弟。
龍偉掏出煙,丟給我一支,自己也叼上一支。我們坐在球場上,使勁拉著煙,頭頂飄起兩縷煙霧。龍偉抽完一支煙,伸手拍拍我的肩膀,低聲說,哥們兒,告訴你一件事吧,你的證書丟失的前一天,黃婷婷是最后離開辦公室的。
我悚然一驚,說,你的意思,黃婷婷拿了證書?
龍偉笑笑,我可沒這樣說,你好好想一想。
可是,她為什么要拿我的證書?
這還不簡單,為了干掉你啊。你可能不知道吧,黃婷婷沒有省級優秀,也沒有市級優秀,她能拿得出手的,只是一張優質課獲獎證書,比你的條件差遠了。
丁零零,耳邊傳來清脆的鈴聲。
龍偉起身,拍拍屁股說,走吧。
我看了看天,說,走吧。
六
黃婷婷穿著珊瑚紅連衣裙,站在學校門口法國梧桐下,大波浪頭發隨風拂動。胡師傅站在伸縮門外,張著嘴看她,露出漆黑的齙牙,嘴角掛著兩線涎水。我低下頭,加快步子往前走。這時,耳邊響起一個聲音,王老師,王老師。
我抬起頭,看見黃婷婷正笑瞇瞇地看著我。
王老師,一起走走。黃婷婷說。
黃老師,有事嗎?我有點兒蒙,看了她一眼。
沒什么事,找個地方吃午飯,聊一聊嘛。
黃婷婷與我挨得近,時不時碰一下,讓我心跳加速。她身上散發出含混的香水味,一陣陣往鼻子里鉆。我頭腦發蒙,覺得手不是手,腳不是腳,只能機械地跟著走。五六分鐘后,我們拐進一條清凈的巷子。黃婷婷指著一家館子說,就這兒了。
我點點頭,跟著她走進去。
黃婷婷要了個小包間,點了辣子雞火鍋,兩瓶生啤。包間很小,我感覺透不過氣來。黃婷婷撬開啤酒,笑著說,當了這么多年的同事,還是第一次聚呢。我點點頭,是啊是啊,大家都忙。她笑笑,確實忙,不過魯迅說過,時間是海綿里的水,只要肯擠,總會有的,以后要多交流啊。我沒想到,她竟然知道魯迅,使勁點著頭說,是啊,是啊。她把一瓶啤酒遞給我,喝一點兒。我擺擺手,不行不行,下午還要上班。
男人不能說不行哦,怕什么?她把啤酒遞給我,笑著說。
我們一邊吃喝,一邊聊天。確切點兒說,主要是黃婷婷說,我聽。黃婷婷口才不錯,甭管什么事情,只要從她嘴里說出來,就會變得活色生香。我也想表現表現,但舌頭不聽使喚,什么也說不出來,只會說是啊是啊,對啊對啊。
沒多久,我們各自吹干了酒瓶。黃婷婷說,再來一瓶?
我大著舌頭說,好啊,好啊好啊。
吃著喝著聊著,不知不覺中,上班時間快到了。在這過去的兩個小時里,幾乎顛覆我了對黃婷婷的看法。以前總覺得她高冷,尖酸,刻薄。現在看來,她完全是另一個人,能說會侃,風情萬種。也許,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們真該多聚多聊。
黃婷婷舉起酒瓶,說再敬我一杯。碰了杯,干了酒,她好看的眼睛看著我,壓低聲音說,我叫你王哥,不介意吧?我趕緊說,叫王哥好,比較親切。黃婷婷說,王哥,我把你叫出來,是想為你提供情報呢。我望了望她,什么情報?
你保證,不要對任何人提這件事。她把嘴巴湊近我的耳朵。
我保證,誰亂說誰他不是人。我舉起手發誓。
你的證書,可能是老張拿的。她看了看四周。
真的嗎?你看見了?他為什么這樣干?
我沒看見,但我認為是老張拿的。黃婷婷好看的眼睛看著我,壓低聲音說,你還記得嗎?按教育局的文件,普通話等級是評職稱的一個重要條件。
不錯,是重要條件。
老張的普通話級別低,只是三級甲等。
可是,他資格老啊。
資格老有什么用?評職稱主要看硬件。
可是,他為什么拿我的?
為了保險起見,提前清除對手。
想起老張油膩的老臉,還有土得掉渣的方言,我有點兒恍惚。
吃了飯,黃婷婷不由分說,搶著把賬結了。
七
剛進家門,老張的電話就追了過來,說好久沒聚了,叫我出去吃烙鍋。我不想去,上了一天班,只想睡一覺。老張不依不饒,說他在“老城烙鍋店”,叫我趕緊去。我說老婆身體不舒服,要幫忙照顧孩子。老張笑起來,叫我別扯犢子,趕緊過去。
包房里除了老張,還有四個人,一男三女。那男的以前見過,是老張的堂弟,開裝修公司的。幾個女的都很年輕,就像同一個模子出來的,細眉毛,紅嘴巴,尖下巴。
老張要了兩件啤酒,一人先發一瓶,提議先吹一瓶。眾人齊聲叫好,紛紛把酒瓶舉到空中。我只得跟著舉瓶,發出乒乒乓乓的聲響。不大一會兒,他們全吹完了,我還剩下大半瓶。真看不出來,那幾個二十出頭的小女生,喝酒如喝白開水。他們丟下酒瓶,催我趕緊完成任務。老張拍了拍一個女生的肩膀,說,小李,幫你王哥喝一杯。
小李把我的酒瓶搶過去,倒了滿滿一杯,嫣然一笑,王哥,我敬你。說完,舉杯,張嘴,一飲而盡。我仰起頭,把酒瓶塞進嘴巴,咕咚咕咚往里灌。由于喝得太猛,我被啤酒嗆著了,發出吭哧吭哧的咳嗽,引起了一陣快活的笑聲。
吹完第一瓶,老張提議大家自由發揮,愛咋搞就咋搞。大家拍掌叫好,劃拳,碰杯,翻牌,人聲鼎沸。起初,我還有點兒拘束,試圖置身事外。不一會兒,禁不住幾個小女生的輪番轟炸,身不由己陷入了混戰。后來,我索性放開了,來者不拒,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喝著喝著,頭就變大了。放眼望去,人影晃動,墻壁晃動,樓頂也在晃動。
老張端著一杯酒,跟我碰了一下,大聲說,兄弟,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美酒美女,不醉不歸。我大著舌頭說,好,好,不醉不歸。老張揮揮手,對小李說,小李啊,陪你王哥整幾杯。小李坐到我的身邊,舉起酒瓶,笑盈盈地說,王哥,我敬你。
看著小李晃來晃去的臉,我舉起酒瓶吼道,喝,喝,喝。
小李說了聲干,我也吼了聲干,兩酒瓶碰在一起,發出垂死的慘叫。
醉意朦朧中,老張把我扶起來,走出了烙鍋店。一陣涼風吹來,我感到肚腹里翻江倒海,趕緊丟開老張,跌跌撞撞地跑到一株樹下,張開嘴巴吐起來。
吐過后,老張拿來一瓶礦泉水,叫我漱口。我漱了口,將礦泉水瓶扔到地上,連踢幾腳,竟然沒有踢中。老張把我拖到一幢高樓前,我們肩并肩坐在臺階上。天空忽高忽低,像一口搖晃的灰黃鍋蓋。路燈也跟著搖來晃去,如一只只螢火蟲。
兄弟,你醉了?能聽見我說話不?老張搖了搖我。
我哼了一聲,示意他有話就說,有屁就放。
你想過沒有,是誰拿了你的證書?
要是老子知道,老子不弄死他。
有句話,不知當說不當說。
說,說,有什么不敢說的?
那好,我懷疑,龍偉拿走了你的證書。
我仰頭大笑,為什么?憑什么?
很簡單,他資歷淺,條件軟,沒有過硬的拿得出手的獲獎證書,如果硬拼,他根本沒機會入圍,只要把你干掉,他才能順利過關了。
我看了看老張,覺得他說得有理。長期以來,龍偉瞧不起教語文的,說教語文的有股窮酸味兒,個個都是孔乙己。我也瞧不起他,說他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原始人。曾經有幾次,我們還吵過嘴。在這評職稱的生死關頭,他會不會先下手為強,把我直接干掉?
可是,可是,他為什么不干掉你?我想了想,問老張。
只能說我的運氣比較好,如此而已。
八
丟了證書,對我的影響顯然易見。最直接的結果,讓我喪失了申報高級的資格。老張、黃婷婷、龍偉,三人順利晉升。想一想吧,換作是誰,這滋味好受嗎?
事實上,丟失證書不僅讓我錯過了高級,還影響到方方面面。比如,按照職稱進崗文件,我本可晉升一檔,但因拿不出證件,只得干瞪眼。省里下發了關于成立名師工作室的文件,一旦申報成功,將給予資金扶持。我完全符合條件,但交不出證書,只能望洋興嘆。除此之外,諸如申報省級骨干教師、優質課評委、課題研究、校際交流活動等機會,我只能靠邊站。在這期間,龍偉被評為市級優秀教師,黃婷婷申報了省級骨干,老張成立了名師工作室。就連那些嘴上無毛的小年輕,或搞了課題,或參加優質課比賽,或漲了工資。一句話,其他老師都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只有我被晾在沙灘上,成為一條發臭的咸魚。
不錯,沒了證書,我成了一條死魚。每天走進校園,我感覺腳桿打戰,心里發虛;每次走進辦公室,我低著頭顱,臉龐發熱;每次走上講臺,我彎腰縮脖,不敢直視學生,嘴唇哆哆嗦嗦,說話顛三倒四……總之,我像個冒牌貨,沒有半點兒底氣。有幾次,馬校長攔著我說,王老師,怎么搞的?你的魂丟了?你看你教的班級,成什么樣子了?聽了他的話,我產生了一種巨大的危機感:長此以往,我難保不會丟掉飯碗?不行不行,沒了證書,我就不是我,我的魂就回不來。我下定決心,哪怕上天入地,也得把證書找回來。
我沉下心來,仔細梳理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發現漏掉了一個關鍵——那些上鎖的抽屜。顧不得那么多了,我得想辦法打開抽屜,揭開里面的秘密。
好不容易挨到周五,臨到下班之際,我溜進洗手間,反鎖門,蹲于坑上。十幾分鐘后,我走出洗手間,辦公室已空無一人。門已關上,辦公室只屬于我一人,再也不用看臉色了。我松了口氣,坐在一張椅子上,打量一個個抽屜,準備天黑就動手。
暮色漸濃,對面的山頂上升起一輪月亮,像一枚碩大的夜明珠。按我的意思,沒有月亮更好,安全性更高。不過,有月亮也不錯,就像有人亮起了一把手電筒。我站起來,提起大號螺絲刀,走向老張的抽屜,將螺絲刀殺進縫隙,稍一用力,吱嘎一聲,抽屜就被撬開了。我拉出抽屜,空空如也,水洗一般干凈。
我提著螺絲刀,走向了一個又一個抽屜,龍偉的,黃婷婷的……吱嘎,吱嘎,吱嘎……持續不斷的吱嘎聲中,一個個抽屜被打開。空的,空的,空的,還是空的……
我丟下螺絲刀,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喘氣。
那些被打開的抽屜,像一張張大嘴,齜牙咧嘴地對著我。
我發了一會兒呆,忽然跳起來,奔向我的辦公桌,拉開了抽屜。
一疊紅紅綠綠的證書躍入眼簾!
我愣了一下,伸出顫抖的手,抽出一張證書,赫然看見上面刻著我的名字。我定了定神,又抽出一張,還是我的名字。我不敢相信,對著月光翻開了所有的證書。不錯,是我的,每一張證書上,都寫著我的名字,熠熠生輝,光芒四射。
我那些不翼而飛的證書,莫名其妙地飛回來了!
我長吁一口氣,把證書裝進資料袋,打算離開辦公室。門猛然被撞開了,胡師傅帶著兩個保安沖進來。他們穿著保安服,手里拿著高強度的電筒。我正要打招呼,他們卻將強烈的電筒光敲到我臉上。我只覺得滿眼白亮一片,什么也看不見。
王老師,你這是干什么?一個嘶啞的嗓音吼起來。
我聽出是胡師傅的聲音,趕緊解釋,誤會誤會,請聽我說。
這一次,我幫不了你,你去跟馬校長說吧。
胡師傅,你聽我說,聽我說。
胡師傅冷哼一聲,下令說,帶走,帶走。
幾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電筒光從我臉上移開了。
我看見自己像一個犯人,夾在兩個保安之間。
放手,放手。我喊起來。
別理他,帶走。胡師傅跺著腳說。
這時,我又看見他滿嘴閃閃發光的齙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