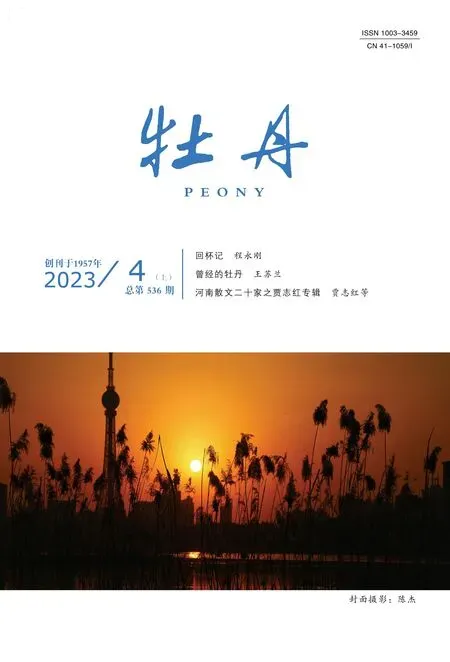另一種交流
楊紹敏
1
你仿佛在說,深秋的樹葉既是告別,也是開始,隨風飄落,鋪滿地上,總是在尋找什么,又在等待著什么。你壓低的聲音里透出與這季節相匹配的清冷,猶如一股清澈的山泉浸潤心田,像受到某種輕微的碰撞,我全身顫抖起來。這時,你又說:“你爬上石仙山試去看看。”
那天下午,我靠在車窗邊,瀏覽著手機里有關孫應鰲、張畢來的文字介紹,正乘車趕往他們生活過的地方——凱里市爐山鎮。此行的目的算是一次純粹的文藝采風,在爐山這片土地上,不僅涌現出像孫應鰲這樣的大儒,而且還有近現代著名學者張畢來等人。在這地處偏僻的山區,這些馳名國內外的人物,在這里長大,在這里生活,然后從這里走出去,建功立業,聲名遠播。同行的都是文藝界人士,也許大家和我一樣,都對前往的小鎮有著濃厚的興趣。是什么原因讓這個曾經窮鄉僻壌的地方,產生出如此聞名遐邇的人物?又是什么力量,支撐著這些人在那個艱苦的歲月里,依然不放棄心中的夢想,并用執著的追求去實現人生的目標?我從紛繁的思緒中回過神來,往車窗外望去,連綿起伏的群山慢慢向車身背后退去,一直沿著公路邊向前延伸的兩排銀杏樹,掛滿金黃的樹葉,此時秋陽輕薄,風吹過,葉飄落,如灑下片片金色的陽光。
小鎮離鬧市不遠,半個小時的路程,有時真來不及在車上想更多的事情。事實上,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由于工作關系,究竟有多少次踏上小鎮這塊土地,已經數不清了。每個人都奔波在時光的洪流中,對于某些地方和某些事物,擦肩而過或是短暫停留,記憶深刻或是漸漸淡忘,再正常不過。重要的是,無數次來到小鎮,竟然一次也沒有瞻仰過當地歷史名人的故居,作為一個從事文字的人,實則汗顏而無地之容。我記起,有那么幾次,坐在車上前往小鎮,我和大多數人一樣,不停地刷著手機的屏幕,樂此不疲。有時,我弄不明白,為什么很多人如此沉迷于碎片化雞湯式的淺閱讀,而對人類歷史上那些熠熠生輝的經典著作充耳不聞。遠的不說,就在我們身邊,像孫應鰲、張畢來這樣的大師級人物,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我竟在他們的眼皮底下隨波逐流,心里的愧疚感又加深了一層。孫應鰲何許人?只說起他是明朝萬歷皇帝的老師,就足以證明他地位的顯赫,此外他還是王陽明心學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張畢來,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翻譯家、史學家,其編寫的《新文學史綱》,一度成為大學中文系的教材,他還是“紅學”研究的權威學者,《漫說紅樓》《紅樓佛影》等論著影響巨大。
落葉飄落街頭,秋天越來越深,時光似乎也越來越深,人深陷其中,周身纏繞著濃得化不開的回憶。陽光從云層里穿透而出,打在舊磚沉瓦的皺褶,氤氳出老時光的味道。這樣的味道讓我想象著孫應鰲所處的年代,是否也是在一個下午的時光,天空中是否也是這樣薄薄的秋陽,不!應該是飄著綿綿細雨,那是在北方的京城,風雨飄搖,內憂外患,是當時明王朝最真實的寫照。霜染鬢發的他,曾經的躊躇滿志,已被殘酷的現實消磨得心灰意冷,他心里清楚,大廈將傾,無力回天,時代潮流,滾滾向前。他用東方哲學的眼光透視著那個時代,他努力過,也抗爭過,但事物的發展,終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最終,他選擇了隱退,那一年,他辭去帝師和國家最高教育行政長官職務,回到爐山這塊養育過自己的土地上,繼續從事著他最擅長的教育事業。此時此刻,我漫步在這塊充滿生機的土地上,追尋著他的足跡,仿佛前方腳步匆匆的人群,都在我眼前幻化成他的背影。我多么想迎上去拉著他飄然的衣袖,冒昧但又虔誠向他提一個問題,“先生的祖籍在江蘇,為何辭官后回到這里?為何整個晚年都在這里度過?”他笑而不語,但我從他深邃的目光中,找到了答案,因為他深深地眷念著這片土地。
遠處的鳳凰山,依然蔥蔥郁郁,淡淡的陽光下,如一幅水墨畫。千百年來,它就這樣靜靜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視著這里發生的一切。小鎮的人都說,他就是一只從爐山飛出的金鳳凰,它展翅高飛,翱翔藍天,不管這只鳳凰飛到哪里,永遠都是爐山的驕傲。時光倒流,幾百年前,這里還是荒漠之地,小鎮的規模,雞犬相聞就足以丈量出它的寬長。更多的人家,隱沒在濃密的山林中,阡陌小路,將人情與往來緊緊地連接在一起,也將這一方淳樸的風情融合在一起。金鳳凰從這里起飛,帶著山野的純樸和靈氣,同時,山的堅韌與傲骨與生俱來。這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所擁有的優秀品質,也是對這一群人的集體畫像,抱負遠大理想,學以致用,齊家治國。只不過,在封建統治的時代,禁錮了他飛翔的翅膀。有一天,這只金鳳凰又飛回來了,他棲息在這片土地上,再也不愿離開,借助這一方難得的寧靜與祥和,他將教育與哲學的光芒靜靜地釋放,回報著這里的鄉里鄉親,滋潤著這一方熱土。因為有他的引領,在這里積淀成一種地域文化——清平文化,影響至今。公元1584 年7 月25 日,夜晚,帶著壯志未酬的遺憾,他永遠閉上眼睛。他墳墓的前方,就是高聳云端的鳳凰山。
其實,他一直都沒有離開過我們,走在小鎮的大街小巷、郊外農村,到處都是他的影子。他捐修的宗伯橋依然橫跨在溪流之上,旁邊就是寬闊的公路,車水馬龍,但總會有人不時來到橋上,憑欄眺望,撫今追昔;摩崖石上,他題寫的“云晴天影闊,山靜水聲幽”已被水庫淹沒,我已經無法目睹這幅書法的蒼勁,但我站在水庫邊,口中默念著對聯中的文字,長久地沉浸在句中優美的意境和眼前如畫的景色中;他親手修建的學孔精舍、平旦草堂已不復存在,當年,他就在這里教書育人,每天,朗朗的讀書聲從這里響起,而此刻,我仿佛就端坐在教室里,聽他講解詩詞歌賦……
太陽偏西,云層時聚時散,光影時明時暗,像一首朦朧詩。他身居廟堂,看著日落西山的明王朝,看著層林盡染的茫茫群山,抑或是獨倚高樓,目光投向故土的方向,沉沉暮靄,鄉音阻隔,心生惆悵。他詩興大發,濁酒一杯,臨風低吟,將無盡的思緒寄予或鏗鏘或宛轉的詩句中。他是博學多識的大儒,同時,他也是一位多產的詩人,光一本《黔詩紀略》,就收錄了他的詩作457 首。我走進位于小鎮街邊的孫文恭公祠,祠內寂寥,我放輕沉重的腳步,生怕打擾他靜心的思考。在四合院露天處,只見爬滿青苔的地上,長著一簇碧綠的野草,圓圓的葉子向上伸展,迎接著屋頂那一小方天空灑下來的陽光,時序已是深秋,我詫異和敬佩它旺盛的生命力。我注視良久,陷入沉思,當我轉身離開,快要跨出大門的時候,猛然回頭,目光再次觸碰這些叫不出名的野草,斑駁的陽光下,它依然不事聲張地站立著,沒有挽留和歡送我的意思,平平淡淡,但真真切切。我突然發現,它就像從幽深歲月里凝結出的一首詩,一首飽含了人生況味和生活哲理的詩!
在小鎮里漫步,時常有穿越時空的感覺。鎮子不大,街面不寬,走著走著,仿佛就掉進了五百年前的時光里,尋著先哲的足跡,跟著他回家。或者,他就走在我前面,與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我加快腳步,但始終未能趕上,他永遠留給我一個模糊的背影。空氣中彌漫著水墨的氣息,甚至一磚一瓦,一花一草,都充滿了古典的寫意,如同想象的結果,或者說想象與現實交替呈現的結果。一座小鎮,一條小路,一位大儒,一人追尋,放在時空的畫面,便成為非常有意義的組合。這像是一場沒有終點的人生旅行,旅行的目的也是尋找,尋找心儀的風景,尋找心動的情節。而這一次,我來到再熟悉不過的小鎮,于司空見慣的山水間,尋找心底的答案。五百年前,王陽明跋山涉水,來到貴州,“龍場悟道”開創心學先宗,提出“知行合一”。他追隨先哲上下探索,成為其門下得意的弟子。我無法靠想象揣摩他當時的心境,只能沿著當年他走過的地方踽踽獨行,這里早已不是他走過的模樣,整潔的水泥路面清風微拂。但我又分明感覺到它仍是當年他走過的小路,他走過無數次的寧靜的小路、思考的小路、探尋的小路,時而沉重悲傷時而豁然開朗的小路,擁抱風霜雨雪與燦爛星空的小路。
2
飄飛的落葉,是不是紛至沓來的記憶?一條窄逼的小巷,一扇陳舊的木門,一幢低矮的木屋,這就是張畢來的故居。首先吸引我的,是門前圍墻邊那棵軀干遒勁的皂角樹,至少有上百年的歲數了,我猜想是張畢來親手種植的。它從石縫里挺拔而出,彎曲著身子,枝繁葉茂,垂掛著片片青色的皂角,像從歲月深處掉下的絮語。家境貧寒,小時候的他,趁讀書的空閑,幫著家人做些染布的粗細活路。皂角是天然的上好染料,每年秋天,他爬到樹上摘下彎彎的皂角,搗碎,取汁,浸染,晾干……整個染布的程序,他熟記于心。勞動錘煉意志,同時又帶來無窮的快樂。從事染布小本生意,需要一定數量的染料,那個時候,這一片山坡,一定栽種著很多皂角樹,樹林里晃動著他幼時的身影。我趕忙把目光投向木屋的周圍,試著去捕捉永恒的瞬間,但我看到的,全是高低不一的磚房,房屋與房屋的空隙,分割出大小不一的天空。
木屋很老了,兩層,屋檐上的瓦片,一樣的古樸蒼老,像是時鐘永遠停住。屋前窄小的水泥曬坪上,閃動著參觀的人影。故居一樓的木壁上,懸掛著他的半身黑白照片,白襯衣,花格領帶,西裝,雙手并攏,輕放在膝上,稀疏的頭發整齊地梳向后面,前額飽滿寬闊,戴一副眼鏡,面帶微笑。照片中的他,坐靠在一張椅子上,身子向前微傾,始終保持著大師一貫的謙虛風度。他就像坐在自家門前,曬著太陽,目視前方,一邊思考著學問,一邊歡迎著來者。對不起,門虛掩著,我沒有敲門,就擅自闖了進來,冒失地來到他面前,小學生般畢恭畢敬站著,接受他的教誨。他沒有怪罪我的失禮,而是用家鄉話招呼我進家,鄉音未改鬢毛衰。他十五歲離開家鄉,只身到省城貴陽求學,直到1991 年病逝北京,這期間,一共只回家三次,盡管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異地奔波,每次回家,他都操著純正的家鄉口音,與父老鄉親和兒時的伙伴擺龍門陣,一起吃腌肉和血豆腐,大伙都親切地叫他“張家的才子”。他學富五車,但故居卻是如此的簡陋寒磣,我走遍故居的每一間房屋,除了一些日常的家具擺設,再也沒有其他多余的東西。某種意義上說,治學就是一件簡陋的事情,往往占有得越少,擁有的就越多。我站在他的書房里,室內單純,室外豐富,陽光如洗。
迎著陽光,一心向黨,張畢來一生都在追求著光明。初到貴陽不久,他加入進步組織,閱讀進步書籍,創辦進步報刊,堅定地走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道路;哪怕是被捕入獄的艱難日子里,他依然百折不撓,信念堅定,一邊鬧革命,一邊做學問,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最終成為一位“一輩子搞政治的大學者”。在他的《回顧我走過來的道路》一文中,記述了小時候家鄉的落后和貧窮,這些,深深觸動著他幼小的心靈。在求學和革命的生涯里,他逐漸意識到,只有知識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他也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先進的理論和正確的道路,才能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和未來。
離開故居的時候,木屋靜默無語,又像是欲言又止,如一位老人端坐在那里,目送著我。圍墻邊的那棵皂角樹,果實累累,掛滿樹枝,此時,在我看來,仿佛就是張畢來辛勤耕耘的那些著作。青燈,多次點亮在他回憶的文章里,它是青澀、苦澀的代名詞,同時,也代表著永不言棄的執著。一盞青燈,寒窗苦讀,剪畫出少年時的他徜徉學海的身影,也映襯出故鄉的貧窮和家境的寒酸。如今,青燈早已被明亮的電燈所代替,更令人欣慰的是,他每一次回到故鄉,目睹這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更堅定了他心中的信念和理想。每一個人,只有將自己的命運,同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聯在一起,才是最絢麗的人生。
黃昏,小鎮的燈火依次亮了起來,今夜沒有月亮,但有幾顆星星閃爍在天幕,混合著人間的光亮,合力營造出如夢似幻的意境。歷史的與現實的,詩意的與生活的,在此刻,也共同釀造出一壇美酒,這正是小鎮純正的味道,也正是小鎮獨特的魅力。喝了這杯酒,就要和小鎮告別,我突然想起行程的最后一站,登上離城鎮不遠的石仙山,想起飄落地上的那些樹葉,是那么安詳地伏身大地,我站在它們中間,內心震撼,像進行著一場無聲的交流。這滿山遍野的落葉,正積蓄著自己所有的能量,愿化為泥土,靜候著下一個更美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