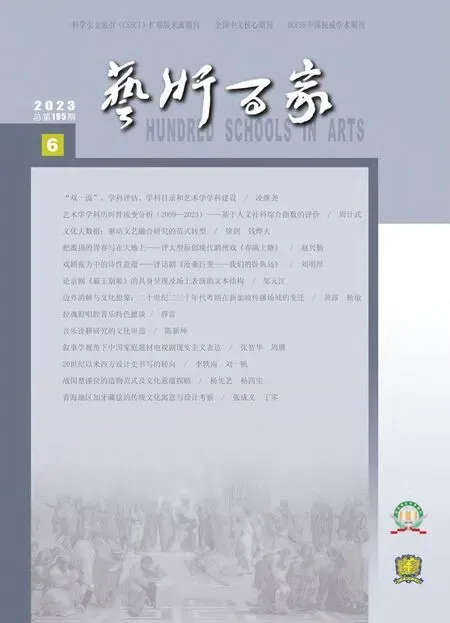明清桃源主題圖像的空間建構(gòu)*
孔 翎
(南京曉莊學(xué)院 美術(shù)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1171)
桃源圖像是明清時(shí)期的繪畫主題之一。桃源是中國文人結(jié)合民間傳說創(chuàng)造出來的仙境。關(guān)于桃源的傳說,主要有天臺桃源和武陵桃源兩種文本流傳。天臺桃源指向了一個(gè)典型的神仙山水空間,空間結(jié)構(gòu)與其他仙境區(qū)別并不大;而武陵桃源則指向了一個(gè)與田園村居融合的仙境空間,其空間結(jié)構(gòu)與景觀元素成為明清桃源主題圖像的典型特征。
一、文本中“桃源”的空間建構(gòu):文字的圖像化
桃源文本關(guān)于空間的描述具有視覺化特點(diǎn)。后世畫家根據(jù)文字塑造出具有典型特征的桃源圖像,并衍生出多樣的圖繪模式。石守謙在《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中歸納了中國桃源的四種圖繪模式:仙境山水圖繪模式、“人世化”桃源圖繪模式、古代風(fēng)俗圖繪模式、隱居山水圖繪模式。[1]32-50不同的圖繪模式從不同層面承續(xù)了桃源文本中的空間建構(gòu)。文本的流傳使得“桃源”成為語圖互補(bǔ)、具有典型性的繪畫主題。不同的文本在表達(dá)上也各有側(cè)重,給畫家提供了靈活開闊的創(chuàng)作空間。明清畫家在傳承中不斷豐富其內(nèi)涵,在文本基礎(chǔ)上用圖像語言建構(gòu)起不同結(jié)構(gòu)類型的空間,塑造出具有典型特征、不同意蘊(yùn)的桃源。
(一)天臺桃源的空間建構(gòu)
天臺桃源與“天臺二女”的神仙傳說有關(guān)。南朝劉義慶編錄的志怪小說《幽明錄》及北宋時(shí)的《太平廣記》都記載了劉晨、阮肇在天臺山采藥迷路遂遇見兩姝的傳奇經(jīng)歷,描繪了一個(gè)桃花流水的仙境。
天臺桃源延續(xù)了傳統(tǒng)的神仙山水模式,呈現(xiàn)出“高遠(yuǎn)”的縱深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在古人的觀念里,“仙”與“山”聯(lián)系緊密。“仚,人在山上貌,從人山。”[2]167“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3]152在早期文本記載中,神仙大多生活在遙不可及的崇山峻嶺中。《淮南子·地形訓(xùn)》:“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fēng)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fēng)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4]328可見神仙居于山的高處。因此,神仙山水模式大多采取了“高遠(yuǎn)”的縱深結(jié)構(gòu)。《幽明錄·劉晨阮肇篇》描述到,天臺桃源處于天臺山深處,那里有結(jié)滿果實(shí)的桃樹和流水大溪。文本詳細(xì)記錄了劉、阮二人進(jìn)入仙境的過程:“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再向內(nèi)“逆流二三里”,體現(xiàn)出天臺桃源空間的“高”與“深”。另外,仙境中女仙“其家銅瓦屋”,富麗堂皇。高聳不可及的深山和金碧輝煌的靈臺樓閣是神仙山水空間中的典型景觀元素。(表1)

表1 天臺桃源的空間建構(gòu)
明清桃源圖像有的借鑒了神仙山水模式,如仇英的《桃源仙境圖》,立軸幅式,畫面分上中下三段,青綠山水濃烈奇幻、云霧繚繞,華麗的宮殿點(diǎn)綴其間,渲染出仙境的氛圍。他的另一幅作品《玉洞仙源圖》與此十分相似,可見《桃源仙境圖》建構(gòu)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仙境空間。
(二)武陵桃源的空間建構(gòu)
武陵文本塑造了更為典型的桃花源,相關(guān)文本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并詩)》。“‘桃花源’是凝聚著傳統(tǒng)文人對于自由、和睦等向往的精神原型,但是陶淵明卻能以圖景式的表現(xiàn)方式將抽象的精神原型幻化為可視、可感的桃花源世界。”[5]240他賦予桃源異常樸實(shí)平淡的色彩,武陵桃源并不是縹緲不定、如海市蜃樓般的洞天仙窟,而是落地到現(xiàn)實(shí)世界。文本描繪了一個(gè)可以生活生產(chǎn)、自給自足的微型農(nóng)耕社會,較為清晰地描述出壺天模式的空間結(jié)構(gòu)。這個(gè)空間構(gòu)成“一個(gè)高度理想化的山間盆地景觀模式:一條長長的溪谷走廊,一個(gè)僅容一人蛇行的豁口和一個(gè)豁然開朗的洞天。這一‘走廊+豁口+盆地’的世外桃源為歷代文人墨客所尋訪、所追求”[6]46。至于古代傳統(tǒng)的仙境,著名的有昆侖仙境與蓬萊仙境,二者都指向遙不可及的隔絕模式。而壺天模式卻將仙境與現(xiàn)世通過小小的通道聯(lián)結(jié)起來,成為后世津津樂道的仙境模式。
武陵桃源的景觀元素有桃林、山口、漁船、田園等。“桃花”自古就是美好的文化意象,如《詩經(jīng)·周南·桃夭》中就以桃花象征家族繁榮:“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源以桃林為始建構(gòu)起興旺的農(nóng)耕社會;“山口”是武陵桃源的空間通道,它不同于天臺桃源,天臺桃源并沒有明顯的界限或通道;“漁船”是隱逸文化的典型代表,它與天臺桃源的神仙文化亦有所區(qū)別;“良田美池桑竹”則是武陵桃源中具有生活生產(chǎn)特征的典型景觀。(表2)

表2 武陵桃源的空間建構(gòu)
二、桃源空間建構(gòu)的視覺表達(dá):文本的圖像轉(zhuǎn)譯
天臺桃源是典型的神仙山水模式,典型場景元素有仙山、云霧、樓閣、桃樹等。空間的基本范式為云霧繚繞仙山,其間點(diǎn)綴靈臺樓閣。武陵桃源是田園隱居與仙境結(jié)合的空間模式,分為自然生態(tài)景觀和生活生產(chǎn)圖景兩大空間。明清桃源圖更多參照了武陵桃源。
(一)桃源圖像中的空間劃分
依托于文本,武陵桃源圖的空間主要劃分為“源外”“山口”“源內(nèi)”。“源外”桃林與“山口”側(cè)重于自然生態(tài)景觀。“源內(nèi)”又劃分為“田園”“仙境”空間模式,前者側(cè)重于生活生產(chǎn)圖景,著重表現(xiàn)田園農(nóng)耕生活,這是明清桃源主題的經(jīng)典圖式;后者援引傳統(tǒng)的神仙山水模式,比如靈臺樓閣在武陵仙境中的呈現(xiàn)。(圖1)

圖1 武陵桃源圖像中的空間劃分,筆者繪制
文本中的空間分類各有側(cè)重點(diǎn)。比如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對兩大空間的描述不分主次,而在《桃花源詩》中卻舍棄了對“桃花林”“山口”等景觀空間的描述,著重描繪了更為詳細(xì)的、順應(yīng)自然時(shí)節(jié)的源內(nèi)耕織生活,直接表達(dá)他對桃源的真實(shí)構(gòu)想——一個(gè)平凡的田園村居空間。除了陶淵明文本,王維的《桃源行》對桃源圖像的空間建構(gòu)影響也較大。《桃源行》取材于《桃花源記》,二者敘事內(nèi)容十分相似,但與陶淵明描繪的日常農(nóng)耕圖景不同,王維的整篇詩歌偏重于優(yōu)美景觀的描寫:“紅樹”“青溪”;由遠(yuǎn)及近的“云樹”“花竹”;以及“月明”時(shí)的松影、“房櫳”,“日出”時(shí)的云彩、“雞犬”。王維建構(gòu)的是有著絢麗視覺奇觀的“靈境”“仙源”,這為偏重自然景觀空間的桃源圖像提供了范式。(表3)

表3 “桃花源”空間分類的文本比較
桃源圖像除了具有完整敘事性的空間模式外,還有對空間元素的解構(gòu)與重塑模式。不同的空間側(cè)重點(diǎn)表現(xiàn)出不同的意趣:有的圖像偏重于表現(xiàn)綺麗的勝景,如清代王翚的《桃花漁艇》只截取了“桃花流水”的空間片段,明代項(xiàng)圣謨的《桃源圖卷》著重描繪了旋渦狀的奇幻山洞;有的圖像偏愛和樂融融的鄉(xiāng)村生活,如清代吳偉業(yè)的《桃源圖》重點(diǎn)描繪了星羅棋布的千里農(nóng)田。
(二)敘事場景的空間建構(gòu):《桃花源記》的圖像轉(zhuǎn)譯
《桃花源記》有著完整的空間敘事與場景建構(gòu),是創(chuàng)作明清桃源圖的藍(lán)本。“陶淵明詩文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出明顯的圖像與空間意識,例如,《桃花源記(并詩)》的文學(xué)語言在創(chuàng)造‘桃花源’世界中就超越了文學(xué)的表現(xiàn)常態(tài),模仿圖像符號的表現(xiàn)方式,形成了圖景式的表現(xiàn)狀態(tài)。”[5]240比如明代仇英的《桃源圖卷》(圖2),其圖像依據(jù)文本建構(gòu)出具有完整敘事性的桃源空間,可分為三大空間、五段場景(表4)。

圖2 〔明〕仇英《桃源圖卷》,33cm×472cm,美國波士頓藝術(shù)博物館藏

表4 《桃花源記》文本和圖像的場景空間建構(gòu)
圖像從右至左,在文本敘事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三大空間的分割,清晰劃出桃源的內(nèi)外空間:圖中自右至左,從兩株松樹開始到山洞口為空間①,即源洞前的空間。這段空間結(jié)構(gòu)清晰,上山下水,充分體現(xiàn)了桃花流水、山高水長的特點(diǎn)。漁人在這里發(fā)現(xiàn)并進(jìn)入桃源。空間②從“洞”開始,漁人穿過長長的山洞便進(jìn)入了桃源的內(nèi)空間。經(jīng)過這段隱秘的通道,畫面豁然開朗,出現(xiàn)了大片農(nóng)田,由此才真正進(jìn)入了空間②(桃花源內(nèi))。除了自然景觀和鄉(xiāng)村景觀,陶淵明還重點(diǎn)描繪了源內(nèi)居民的活動。這種日常安穩(wěn)的田園家居生活才是武陵桃源真正的魅力所在。空間③以最左邊的松樹、山路為界,界外就是源外空間,占整體畫幅的1/32。源外空間在畫幅中一般占幅較小,有的甚至省略。桃源圖像雖然依據(jù)文本建構(gòu)空間,但在圖像視覺呈現(xiàn)上具有自身的語言特點(diǎn)。(圖3)

圖3 〔明〕仇英《桃源圖卷》中的空間建構(gòu)圖,筆者繪制
三、“深”而“隱”:明清桃源圖像的空間特征

“隱”是桃源空間的另一特征。豐富的空間層次使得仙境愈加隱秘。首先,桃源的“隱”體現(xiàn)在壺天模式的空間建構(gòu)上;其次,空間上顯隱關(guān)系的處理使得圖像空間層次更加豐富,語言表達(dá)更具藝術(shù)性。
(一)“深”:桃源圖像空間層次的建構(gòu)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對空間層次的描述較為具體。他將桃源空間主要分為自然圖景、生活圖景與社會風(fēng)尚圖景[5]240,又“從遠(yuǎn)近、上下、內(nèi)外等空間構(gòu)成描繪出桃花源自然圖景的不同層次”[5]241。因此,明清畫家在建構(gòu)桃源圖的空間時(shí)將不同的層次加以疊加以凸顯空間的“深”。如明代周臣的立軸式《桃源圖》,縱向的畫幅中分為源內(nèi)、源外兩大空間,而畫家描繪的重點(diǎn)是源外空間,即空間①部分。空間①層次復(fù)雜:“溪”“桃花林”“山口”置于畫面下方1/6處,一塊斜置的巨型山體遮蔽住了“山口”,使得這里多出了一層空間。這樣的處理使得源外山口更為曲折幽深,猶如游走于中國園林里的假山石空間中;從圖像空間分割看,空間①又暗含多個(gè)“△”構(gòu)圖以進(jìn)行層次疊加——第一層次的“△”由三組松樹組成,第二層次的“△”由最前面帶有山洞的山體圍合而成,第三、四層次的“△”依次是后面的山體。(圖4、圖5)

圖4 〔明〕周臣《桃源圖》,161.5cm×102.5cm,蘇州市博物館藏(左);圖5 〔明〕周臣《桃源圖》的空間建構(gòu)圖,筆者繪制(右)
另外,圖像中山石與樹木“隱”與“現(xiàn)”的交替變化,也起著豐富空間層次的作用。比如仇英《桃源圖卷》中巨松的空間處理:松樹②、③組群與周圍山體一同將源內(nèi)圍合成盆地狀空間,源內(nèi)的松樹和其他樹木又進(jìn)一步將源內(nèi)空間分為三組小單元空間——依山處的三個(gè)村落,在壺天空間模式中疊加了“一池三山”的蓬萊空間模式。(圖2、圖3)在大空間層次中又層層分割小空間,空間多層次疊加凸顯桃源深深。
此外,“奧”“曠”的節(jié)奏變化使得空間張弛有度,給人適宜的審美體驗(yàn)。王維的《桃源行》對空間節(jié)奏的描述簡潔而清晰:“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從彎曲的山口進(jìn)入,沿著幽深曲折的水路行走,突然間豁然開朗,視線所及的是平闊的土地。“山口”與“山開”這兩處空間呈現(xiàn)出“隈”“隩”—“曠”“平”兩種截然不同的空間特點(diǎn)。如周臣《桃源圖》,前景幽深崎嶇的山口與后景空曠疏朗的田園在空間節(jié)奏上就形成了強(qiáng)烈對比。仇英《桃源圖卷》中,還以山的“遠(yuǎn)近”視角強(qiáng)化其空間節(jié)奏。畫面中的山有兩處與眾不同,第一處是山洞所在的山體,從“進(jìn)洞”到“出洞”,圖中展示了隔絕源內(nèi)外空間的巨大山體。仇英為了表現(xiàn)這處不同尋常的空間,從“洞”開始描繪,因此在視覺上就拉近了這段山體,它如一個(gè)巨大的屏障,頂天立地,嚴(yán)實(shí)地遮蔽了桃源世界;山體意象處理得格外崎嶇復(fù)雜,與入洞前具有程式化風(fēng)格的“△”山體形成了鮮明對比。第二處是最左邊空間③的山體,與第一處山體相同,其視線是拉近的,也是山的局部截?cái)?山體充斥于整個(gè)畫幅的上下空間。(圖2、圖3)從視覺感受上看,這兩處山體遮蔽并圍合源內(nèi)空間,將其在地理空間上隔絕出來,并在視覺心理感受上通過這兩處山體的逼仄彰顯源內(nèi)空間的疏朗。(表5)

表5 仇英《桃源圖卷》的空間層次建構(gòu)
桃源空間的“深”還伴隨著找尋的動態(tài)過程。“深”與“探”字同一字源,其甲骨文狀如一只大手在一個(gè)洞穴里探測深淺。“自山前而窺山后,謂之深遠(yuǎn)”,深遠(yuǎn)與高遠(yuǎn)、平遠(yuǎn)所體現(xiàn)的空間特點(diǎn)相異。“所謂‘高’,是由下而上的縱向體會,‘深’是由前而后的軸向體會,‘平’是由近及遠(yuǎn)的橫向體會。”[8]59“仰”“望”是山水畫“以大觀小”的觀察方法,有一定的距離感,而“窺”是一種視覺找尋活動,指“從小孔、縫隙或隱蔽處偷看”,空間上有遮蔽的意味,并伴隨找尋過程的時(shí)序。因此,觀眾觀看山水圖像是一種互動的過程。仇英《桃源圖卷》遵循《桃花源記》的完整敘事時(shí)間線,按照入源、出源的時(shí)間順序從右至左,觀者順著漁人的視線,分別經(jīng)歷了發(fā)現(xiàn)桃源、進(jìn)入桃源、源中見聞、離開桃源、桃源問津五個(gè)典型場景,圖像展示了完整的深入桃源的過程。
除了典型的空間時(shí)序外,有的圖像則采取了倒敘的手法。明代陸治的《桃花源圖》,按照手卷的觀看模式,其空間設(shè)置與敘事情節(jié)正好相反,畫幅的右手邊先出現(xiàn)的是平闊疏朗的源內(nèi)風(fēng)景,約占畫幅總空間的2/3;畫幅左邊1/3空間里安排了一個(gè)巨大的山洞。按照時(shí)間順序,觀者觀看時(shí)是由虛幻的桃花源回歸到現(xiàn)實(shí)世界。(圖6、圖7)這種空間建構(gòu)的逆向序列也出現(xiàn)在其他“桃花源”主題繪畫中,比如清代石濤的《桃源圖卷》等。無論時(shí)間順逆,桃源圖像都遵循空間敘事的邏輯。

圖6 〔明〕陸治《桃花源圖》,尺寸不詳
(二)“隱”:桃源圖像空間顯隱關(guān)系的表達(dá)
桃源是仙境空間。武陵桃源的空間結(jié)構(gòu)是帶有窺視性的壺天模式。《后漢書·方術(shù)傳下·費(fèi)長房》記載,集市上一賣藥老翁懸一壺于肆頭,每日市罷就跳入壺中,費(fèi)長房從樓上窺見其不同尋常,次日與老翁一起入壺游歷。這是一個(gè)不斷深入的窺視過程,在壺外看不見壺內(nèi)景觀,入壺方知壺內(nèi)另有乾坤。壺的內(nèi)外空間有著“顯”“隱”關(guān)系的對比。典型的桃源圖像亦重視表達(dá)空間的顯隱關(guān)系,如仇英、陸治、周臣、石濤等繪畫。
例如周臣的《桃源圖》,圖像中空間①部分如壺腔一般包裹住了低洼盆地般的空間②(源內(nèi)空間)。其屏障,即山體的空間層次處理得豐富復(fù)雜。除了密合的山體,三處松樹在空間層次安排上亦起著重要的遮蔽作用:松樹①遮住“山口”,松樹②③使得近處如屏障般的山體更加高聳。(圖4、圖5)周臣在空間處理上更加偏重表現(xiàn)壺天模式的屏障和入口,這里空間的“顯”使得整個(gè)著墨不多的源內(nèi)空間更加隱秘。源內(nèi)空間是平實(shí)普通的鄉(xiāng)村圖景,在畫面中占幅不大。
石濤的《桃源圖卷》在空間建構(gòu)上是橫向的壺天模式,共描繪了三個(gè)空間:源內(nèi)的田園空間;源外空間,“溪流”與“山”隔離了內(nèi)外空間;城內(nèi)空間,由“城門”和“城墻”作為空間隔離物。石濤《桃源圖卷》與陸治《桃花源圖》雖時(shí)空序列一致,但空間的顯隱關(guān)系卻不同:卷首空間①(源內(nèi))和卷尾空間③(城內(nèi))都采用虛化處理,從而凸顯了空間②——一段云煙繚繞的源外山水,約占畫幅的1/2。在空間②中最引人入勝的是前景處呈“U”形的兩座山峰擠壓并圍合起來的桃源入口,其宛如山口隧道,雖然沒有顯現(xiàn)的“山口”,但彎曲的溪道和一艘空船點(diǎn)明了桃源主題。(圖8、圖9)石濤《桃源圖卷》著重顯現(xiàn)壺天模式中的仙境通道(曲折悠長的溪水)和屏障(如山口的“U”形山峰),與其他表現(xiàn)該主題的繪畫相似,這里仍是用頂天立地、密不透風(fēng)的山體作為屏障以遮蔽源內(nèi)空間。

圖8 〔清〕石濤《桃源圖卷》,25cm×157.8cm,美國弗利爾美術(shù)館藏

圖9 〔清〕石濤《桃源圖卷》的空間建構(gòu)圖,筆者繪制
周臣《桃源圖》和石濤《桃源圖卷》在圖像的空間建構(gòu)上有著明顯的顯隱關(guān)系,都突出表現(xiàn)壺天空間中的屏障和入口。而仇英《桃源仙境圖》則塑造了完整的桃源空間,除了屏障和入口,他更為詳細(xì)地描繪了源內(nèi)空間。他將整個(gè)源內(nèi)山水在視線上推遠(yuǎn),而源外山水在視線上卻被拉近,視線上遠(yuǎn)近的區(qū)別,使得源內(nèi)空間更加虛幻隱秘,如盆景般嵌入整個(gè)桃源空間中,空間上的疏離感易于為觀者所感受到。
由宏大縹緲的昆侖、蓬萊模式,轉(zhuǎn)向空間小而層次豐富的壺天模式,這種空間建構(gòu)有其所遵循的規(guī)則。首先,無論是昆侖還是蓬萊模式都描繪遙不可及、難以掌控的景觀,而壺天模式的規(guī)模卻是可以掌控的。在仙境傳說中,壺隱喻仙境,壺腔的包裹狀也給人安全感。其次,壺天景觀空間是內(nèi)向含蓄的,是藏匿的、多層次的空間疊加,而非向外擴(kuò)張。這源于傳統(tǒng)中國農(nóng)耕文明天人合一、物我融合的思想。最后,壺天仙境與現(xiàn)實(shí)世界有著一定的、必要的聯(lián)結(jié)。壺天仙境之所以成為最吸引后世文人的空間,是因?yàn)槠渑c世俗聯(lián)系緊密,其空間底色是“深”而“隱”的。
四、結(jié)語
桃源是一個(gè)融合了日常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的仙境空間。從文本到圖像,從想象仙山幻境到向往田園之樂,桃源都是美好自然空間與和諧社會空間的交融。武陵桃源建構(gòu)了“深”而“隱”的壺天仙境空間模式,將田園村居的人世生活圖景移入仙境空間之中,形成了典型的桃源空間模式。明清桃源主題圖像延續(xù)了這種典型的空間模式,強(qiáng)調(diào)完美山水形象的人世化,關(guān)注人與自然空間的交融,從而建構(gòu)理想的人居空間。桃源意象在后世逐漸泛化,由仙境落地到田園,再轉(zhuǎn)向山水、進(jìn)入書齋,最后簡化為“桃花”意象,成為傳統(tǒng)文化中典型的空間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