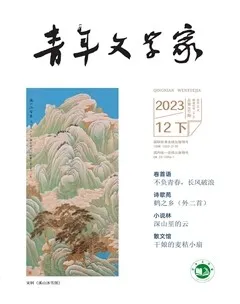一個一吃到糖糕就會想起的故事
欒奕
前段時間生病,我大半夜去了急診。診斷后,醫(yī)生跟我說要打幾天點(diǎn)滴。開完單子繳了費(fèi),我在注射室找了個靠角落的位子坐下后,護(hù)士走過來給我的靜脈扎上了針。由于發(fā)燒,此時的我頭痛欲裂,全身也像散了架一樣,因此整個打點(diǎn)滴的過程我都耷拉著腦袋,昏昏沉沉的,完全沒注意到點(diǎn)滴的藥物已經(jīng)滴完。坐在對面同樣在打點(diǎn)滴的一位中年大叔見我的血已經(jīng)反流到輸液管里,趕緊開口提醒我,并按響了護(hù)士鈴。拔完針我向他道謝后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的狀態(tài)好了不少,燒也退了,但還是按照醫(yī)囑繼續(xù)去打點(diǎn)滴。這次是在下午,穿過嘈雜的人群,我來到前一天的老位子,又看到了這位高高瘦瘦的大叔在打點(diǎn)滴。因為他一直都戴著口罩,我又有點(diǎn)兒臉盲,再加上前一天燒得厲害,所以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同一個人。正當(dāng)我猶疑之際,他也看到了我,跟我點(diǎn)了點(diǎn)頭,主動打起了招呼:“又來啦?”我也點(diǎn)了點(diǎn)頭回應(yīng),依舊坐在他的對面。可能是掛水的幾個小時漫長又枯燥,大叔開始跟我聊起了天兒,他說他是膽囊炎,已經(jīng)好幾天沒有進(jìn)食了,只能打營養(yǎng)液點(diǎn)滴。我好奇地問他會不會覺得餓。大叔笑了笑,說:“就是之前一直不讓肚子餓,現(xiàn)在只有餓著的份兒了。”我也跟著笑了。我們一來一回地閑聊著。原來眼前的這位大叔快六十歲了,明年就可以退休頤養(yǎng)天年了。另外,他還有一個跟我一般大的兒子。讓我意外的是,即使他戴著口罩看不清臉,但從他的穿著打扮和聲線來判斷也就四十幾歲的樣子。“老啦,不像你們年輕人,昨天看你還臉色蒼白的,今天已經(jīng)健步如飛了,不用我再提醒你拔針頭了吧。”大叔開著玩笑,他的言談很親和,但邏輯又異常清晰。大叔問了我的工作。我告訴他我喜歡收集不同人的故事,并把這些故事寫出來。他又笑了,說他必須是故事大王。在不知不覺中,我的點(diǎn)滴也結(jié)束了,而大叔還剩好幾袋。我向大叔打了個招呼,先行離開了醫(yī)院。
到了第三天,還是差不多的時間和同樣的位子,那個熟悉的身影依舊坐在那里。我笑著走過去,問道:“故事大王,今天能不能跟我透露一下啊?”于是很神奇的一幕發(fā)生了,醫(yī)院的急診注射室里,一個人用左手笨拙地操縱著手機(jī),記錄著另一個人的娓娓道來。
大叔姓何,祖籍是江蘇揚(yáng)州,家境普通,五六歲的時候跟父母來到上海定居,所以能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也算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了。他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受到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又是家中長子,大叔身上背負(fù)著父母殷切的期望。而他天資聰穎,憑借自己的努力,不負(fù)眾望地考入了名牌大學(xué),畢業(yè)后成了一名律師。
我本以為大叔會分享一些他工作上的奇聞逸事,但這個已近耳順之年的大叔注定不是普通的大叔。
“她是我的初戀。因為戶口遷移,就讀的學(xué)校也需要跟著變化,所以她高中第二年轉(zhuǎn)到了我們班。跟你們在電視劇里看到的那個年代的學(xué)生樣子差不多,女同學(xué)大多喜歡扎麻花辮兒,或者剪一個蘑菇頭,白襯衫,藍(lán)裙子,一雙圓頭黑皮鞋。”大叔不緊不慢地繼續(xù)說道,“雖然大家穿著類似的衣服,但見到她的第一眼,就是不一樣,很不一樣。她學(xué)習(xí)成績總體不錯,尤其是英語,聽說都很流利,甚至比我們的外文老師說得還要好聽,因為她的外婆是加拿大籍,總之就是‘歪瑞古德。”大叔冷不丁蹦出個上海口音的英語單詞,“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心動,也不知道當(dāng)下的感覺就是心動。我們那個年代雖然不是很封建閉塞,但異性同學(xué)之間還是保持著一定距離的,哪個男同學(xué)和女同學(xué)表現(xiàn)得親近些,在老師和家長眼里都是炸彈新聞。但她就是像有磁性一樣,讓我很想去靠近她、了解她。我想了很多方法,怎么才能跟她有正當(dāng)?shù)睦碛山咏恍医栌梦腋卑嚅L的私權(quán),在大掃除的時候和她分一個組。體育課的時候,我讓作為體育組長的‘死黨故意漏給她發(fā)球,我再單獨(dú)拿去給她。冬天上課很冷,我看她穿得不厚,就特地帶了一件我母親新做的棉大褂兒,跟她換她的外套,但又怕把她的衣服弄臟,我就小心地放在袋子里存好,自己被凍得跟過篩似的。她看到我這樣,把袋子里的衣服拿出來讓我披著。當(dāng)時是心理作用吧,我覺得她的衣服也挺暖和。”大叔說到這兒的時候笑了,他舉起手推了一下眼鏡,又挺了挺腰板,“你別小看我這件棉大褂兒,我母親是在服裝工廠工作的,做衣服是一把好手,用的都是最新、最好、最保暖的棉花,我看到她穿著這件厚厚的棉衣時,真的特別滿足,就是回去之后跟我母親說衣服丟了,被追著說了好久。”
我的腦海中浮現(xiàn)出一個男孩子被自己的母親咆哮的同時又滿心暗喜的樣子,不由得忍俊不禁。年少的我們,大多是在讀書的時候,會為了心儀的人,鼓足全部的勇氣,放下全部的身段,全心全力做盡各種不求回報的事情,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灌注到對方身上,“有情飲水飽”是真的會存在的一種狀態(tài)。不過那也僅局限于青春年少時,受到社會化的影響,成熟之后的感情不可能再那么純粹,人也不可避免地變得功利化,多了各種考量、對比和權(quán)衡,計較自己的付出與回報是否能夠大致平衡。我們想要的更多,卻吝嗇給予,或者是害怕,害怕輸了這些超出平衡之外的給予,害怕最后換不來想要的結(jié)果。
“一晃眼半個高二過去了,即使我使了各種小伎倆,我們的關(guān)系也就比普通同學(xué)熟悉點(diǎn)兒,我不知道她對我怎么想的,至少沒表現(xiàn)出多大的好感,也可能她一門心思都在準(zhǔn)備高考上吧,不過這倒真給了我一個大好機(jī)會。”護(hù)士走過來,給大叔的點(diǎn)滴的藥物換了一袋,大叔調(diào)了調(diào)點(diǎn)滴的速度,繼續(xù)開口道:
“那年恰逢高考第一次改革,大學(xué)的錄取率提高了不少,不像三四年前那會兒‘萬人過獨(dú)木橋。因為考的是全國卷,英語只占很少的分?jǐn)?shù),當(dāng)年工科又是熱門,大伙兒都憋著勁兒想去好的工科大學(xué),所以理科偏弱的她有點(diǎn)兒著急。數(shù)學(xué)和化學(xué)可是我的強(qiáng)項,經(jīng)常考年級前五,我就找了個機(jī)會跟她說,能不能互相幫助,她幫幫我英語,我教教她數(shù)學(xué)和化學(xué)。她幾乎沒考慮就同意了。我高興得一晚上沒睡著。第二天開始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們就會湊在一起講題,有時候晚上放學(xué)了也會約到她家附近的小餐館完成當(dāng)天的作業(yè)。我也因此更加努力地提高我自己的數(shù)學(xué)和化學(xué)水平,不能有她問我的題不會做啊,那多丟臉!另外,我會找一些英語的問題去問她,即便我有可能做出來。她跟我講的時候,我滿眼都是她,哪兒還有什么題啊。
“慢慢地,我們接觸多了變得熟悉起來,也會聊聊未來。她說她想考化工專業(yè),以后去做醫(yī)藥研發(fā)和制造,她聽外婆說國外的醫(yī)藥業(yè)非常發(fā)達(dá),但藥物進(jìn)口到國內(nèi)就很貴,她希望自己也能研發(fā)出大家用得起的國產(chǎn)好藥。說這些的時候,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滿著憧憬和期望。‘你呢?她轉(zhuǎn)頭問我,‘你之后想做什么呢?我頓了一頓,我真的很想告訴她,我想賺很多的錢,然后和她一起,陪她慢慢實現(xiàn)她的夢想。但我最終只是說,我想考清華。
“那近一年的時間是我高中最快樂的時光,每次和她的見面都如沐春風(fēng),我其實也是個很愛探索的人,我知道一些弄堂底、巷子尾好玩兒和好吃的地方。經(jīng)過我的數(shù)次邀請,她終于被我打動了。在一次放學(xué)后,我?guī)ツ鲜袇^(qū)城隍廟逛了很久,吃了豆沙圓子、赤豆桂花糕、芝麻餅。她很喜歡吃甜甜的東西。于是,我特地帶她去一家店吃糖糕,就是炸得金黃酥脆的糯米團(tuán)子外面裹一層糖粉的那個。她吃得很開心,她說她很少能吃到這樣的東西。我想再給她買幾個帶回家,而她拒絕了,跟我說‘要留一個想再次來這里的理由。那次以后,她幾乎每次都能欣然接受我的邀約。我們?nèi)チ撕芏嗟胤剑ネ獍锥蓸虼碉L(fēng),去人民郵電大樓買郵票,去東風(fēng)飯店大門前看卡車,去豫園商場新華書店淘書。她有好多次要主動付錢,都被我攔下了,怎么都不能讓女孩兒花錢啊,但我的家庭條件一般,零花錢很少,也不好伸手跟父母要。幸好那個時候鄰里之間都熟悉,我求著送光明鮮奶的爺叔好久,他才同意每天早上我家那一片的鮮奶由我負(fù)責(zé),送完之后給我點(diǎn)兒小報酬,另外我再去給隔壁菜市場里的賣菜攤主送送菜,也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外賣的鼻祖了,哈哈。
“我們第一次牽手,是在溜冰場上。那時候的溜冰就是四個輪子在平地上滾,她第一次穿上溜冰鞋,扶著邊上的圍欄像在蹣跚學(xué)步,沒一會兒就不小心摔了一跤。我趕緊去扶她。她自己反而先笑了,站起來說,‘真有趣,今天一定要學(xué)會。我不知道自己當(dāng)時哪兒來的勇氣上去牽住她的手,小聲和她說,‘我教你吧。她頭低了一下,沒有拒絕。就這樣,那天我牽著她,在那個溜冰場,從下午一直滑到了天黑。她真的很聰明,也很有勇氣,才半天的時間就能夠很好地保持平衡了,但我一直沒舍得松開手,即使我已經(jīng)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
“我們的頻繁接觸還是被老師發(fā)現(xiàn)了,家長被請來,和我們一起在辦公室里被很嚴(yán)肅地教育,雖然我自始至終都堅稱是我先找她尋求學(xué)習(xí)互助,試圖將她的責(zé)任撇清,也試圖解釋清楚我們接觸的最初目的。但我依舊從她父親的眼里看到了深深的敵意,他仿佛能看透我的心思一般,從頭到尾都皺著眉頭盯著我。我被他看得心里毛毛的,像真的做錯事那樣低下了頭。”
大叔說著的同時也低下了頭。我能清楚地感覺到他的情緒從飽滿到大幅回落。我沒有插話。過了一小會兒,大叔的聲音緩緩響起:“那次之后,每天放學(xué)她的父親都會來接她,如果見到我,就會用警惕又審視的眼光看我。老師也會特別關(guān)注我們。我知道她沒有在刻意躲我,但我也沒有再去找她,我不想再給她帶來麻煩。而且到這個時候為止,我也只能單方面確定自己的心意,卻一點(diǎn)兒也不了解她對我的想法。我也不知道我做錯了什么,讓她的父親如此不滿,可能在那個年代,早戀就是禁忌吧,即使也許只是單相思,也都是不被允許的。這個時候距離高考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了,我也被自己的父母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在復(fù)習(xí)中,我不得不先跟著洪流向前走。我想等到高考結(jié)束的時候,或許就能邁出等待兩年的這一步了。可就在快要高考的前一個月,有一天上課前她站在了老師身邊,老師說她三天之后即將要出國,去加拿大念大學(xué)。后面的話我已經(jīng)聽不清了,只覺得腦子嗡嗡的,像有幾百只蜜蜂在耳邊。我趁著體育課,把她拉到了器材室后面,我憋得滿臉通紅,卻又一點(diǎn)兒聲音都擠不出來。”大叔說到這里搖了搖頭,“她看我這樣子,走過來抱了我一下,‘我知道你喜歡我,我也喜歡你。她的聲音像驚雷一樣在我心里炸開。我看到她眼睛里有了一層薄霧,‘我爸爸在高中的時候就想讓我去奶奶那里念書,但我不愿意,我真的很喜歡上海,尤其是遇到你之后,我嘗試了好多之前沒嘗試的事物,但現(xiàn)在奶奶身體不太好,我必須去。我聽她說完這些,才終于理解老師口中說的‘女同學(xué)比男同學(xué)成熟得要早到底是什么意思,原來一直揣著心事的不止我一個人,對方早在比我更成熟的思維里糾結(jié)了更多次。三天后,她再也沒來學(xué)校了。她帶走了我送她的那件棉衣,把她的羽絨服留給了我。”我停下按鍵的手,抬起頭看著大叔。他的鏡片有點(diǎn)兒微微反光:“沒想到吧,難怪當(dāng)時我覺得她的這件衣服不厚但很暖和,我得意揚(yáng)揚(yáng)的厚棉衣,價格抵不上人家的一個袖子管。也不怪她父親一定要將她這個獨(dú)生女送出國,在那個年代,國外確實發(fā)達(dá)得多,而我是沒有可能跟她一起去的,這點(diǎn)我清楚,她更清楚。當(dāng)然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也不僅僅是家境上的懸殊。后來我上了大學(xué),她也如愿進(jìn)了醫(yī)學(xué)院。我們寫過信,打過電話。她說她真的很想念那時吃的糖糕,也從我口中驚嘆上海這些年的變化。我們心照不宣地沒有再提起過之前的情感。在若干年后,她在國外結(jié)婚生子,我也遇到了我現(xiàn)在的太太。”
“好了,故事就說到這兒。”大叔喝了口水,輕輕嘆了口氣。
我停下了飛快鍵入的左手,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么回應(yīng)。情感是最不受控制的東西,沒有辦法壓抑,沒有辦法強(qiáng)求,但情感面臨太多考驗,無法避開社會的洪流和家庭的旋渦,這些身不由己的緣由和不可控的距離導(dǎo)致的無可奈何都會造成遺憾,而有些遺憾是會陪伴著人生旅途好久好久的。
護(hù)士走過來給我拔了針頭,我壓著止血棉,直了直僵硬的后背,還是忍不住發(fā)問:“我怎么覺得您講的這些這么像現(xiàn)在的青春愛情片的劇情呢?”
大叔的眼角笑出了魚尾紋:“年輕的時候都會有錯過的人,錯過的事情,你當(dāng)下覺得懊悔,后來想想也還是覺得懊悔。”
“這都很正常,這是年輕的常態(tài),也是年輕的資本。”
“雖然懊悔,但是也不妨礙你接著往下走啊。”
“到了我這個年齡,只會對這些曾經(jīng)感到懷念和感激,感激所有這些錯過的人和事,感謝這些懊悔,它們豐富了我的生命,填滿了我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