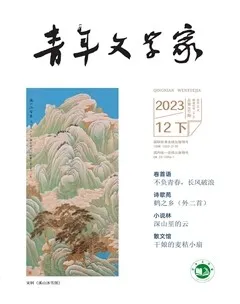向日葵
陳繼軍
現在的農村大概沒有人再種向日葵了吧?我一邊從紙袋里抓了一把葵花子嗑著,一邊在腦子里開起了小差。我的眼前仿佛又出現了那立于道路兩側筆直、粗壯的向日葵稈。眾所周知,向日葵是有著追尋太陽的特性的,可我從來沒有關注過這個問題,童年的我并非一個好學的孩子,正常的情況下,我的手里一定會拎著一根木棍,至于干什么,那就隨心所欲了,道路兩旁的花花草草、樹干樹枝,或是隨風飛舞的塑料袋,這些都是我瞄準的對象。
那天下午,家里來了一個不速之客,是村里的一個老大爺,屋子里的氣氛似乎有些尷尬。“那些葵花餅子都被砍掉了!”大爺心疼地說。我的心咯噔一下,腦袋里一片空白。父親抽著煙,陰沉著臉,沒有說話。雖然兩個人都沒有直視我,可幼小的我心里猜到這件事情大概與我有關!大爺看著我父親,目光有些游離。
我手里拎著一根小棒子,啪啪地敲著家里的泥地面。腦子里那一個個飛舞的葵花餅用極其陽光燦爛的面孔朝向空中,然后又無辜地重重摔向地面,一陣陣灰塵次第地揚起。大爺從我這里沒有得到答案,然后自言自語地說:“不過,你個小孩子,怎么能把那么高的葵花稈砍掉呢?對了,那是刀砍的,應該是個大人干的!”大爺又自顧自地罵了幾句,然后,向我父親打了個招呼:“搞錯了,搞錯了,這個孩子很老實的,我知道!”
父親從頭到尾沒有說過一句話。一場近在眼前的災難就這樣消弭于無形。那幾個向日葵花餅隕落的戰場,就在我家門口大路朝東不遠,我幾乎每天都要從那里經過,每次我都會閉著眼狂奔而過。可即使這樣,我也沒法兒把當時用鋒利的刀掠過向日葵花稈脖頸時的感受忘掉,反而越來越明顯,那種如六月里涼水過身的爽快,讓我對自己的暴虐產生一種強烈的憎恨和懷疑。
我把一顆葵花子的尖端放到牙齒中間,然后輕輕咬動,它的外殼頓時裂開,這個裂開不是整個地爆開,只是尖頭的那端裂開,是一種恰到好處的裂開,這個時候再用舌尖抵住尖端的裂口,利用舌頭的唾液的黏性把其中最美味的葵花子仁兒黏出來,用牙齒輕輕地磨碎,這個咀嚼過程是最美妙的時刻。這種美妙感受,我曾經有很多年無法觸及。我含著葵花子時,甚至會感受到一股濃烈的血腥味,不對,應該說是濃烈的草腥味。然后,我的腦子會一遍遍播放那個畫面,放到最后,場景越來越逼真,但也越來越模糊,我越來越懷疑那些向日葵花稈是不是我砍的。直到數十年后的一天,我才想通了,有沒有砍,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困住了自己。兒時的懦弱在當時救了我,但似乎也毀了我。經過剛才一番苦苦探尋,終于獲得了美味的葵花子仁兒,這種享用當然是幸福的,雖然葵花子仁兒非常細小,細小得掉到地上,你都沒辦法找得到,但這并不妨礙它的甘、香、脆。這固然有其本身的特點,但我一直認為在嘴里咀嚼的過程,充分調動嘴、舌、齒這些器官,讓它們進行默契地、高效地配合,這應當也是它美味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已記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何時重新獲得葵花子的原諒,讓我可以重新感受它的香脆,那種感受真的很美妙。
我家鄉的那種土壤叫沙土,這種土很松,沒有什么黏性,好像也沒有什么肥力,可以算得上貧瘠了,但是很奇怪,這種土適合種花生、向日葵。那條道路兩側長著無數的向日葵,它們曾經伴隨著我上學的路途,學校在我家東面,所以我每次行進的方向都是和向日葵是一致的,就像向日葵和太陽的方向永遠保持一致那般。那斑斕的色彩特別像家里被子上的圖案,那毛茸茸的葵花子密集地生長著,變幻著各種瑰麗的圖案。那個下午,一個小男孩兒在想和一棵向日葵親密接觸時,被蜜蜂給更親密地接觸了,極度的疼痛讓他揮起了刀,砍向一棵無辜的向日葵花餅。我在某一個不眠的夜晚,突然把所有事情連了起來。可那已經是很多年之后了,也就是那天起我又能用嘴巴感受葵花子噴香的洗禮了。可惜的是,不是鄰家大爺那年冬天送給我的葵花子了!
現在,農村到底還有沒有人種向日葵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