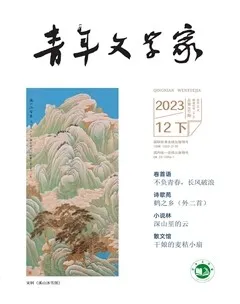冬日隨想
周文維
霜降過后,就意味著冬天要來了。秋日里,迷人的桂香已杳無蹤跡,桂樹下尚有發蔫的干干的花蕊,無聲無息包圍著母體,將自己徹底地交給大地。美人蕉雖耷拉著腦袋,葉片卻煥發活力,淺綠色的條紋清晰明凈,井然有序,不得不讓人感嘆大自然的魔力與造物主的恩賜。
深秋時分的“加拿大一枝黃花”(桔梗目菊科的植物,又名黃鶯、麒麟草)真是太招搖過市了,花兒坦蕩地開在末梢,一枝獨秀。然而,懂它的專家知道,它其實不受歡迎,因為它會破壞周圍植物的多樣性。斑茅已經長到了生命的盡頭,長而尖細的葉子如女人頭上的大波浪,風吹過,一浪一浪漾成漣漪,有時候也會觸及我們心底的故事—那個嘴里叼著白茅,外穿著的確良材質的藏青色西服,內襯著白色襯衫的青年哪兒去了呢?風兒輕輕,心事隱隱……
冬季的田野藏著無數的秘密,且不說收割了的立于蒼穹之下的草垛是如何靜默地想著它的前生今世,也不說藏匿于地下的某個角落冬眠的動物是怎樣度過寒冷的時節,就是一畦簡單的番薯地,也讓我們細數不清其間的秘密。掏番薯時,一鋤頭下去,卻見蚯蚓在地里兩頭打滾兒,然后迅猛翻身,很快又鉆回到黑暗的世界里去了。小時候,父親說,蚯蚓在的土壤,質地疏松。那新翻的濕潤的土地在父親的眼里無比珍貴,他會用鋤頭輕輕推開泥土,小心探尋,如果感覺觸及番薯了,就用鋤頭輕輕插入地下深處,然后果斷一撬。隨著父親額頭的頭發一抖一抖,一個個結實的番薯帶著泥土清新的氣息就躺在了大地上。
冬日里,燒灰積肥也是農村的一道風景線。農人在田野里和村舍旁收拾牛糞、豬糞、雜草等肥料,聚成一個土堆,土堆內部放上火種。不一會兒,煙霧就從土堆不同方向絲絲縷縷竄出。小時候,我的外公總是徘徊在煙堆旁,不時用木棒這邊捅捅,那邊戳戳。我上初中時,讀到“滿面塵灰煙火色”時,便覺得“賣炭翁”似乎就是我記憶中外公的樣子。而外公的形象也始終跟滿臉汗水、兩腳污泥、頭發凌亂聯系在一起。在這樣年年相似的冬日里,我又一次想起了曾給予我無限溫暖的外公!往事如昨,親情殷殷……
雪是冬天的標配。雪,凝固的水,可是你眼中晶瑩的淚,還是我心里靜靜的海?下雪的日子,置身于潔白的世界,冷峭和清冷包裹著我,滄桑感將要溢滿每一個細胞,這種感覺是莫名的。現在的南方,已經很難看到大雪了,于是,飄雪點點時,少男少女就會欣喜若狂,他們的童年跟我的童年相比,仿佛就是差一場大雪的距離。
冬日里,白天的鳥聲是零星的。鳥兒暗藏在樹梢間,偶爾發出一兩聲鳥鳴,深深呼喚,長長啼叫,似在感嘆光陰的荏苒,又如吶喊命運的無常。傍晚時分,遠處朦朧,近處迷離,側耳聆聽,初冬的田野又是一曲別樣的交響樂。天擦黑兒后,路燈也亮了,漏過樹縫,風兒晃動,落下的影子擾亂了我們的心。白天的忙碌、奔赴、喧囂都安靜了,只有微風拂動,蟲聲呢喃。地上的落葉隨風兒翻轉,颯颯作響。不遠處一只貓無聲無息跟我對視了一眼,我在想,從前我是你的主人嗎?我曾養了很多貓,可它們一個個都棄我而去。貓不似狗,它喜歡流浪。
我家的貓和狗曾經為爭地盤而出現了有趣的一幕。那是一個暖陽高照的冬日,貓兒名永福,渾身黑色;狗狗名小白,通體雪白。永福蹲在天井的墻頭,不斷甩著尾巴。在地上的狗狗小白見狀,一直對著永福狂吠。它用爪子不斷扒拉墻壁,挺直身子,繃緊尾巴,引頸向上挑釁永福。可是,永福自始至終不大搭理小白。陽光明媚,風輕云淡,它悠閑地瞇著眼睛,繼續享受日光浴。最后,小白力竭,悻悻然地回到狗屋,倦怠、傷心地偃臥著。如今,養大了四個兒女的永福已不知去向,小白也已換了另一種方式躺在了我的抽屜里,陪我日日夜夜。
歲月靜好,朝陽落日,春花秋月,夏風冬雪,一切都是最好的樣子。我們就悄悄地帶著微笑走進冬季,帶著回憶,帶著喜憂,一路前行。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冬天來了,春天也一定會接踵而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