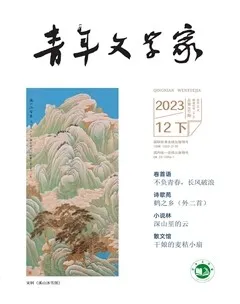陽羨詞派的余韻流響
張書杭
“陽羨詞派是清初變幻動蕩的歷史背景下聚合起來的一個既有著鮮明的政治傾向,又帶濃厚鄉土色調的詞派。”(嚴迪昌《清詞史》)嚴迪昌先生將陽羨詞派的基調概括為“郁勃奇崛、凄蒼清狂的‘商音”(嚴迪昌《清詞史》)。陽羨詞派活躍于清初詞壇,但在清中期依然余韻猶存。本文即以清代中期詞人儲秘書為例,在探究其詞作特點的同時,分析陽羨詞派在清中期的詞風特點。
一、落拓士人苦情詞
陽羨自古人文薈萃,至明代中后期于科舉中崛起眾多世家大族,如北渠吳氏、亳村陳氏、洑溪徐氏,以及蔣氏、史氏、萬氏、曹氏等。而其中尤以儲氏的科舉成績最為顯耀。憑借著出色的科舉成績,儲氏家學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儲欣所創立的“在陸草堂”享譽一時,不僅為族內弟子提供了良好的教育,也吸引了當地其他氏族的學子前來求學,為陽羨一地的文化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厚重的家學積淀產生優質的家族教育,儲氏各支在文學上造詣頗高,詩詞文各有所長,才人輩出,人各有集,尤以古文為擅。以儲欣為首的儲氏古文群從在當時產生了巨大影響。其家族中以詞聞世的主要有儲福宗、儲福觀、儲貞慶、儲國鈞、儲秘書等人。儲秘書即儲貞慶兄儲方慶的曾孫。學界習慣將儲氏詞人群分為兩代:第一代儲氏詞人以儲福宗、儲福觀、儲貞慶為代表,活躍于順治、康熙時期;第二代即以儲國鈞、儲秘書為代表,活躍于乾隆時期。下文即簡要探究儲秘書詞作的思想內容及藝術特點。
儲秘書(1718—1780),字玉函,江蘇宜興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曾任湖北鄖陽府和黃州知府,因事被免職。儲秘書博覽群書,詩詞造詣頗高,著有《緘石齋集》《過嶺集》。詞集則有《花嶼詞》,多創作于乾隆二十年(1755)之前。《全清詞》中收錄儲秘書詞作72首。
儲秘書43歲才得中進士,而后在知府任上又因事被免職。而詞作又多成于其37歲之前。因而,其落拓不遇的苦悶必然體現在其創作中。72首詞作中有31首言及“愁”字。其中固然有描寫閨中思婦之愁,但諸如“下帷愁對燭光搖。睡無聊,夢難招”(《江城子·漏聲》),“縱有閑愁萬斛,深燈畔、訴與誰聽”(《滿庭芳·寄懷位存、衎存武昌》),“貂裘容易脆,也共愁顏,客里暗消磨”(《渡江云》),“起舞燭光冷,顧影不勝愁”(《水調歌頭·謁東坡書院》)一類詞作不能不將之視為內心苦悶的抒發。“春山無限好,只是帶愁看”(《臨江仙·溪行》),想來他帶愁看的必不只春山。
儲秘書現存的72首詞作大致可按題材分為詠物、閨情、羈旅、友情幾類。茲分別予以簡要論述。
受浙西詞風的影響,雍正、乾隆時期的詞人多熱衷于創作詠物詞,儲秘書也深受詞壇風氣的浸染。在儲秘書的詠物內容中,除了諸如秋海棠、桂花、菊花、蠟梅等常見物象之外,還有不甚常見的如綠陰、漏聲等。儲秘書繼承了儲氏家族詞學中細膩幽深的筆觸,詠物生動有情致,亦常寓情于物,借詠物以抒己懷。試看《綺羅香·落葉》:
霜落千林,寒生萬木,斜日空山起舞。極望亭皋,一片紛飛秋暮。初飄墮、旅雁來時,漸驚斷、露蛩吟處。最憐他、吹到長安,競傳千載斷腸句。
天涯搖落如許。惆悵青青未幾,總歸塵土。不住秋聲,誰向風前細數。助離人、淚眼凄涼,稱孤客、閉門情緒。任蕭蕭、覆滿蒼苔,夜深和暗雨。
千林著霜,萬木生寒,詞人在開篇點明時令的同時也定下了全詞“寒”的基調。被擬人化的空山在詞人眼中似有起舞之勢,而斜日則暗示出此時已夕陽西下,更加深了凄清孤寂的氛圍。山中靜寂,唯有落葉紛飛,耳邊似響起陣陣秋風。望之所極,皆如此景。初、漸二句由落葉飄零點出時序漸漸轉入深秋,詞人的愁緒亦隨之加深。無論是離去的旅雁,抑或回蕩的蛩聲,都為秋日增添了一抹凄涼。寫滿詞人斷腸句的落葉飛入長安,也由此從寫落葉轉到寫人。以“千載斷腸”收束上片,令人心驚。下片以落葉喻人,“天涯搖落”的豈止是落葉,更是詞人自身。科舉屢試不中,人生前途未卜,“無邊落木蕭蕭下”之景讓羈旅漂泊的詞人產生深切的共鳴。而樹葉青綠未久,轉瞬即飄落于地,最終歸于塵土,一如詞人功業未立,而年華已逝。“助離人、淚眼凄涼,稱孤客、閉門情緒”,詞至結尾,一腔孤憤噴薄而出,已再難抑制。歇拍回歸現實之景,一個“任”字既體現出時序的轉換終非人力所能掌控,也表明詞人此刻心灰意冷之感,似有著自暴自棄的心態。其人生亦如凄風苦雨的秋夜般充滿了蕭瑟之感。
“平生蹤跡縱飄零”的羈旅之苦在儲秘書詞作中隨處可見。詞人常年漂泊異鄉,居無定所,雖時常會對自身境況產生不滿之心,卻又常懷對故鄉的思念之情,如“每到莼鱸時候,頓懷鄉國”(《石州慢·秋水》),“遙想故園花似霰,簾幕皆香”(《賣花聲》),“最恨濤聲徹夜,天涯歸夢難尋”(《風入松》)。在《臨江仙·都下寒食》中詞人寫道:
店舍無煙宮樹綠,匆匆過卻繁華。黃昏依舊薄寒加。不知花勝雪,惟有月籠沙。
千里鄉關凝望遠,羨他點點歸鴉。半床幽夢落天涯。夜如邊塞杳,門似亂峰遮。
繁華過眼,稍縱即逝,殘陽如舊,寒氣倍增。鄉關遠在千里之外,自己竟不如歸鴉有巢可依。心情的低落讓本就是個凄冷之日的寒食節更加寒氣逼人,“斗酒雙螯”的“故園風味”(《臺城路·位存招飲南樓》)不知何日再得的悲哀之情溢于言表。這種對故鄉的思念也常體現在其傷春悲秋之作中,如《風入松·榕城春感》《風入松·蕪城秋感》均為此類佳作。在此且引一首《風入松·蕪城秋感》:
淺深紅樹隔江晴。秋色淡蕪城。青衫恰似隋堤柳,著新寒、容易飄零。何處簫聲明月,青樓好夢無憑。
繁華過眼客心驚。難忘故園情。歸期曾約黃花候,惜花人、空護金鈴。待趁扁舟一葉,歲闌柏酒同傾。
“風入松”這個詞牌不甚常見,至清代已少有人作,即便有人創作,也難稱佳制。而這個詞牌在儲秘書的筆下尚有可觀之處。開篇兩句不僅點明時序乃初秋,“淡”字更可見出此詞起筆時的心緒尚屬平和,但緊接著詞人睹物傷情,從堤上之柳再次轉而感慨自身的飄零境遇。下片的一個“驚”字奠定了全詞基調,上片的淡淡愁緒至此成倍增加,“難忘故園情”更是直抒胸臆。昔日回鄉之約已然辜負。雖然并不知曉“扁舟一葉”何日可得,但無論如何還是要對未來抱有一絲期許的,同傾柏酒的美好愿景終會實現。整首詞的心境從平和至心驚,至嘆息,再至期許,波瀾起伏,頓挫有致。
羈旅漂泊與繁華易逝之感同樣彌漫在其贈友之作中。儲秘書有不少寫給位存的詞作,位存即其同鄉好友史承謙。史承謙(1707—1756),字位存,號蘭浦,著有《小眠齋詞》四卷,堪稱雍正、乾隆時期的詞壇名家之一。兩人頗多相互贈答之作,真摯友情顯而易見。面對友人,儲秘書自可敞開心扉,除去向史承謙傾訴內心苦痛外,儲秘書更是在詞中頻繁流露出隱居之意,如《臺城路·位存招飲南樓》:
秋光看到丹楓候,登臨盡成詩意。露白霜紅,山濃水澹,畫出小春天氣。流連未已。有斗酒雙螯,故園風味。硯北開尊,陶然共入醉鄉里。
當年偕隱有約,悔風塵浪跡,誤了生計。長鋏才歸,輕裝又去,終歲為歡能幾。危欄倦倚。剩一片清愁,蒼茫無際。歌罷新詞,月華煙外起。
上片寫景,縱覽故園好風光。更何況有酒,有蟹,有密友,陶然共醉,何其愜意!然下片轉而生出失落之感。曾經共同歸隱的約定終被風塵俗事所誤,終其一生又有幾載能夠盡享清歡。眼前的繁華也只不過是過眼云煙而已,終是只有清愁常伴我身。世網難逃,所謂的世外桃源只能心向往之,此身卻終不能至。以“月華煙外起”收束全篇,意境甚佳。
無論是身世飄零之感,抑或羈旅思鄉之情,萬般情緒一定要有所宣泄的。陽羨詞風向來以慷慨悲涼著稱,而儲秘書的《金縷曲·歲晚吳中作》足可視作陽羨余響的最好例證:
木落冰堅矣。悵無端、匆匆閱遍,蘇臺佳麗。可奈閑情消未盡,還趁吳姬酒肆。不道是、天涯游子。爆竹千門驚歲晚,漫飄蓬、倦擁舟中被。怎禁得,凄涼意。
金閶自是繁華地。最堪憐、薄游歸去,清愁無際。今夜關河風雪暗,誰念囊空裘敝。始信道、依人非計。廣廈萬間原不少,只古今、寒士何曾庇。空短盡,英雄氣。
萬間廣廈何時曾真正大庇天下寒士?這既是詞人自身境遇的真實寫照,也同樣將這一時期陽羨一地文人的凄涼狀況表露無遺。“囊空裘敝”的日子畢竟是“英雄氣短”最直接的誘因。
除卻凄清苦情的長調之作,儲秘書的小令則呈現出迥乎不同的面貌—節奏明快,自有清新之感,同樣頗有佳制。在此不加贅述,且以一闋《鷓鴣天》為例:
煮雪聲中夢乍還。水心亭子午陰間。橫鋪小簟當窗坐,愛看溟濛雨后山。
涼吹卷,濕云殘。晚晴天氣畫圖間。斜陽籬落疏花吐,一片秋光到石欄。
全詞靈動空明,幽靜淡雅的意境體現了儲氏家族細膩文風的傳承。
二、陽羨余韻有異調
自陽羨詞派接踵云間詞派,以敢于“拈大題目,出大意義”(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八)拉開清詞中興大幕后,陽羨當地許多世家大族群起而和。其中,儲氏家族功不可沒。第一代儲氏詞人大多親歷家國淪喪,山河易主之悲,加之其身世的坎坷沉淪,此等經歷化入詞作中,正與湖海樓主陳維崧所宣揚的悲慨之風同氣相和,足以稱為陽羨詞人群的中堅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儲氏家族還和陳維崧有親家關系。但從儲氏家族的詞風來看,即便在悲慨雄渾的陽羨之風席卷鄉邑時,儲氏詞人也遠不如陳維崧等人感情濃烈,洶涌澎湃。他們更傾向于抑制自己的情感,避免感情的宣泄過于猛烈。冷峻,或許是對儲氏詞風的最好概括。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清初山河易代的苦痛在人們心中漸漸淡去,整個社會也漸趨穩定,悲慨蒼茫的陽羨詞風逐漸被清空騷雅的浙西詞派所取代。于此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第二代儲氏詞人群,從題材的角度看,他們的詞作中缺少對國破家亡的抒寫和民生多艱的憤慨,因為朝代更迭之痛在其心底已然淡化。然而其詞風中仍保留有疏朗沉郁之氣。這一方面說明自蔣竹山一路沿襲至儲氏祖輩父執的悲涼之氣仍有殘存,而另一方面則源于詞人自身際遇的沉淪所引發的知識分子的苦寂。但正是因為這種苦痛多源于自身,因而詞作缺少磅礴的氣勢與時代的厚重感,局限于一己之悲的小我天地,終是與陳維崧論詞時所提出的“為經為史”(陳維崧《迦陵文集》卷三《詞選序》)一路漸行漸遠。
深究其源,儲氏家風對家族成員性格的影響不容忽視。陳維崧的祖父陳于廷向來以耿介著稱,而其父陳貞慧一生以義為重,行跡光明磊落,身列明末四公子,堪稱晚明清流殿軍。陳氏家族更是不缺少慨然就義的烈士。相比之下,儲氏族人則更具書生氣,或專研經義之學,或專注于家族教育事業,性格普遍偏于內斂。這種性格反映在詞作中,其風格自是較為含蓄。
再者,時間推移到歌舞升平的盛世時代,浙西詞風籠罩詞壇。陽羨后人雖不追隨浙西詞派,但對于同鄉前輩陳維崧的態度也頗為復雜。他們雖然敬佩這位詞壇巨匠,但其內心已逐漸傾向婉約一路。史承謙論詞強調多情才近,恪守婉約,尚法自然。儲國鈞也多秉持著風流婉約的創作原則,如《阮郎歸》訴相思之情:“昔年猶記寺門前,歌臺隔柳煙。幾絲香雨濕繁弦,催人歸畫船。”不少詞作溫婉有情致,頗得晏幾道精髓。儲秘書的閨情詞亦多此類之作,如同訴相思之情的《采桑子》:
匆匆燈夕愁中過,月浸簾衣。畫燭風凄。夢逐釵頭彩燕飛。
魚箋遞到香閨信,錦字親題。不說相思。只說梅花盼我歸。
總體來看,儲秘書詞作的核心特點為愁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舊保有陽羨詞風的峭拔與悲沉清蕭,但因其源頭乃是自身境遇的坎坷,而非家國淪喪之悲,故而少了幾分厚重。同時,因受到身邊史承謙、儲國鈞等人努力回歸“詞為小道”的婉約之風的影響,儲秘書的作品還有著幾許清麗淡雅之態,于悲慨之中又多了一絲溫婉蘊藉。可以說,史承謙帶領雍正、乾隆之際,宜興詞人群謹守詞之本色、追求天然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