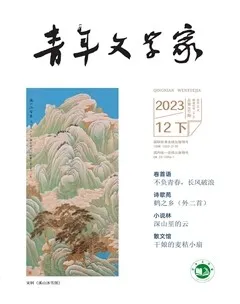志賀直哉《和解》中主人公與敘事主體的考察
周昕菀
《和解》是作者志賀直哉以自身與父親和解的經歷為原型完成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私小說”。小說從“去年”(1916年)7月31日作者第一個孩子夭折的一周年忌日開始,回顧了“前年”和“去年”年初與父親之間發生的幾次紛爭,到“今年”(1917年)8月30日與父親和解,并在9月中旬收到叔叔來信的故事。可以看出小說的作者,也就是小說的敘事主體,站在書寫小說的“現在”的時間點上,在特定章節內回顧過去的“我”和父親之間的矛盾,并觀察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我”和父親發生的幾次爭吵。因此,小說中存在著兩個主人公:回憶中的“我”,和觀察、記錄回憶中的“我”的現在的“我”。在第三章至第十章回憶的部分里,小說的主人公(回憶中的“我”)與敘事主體(現在的“我”)之間存在著時間差,有許多不同之處。因此,本文將集中考察因時間差產生的小說的主人公與敘事主體之間的差異,以及該差異在敘事主體與父親和解的過程中擁有著怎樣的作用。
一、《和解》中的時間線
如前文所述,小說中存在兩個“我”—即主人公(過去的“我”)和敘事主體(現在的“我”)。首先,小說中的主人公與敘事主體是怎樣連接的呢?二者又是如何出現在同一文本中的呢?這其實跟小說中的時間處理有著密切的聯系。以下是小說章節與對應時間和事件的整理:
第一章 ? ?7月31日? ??慧子逝世一周年;去東京;掃墓;探望祖母
第二章 ? ?8月15日? ? 完成《夢想家》小說寫作
8月16日? ? ? ? ? ? ? ?去東京;探望祖母;時隔兩年再見到父親
第三章 ? ?8月19日? ?決定為投稿十月的雜志,重寫《夢想家》
回? 憶 ? ?前年春天? ?拒絕在京都見父親
6月10月 ?秋? ? ? ??住在赤城住在我孫子市去東京;與父親發生沖突
第四章 ? ?去年6月? ?妻子去東京,生下慧子
7月上旬? ? ? ? ? ? ?妻子和慧子移居我孫子市
7月下旬? ? ? ? ? ? ? ? ??來到我孫子市的祖母一起去東京
7月30日? ? ? ??返回我孫子市
第五章? ? ? ? ? ? ?慧子生病
第六章 ? ?7月31日? ? ? ?慧子去世
第七章 ? ?8月1日? ? ? ? ?舉辦慧子的葬禮
第八章 ? ?8月20日? ? ? ?與妻子啟程出行
10月初? ? ? ? ? ? ?回到我孫子市
第八章 ? ?11月? ? ??妹妹分娩;與妻子去鐮倉
第九章 ? ?從鐮倉回來? ??妻子懷孕
今年2月? ? ? ?創作活動逐漸活躍
第十章 ? ?7月23日 ? ? ?女兒(留女子)出生
25或26日? ? ? ??去東京;祖母為嬰兒取名
第十一章? ? ?8月23日? ? 去東京; 祖母病重,放棄寫《夢想家》
第十二章? ? ?8月24日? ? ?放棄給父親寫信;再次決定創作《夢想家》
第十三章? ? ?8月30日? ? ?生母忌日; 去東京;與父親和解
第十四章? ? ? ? ? ? ? ? ? ? ??掃墓;回到我孫子市
第十五章? ? ?8月31日? ? ?父親和其他親人拜訪我孫子市
第十六章? ? ?9月1日? ? ? ?放棄繼續寫《夢想家》
9月2日? ? ? ? ? ?去東京;與家人共進晚餐
由上面的情節發展可以看出,小說中存在著兩條時間線:一條是敘事主體的“現在”的時間流逝,即從第一章的7月31日到結尾的9月2日,作者在創作這本小說的過程中,時間也在流逝;另一條是主人公的“過去”的時間變化,即站在“現在”時間點上,作者回憶的過去—從小說第三章的“前年”到第十章的“今年”7月23日留女子出生時的回憶。第十一章開頭寫道“現在,這已經是四星期以前的事了”,也證明了第十一章的時間正是“過去”時間的延伸,第十一章再次回到了“現在”的時間點。
基于上文整理出的時間線,我們得知:《和解》中的主人公與敘事主體存在著“過去”和“現在”的時間差。事實上,小說中“我”與父親“和解”的背后,隨著時間的推移,敘事主體相較于主人公,其對父親的感情也產生了變化。之后的章節將具體討論主人公、敘事主體對父親感情的具體變化和原因。
二、“我”對父親感情的變化
從文中第三章到第十章的回憶部分來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主人公(過去的“我”)對父親只抱有怨恨的情緒。尤其在第六章中,父親在主人公的大女兒慧子去世后拒絕將其棺材抬到麻布房,這讓主人公心頭“冒火”。在這種憤怒中,主人公想起了他曾多次想寫的一部講述他與父親之間分歧的長篇小說—《夢想家》。主人公描繪的《夢想家》結構如下:
某一個臉色陰沉的青年來訪問我。那時他正在松江報紙上發表一篇連載作品。我陸續讀著他寄來的報上連載物。內容寫的是他和他父親不和的事。可是不久,這連載作品突然中斷了。青年非常激動地到我這里來。據他說,作品上雖然用的是筆名,但他的父親卻看出來是他寫的,于是就從東京派了一個人來,買通報社不再登載這篇東西。
從此之后,青年和他父親之間就發生了種種不愉快的事。這一切我都用第三者的立場一一寫出。過后,青年已經有些自暴自棄了。他由于憤恨,跑去和父親吵鬧。父親因此絕對不準他再進家來。諸如此類,凡是在這種情形下可能發生的不快事件我都寫進去了。我的意思是把這些情景露骨地在小說里寫了出來,反而能夠防止實際上發生這一類事。我想這樣一寫,我們就不會照著所寫的那樣做了。在這篇小說的結尾,我又打算把祖母臨終時發生的悲劇作為最高潮寫出來。假定祖母要快死了,那青年不管怎樣禁止仍然闖進了父親的家。這時,青年的激動已經達到極點,便和他父親發生斗爭,多半是打架以上的粗暴的斗爭。
但創作《夢想家》這種以父子不和為主題的小說,無疑會讓其與父親的關系更加“雪上加霜”。《夢想家》在創作期間多次中斷,主人公分析自己中斷的原因:自己并不是非要與父親在未來的某一天和解,也并非顧慮同父親的關系會受到《夢想家》發表的影響,只是不希望“讓自己和祖母的關系成為小說創作的殉葬品”。也就是說,主人公雖然放棄了《夢想家》的創作,但歸根結底并不是因為顧慮自己與父親的關系,而是顧慮自己與祖母的關系。
而敘事主體在寫《和解》時評價道:“我在擬這個結構時,一面想象著這個場面,一面想下一個決定:究竟是父親殺死了兒子呢,或是兒子殺死了父親?可是突然間,出現在我心里的卻是斗爭到了最高點時,兩人忽然抱頭大哭起來了。這個突然而來的場面完全是我意想不到的,我滿眼含著淚了。”可以看出敘事主體盡管此時未與父親和解,但心中仍然感念父子之情,內心深處盼望父親與自己和解。而敘事主體隨著時間的變化和父親和解后,重新看待了《夢想家》一文:
我無意繼續創作以父子不和為題材的小說《夢想家》。我必須尋找其他素材。素材還是有一點的,可用心體味這些素材需要時間,而很多時候花了時間也未必做得到。這時如果勉強提筆,寫出來的也是沒有血肉的失敗之作。今天是九月一日,在十五六日之前,我能否交出令人滿意的稿子呢?
可以看出,敘事主體對《夢想家》這部小說創作也有其新的思考,他認為自己對父親的心境不再像《夢想家》中表現的那般偏激、自我,而是轉變為一種溫和、和解的態度。也就是說,敘事主體(現在的“我”)隨著時間的流逝,對父親的感情發生了一定的轉變—敘事主體從原先主人公想要寫《夢想家》卻因為顧慮祖母中斷多次,到想讓《夢想家》以父子兩人抱頭痛哭為結尾,不禁熱淚盈眶,再到其同父親和解后放棄創作《夢想家》。敘事主體對父親的感情變化也體現在了《夢想家》的寫作中。
此外,敘事主體相較于主人公,其對父親的感情變化也體現在其他方面。敘事主體來到東京老家時,卻回避與父親的見面,其內心也充滿了凄涼:
實際呢,在我的心里確是存在著私憤的。但是這當然不是我全部的感情。就是說在另一方面,又同時存在著我對父親的衷心同情。不但如此,十一余年前,父親曾經對別人說過:“從此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我都決不再為那東西流一滴眼淚了。”在父親說出這句話以前,我曾經對他表示了同種態度。一想到當時的情景,自己都不禁十分惶悚。過去究竟有多少做父親的人曾受過兒子這樣的對待呢?因此,當我聽見父親對別人說了這句話的時候,我覺得很難怪父親要這樣說的,我自己也感到凄涼。
從這一段中可以看出,敘事主體開始設身處地站在“父親”的立場上思考,反觀作為“兒子”的自己,他對父親不再只抱有“私憤”這一情感,而是漸漸開始抱有同情。
在第一章敘事主體與父親相處過程中,他分析自己的心情時,重復出現了五次“不愉快”一詞。在小說中,他無一不是對自己說的,都回避了對于父親的感情,如“一想到只因我和父親不愉快的關系,就連這點感情都得犧牲掉,真是無聊透了頂。祖母和母親對于這種事情有著顧慮,那是沒有辦法的。不過連我也跟著顧慮起來,實在太沒道理了。別的不說,一定要等父親出去之后,才偷偷地跑去看祖母,自己都覺得這樣子實在太丑,也太叫人生氣了”。
簡言之,在書寫小說的“現在”時間點,與其說敘事主體是對父親不滿,不如說他是對偷偷跑去看祖母的丑陋的自己的不滿,甚至對自己因為與父親意見不合而不能付諸行動感到憤怒。
敘事主體相較于主人公的情感變化還體現在他與父親的兩次對話中。在第三章中,主人公向父親講述了兩人在京都發生的不快:“那次京都的事很對不起您。現在我對您的感情已經改變得很多了。可是那時我那樣做,我到現在還是以為是對的。”此時,盡管主人公對父親產生了愧疚感,但他堅信兩人的爭吵并非主人公的錯,而是父親的問題,并且對父親隱隱含有一種埋怨情緒。而在第十三章中,在“現在”的時間點上,敘事主體對父親說:“以前的事是沒有辦法的了。我覺得很對不起父親。在某些方面是我的不是。”此時,敘事主體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完成自己作為兒子向父親的低頭。
如上所述,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父親的感情也在不斷變化。從第三章開始回憶過去到第十章回憶結束,第十一章回到現實的時間點再到第十三章與父親完成和解,中間經歷了“我”對父親的不滿,“私憤”逐漸轉變為對“丑陋的自己”的不滿,也開始嘗試站在父親的立場,反觀作為兒子的自己的所作所為,從而對父親抱有了同情心。從中也可以看出過去的主人公與站在現在時間點上的敘事主體之間對父親感情上的差別。敘事主體相較于過去的主人公對父親的感情變化無疑影響了自己在第十三章中與父親和解的決定。那么,為何敘事主體相較于主人公對父親的感情產生了變化,為何之前一直無法站在父親立場上思考的“我”能夠站在父親的立場上思考了呢?其中,敘事主體相較于主人公的兩個變化促成了其對父親感情的轉變。
首先,留女子出生時,敘事主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父親”。在第十章回憶過去的時間點里,留女子的平安降生,使敘事主體成為父親,他期待自己子女未來的樣子,這時的他開始站在父親的立場上進行思考。而這一立場的轉變也讓他在分析自己與父親的分歧時,能夠站在父親的角度思考自己作為兒子的行為是否妥當、得體。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他漸漸意識到:“過去究竟有多少做父親的人曾受過兒子這樣的對待呢?”他發現自己作為父親時,無法忍受孩子這樣的態度。
此外,祖母的身體也出現了不適。在第十一章,也就是在書寫小說的現在的時間點,祖母的“下巴掉下來了”,她變得不再像以前一樣有力和好勝,開始“像容易破損的東西一樣”,“我”開始意識到“我擔心的事情終于來臨了”。事實上,無論是主人公還是敘事主體,有一件事自始至終未曾改變:對“老家”的重視態度。例如,當“我”與父親和好后來到SK家時,“我”把自己的長途跋涉的疲勞比作了“像深山里給濃霧抱著的小湖水一樣,稍微有些頭昏的那種寧靜的疲勞,又像經過長途跋涉的不快的旅行之后,終于回到老家來的那種旅人的疲勞”。這里使用了“老家”而不是簡單的“家”這個詞,不是自己與妻子的位于我孫子市的家,而是強調了“我”對父親、祖母所在的老家的歸屬感。然而,這種對于老家歸屬感因親生母親的去世、與父親的不和,只能由自己和祖母的關系連結,但祖母病后,“我”開始擔心自己與老家的連結有一天會因祖母的去世而消失。在老家中,除了祖母之外,唯一與“我”有血緣關系的人就是“我”的父親。因此,祖母身體的變化逐漸使“我”不得不將這種歸屬感從祖母轉移到了父親身上,“我”開始期待能夠和父親和解,重新建立自己與老家的聯系。
因此,在敘事主體相較于主人公對父親的感情發生變化的背后,還有另外兩個變化:即敘事主體因為留女子的平安出生成了父親,開始站在父親的立場上思考子女的問題,以及祖母的身體變得虛弱,迫使“我”需要和父親和解,來確保自己與老家的緊密聯結,滿足自己對老家的歸屬感。這兩個變化影響了敘事主體對父親的感情。
以上,本文通過呈現小說中的兩條時間線,分析出了小說中的“我”存在敘事主體和主人公兩個不同身份,之后對比了敘事主體和主人公對父親的感情,發現敘事主體相較于主人公,對父親的感情隨著時間的流逝,也產生了一定變化。志賀直哉的代表作《和解》乍一看,小說在時間處理上給人一種“混亂”的感覺—從現在寫作的時間點開始寫起,中間陷入與父親矛盾分歧的回憶,隨著過去事件的講述完成又回到了現在的時間點,繼而再次與父親發生沖突、矛盾,直至和解。但事實上,它的結構又是一以貫之的:小說中敘事主體和主人公的同時存在體現了小說中“我”自身的變化,和“我”的變化對與父親和解這一事件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