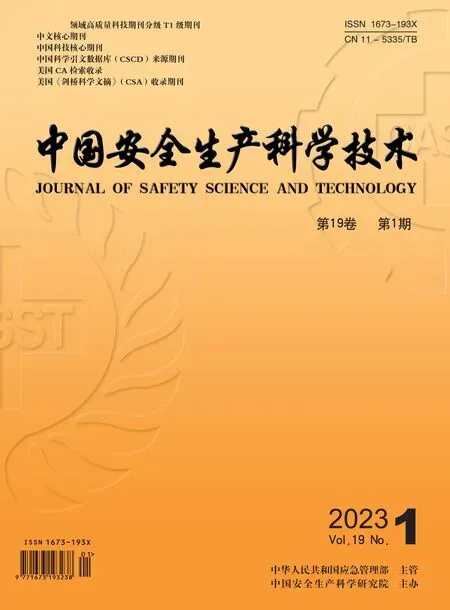基于數據挖掘的施工危險識別注意投入與分配研究*
張 帥,韓 豫,裴中玉,張涇杰,吳 晗,張夢月
(1.江蘇大學土木工程與力學學院,江蘇 鎮江 212013;2.江蘇大學城市環境與工程安全行為系統研究中心,江蘇 鎮江 212013;3.江蘇大學管理學院,江蘇 鎮江 212013)
0 引言
建筑業是事故頻發的高危行業,建筑施工現場復雜、動態特性,加重危險識別難度,導致安全事故發生。事故分析表明,當事人沒有對危險目標投入足夠的注意資源,未能準確識別危險是產生事故的重要原因[1],此外,工人在施工活動中首要任務是施工作業,而不是危險識別[2]。多重任務和干擾的不利作業環境,導致工人未關注到危險目標,進一步加劇對危險目標不合理的注意資源分配問題,并且傳統施工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顯因素層面,對內隱問題關注較少。因此,迫切需要進一步采用多學科交叉的先進手段揭示危險識別內隱特性,了解施工情境中危險識別注意資源動態分配規律,掌握工人對不同危險目標的注意投入偏好,協助工人更及時、有效地識別危險,從根本上減少事故數量。
危險識別在預防和減少事故發生中發揮基礎和先導作用,是行為安全研究中的重要主題,也是安全行為與認知心理學交叉領域研究重點。現有研究從認知負荷[3]、注意分心[4]、注意盲視[2]等角度分析危險識別等深層問題以及認知結果的差異[5]、特性、成因[6]和失誤識別[7],并證明提高對危險目標的注意有助于控制和調節施工失誤和不當操作[4]。目前,采用動態指標分析危險識別注意資源分配與投入變化研究較少,部分文獻從注視軌跡分析危險識別的視覺搜索策略[8]和不同年齡的視覺搜索差異[9]。但現有研究主要以危險識別靜態表征為主,未能揭示工人危險識別主動搜索行為中注意資源對目標的投入動態過程,缺乏從前期到后期注意投入目標傾向特征和時空分配變化規律研究,研究結果缺乏針對性,無法及時有效進行危險識別前攝引導。
因此,本文擬通過眼動試驗和數據挖掘相融合的新視角,以重心平均動態時間規整(DTW Barycenter Averaging,DBA)算法挖掘施工情境中注視軌跡序列,表征注意資源動態分配,利用k-means聚類和注視熵分析注意資源在施工情境中時空分配變化規律,并采用Needleman-Wunsch 全局序列對齊算法和統計方法分析工人注意資源對危險目標投入傾向差異。研究結果可為改善施工安全培訓、提高工人危險識別績效、優化注意資源分配、減少建筑事故等提供科學建議。
1 研究設計
注意資源分配蘊含在當事人對危險目標的主動識別搜索過程中,是對危險目標偏好和注意投入的體現,具有不易觀察的內隱特征。眼動追蹤試驗可以獲取當事人危險識別注視軌跡等眼動數據,反映危險識別注意資源投入變化規律、時空分布特征等信息。
1.1 眼動試驗方案
通過工地調查走訪,利用照相機廣泛采集588 張包含住建部通報的高處墜落、物體打擊、土方、基坑坍塌、機械傷害等典型事故原始狀態施工的照片,作者團隊經過初步篩選,剔除質量較差和不含危險目標的照片,得到有效照片297 張,經專家、施工現場安全人員和作者團隊討論,最終篩選確定20 張施工照片作為眼動試驗素材,包含腳手架踏空墜落、鋼筋機械加工和電焊作業等場景,以體現不同事故特征及施工階段。試驗采取非侵入方式追蹤眼球運動,能夠較大程度滿足被試在試驗中的自由度,設備頻率60 Hz,可在17 ms內自動測定被試對危險目標的刺激,獲取被試在施工情境中危險識別任務的注視軌跡序列。
為避免采用具有施工經驗、不同工種工人產生的認知慣性及思維定勢等帶來的危險目標偏好[10],研究選取55 名裸眼或矯正視力正常,無色盲、色弱等眼部疾病的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專業本科生和研究生作為被試,所有被試均要求專注于施工情境中的危險識別任務,以獲取完整的注視軌跡序列。
本文研究旨在探索當事人在危險識別過程中對不同危險目標特征的注意資源投入與分配時空變化規律。為方便后續注視點編碼和對比,以注視軌跡的完整性、危險目標的易識別性等條件篩選試驗數據,初步選取既包括機械傷害、高處墜落、觸電、坍塌等高危、頻發的典型施工場景,又滿足注視軌跡數據完整性等要求的3 張施工情境試驗素材數據。
根據情境中潛在危險目標數量、情境開放性等標準將其劃分為3 類復雜程度情境。例如在情境a中,危險目標主要包括機械切割傷害、材料堆放和工人等;在情境b 中,危險目標主要有腳手架踏空墜落、木板掉落失穩和工人等;在情境c中,危險目標由配電箱、混亂的電線、工人、堆放木板、工具等組成,危險目標數量多,情境復雜;考慮到情境a,b 危險數量相似,但情境b 為開放情境,干擾因素較多,比情境a復雜,因此,將3 張施工情境根據專家、施工經驗豐富的工人和作者團隊討論的危險目標數量、情境開放性等標準,按照復雜程度遞增順序劃分為施工情境a,b,c。研究以最終確定的3 張試驗素材的165 組序列數據為支撐,分析危險識別過程的注意投入和分配規律,如圖1所示。

圖1 眼動試驗素材Fig.1 Eye movement test mater ial
1.2 數據挖掘方法
眼動追蹤注視軌跡是當事人在危險刺激下,按時間先后順序產生的注視點連線,包含注意資源在時間和空間分配變化等信息,是表征危險識別注意資源動態投入變化的重要眼動心理指標。但集合中的每條序列長度不等,且其在時間軸上的特征可能是錯位的。針對時間序列集合,數據挖掘領域提出動態時間規整(Dynamic Time Warping,DTW)算法[11],用于比較長度分別為m,n的時間序列,即X=(x1,x2,…,xi,…,xm)和Y=(y1,y2,…,yj,…,yn)。DTW 算法主要包括以下2 個步驟:
1)根據2 個序列,構造m×n 的距離矩陣D,如式(1)所示:
式中:dij表示xi和yj之間的歐式距離;m,n 分別表示序列X,Y的長度;D為2 序列的距離矩陣。
2)利用動態規劃思想在D中尋找最優規整序列。為找到最優規整序列,定義規整序列W=(w1,w2,…,wk,…,wK),其中,序列中第k個元素wk=(i,j)k。為確保序列為全局最優、累計距離最小,如式(2)所示:
式中:d(wk)=d(xi,yj),表示在序列k處對應的i、j;K滿足max(m,n)≤K≤m+n-1;DTW(X,Y)即序列X,Y的DTW距離。
式(2)需要滿足邊界性、連續性和單調性3 個約束條件,即DTW 算法必須從d(1,1)到d(m,n)且不允許跨越匹配和交叉匹配,利用動態規劃方法求解DTW 距離如式(3)所示:
式中:i∈{1,2,…,m};j∈{1,2,…,n};D(0,0)=0,D(i,0)=D(0,j)=∞。
動態時間規整算法主要分為局部平均策略和全局平均策略,局部平均策略導致每次迭代獲取的平均序列長度變長,不利于后續分析,因此Petitjean 等[12]提出重心平均動態時間規整(DBA)算法,以全局平均策略計算時間序列集合的平均序列。該算法是期望最大化迭代算法,其目的是最小化平均序列到序列集T={T1,T2,…,Tn}的DTW距離平方和,即采用該序列作為該情境中危險識別注意序列,計算平均序列如式(4)所示:
式中:X為從序列集合中隨機選擇的初始化序列;Ti為序列集合除X外,從集合中隨機選擇的其他比對序列,由2 者計算更新生成新的X序列。
更新生成新的X序列主要包含2 個階段:1)隨機選取1 條時間序列X作為初始序列,計算每個單獨序列和該初始序列的DTW 距離,以便找到初始序列坐標和序列集坐標之間的關聯;2)將初始序列上的每個序列坐標與其關聯的序列坐標分為1 組,計算平均值,將該序列更新為初始序列。
2 數據處理與分析
2.1 注視軌跡序列聚類和注視熵分析
首先,將注視點跳出施工情境等不完整的注視軌跡剔除,構建完整的注視軌跡序列數據集。注視屏幕分辨率為1 680 ×1 050,眼動追蹤設備可以記錄被試群體的注視軌跡,以像素點的形式保存為坐標,通過Tobii Studio3.2.2 軟件導出。最終試驗施工情境分別導出51,49,47 條有效完整的危險識別注視軌跡,長度范圍為18~153。將序列數據采用DBA算法挖掘,獲取相應平均序列,經計算較低、中等和較高復雜程度施工情境中的注視軌跡序列長度分別為102,131,122,即該情境中注意資源動態投入和分配變化序列。
將數據挖掘得到的序列進行k-means聚類,分析注意資源在施工情境中空間分布特征,采用輪廓系數法(Silhouette Coefficient)確定最佳聚類值。對于任意樣本點xi,其輪廓系數定義如式(5)所示:
式中:a(i)為樣本點與同簇中其他樣本點的平均距離,稱為凝聚度;b(i)為樣本點到與它相鄰最近簇中所有樣本點平均距離的最小值,稱為分離度;S(i)為該點的輪廓系數,聚類效果總輪廓系數是所有樣本點輪廓系數的平均值,該系數介于0~1,數值越大,表示聚類效果越好。
輪廓系數對注視軌跡序列聚類評估情況如圖2所示,試驗選用較低、中等和較高復雜程度施工情境中最佳聚類值分別為3,3,9。不同復雜施工情境中,序列長度和最佳聚類個數呈現較大差異,如圖3所示。如中等復雜程度施工情境序列相對較高,復雜程度施工情境較長,但聚類個數較少,這表明當事人對不同聚類區域中的注意投入不均勻。采用最佳聚類值分別對注視軌跡序列進行聚類,以上三角符號標記為起點,下三角符號為終點,聚類中心以黑色原點為標記,如圖4所示。

圖2 聚類效果輪廓系數變化Fig.2 Change of contour coefficient of clustering effect

圖3 序列長度和最佳聚類個數Fig.3 Sequence length and optimal clustering

圖4 注視軌跡序列聚類Fig.4 Cluster map of gaze track sequence
為討論注意資源在不同區域的分配變化特性,引入“注視熵”的概念[9],注視熵是衡量注意資源在不同聚類區域轉移過程無序化的重要指標,能夠為分析當事人注意資源在施工情境空間分布變化的隨機性提供支撐。注視熵越高,相應注意分布空間范圍更廣、轉移變化隨機性更高。隨施工情境雜亂程度、危險目標數量等復雜性遞增,注視熵出現明顯上升,如圖5所示。這意味著在較復雜的施工情境中,當事人需要處理的危險目標較多,注視點在不同區域轉移變化,此時注意資源在不同區域之間轉移分配變化更加頻繁。注視熵計算如式(6)所示:

圖5 注視軌跡序列注視熵值Fig.5 Gaze entropy values of gaze track sequence
式中:X為總長度為n 的注視軌跡序列;(x,y)為其中某個注視點坐標;p(x,y)為該注視點所屬聚類區域的注視概率。
2.2 注視軌跡序列全局對比和統計分析
為比較分析當事人在不同施工情境中危險識別注意資源投入的目標傾向變化特征,根據施工情境中危險搜索結果,例如注視停留在墻面、木板過路等目標,即判定識別錯誤,編碼為W;停留在工人等低危險目標,編碼為L;停留在切割設備、電線或外凸鋼筋等高危目標,編碼為H,以此對挖掘到的注視軌跡序列逐一編碼。采用Needleman-Wunsch 算法對編碼序列進行全局對比[13],并按照時間順序將其等分為3 段,如圖6所示。根據編碼序列建立相似度矩陣,計算注視軌跡的相似性得分,計分規則為:匹配得1 分,不匹配和間隔空位時減1 分。得到相似度矩陣每個單元得分,利用回溯算法找出最佳共有編碼序列,從上到下分別為低中、低高、中高施工情境注視軌跡序列對比情況,相似度得分分別為58,45,81分。由圖6可知,不同復雜程度施工情境中,危險識別注視軌跡序列具有較高相似性,尤其是進入危險識別穩定階段,注視序列集中在施工情境中具有較高系數的危險目標和區域;結合時間序列觀察,在危險識別進入后期時,當事人注視點分布區域進一步擴大,對整個視野進行復查,注意資源重新分布在施工情境各區域中。

圖6 注視軌跡序列編碼對比Fig.6 Coding comparison of gaze track sequence
根據編碼后的序列,采用統計方法分析危險識別開始到結束動態過程中,當事人注意資源在不同危險目標上的投入傾向。相關眼動追蹤研究表明[14],大約10 次注視點后,會形成穩定的任務驅動注視軌跡。以前10個注視點為前期注意投入,最后15%的注視點作為后期注意投入,剩余中間部分為中期穩定注意投入,分別對試驗選取的較低、中等和較高復雜程度施工情境中注意資源投入到墻面等錯誤目標(W)、工人等低危險目標(L)和切割設備、電線等高危險目標(H)進行統計,結果如圖7所示。由圖7可知,在前期注意投入,當事人傾向將注意資源投入到施工情境中的顯著位置和目標;進入穩定識別階段后,注意資源傾向集中在施工情境中高危目標,例如在較高復雜程度情境中,中期穩定識別階段占比95%,而識別錯誤率僅為1%;在后期注意投入,注意資源傾向在不同區域進行切換,識別錯誤注視點較少,但后期識別錯誤率均超過20%,高于前期和中期識別錯誤。

圖7 注視軌跡序列過程變化Fig.7 Process change of gaze tr ack sequence
3 施工危險識別的注意資源投入與分配
3.1 危險識別中的注意資源在目標上的投入傾向
危險識別活動通常包括目標搜索和判斷過程。通過對危險識別注視軌跡序列編碼分析,危險識別準確率較高,這是因為在形成注視點之前,當事人會對施工情境進行掃視,繼而集中注意資源形成注視點,完成對危險目標的判斷和確認。注視點是危險目標辨識判斷的結果,視覺搜索主要通過掃視完成,不易形成注視點。由此可知,當事人在危險識別時,首先投入較少的注意資源進行掃視,完成對施工情境中較為直觀、危險系數較大的危險目標和區域的快速篩選,無法形成高注意資源消耗的注視點,具有自動化行為特征[15]。
此外,當事人在危險識別時,首先由自下而上的注意資源加工啟動,隨后被自上而下的注意機制驅動完成任務。經過對注視軌跡序列編碼并結合聚類圖分析,發現當事人首先將注意資源投入到顯著位置,即首次注視點主要位于施工情境中心位置,這表明危險識別任務啟動后,當事人易受施工情境中自下而上視覺顯著因素的無意識引導。經過大約10 個注視點進入危險識別穩定中期階段,當事人將注意資源投入到施工情境中切割設備、外凸鋼筋等高危目標,并形成較高危險目標的集中識別序列,相關研究也驗證在復雜施工情境中,注意資源受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更強[16]。進入危險識別后期,當事人注視點在不同聚類區域間出現較為頻繁的注意切換,重新檢查施工情境危險目標,導致危險錯誤率提高,例如在中等復雜情境中,后期錯誤率達40%,隨后結束危險識別任務。因此,在施工安全教育培訓中,應考慮當事人危險識別注意投入傾向特征對改善安全培訓的積極影響,規范施工現場生產秩序,減少來自現場雜亂物體的干擾,引導和強化2 種視覺注意加工機制融合識別,有助于提高當事人危險識別行為績效。
3.2 危險識別中注意資源空間分配變化
首先,當事人危險識別過程的注意資源隨施工情境復雜性增加呈均勻分配的空間特征。危險識別注視軌跡序列最佳聚類個數隨施工情境復雜性增加而增多,但最佳聚類值和序列長度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如圖3所示。危險識別注意資源分配與情境危險數量、雜亂等復雜危險目標區域密切相關,并直接表現為最佳聚類個數。在危險目標較多、區域分散的復雜施工情境中,危險目標聚類區域更多,但每個區域注視點較少,這可能與復雜施工情境中帶來的認知負荷有關[3],每個區域只能分配較少的注意資源,導致無法產生更多的注視點,注意資源更加均勻的分布在施工情境中,不利于重點識別施工情境中的危險目標。
此外,隨施工情境復雜增加,當事人危險識別注意資源在不同聚類區域之間分配變化更加頻繁無序。結合注視熵發現,在危險更多、秩序更為混亂的復雜情境中,注視熵更高,當事人的注意資源需要在不同聚類區域頻繁轉移變化識別更多的危險目標。這意味著注意資源分布更加分散,當事人環境意識更強,該情況與駕駛情境中危險識別特征較為相似[9],當事人需要不斷調整注意,擴大關注區域,以便在各區域進行切換,獲取更多危險信息;而在復雜性較低的情境中注視熵較低,當事人往往投入更多的注意資源在確定的區域檢查,注意資源分布較為集中。因此,在施工現場安全管理中,相對復雜的施工情境中應分配更多的注意資源,以提高危險識別績效。
4 結論
1)當事人危險識別各階段注意資源投入具有明顯的目標傾向差異,在自下而上的注意機制引導危險識別前期,當事人傾向于情境中顯著的位置和目標,進入穩定識別階段,由自上而下的注意驅動傾向集中在危險系數較高的目標。
2)當事人危險識別注意資源空間分配區域和情境危險目標、雜亂程度等復雜特征密切相關。隨施工危險目標、區域增多,注意資源在情境中分配更加零散、均勻,轉移變化更加頻繁,這不利于有效重點識別危險目標。
3)后續將借助虛擬現實、腦電試驗等開展更具情境化的危險識別研究,進一步探索注意資源在多重任務和干擾復雜情境下的投入和分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