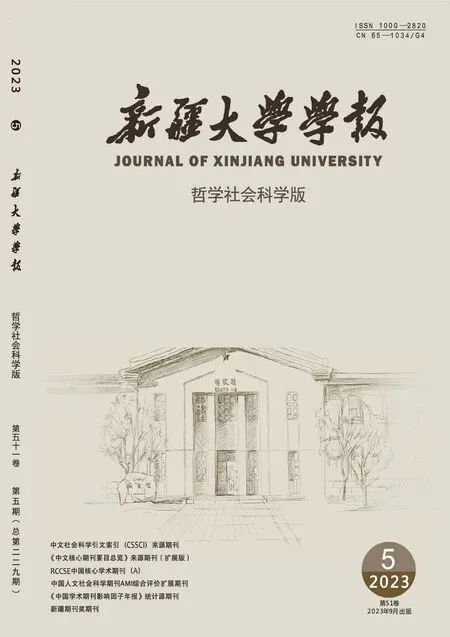新疆出土佉盧文書所見漢晉鄯善國習慣法研究*
韓樹偉
(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甘肅 蘭州 730071)
古鄯善非今鄯善。今鄯善在吐魯番市以東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是隸屬于吐魯番市的縣,漢代屬于車師前國,維吾爾語稱為“辟展”,①參見李志敏《“鄯善”縣名由來問題——兼校〈通典〉筆誤一則》,《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第31-35頁。清末新疆巡撫饒應祺在《會奏新疆增改府廳州縣各缺》中亦說辟展地為古鄯善國,以致光緒二十八年(1902)改辟展為鄯善縣。而古鄯善地處塔里木盆地東南緣,扼東西交通要沖,在中西關系史及西域史研究中頗負盛名,②近有學者結合文獻記載、考古材料和佉盧文文書檔案,探討了鄯善與中原之間的交流關系。參見吳昊、葉俊士、王思明《從〈宋云行紀〉路線看中原與西域的交流——以鄯善、左末城、末城為例》,《中國農史》,2018年第1期,第86-96頁。“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今若羌縣境內)”[1]3875,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命趙破奴“與輕騎七百余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2],漢昭帝元鳳四年(前77),大將軍霍光派遣傅介子殺樓蘭王,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1]3878,并應尉屠耆之請,派軍駐扎伊循進行屯田保護。③參見李炳泉《西漢西域伊循屯田考論》,《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1-9頁。鄯善國在極盛時期(公元1—3世紀)疆域囊括今羅布泊(有樓蘭遺址)、若羌(有米蘭遺址)、且末(唐播仙鎮)至民豐(有尼雅遺址、安迪爾遺址)在內的廣大地區,與塔里木盆地西南緣的于闐為鄰。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率輕騎兵臨鄯善城下,“執其王真達,與詣京師”[3]。三年后(448),北魏“以交趾公韓拔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鎮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4],至此,鄯善國歷史結束。
20 世紀初,外國探險家在新疆尼雅遺址等處發現大量的佉盧文簡牘,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佉盧文起源于古代犍陀羅,記錄于木牘、木簡、絲綢、錢幣、羊皮等載體上,內容有佛經、國王的敕令、官方與私人之間的信札、契約等,使用年代大致在漢晉時期,后來流行于中亞廣大地區,公元2—5 世紀被鄯善、于闐、龜茲等西域古國用來書寫公文、書信、宗教典籍、契約等,5世紀后,佉盧文因最后使用文字的鄯善國滅亡隨之成為死文字。④參見韓樹偉《絲路沿線出土佉盧文書研究述要》,《青海民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第96-106頁。經文字學家的釋讀,這些出土的佉盧文簡牘內容涉及古鄯善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經濟社會、政治法律等方面,使得這個古國的社會面貌逐步清晰起來。其中,一些國王敕諭、籍帳、信函為代表的法律判例文書以及其他契約經濟類文書,對研究漢晉時期鄯善國習慣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下面筆者依據《沙海古卷》《沙海古卷釋稿》《新疆出土佉盧文殘卷譯文集》等,擷取一些佉盧文書,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從環境保護法、牲畜使用與保護法、禁止公務人員身兼數職、王室政令不暢、女巫法、僧侶習慣法、收養子女須立契約等七個方面進行闡述,不足之處,祈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環境保護法
主要是以禁止樹木砍伐、水源管理保護為主,這與當時環境的變化有關系。對照時下河西走廊為例,這里屬于溫帶大陸性干旱氣候,祁連山部分地區生態環境遭到人為破壞,于是國家出臺一系列整改方案,加強對祁連山地區生態環境的保護。同樣,在古代塔里木盆地南緣氣候干旱,砍伐樹木似乎到了很嚴重的程度,尤其是對人居環境更為不利,為此鄯善王廷出臺政策,禁止人們砍伐樹木,違禁者根據不同情況罰馬一匹或者罰牛一頭。如佉盧文書482號①See〔英〕T.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0,p.94.漢譯文引自林梅村《沙海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1-122頁。:
封牘正面
致州長(勤軍和布伽)
底牘正面
1 威德宏大、偉大之國王陛下敕諭,致州長勤軍(?ama?ena)和布伽(Pu?o)諭令如下:
2 今有沙卡(?akā)向本廷起訴,牟利那(Molyina)已接受彼之領地上的土地。但是百戶長(?adavidas)和甲長(karscna?as)強占該地,不讓彼耕作。
3 彼等將該土地上的樹砍伐并出售。砍伐和出售別人的私有之物,殊不合法。當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牘時,
4 應即刻對此案及誓約、證人一起詳細審理,確認是否如此,應制止百戶長和甲長,
封牘背面
1 絕不能砍伐沙卡的樹木。原有法律規定,活著的樹木,禁止砍伐,砍伐者罰馬一匹。若砍伐樹杈
2 則應罰母牛一頭。依法作出判決。倘若并非如此,汝不能澄清此案,應將彼等
3 押送皇廷。
底牘背面
沙卡[5]121-122
從文書可知,砍伐和出售別人的私有之物,殊不合法,而百戶長和甲長砍伐并出售了沙卡土地上的樹,故屬于非法。類似這種保護私有財產的習慣法,在佉盧文簡牘中比比皆是,反映了塔里木盆地早期人們的私有財產保護觀念。同時,按照當時頒布的法律,即引文中加點“活著的樹木,禁止砍伐,砍伐者罰馬一匹。若砍伐樹杈則應罰母牛一頭”,顯然是百戶長和甲長依律賠償沙卡一匹馬。這份文書表明:當時已有禁止砍伐樹木的法律條文,而且有詳細的懲罰措施,即便是私人土地上的樹木,包含經濟樹種,都是不允許砍伐或出售的,否則按照法律處置。
鄯善國在禁止砍伐樹木外,還對水源管理方面采取了保護措施,像使用水的話需要交納水費(Kh.160)、記錄用水情況(Kh.72)或者用牛等作為酬金(Kh.157、Kh.639),嚴控水管員的任免(Kh.310、Kh.376)和玩忽職守(Kh.397),還有關于因無水使用借水的情況(Kh.347、Kh.368、Kh.502、Kh.604、Kh.722)。其中Kh.157 號文書提及到了在泉水邊要向賢善天神祭牛一頭,體現了對水神的虔誠。在塔里木盆地南緣綠洲地區,水資源是非常珍貴的,當地政府采取措施保護水源,進行有效的管理,是合情合理的。
二、牲畜使用與保護法
在綠洲地區,牲畜的用途非常廣泛,像駱駝、馬、牛、羊等,既作交通工具使用,又能負重馱運,還能作為肉飲、衣氈、皮靴等生活用品來源,同時還充當貨幣的功能進行交易,凡此種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為此,鄯善國禁止獵殺、傷害牲畜(Kh.13、Kh.78、Kh.156、Kh.262)。對于皇家或者私人牲畜,使用時需繳納租金(Kh.52、Kh.83、Kh.213、Kh.223),據Kh.83 號文書透露,橐駝之租金為八掌之白色布匹。不得強行占用牲畜(Kh.545、Kh.584),私有財產受到法律保護。如果牲畜在借用途中死亡,那么借用者要進行賠償(Kh.359、Kh.570);若牲畜逃往某處,則某人要歸還(Kh.685、Kh.686);若牲畜在另一人處死亡,則該人也要賠償(Kh.356)。如果委托馴養的牲畜死亡,那么負責馴養的人以同等價值的物品賠償,賠償物可以是一名女奴(Kh.578)。廄吏不得隨意私借(Kh.509)、出售(Kh.524)公家用馬、駱駝等,法律中明確規定“將他人私有之物借予別人,殊不合法”[5]126-127。使者、郵差出行使用的駱駝、馬匹由公家提供,牲畜的飼料亦由各州負責供應(Kh.214),若牲畜為公而亡,則由國家賠償(Kh.435),即“依原有國法,凡為國家服役的人或牲畜死亡,應由國家賠償”[5]114。
對侵占自己牲畜的行為,原主可以上訴。但是原屬于自己的牲畜被第二者侵占后轉手給第三者,那么這個時候牲畜不再屬于原主所有,如Kh.570號文書①See〔英〕T.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0.pp.113-114.漢譯文引自王廣智譯《新疆出土佉盧文殘卷譯文集》,載韓翔、王炳華、張臨華《尼雅考古資料》(內部刊物),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1988年,第247-248頁。:
此一有關舍羅犀那(?ara?ena)之牝駱駝一峰之文件,由蘇笈多(Su?uta)及蘇祗(Su?i)保存。此系ogus 達缽耶(?hapaya)及舍摩犀那(?ama?ena)之印。
茲于偉大國王、上天之子夷都伽·邁利(Ji?ugha Mairi)陛下在位之11 年2 月1 日,ogus 達缽耶及舍摩犀那。Kori 托伽阇(To?aja),cozbo芘摩犀那(Bimma?ena)審訊該案。蘇笈多及蘇祗提出關于駱駝一峰之控訴如下:此事之發生為,鳩缽蘇多(Kup?uta)曾強取舍羅犀那之駱駝一峰。彼因欠債又將該駱駝交給蘇笈多及蘇祗。該駱駝在蘇笈多及蘇祗處已有二年。后來,舍羅犀那從蘇笈多及蘇祗處將該駱駝牽走。彼使駱駝死于沙漠中。余等現作判決,應由舍羅犀那將同年齡之kirsosa 牝駱駝一峰交給蘇笈多及蘇祗收取,以代替該懷孕之牝駱駝。舍羅犀那有任何控訴,彼必須對鳩缽蘇多提出。該三歲之牝駱駝一峰必須付給。[6]
這是一份由蘇笈多及蘇祗保存的關于舍羅犀那賠償一峰牝駱駝的文書,時間是夷都伽·邁利(即馬希利王)在位之11年,根據學者研究,即西晉永興三年(306)。②參見乜小紅、陳國燦《對絲綢之路上佉盧文買賣契約的探討》,《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第71頁。從內容可知,牝駱駝的原主人是舍羅犀那,不久被鳩缽蘇多強取占為己有,后因鳩缽蘇多欠債,牝駱駝被鳩缽蘇抵押轉給第三者蘇笈多及蘇祗。兩年后,原主人舍羅犀那直接從第三者那里牽走牝駱駝,不幸的是牝駱駝死于沙漠。經法庭判決后,原主人舍羅犀那須向第三者蘇笈多及蘇祗賠償同齡牝駱駝一峰。由此可知,該牝駱駝已不再屬于原主人所有,且因原主人將該牝駱駝牽走并造成了死亡,故原主人須向第三者賠償同齡牝駱駝一峰。通過以上佉盧文書,說明牲畜在當時受到鄯善國的高度重視和保護。
三、禁止公務人員身兼數職
從相關的佉盧文書看,鄯善國禁止公務人員身兼數職,這可能與當時繁重的差役和負責重要的任務有關。有的是被類似監察人員發現某人身兼數職,如Kh.562 號指出一位叫鳩元格(Kuun?e)的騎都,本系四支軍隊的騎都,后被其長官派至皇家兼牧駝人,故皇廷諭令讓鳩元格交還橐駝,仍執行其騎都任務,不得再服國家任何差役。還有的是自己抱怨承擔差役過多(Kh.520、Kh.775),主動上訴請辭過兼職務,如Kh.430、Kh.439 兩份文書都提到了一位叫怖軍(Bimma?ena)的司稅,他一直掌管著一種叫作“Ku?ana”的稅,同時又是葉吠縣(Ya?ea?ana)的牧羊人,共身兼五職,于是上奏皇廷,當上級知道此事后,批示“殊不合法”,同意其不再擔任牧羊人,并將此職轉于其他未擔任何職務的人。
有一份文書比較特殊,是身兼數職的葉吠縣人怖軍揭發一位受雇于當地的精絕人伏斯彌伽。請看Kh.532號文書③See〔英〕T.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0,p.105.漢譯文引自林梅村《沙海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131-132 頁。亦可參見王廣智譯《新疆出土佉盧文殘卷譯文集》,載韓翔、王炳華、張臨華《尼雅考古資料》(內部刊物),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1988年,第243頁。:
封牘正面
致且渠僧茲耶、諸州長左摩和索達羅
底牘正面
1 威德宏大、偉大之國王陛下敕諭,致且渠僧茲耶、諸州長左摩和
2 索達羅諭令如下:今有司土兼判長怖軍(Bhimasena)上奏,葉吠縣領地有一人,
3 名伏斯彌伽(Vusmeka),靠其母之權利遷居葉吠縣。其實,彼系精絕(Ca?ota)人。4 彼自精絕逃出,受雇傭于葉吠縣。
封牘背面
1 但是,唯有葉吠縣人才能受雇傭于葉吠縣。彼等卻雇傭
2 此人,支付sikh 谷物作彼此之傭金。當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牘時,應即刻詳細審理此案,伏斯彌伽其人現
3 受雇于何處,應將彼和工錢及諸沙門一起交左施格耶(Ca??eya)。
4 若有爭執,送彼等至本廷。[5]131-132
從內容可知,外鄉男子屬于精絕人,是逃跑至葉吠縣的。他之所以能夠被雇傭到當地,是通過他母親的權力,不難推測葉吠縣可能是其母親的娘家,在塔里木盆地早期,婦女擁有自己的財產權,有相對獨立的經濟。①參見文俊紅、楊富學《佉盧文書所見鄯善國婦女土地問題辨析》,《石河子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第40-44頁。然而,當時葉吠縣流行的習慣法是只雇傭本地人,類似于今日的地方保護主義,為此伏斯彌伽被要求交還工錢,連同和他一起的工友被交至管理人員左施格耶那里接受處置。谷物作為傭金充當貨幣的功能,這在當時似乎很普遍,類似情況在其他佉盧文書中比較多見。
四、政令不暢
佉盧文簡牘中有很多法律文書,以國王敕諭、信函為主,記錄著諸多法律案例,從格式看,文書開頭皆使用一整套的敬語;從內容看,大多是某人像上級反映某事,然后上級下達命令或者指示。從表征而言,這種管理制度似乎是垂直的,但實質上這種管理體系非常松垮,甚至很多政令下達地方后,不被下級官員執行,導致很多案件被上級三番五次督促下級按照規定執行。
據不完全統計,有16 份法律文書就存在這樣的情況。從中可知,當時的政權并不是很穩定,地方官員尤其是認為“山高皇帝遠”的基層官員,通常有自己的一套制度,并未嚴格遵循上級的旨意,更未執行上級的指示。以Kh.144號文書為例②See〔英〕T.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0,p.26.漢譯文引自林梅村《沙海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67頁。亦可參見王廣智譯《新疆出土佉盧文殘卷譯文集》,載韓翔、王炳華、張臨華《尼雅考古資料》(內部刊物),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1988年,第199-200頁。:
底牘正面
1 威德宏大、偉大之國王陛下敕諭,致州長索阇伽(So?jaka)諭令如下:今有
2 司土黎貝耶(Lyipeya)上奏本廷,彼之奴仆,名迦左那(Kacana),遭索迦那(Sa?ana)毆打,于第八日被打死。
3 汝,州長索阇伽已接到過指令,
封牘正面
1 務必命證人起誓。如果迦左那確系為索迦那打死,須償還一人。汝對此事
2 竟然如此玩忽職守,迄今未作出任何決定。當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牘時,應立即命證人起誓。如果索迦
3 那毆打迦左那后,未作處理……以致死亡,也須償還一人。
4 汝若不明真相……寫于信內。[5]67
州長(主簿)③關于“Cozbo”,之前學者譯為“州長”,近段晴先生釋為“主簿”,可從。筆者認為兩種譯法皆表達的是一個主旨思想,類似于今日中國省、美國州、英國郡,而新疆綠洲“Cozbo”管理的地盤與權限,其實很有限,故“主簿”更貼近于中原王朝的文書表達。可參見段晴《公元三世紀末鄯善王國的職官變革》,載段晴、才洛太《青海藏醫藥文化博物館藏佉盧文尺牘》,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第37頁。索阇伽、司土黎貝耶在很多文書中多次出現。從該文書看,上訴者為司土黎貝耶,緣由是他的一名奴仆迦左那,被叫索迦那的人毆打致死。因州長索阇伽在處理此案時,沒有作出任何決定,導致原告將案件上訴到皇廷那里。故此,諭令中責備州長索阇伽“玩忽職守”,沒有及時妥善處理此案。由此可知,地方官員存有不盡責的現象。又從文書得知,毆打奴仆致死,按照當時的習慣法,毆打者索迦那須向原告黎貝耶賠償奴仆一人。上面這份“玩忽職守”的案例至多屬于地方官員不作為,還有一些案例是官員處置結果與上級相悖,如Kh.312號中提到“若皇廷以前曾作過判決,應維持原判,絕不可作出相反的判決”[5]92,言外之意即當時存有判決相反的情況。另有一些文書,反映了地方官員扣留稅收(Kh.307、Kh.387、Kh.714)、拖延繳納稅賦(Kh.358)甚至是不納稅(Kh.211)的現象。綜上可見,當時鄯善國存在政令不通的現象,地方官員之所以無所顧忌、“膽大包天”,可能是因為自有一套慣用的制度,逐漸形成不成文的辦事規矩即當地的習慣法。
五、女巫法
女巫,在古代中外的歷史中,一直神秘的存在。在三份佉盧文書中,有關于女巫(巫婆)的記錄,分別是Kh.58、Kh.63、Kh.248。其中,Kh.58 號文書提到:“1.彼等已將其殺死,第二次再未獲其他供詞。如果再未見到和聽到她的下落,如果……并非巫婆,人們必須賠償。2.該女子的身價并由布伽(Pu?o)和黎貝耶(Lyipeya)收訖。依法作出判決。布伽和黎貝耶還要收回彼等從她那兒所獲財物及其私有之物。”[5]60顯然,殺死一般女子是需要賠償的,但是巫婆除外,這說明巫婆是不同于一般女子的,是被當時社會所鄙夷與不認可的,故而殺死巫婆不需要賠償,這在側面反映了當時政府默許巫婆不能享有生命保障權。與這份文書內容相似的Kh.63 號文書①See〔英〕T.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0,pp.13-14.漢譯文引自林梅村《沙海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61 頁。亦可參見王廣智譯《新疆出土佉盧文殘卷譯文集》,載韓翔、王炳華、張臨華《尼雅考古資料》(內部刊物),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1988年,第192頁。,談到了婦女被搶走殺害的事實,可能是因為受三名巫婆牽連,內容如下:
封牘正面
致州長索阇伽(So?jaka)
底牘正面
1 威德宏大、偉大之國王陛下敕諭,致州長索阇伽諭令如下:今有
2 黎貝耶(Lyipeya)上奏本廷,彼等曾帶走三名巫婆,唯將屬彼所有之婦女殺死。其余均被釋放。關于此事,汝已從烏波格耶(Ap?eya)處接到指令,應賠償屬黎貝耶所有婦女之身價。當如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牘時,務必速對此案詳細審理,遵從州長汝從本皇廷得到的指令,務必依指令賠償屬于黎貝耶所有之婦女之身價,
封牘背面
并將彼等送押,送至本廷。
底牘背面
關于黎貝耶之巫婆……[5]61
對照Kh.58 號,我們發現Kh.63 號文書中三名巫婆被人帶走,其中屬于黎貝耶的女人被殺死,剩下的被釋放。案件上報到皇廷后,諭令賠償黎貝耶婦女之身價。如此一來,二份文書在內容上存有差異。其實不然,筆者認為應如此理解:巫婆在當時是不受待見的,可以逮捕,也可以被處死,嚴禁巫婆擾亂民心和破壞社會安定。Kh.63 號文書中被帶走的三名巫婆中,恰好有一位是隸屬于黎貝耶的,可能是因為被錯殺,所以要求賠償。筆者在其他三份文書中發現黎貝耶不止擁有一名婦女(Kh.20、Kh.29、Kh.53),這些婦女同樣遭到被搶走甚至毆打致傷的情況,由此推測,黎貝耶因擁有眾多婦女(可能含有女仆、巫婆),故遇到搜查巫婆的情況時,很容易招惹搜查者找上門來。而Kh.58號文書啟示我們,屬于黎貝耶的那位婦女去向未明,而且她究竟是否為巫婆,并不確定,所以導致案件撲朔迷離。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即該婦女若為巫婆,則必死無疑,更談不上賠償,因為只有非巫女者才被要求賠償,巫婆是不用賠償的,還會受到懲罰,這在Kh.248號文書中反映的尤為清晰:“(殘缺)應處罰并嚴禁女巫,務必現在即對其處罰并禁止(殘缺)。”[5]77-78
六、僧侶習慣法
在佉盧文書中,有大量的“沙門”記錄。②如Kh.69、Kh.113、Kh.130、Kh.152、Kh.164、Kh.203、Kh.265、Kh.288、Kh.358、Kh.385、Kh.386、Kh.399、Kh.473、Kh.474、Kh.475、Kh.491、Kh.492、Kh.494、Kh.502、Kh.504、Kh.519、Kh.552、Kh.553、Kh.546、Kh.564、Kh.599、Kh.603、Kh.606、Kh.621、Kh.646、Kh.706。據學者研究,“署名沙門某某者多達60 有余”[7],其實還不止此,像擁有財產(土地、牲畜、奴隸)、家庭的僧侶來說,自然在文書中赫赫有名,而對于被收養、奴役的僧侶而言,文書中很可能就以某代號書寫,加上其他各行各業的沙門,就不計其數。漢晉時期佛教在鄯善國非常流行,信眾普遍“以小乘為主,間以大乘,有信而無戒”[8],而且佛教世俗化,鄯善國的僧人可以娶妻生子、擁有養女,可以蓄奴,可置耕地、葡萄園等私產,并擅長交易,還可以飲酒食肉,同時積極從政、參與事務,跟當時的王權政治有較密切的互動。因學界已有相關研究,茲不贅。③參見陳世良《魏晉時代的鄯善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第79-90頁;夏雷鳴《從“浴佛”看印度佛教在鄯善國的嬗變》,《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45-52頁;《從佉盧文文書看鄯善國佛教的世俗化》,《新疆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第116-122頁;楊富學《鄯善國佛教戒律問題研究》,《吐魯番學研究》,2009年第1期,第59-76頁。
七、收養子女習慣法
據不完全統計,佉盧文書中有11 份收養子女的文書,有些是過繼給他人,有些是因為生活所迫賣給他人,還有的是作為奴仆身份賣給他人的。①參見李博《三至五世紀鄯善國收養問題研究——以新疆出土佉盧文文書為例》,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陳國燦《略論佉盧文契約中的人口買賣》,《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第46-50頁。從我們觸及的文書看,當從事收養行為時,雙方要簽訂契據,并且由當地執政官出面見證,結束后契據歸收養方單獨保存,可見這種行為是受到官府重視的,這種契據帶有官契的性質,目的是為了保護正常的子女收養行為,嚴防略人略賣人的現象發生。②參見韓樹偉《論清代的略人略賣人》,西寧:青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然而,當收養行為產生后,人口買賣的現象伴隨著出現,以收養子女為借口的人販子到處搜羅婦女和兒童并從事買賣交易,以黎貝耶為例,經他手的收養子女、人口買賣交易就有好幾例。類似黎貝耶這樣的人牙子,應該不在少數,因為他們在進行交易時可以從中牟利,比如“奶費”(撫養費)這樣的好處。請看Kh.39號文書③See〔英〕T.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0,pp.9-10.漢譯文引自林梅村《沙海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1-52頁。亦可參見王廣智譯《新疆出土佉盧文殘卷譯文集》,載韓翔、王炳華、張臨華《尼雅考古資料》(內部刊物),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1988年,第190頁。:
封牘正面
致州長勤軍和布伽
底牘正面
1 威德宏大、偉大之國王陛下敕諭,致州長勤軍和布伽諭令如下:今有
2 黎貝耶(Lyipeya)上奏本廷,彼等之婢女支彌伽(Cimilae)擅自將女兒送與迦波格耶(Kap?e)諸奴仆作養女。該養女
3 由彼等撫養成人,撫養費(The pay ment for milk)用亦未支付。當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牘時,務必親自對此案詳細審理。若其婢女確實
4 擅自作主,給迦波格耶一養女而未付撫養費用,
封牘背面
1 黎貝耶理應向迦波格耶諸奴仆索取三歲之牝騾一匹或三歲之牝馬一匹,而養女則完全為彼等所有。倘若再有何糾紛,
2 應依法作出判決。汝若不能澄清此案,應將彼等關押,送至本廷,在此再作裁決。
底牘背面
關于黎貝耶和迦波格耶之事。[5]51-52
由上可知,黎貝耶之奴婢支彌伽,未經主人允許,擅自將自己的女兒送給迦波格耶的一奴仆作養女,但是沒有收取撫養費,為此,黎貝耶將此事上奏官府。這筆撫養費,應理解為當主人的“財產”(即奴仆的女兒)轉與他人時,需要對方花錢來買。奴仆的子女依然是奴仆,身份沒有變化,仍然屬于主人的私有財產,受到王室法律保護,哪怕是支彌伽親身的女兒,也由不得支彌伽做主送與他人。從一些文書看,奴仆是可以用來贈送、交換、賞賜、買賣的,這種特征與中原奴婢制、古羅馬奴隸制如出一轍。④參見李天石《試論3—5 世紀鄯善王國奴隸制的幾個問題——兼與中原奴婢制、羅馬奴隸制比較》,《山西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第19-26頁。可見這種現象在當時是約定俗成的觀念,所以官府的最終處置結果是迦波格耶須向黎貝耶賠償一匹三歲的牝騾或者一匹三歲的牝馬。從賠償的對象看,養女跟一匹三歲牝馬/牝騾相差無幾,奴仆的地位何其低下,反映了當時鄯善國社會的性質和奴仆的身份特征。⑤參見楊富學、徐燁《鄯善國社會性質再議》,《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第84-89頁。有趣的是,我們在有同樣內容的Kh.45 號文書中發現Kh.39號的判決結果并未得到有效執行,因為Kh.45號文書中有王室諭令責備州長(主簿)的話語:“關于此事,曾再三給汝發出楔形泥封木牘,時至今日汝卻尚未作出決定。”[5]54如前所述,上級政令下達未得到執行,是常有之事,Kh.45 號文書顯然是下級沒有遵循上級的判決結果。總而言之,收養、過繼子女,需要付撫養費(“奶費”),而且要在官方證人的見證下,撫養雙方簽字立契,交給收養方單獨保存,官府也要備案,這種做法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正常的收養子女行為,嚴防人販子打著收養子女的旗號從事人口買賣的交易活動,側面反映了漢晉時期塔里木盆地南緣較高的社會管理狀況。
綜上所述,塔里木盆地南緣出土的佉盧文書,不論是在禁止樹木砍伐、水源管理,牲畜的使用、保護方面,還是禁止公務人員身兼數職、嚴禁女巫擾亂人心方面,或是王室政令不暢、佛教世俗化、收養子女需要立契等方面,都再現了漢晉時期鄯善國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習慣法,彌補了傳世文獻關于西域史尤其是古鄯善國的稀缺材料,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