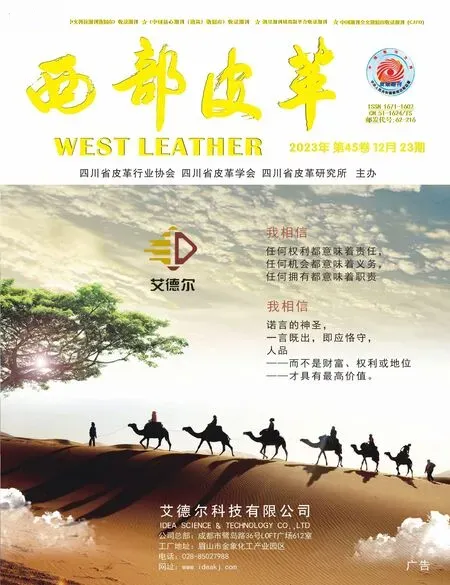美學視角下的中國披帛服飾內涵分析
李可
(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江西 南昌 330000)
0 引言
傳統披帛服飾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服飾文化的一角,其發展經歷了初興、過渡、定型三個主要時期;然而在如今中國大眾常服系統中,披帛這一服飾品類幾近消失。直至今日學界對其研究僅立足于歷史文化發展和具體形制角度是遠遠不夠的,認識分析披帛服飾的美學價值,不僅可以幫助設計者把握披帛這一服飾品類,在當前時代的設計要點,更有利于推動傳統服飾文化廣泛傳播。
1 中國披帛服飾研究概述
1.1 “披帛”服飾名詞解釋
肩背披搭帛巾,是我國古代唐朝至宋初時期,女性裝扮中常見的搭配方式;“披帛”這一詞匯,最早可考的文獻為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女人披帛”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畫披帛,至今然矣。至端午日,宮人相傳謂之奉圣巾亦曰續壽巾、續圣巾,蓋非參從見之服[1]。
關于“披帛”這一名詞的界定,存在多種看法。沈從文在著作中稱之為“披帛”[2];黃能馥、陳娟娟、孫機等則將其命名為“帔帛”,這兩種稱謂方式對后來的研究學者影響也最為深遠。又如王曉莉《談乾陵唐墓壁畫線刻畫仕女人物的披帛》、趙敏《敦煌莫高窟菩薩披帛及隋唐五代世俗女性披帛研究》等均稱其為“披帛”,而馬希哲《中國中古時期帔帛的文化史考察》則稱之為“帔帛”。此外,為防止混淆,葉嬌經對比在其文中對“披帛”“帔子”“領巾”等服飾詞匯,從文學角度出發做出了研究并加以區分,指出雖然它們大體形制相似,但實際用途及具體形制上又有區別[3]。宋丙玲則通過研究北朝圖像藝術以及文字記載,對“領帶”“帔”“領巾”等詞匯進行分析,指出它們之間的聯系與區別,更指出它們是受不同文化所影響[4],筆者在研究披帛服飾美學內涵之時,主要描述分析對象為以披掛裝飾作用為主,造型相對長且窄的披帛服飾品,且關注其總體共性,具體分析蘊含其中的傳統美學文化內涵。
1.2 傳統披帛服飾的起源
披帛服飾品類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進程中存在時間雖長,然而具體可考的實物極少,關于其起源,也存在諸多不同看法。明代著作《三才圖會》中記載:“《實錄》曰:‘三代無帔說。秦有披帛,以縑帛為之。漢即以羅。晉永嘉中,制縫暈帔子,是披帛始于秦,帔始于晉。’唐令三妃以下通服之。士庶女子在室搭披帛,出適披帔子,以別出處之義。宋代帔有三等,霞帔非恩賜不得服,惟婦人命服,而直帔直通民間也。”將中國披帛服飾的最早起源追溯到了秦漢時期;孫機認為宋代霞帔的前身是唐代的帔帛,是“佛教藝術通過中亞東傳時帶來了這種風習的影響”[5];黃能馥、陳娟娟則認為“帔帛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西亞文化,與中國當時服裝發展的內因相結合而流行開來的一種‘時世妝’的形式”[6]。
披帛服飾在中國的大量出現,可考于公元3 世紀上半葉,就開始建造的新疆克孜爾石窟壁畫,壁畫上描繪的菩薩、力士等形象就多以此類披掛布帛作裝扮;在印度地區,佛教產生之前,披帛就已經出現在雕刻藝術作品之中,而中國佛像的制作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古代印度的藝術方式[7]。受制于實物史料,起源于秦漢時期這一觀點還有待研究予以佐證,而在中國隋唐墓室、佛教壁畫以及文學繪畫作品中披帛服飾大量可見。由此筆者認為,披帛這一服飾品的服用習慣在中國服飾文化發展進程之中由來已久,但其能夠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品類并在中國古代世俗中流傳開來,卻與佛教在中華大地的傳播密不可分。
1.3 傳統披帛服飾的發展
根據文物資料顯示,在中國古代早期流傳的佛教圖像中關于人物形象的藝術呈現多為半裸體,披帛是他們身上非常顯著的服飾裝飾物件。隨著北魏時期,佛教佛像雕刻藝術在發展過程中逐漸逐漸中國化,其中關于人物形象著裝的描繪,也開始顯現出與中華民族傳統服飾相融合的面貌,隨著佛教在中國日益興盛,披帛服飾形象亦開始成為世俗婦女穿著模仿的對象,于南北朝時就開始大量出現在世俗婦女著裝中,到隋唐時期則在各階層婦女著裝上大為興盛,具體可參考《搗練圖》《步輦圖》等傳世畫作;宋代之后,披帛更是進入了朝服系統,分化出了具有封建禮制象征意義的形制——“霞帔”,作為皇后及命婦的專有服飾之一為中國傳統服飾歷史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影響至今。由此分析,筆者認為,披帛這一服飾形制在中國由來已久,而佛教文化影響的擴大化,則是披帛服飾在古代中國流行發展歷程中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同印度佛教披帛服飾相比,中國傳統披帛服飾在漫長的時間洪流之中經歷發展,在造型樣式以及穿戴方式等方面同樣走向了兩條風格各異的演化路徑;傳統服飾視域中的披帛服飾如今在民眾的日常服用習慣中幾乎消失,其服用主體主要為漢服愛好者,除此之外幾乎只在戲劇影視服裝和中式婚服上有跡可循外,并不多見于其他場合,與其形制相似的長圍巾或方巾,則因為實用功能十分突出,而在現代社會中廣泛流行。
2 披帛服飾產品市場現狀
目前,披帛類服飾產品的設計開發還面臨著諸多制約,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從實用角度來看,傳統披帛在形制規格上長度過長,或在部分國人認知中已然形成了不實用的主觀印象;其次,當今中國人日常穿著的服裝,無論是審美習慣、生產的工藝、技術手段、設計元素或流行風格,都受現代西方服飾文化影響深遠,而披帛作為蘊含著多重中國傳統美學文化內核的服飾品,在當前市場文化背景下無法很好地體現作為服飾品的組合適配性,從而也間接導致了披帛這一品類的服飾銷售對象主體小眾化、年輕化,總體市場接受度不高的情況;最后,披帛常常與漢服相關產品相搭配出現,由于漢服受眾群體小,主要消費者消費能力偏低,披帛作為其常配配飾在設計過程中更容易被忽視,從而導致其總體設計和創新水平不高。
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牽動著大眾民族意識覺醒,文化自信有所提高,民眾復興和宣傳傳統文化的熱情空前高漲,原本留存于書畫藝術和考古記錄中的歷朝歷代服飾文化,也得以依托便捷的網絡宣傳渠道、優質的視聽節目和古裝影視劇等媒體渠道,正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和了解到。市場是檢驗和擴大文化傳播及其影響力重要途徑,披帛產品的設計開發有待進一步推進,對披帛服飾之中蘊含美學思想進行研究,則有助于幫助設計者更好地認識把握和開發相關服飾產品。
3 披帛服飾中所蘊含的美學思想分析
3.1 傳統造物美學思想
在美學視角下,分析事物所蘊含的具體美學思想,要重點關注形式美和功能美。在形式造型美這一范疇里,“對稱美”無疑是中華民族傳統造物和審美習慣中最典型的代表,不僅有對稱莊嚴的飛檐斗拱、秩序和諧的圖飾紋樣,還有對仗工整的詩詞歌賦麗句華章,從建筑到服飾,從造物形式到思想文化,無一不展現著“對稱”這一美學概念;而對稱美也在披帛服飾的造型和裝飾上展現得淋漓盡致。除造型對稱營造美感以外,披帛更體現了線條美以及裝飾美;點,線,面是普遍公認的現代繪畫造型基本構成要素之一,“線”字字形上也有水的特征,所以又可稱其為水性字,表示柔性的、靈動的、富于變化的,具有極強的裝飾意味。中國傳統披帛服飾造型式樣,主要以線性表達為主,與服裝主體進行搭配,在整體裝扮造型上完成了線和面的組合過程,往往以線破面;在裝飾上,傳統披帛服飾的色彩圖案裝飾主要分為純色及裝飾圖案兩種,工藝裝飾則主要有刺繡、印染等手法;在視覺呈現上,或有類似隋唐式樣的飄逸靈動、一氣呵成,又或是宋代及以后命婦服飾的端莊典雅、工整細膩兩種典型面貌。功能美不僅僅要求實用,更要求好用,服飾品主要服務于營造服飾造型整體的完整及和諧,適當豐富主體服飾造型,最終起到使人“更美”的作用,而披帛服飾品乃是服裝主體的點睛之物,穿戴方便不僅“實用”,也“好用”。中國傳統披帛服飾立足各個時代的生產工藝技術基礎以及審美基礎,結合各個時代不同流行元素,已然在歷史洪流之中成為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之中獨具特色的璀璨明珠。
3.2 傳統哲學美學思想
先秦時期,出現了“諸子并起”“百家爭鳴”的文藝繁華局面,美學思想同樣獲得了很大的發展進步,而其中又以儒家、道家和墨家為首的思想派系,對中國傳統美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儒家思想強調三種美:“中和之美”“盡善盡美”和“天人合一”[8]。其中“中和之美”是穩定和秩序之美,其主要思想主張在藝術創作中避免走向極端和片面,設計元素之間的組合要適而不過,這也是儒家“中庸之道”在美學思想上的一種體現;“盡善盡美”則是中國傳統美學的最高境界,它意在追求美的極致狀態,也是儒家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天人合一”旨在追求與自然相和諧之美,這是一種完全浸入式忘我境界。道家思想中,關于美的追求,主要有“無為”“虛無”之美,道家崇尚天然,在藝術創作原則上反對人為的審美標準,講究原始和自然,排斥人為的痕跡,尤其是刻意的雕琢和夸飾;這種對自然美的崇慕和追求,對中華民族的審美思想和中國藝術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墨家美學思想提倡實用之美,主張“非樂”、重實用,認為真正的美是必須與功能和效用相聯系的,否定文采美飾,并以功利為標準看待美,更以實用來衡量美。
一方面,披帛服飾的服用性即服飾品的搭配補足功能,充分體現了儒家思想中的“中和之美”及“盡善盡美”美學主張,另一方面它造型簡潔自然呈流線型、曳態輕盈,裝飾于服裝之上與主體服飾構成一“虛”一“實”,表現出了道家哲學思想中的“原始”和“自然”追求;兼之披帛用途多樣,以近乎對稱的形態披掛于人體上,在裝飾的前提下又可兼顧保暖、遮蔽功能則又可見墨家重實用的思想核心。披帛服飾的“美”,是蘊含了眾多中國傳統哲學文化內核的美。
3.3 佛教美學思想
除儒家、道家和墨家哲學思想外,佛教文化也對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在多元文化的共同影響之下,中國傳統審美情趣和價值觀念得以完成構建,披帛造型在中國世俗中的發展流傳,與佛教文化密不可分。公元前后,佛教就已正式傳入中國,但佛教進入中國后經歷了漫長的翻譯經典時期,且發展緩慢;直至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佛教教義主張因果輪回,追尋精神以及肉體的解脫,十分符合當時統治階級需要,由此佛教開始在中國流行起來;隨著佛教傳入,與之相關的文字典籍,雕塑繪畫也迅速傳入中國,而披帛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逐漸流行,直至隋唐時期興盛于世俗女子穿著之中而成為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一部分。這一時期的披帛服飾,以輕薄的絹紗為主要材質,質地輕盈,行走間隨風飄逸,暗合了菩薩飛天的浪漫想象,不僅能夠滿足中國古代女性對柔美姿態的追求,也符合傳統服飾藝術以實代虛、以動代靜的營造原則,因而得以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延續和發展;此外,佛教思想文化中,禪宗的“靜”“空靈”對傳統文學藝術中寫意和含蓄的表達方式的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學藝術繼而又影響著世俗文化的發展變化。傳統披帛服飾是佛教文化同本土美學思想以及社會發展相結合的產物,而其中蘊含的佛教美學思想,是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內涵,更是融入了古代中國人民的思想情懷和勞動智慧的美學思想。
4 結語
傳統披帛服飾的發展歷程,從簡單質樸的配飾形制伊始,隨著時代發展逐漸在世俗中流行演化并占據一席之地,隨之分化出封建貴族命婦禮儀服飾,最終成為凝聚諸多美學內核的中華傳統服飾組成部分,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深刻的文藝內涵。在現代服裝設計教育模式影響下,成長的設計師群體,普遍習慣從款式、面料以及色彩等主要素上進行設計拓展,截至目前已然較難有開拓性突破,服飾搭配的重要性也愈發凸顯,與服裝相適配的相關服飾品設計則愈發受到關注;中國傳統文化兼容并蓄,從優秀傳統文化以及當代文化思潮中提取設計元素,已然成為了當代服裝與服飾產品設計從業者進行市場開拓和產品開發的重要著力方向;分析傳統披帛服飾美學內涵,不僅可以從中窺見中華民族長久以來凝聚形成的審美情趣,如不過多依靠剪裁加工而流露出的自然簡潔和含蓄氣質、在功能層面上追求“重己役物,致用利人”的人本主義思想外化,更能拓展思路啟發設計,從而幫助設計師們從傳統服飾文化的縱深上著力,創作出別具一格的、具有中華民族文化內核的服飾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