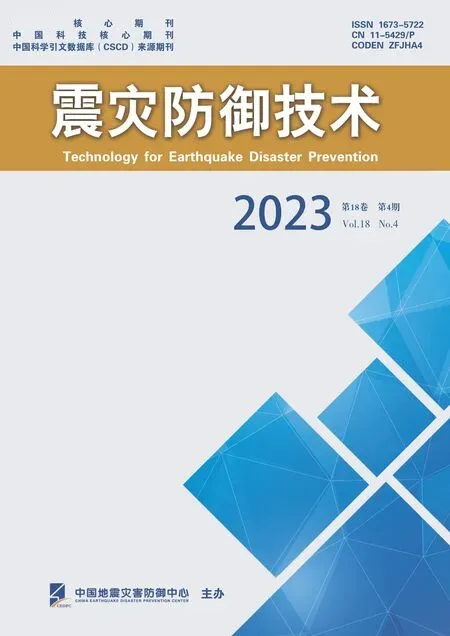內置草繩增強承重夯土墻體抗震性能試驗研究1
虞廬松 宋書豪 李子奇 王 力 李健寧
1)蘭州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院, 蘭州 730070
2)蘭州交通大學, 甘肅省道路橋梁與地下工程重點實驗室, 蘭州 730070
引言
夯土建筑是指用生土作為建筑材料,利用模板將其層層夯實而成的建筑,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從古代至上世紀中葉,夯土建筑因其取材方便、施工簡單、造價低廉、保溫隔熱性能優越等諸多優點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使用(盧家成等,2020)。然而,伴隨鋼材、混凝土等新型建筑材料的出現,夯土建筑逐漸淡出城鎮,僅少量存在于偏遠鄉村(周鐵鋼等,2013;王毅紅等,2015)。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日益加劇,我國在2021 年發表了《國務院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意見強調,使發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資源、嚴格保護生態環境、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礎上。夯土建筑的推廣使用,可有效減少房屋建筑對生態環境的污染破壞,有利于推動綠色發展,實現“雙碳目標”。
盡管夯土建筑優點頗多,但由于土體本身的抗拉強度較低,夯土建筑的抗震性能在側向阻力、位移能力、能量耗散和延性性能方面都較差(王毅紅等,2015;Arslan 等,2017;Karanikoloudis 等,2018),并且我國生土資源豐富,各地生土材料的力學性能參數難以制定統一標準,多數夯土房屋的設計建造主要依靠個人經驗,在承受地震作用時有可能產生較為嚴重的破壞,導致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王蘭民等,2011;李志華等,2016)。因此,提高夯土建筑的抗震性能是其推廣和發展過程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近年來,眾多學者對生土材料開展了研究,且主要集中在材料、結構2 個層面。國內學者劉蕾等(2021)、藺廣涵等(2018)、法國等(2019)以及國外學者Prabakar 等(2002)、Jové-Sandoval 等(2018)通過單摻和復摻的方式對夯土材料進行物理改性和化學改性,來提高土體抗剪、抗壓強度,以此增強夯土建筑的抗震性能;張又超等(2015)、徐舜華等(2011)、Miccoli 等(2017)、王赟等(2021)、張琰鑫等(2012)通過在夯土墻表面布置鋼絲網、竹條、聚酯織物條、構造柱等,以此在結構層面對墻體進行加固,增強其抗震性能。根據已有研究(劉強等,2018)及JGJ 161-2008《鎮(鄉)村建筑抗震技術規程》(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08)可知,在承受地震作用時,多數墻體由于底部和中部夯筑分層處的水平貫通裂縫而呈現脆性破壞。
綜上所述,基于綠色發展理念,為解決夯筑分層處易破壞的問題,提高夯土房屋的抗震性能,本文提出一種內置草繩增強的新式夯土墻,并對其抗震性能進行試驗研究,以期為夯土房屋的抗震設計及應用推廣提供參考依據。
1 試驗概況
1.1 試件設計
試驗以甘肅農村常見夯土墻為研究對象,墻面原型尺寸為4 800 mm×3 400 mm×600 mm,采用1∶3 縮尺比例制作夯土墻試件。以草繩含量及埋置高度為參數,共制作4 片夯土墻試件,編號分別為W1~W4,其中草繩高度分別設置于墻體各夯筑分層處上方。試件具體方案如表1 所示,以W4 試件為例,墻體外形及尺寸如圖1 所示。

圖1 W4 試件尺寸(單位:毫米)Fig.1 W4 specimen size(Unit:mm)

表1 試件方案設計表Table 1 Sample scheme design table
1.2 試件制作
采用鋼筋混凝土底梁作為試驗模型基礎形式,為防止試驗過程中墻底與基礎頂面發生滑移,故在基礎中間開槽。槽口長、寬、高分別與墻體尺寸一致。在凹槽中預留兩排直徑為12 mm,深度為100 mm 的孔洞,夯筑前采用環氧樹脂將草繩錨固于此孔洞中。墻體試件根據《村鎮生土結構建筑抗震技術手冊》(陳忠范等,2012)夯筑而成,如圖2 所示。

圖2 夯土墻試件Fig.2 Rammed soil wall specimens
1.3 加載方案
為模擬實際房屋中豎向荷載作用,采用分配梁以及對拉螺紋鋼筋對墻體施加豎向荷載。原型墻體頂部所承受豎向荷載為505.98 kN,根據縮尺比例關系對各試件施加豎向荷載56 kN,等效壓力為0.15 MPa。
加載制度參考JGJ/T 101-2015《建筑抗震試驗規程》(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5)。水平加載采用等幅位移控制,每級相差1 mm,往復循環3 次,加載速率0.1 mm/s,直至試件有倒塌趨勢或者承載力下降至85%以下,試驗結束。試驗裝置及加載示意圖如圖3 所示。

圖3 試驗裝置及加載制度Fig.3 Test device and loading diagram
2 試驗過程及現象
圖4 給出了各試件的最終破壞形態。W1 試件位移加載至3 mm 之前,墻體以局部不規則干縮裂縫為主;加載至3.5 mm,墻體底部第一夯筑分層處右側出現長約150 mm、寬2 mm 的水平裂縫;加載至5 mm,墻體中部第二夯筑分層處右側出現長約100 mm、寬2 mm 的水平裂縫,并與初期不規則裂縫相交,形成細小的交叉裂縫,墻體底部左右兩側水平裂縫延伸,變寬,有貫通趨勢,此時墻體出現一條較長的斜裂縫;加載至9 mm,斜裂縫并未繼續發展,而墻體底部水平裂縫已貫通,最大寬度達到20 mm,最終墻體在底部水平裂縫處出現滑移并伴有被抬起現象,加載結束。

圖4 各試件破壞圖Fig.4 Failure diagram of each specimen
W2 試件加載至5 mm 前試驗現象與W1 類似,墻體以局部不規則裂縫和底部第一夯筑分層處水平裂縫為主;加載至5 mm,墻體底部水平裂縫長度延伸至800 mm 左右,但寬度未變,此時墻體中有草繩受力繃緊的聲音,在中部第二夯筑分層(內置草繩的上方)左右兩側各出現長200 mm、寬2 mm 的水平裂縫;加載至10 mm,底部水平裂縫逐漸貫通,但受草繩的拉結作用,墻體并未產生滑移;加載至12 mm,中部水平裂縫貫通,部分墻皮脫落,且沿中部出現了滑移,加載結束。
W3 和W4 試件試驗現象基本一致,位移加載至10 mm 之前,墻體裂縫與W2 類似,均在底部第一夯筑分層處和中部第二夯筑分層處出現水平裂縫;加載至10 mm,底部水平裂縫貫通的同時伴隨墻皮脫落,隨著位移增加,在草繩的拉結作用下,墻體出現自下而上的斜裂縫;加載至15 mm 時,墻體在水平裂縫和斜裂縫共同作用下被分割為若干大塊,破壞裂縫呈“V”字形,加載結束。破壞時墻體內部草繩斷裂,如圖4(e)、圖4(f)所示。對比各試件破壞圖分析可知:
(1)墻體夯筑分層處水平貫通裂縫是其脆性破壞的主要原因,水平裂縫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墻體底端彎矩作用而產生的上拔力,上拔力使墻體在其較為脆弱的夯筑分層處出現水平裂縫,導致墻體被水平裂縫分割為上下2 塊,造成破壞。
(2)內置草繩后,墻體夯筑分層處得到有效拉結,使墻體整體性得到提高,避免了水平裂縫的擴大延伸,進而墻體由水平裂縫破壞轉變為剪切斜裂縫破壞。
3 試驗結果分析
3.1 滯回性能
4 個試件的滯回曲線如圖5 所示。曲線正值為推,負值為拉。試件加載初期,各墻體荷載和位移近似呈線性關系,曲線圍成面積較小;達到峰值荷載時,滯環面積逐漸增大,表明墻體此時耗能較為顯著;峰值荷載后,相同位移往復3 次加載中,最大水平力依次降低,承載力呈退化趨勢。對比圖5 可知:

圖5 各試件滯回曲線Fig.5 Hysteresis curves of each specimen
(1)相較于W1 試件,內置草繩的試件(W2~W4)滯回曲線更為飽滿,滯回環捏攏現象逐漸減弱。
(2)各內置草繩試件滯回曲線的飽滿程度與草繩高度呈正相關性,且捏攏現象隨著草繩高度增加得到明顯改善。這是由于在加載過程中,草繩與墻體共同參與受力,從而增大夯筑分層處的粘結力,延緩其水平裂縫的延伸擴展,進而使其滯回環更加飽滿。
3.2 骨架曲線
采用基于能量等效的理想彈塑性(EEEP)方法(ASTM,2007)定義結構的屈服荷載、屈服位移、延性系數。水平力達到最大值時為峰值點,水平力下降至峰值的85%時為極限荷載,若試件破壞時未達到極限荷載,則取最后一次加載的最大值為極限荷載。
表2 為各墻體試件特征點處力學參數,骨架曲線如圖6 所示。結合圖6 和表2 可知:

圖6 各試件骨架曲線圖Fig.6 Skeleton curves of specimens

表2 各試件特征點處力學性能參數Table 2 Mechanical property parameters at characteristic points of each specimen
(1)內置草繩的墻體試件(W2~W4)相較于無草繩的W1 試件承載能力、變形能力均有提升,其中W4 試件提升最大,其峰值荷載、極限荷載分別提升了108%和109.2%,峰值位移、極限位移分別提升了21.9%和35.6%;延性系數提高了1.45 倍。這表明內置草繩增加了墻體的整體性,從而使其承載能力和變形能力得到了更好地發揮。
(2)內置草繩的墻體試件承載能力、變形能力均表現為W4>W3>W2,其中W4 試件相較于W2 試件的峰值荷載、極限荷載分別提升了18.8%和56%,極限位移提升了16.1%,延性系數提升了15.3%。說明墻體承載能力和變形能力與草繩的高度呈正相關,這是因為隨著草繩高度的增加,在各夯筑分層處均有草繩穿過,解決了夯筑分層處黏結較弱的問題,墻體整體性得到大幅提高,因此墻體的峰值荷載和極限位移得到提升。
(3)W2 試件水平承載力和變形能力相較于W3、W4 試件提升較小,原因是草繩高度僅為1/4 墻高,無法對墻體中部第二夯筑分層處產生約束作用,導致其水平裂縫貫通,承載力達到峰值荷載后下降較快。W3 和W4 試件峰值荷載、極限荷載及對應位移大小較為接近,在實際應用中,建議內置草繩高度大于1/2墻高。
3.3 耗能能力
墻體耗能能力通常使用加載過程中的等效黏滯阻尼系數來衡量。墻體的黏滯阻尼系數取決于其自身的開裂、破壞模式。通常把墻體出現第1 條裂縫時的阻尼系數定為開裂阻尼系數。各試驗墻體特征點處等效黏滯阻尼系數如表3 所示。

表3 特征點處等效黏滯阻尼系數Table 3 Equivalent viscous damping coefficient at characteristic points
由表3 可知:
(1)整個加載過程中,各試件等效黏滯阻尼系數逐漸增大;W1 試件從開裂至破壞時的阻尼系數差值最小,這是由于墻體裂縫出現以后貫通較為迅速且裂縫間的摩擦力較小,墻體耗能能力尚未得到充分發揮。
(2)墻體從開裂到破壞,各內置草繩墻體試件(W2~W4)等效黏滯阻尼系數均高于無草繩的W1 試件,表明從墻體開裂至破壞的全過程中草繩均發揮了拉結作用,約束了墻體的變形,增大了各裂縫間的摩擦耗能作用,從而提高了墻體的耗能能力。
3.4 剛度退化
為反映試件在反復荷載作用下的剛度,以割線剛度來表示其有效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5),為減少加載過程中其他因素的影響,以各階段第1 次循環的割線剛度為基準。各試件的剛度退化曲線如圖7 所示。

圖7 各試件剛度退化曲線Fig.7 Stiffness degradation curves of specimens
由圖7 可知:
(1)各內置草繩的試件(W2~W4)初始剛度接近(差值在0.5 以內)且均大于無草繩的W1 試件,表明內置草繩可拉結墻體,提升墻體整體剛度,但草繩高度的變化對墻體初始剛度影響不大。
(2)位移加載至4~10 mm 時,W3、W4 試件剛度接近,且大于W2 試件,說明草繩高度超過1/2 墻高時,能更加有效延緩墻體的剛度退化,這是因為隨著草繩高度的增加,墻體各夯筑分層處均能得到有效拉結。
4 結論
本文主要以草繩含量和草繩埋置深度為參數,對4 片采用分層夯筑的夯土墻體縮尺模型進行了擬靜力試驗,得到了不同參數下墻體的破壞形態、承載能力、滯回性能等參數。通過對數據的分析比較,得到了內置草繩夯土墻體在抗震性能方面的卓越性。主要結論如下:
(1)相較于無草繩夯土墻,含草繩的墻體中,草繩可提升夯層薄弱處的黏結作用,提高了墻體的整體性,有效避免了墻體夯筑分層處的破壞。實際應用中,建議內置草繩高度大于1/2 墻高。
(2)內置草繩可提高分層夯筑墻體的承載能力和變形能力,且提升率與草繩高度呈正相關,相較于無草繩的墻體試件,其承載能力、變形能力分別提升75.2%~108.3%和16.8%~35.6%。
(3)對于采用分層夯筑的墻體,內置草繩可使其耗能曲線更為飽滿,大幅提高墻體耗能能力;達到破壞荷載時,其等效黏滯阻尼系數范圍為0.16~0.23。
(4)內置草繩可使分層夯筑墻體的初始剛度最大提升40%,且加載過程中其剛度始終高于無草繩的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