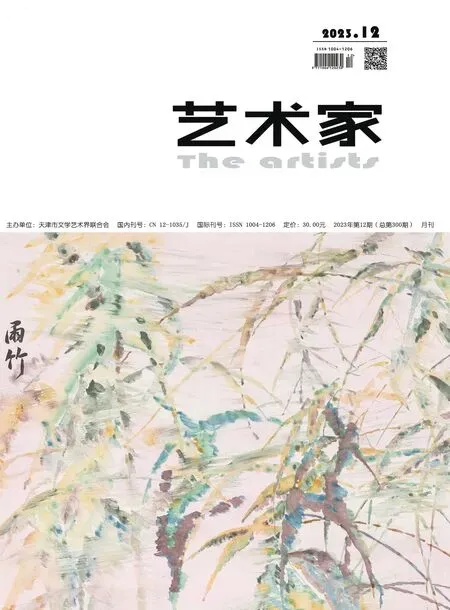精神性
——中國藝術評論中的非顯現因素
□宮曉東
在現當代藝術環境中,中國藝術評論與西方藝術評論有所不同,中國藝術評論的標準中有一個非顯現的因素,即更加重視藝術作品中的精神性。重視精神性不是現當代的新產物,而是中國或東方自古以來的傳統。本文分析中國藝術評論非顯現化的緣由,對中國和西方藝術評論的顯現和非顯現的評論標準進行梳理,對精神性的各種賦予方式及中國特有的精神性群體的繪畫——“文人畫”進行討論。
一、顯現化、非顯現化的藝術評論及其標準
謝赫的《畫品》是中國第一部對繪畫作品、畫家進行品評的著作,提出了“六法”作為品評繪畫的標準: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謝赫把“氣韻生動”這個最主觀感受的標準放在第一位,把線條、造型、色彩、構圖、臨摹,這幾個標準都放在了后面。
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里的繪畫作品品評標準,在沿用張懷瓘“神品”“妙品”“能品”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個“逸品”。唐末宋初的黃休復也沿用了“逸品”“神品”“妙品”“能品”這幾個品評標準,并增加了一個“題品”。唐代張璪在繪畫方面主張“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認為藝術家對外要描繪自然造化,同時創作者內心的構設和感悟也很重要。
可以看出,相較于作品的外在形式,中國更重視精神內核的傳達。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國藝術的評論者會把“氣韻”“神品”“逸品”這種非顯現化的標準加入,甚至放在第一位。包括張璪的“中得心源”,這些標準都不是能具體顯現出來的。“精神性”或者說“道”,是一個意會重于言傳的范疇,我們把這些不能具體顯現出來的標準暫且稱作“非顯現化”因素。
西方的傳統美學中也有用非顯現化的詞匯來評價藝術的。例如,“崇高”的概念,還有18 世紀溫克爾曼的“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這樣的說法。西方美學最早提到崇高概念的是古羅馬的朗吉努斯,他的著作《論崇高》是從詩學和修辭學來分析的,也就是對文章的崇高進行討論。英國經驗主義美學家柏克和德國哲學家康德也對“崇高”這一非顯現化的評價藝術品的范疇進行過討論。與中國評論者提出的非顯現化標準(“神”“妙”“逸”)不同的是,朗吉努斯、柏克和康德都對崇高的范疇進行了逐條分析。如朗吉努斯認為有“崇高”特質的藝術作品要具備五方面內容:(1)莊嚴偉大的思想;(2)強烈而激動的情感;(3)藻飾的技法;(4)高雅的措辭;(5)堂皇卓越的結構。可以看出,西方與中國的藝術評論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西方評論者會對一個非顯現化的概念進行非常詳細的討論和分析,這也是西方文化的特點,即他們總想要以解析的方式來闡述世界,認為精神性的東西也是可以用語言來描述的,正是這種文化特質才衍生出西方的“科學”。
西方對藝術的分析很多是顯化的標準,如早在古希臘時期,畢達哥拉斯派就認為藝術與“數學”“數字”之間有著重要的關系,藝術擁有著一種節奏,不管是視覺藝術,還是聽覺藝術。“黃金分割比例”這種以西方科學的方式來分析繪畫藝術的觀念,自古希臘時期就有了。
事實上,藝術創作、藝術品、藝術評價,是統一不可分割的,中國藝術評論中非顯現化因素的出現,也是中國藝術強調精神性特質的一個表現。
空間透視學的發展,使得西方繪畫可以在二維平面里表現三維立體空間,所描繪的物體具有立體感、體積感和明暗光線的變化,從此西方繪畫可以準確地再現世界。經過巴洛克藝術、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到在光學發展情況下的印象派,再到野獸派、表現主義等西方現代主義流派的諸多藝術風格都與科學發展緊密相關。在西方繪畫史中,透視學、人體解剖學、色彩學、光學等科學領域的發現和發明,都對繪畫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照相技術的發明直接催生了現代主義藝術。科學技術是可解說分明的,以科學為基礎的繪畫同樣也是可以清晰闡述和評價的。
中國繪畫沒有經歷這樣一個系統性的大變革,從現有的史料、考古發現和留存作品來看,中國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從戰國時期到清代,都是用線條、皴法和著色等同樣體系的技法和形式來表現描繪對象。明清時期,繪畫范式已經非常豐富。中國藝術或者東方藝術雖然沒有西方那種寫實的繪畫系統的大變革,但是中國藝術所強調的“精神性”,是世界本源性的范疇,人類的語言是不易言說或不能言說的,這是東方文化的智慧,也是中國藝術評價標準非顯現化的重要原因。
二、藝術中的精神性由什么賦予
我們暫且把藝術作品中帶有的非顯現化、不易明言的范疇,如“格調”高不高,“意境”好不好,“逸品”“妙品”“崇高”“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等此類的范疇,稱為精神性。藝術作品的精神性可以是承載的內容賦予的,也可以是創作者及其身份賦予的,同時也包括藝術家通過合適的藝術形式進行準確表達的。藝術品在時代的社會功能及在此功能基礎上的傳播,也是影響藝術精神性的重要因素。
(一)“引魂升天”的功能
中國戰國時期墓葬出土的經幡、漢代墓葬里的帛畫繪制了墓主人飛升的畫面,有“引魂升天”的功能。喪葬用途,用以希冀人的死亡并不是終點,而是會去到更好的世界。此種繪畫功能在很多文化中都存在,如古埃及。
(二)為宗教服務
宗教藝術自然是具有精神性的。中國藝術史中有大量的佛教藝術、道教藝術,石窟、寺廟留存有大量的雕塑和壁畫,除了我們可以看到的那些線條、色彩等“有意味的形式”,觀者也會接收到或創造出某些精神性的東西。例如,當觀者抬頭看體積龐大的佛像雕塑,而佛像向下看著觀者,嘴角呈現不易察覺的微笑,祥和、慈悲、包容的樣子,其中的精神性不言而喻。
西方中世紀教堂里的雕塑、壁畫、玻璃窗等藝術作品也有為宗教服務的功能,在民眾識字率低的情況下,能夠運用圖像向民眾講述傳播《圣經》中的故事。宗教的精神性,加上與之協調的藝術形式的表達,那么超出藝術品本身形式的藝術精神性自然會產生。
(三)政治歷史、道德傳播的社會功能
謝赫早在《畫品》中說到繪畫的功能:“明勸誡,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如唐太宗李世民建凌煙閣,繪有開國功臣二十四人的畫像。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如圖1),目的是勸誡女子守德。漢代畫像石、畫像磚有很多道德教育內容的繪畫,如各種孝子題材的故事繪制。宋代畫家李唐的《采薇圖》,伯夷和叔齊不食周粟,通過繪畫以史明志、借古諷今。西方也有以史鑒今的繪畫作品,如法國大衛在大革命時期畫的《荷加斯兄弟的宣誓》。在此種功能的基礎上,這些作品會帶有超出作品本身的精神性,如把功臣的有功于世人、守德女子的圣潔、道德氣節等精神性的東西加入藝術作品。

圖1 《女史箴圖》局部
(四)審美功能——藝術的解放
藝術發展到一定階段,都實現了脫離社會功用性。魏晉南北朝時期,花鳥畫獨立出來,有記載的“黃家富貴,徐熙野逸”,黃筌的《寫生珍禽圖》是現存最早的花鳥畫。花鳥畫主要以審美功能來進行各種裝飾。宋代的文人畫、職業畫家的作品都脫離了社會功用,觀看者只是欣賞其中的美,不是受教于它。而早在唐代的草書,就已經是表現純粹形式的美,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筆墨線條的流動、結構安排和節奏感。
西方17 世紀靜物畫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畫科。靜物畫體現自然之美,有時也表達時間與死亡。17世紀出現了荷蘭小畫派,由于荷蘭經濟的發展,富裕起來的市民階層的家庭裝飾需要使得表現日常生活的繪畫作品大量出現,這時藝術終于擺脫了宗教教會和貴族,以審美功能存在。
三、特殊群體創造出的精神性——中國文人畫
除了作品承載的內容賦予藝術精神性,創作者及其身份也會賦予藝術一定的精神性。這也是中國藝術評價不客觀的另一個方面,把對藝術家的評價無意識地加入藝術評價中,我們首先要梳理一下藝術家的社會身份。
中國自古以來的藝術家有不同的身份。那些為宗教服務的創作者,他們畫壁畫、做佛像雕塑,去寺廟里的人不會在意誰是這些作品的創作者,他們更沉浸在佛像、神仙的宗教形象、宗教世界或宗教精神中。宮廷畫家為政治人物服務,他們沒有完全的創作自由,而是根據皇室需要來創作。宋代出現了職業畫家,他們服務于購買者,由市場左右藝術創作。西方歷史中的藝術家也大體相同,他們的訂件人是教會和貴族,在貿易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興起時,出現了新的服務對象——市民階層,包括后來的現代主義藝術、后現代主義藝術,也要考慮市場和收益。
文人士大夫不以繪畫謀生,他們是中國特有的完全獨立的創作自由和審美自主的藝術家群體。之后的繪畫評論對“文人畫”純粹審美的藝術觀念和風格也很推崇。所以,文人畫有很強的個人性,往往會把士大夫做人的品性、格調也加入作品的評價中,而“品性”“氣節”“風骨”這些東西是非顯現化的。文人崇尚傲骨,不功利、不世俗,繪畫行為和作品不用別人來供養,所以作品也仿佛是不功利、不世俗的。有時由于一件作品是某個有風骨的文人創作的,那么這個作品同樣攜帶了一種“風骨”,人們認為其藝術性更卓越。所以中國藝術評論會把藝術家的做人品性也加注到藝術作品中,因為非功利、非功用的精神性往往是高要求的真、善、美。
所以,中國品評藝術家不會像西方那樣,把卡拉瓦喬放在藝術史中很重要的位置上。中國品評藝術家認為藝術家和藝術品是不可割裂的,重視創作者加入作品中的抽象的精神性,所以,這種非顯現化的標準是中西方的藝術批評呈現不同的原因之一。在文藝復興之后,西方藝術越來越重視“人性”,而東方藝術始終崇尚“精神性”。
西方以沙龍的藝術呈現方式發展到后來的美術館,與此同時,一個媒體的、公共討論的機制也逐步完成。藝術品呈現的方式是在美術館展出,藝術品是展出的,藝術家是隱身的。相對于藝術家,大家自然而然會重點對所看到的藝術品進行評價。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西方最終發展出成熟的藝術市場運作體系,這些都是西方藝術批評的大環境。藝術史走到現代之后,世界各國紛紛加入西方的藝術體系,不同文化需要適應融入,并在此體系和規則中找到自己的方式。中國藝術恰當地找到了融合的方式,在遵循規則的前提下,也很好地保留了自己的精神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