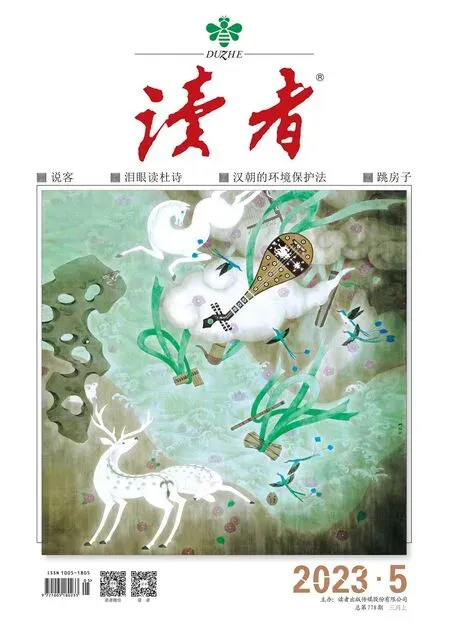淚眼讀杜詩
☉蘇 煒

戴爾是跟我進行“獨立學習”的一位洋學生。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音樂學博士,還是作曲家兼爵士鋼琴手,目前正在耶魯大學做民俗音樂的博士后研究。他有一個地道的中文名字——韋德強。他早年跟隨父親住在香港,學得一口流利的粵語,后來又娶了來自臺灣的妻子,所以普通話也說得不錯。剛開始,我還按部就班地根據他的研究課題,指導他讀一些關于廣東音樂與地方史志的材料。讀著讀著,我們倆似乎都覺得有點意猶未盡,案桌上恰好擺著一本《杜甫詩選》,我便說:“我們一起讀杜詩吧!”
第一首讀的是《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窗外正是秋天日暮,紅葉初妍,東亞系的紅磚小樓里一片空寂。我一邊逐字逐句地跟他解釋字義與韻腳,一邊讓他分別用粵語和普通話高聲誦念詩句。這位極力咬準字音的洋學生鏗鏘讀出的《蜀相》,一時間乘風馭霧地,就在流隔千年的北美秋日黃昏中的小樓里,瑯瑯回蕩起來。他很認真,每次都要用錄音機把我的朗讀和講解錄下來,回去再仔細反復地聽,并表示要把每一首詩都用粵語和普通話背誦下來。于是,我們此后每次見面的第一件事,都是他用南北兩種漢語語音為我背誦杜詩,并講述他自己的理解。那天,我正低頭沉浸在他抑揚頓挫的誦讀中——“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抬起頭,我發現戴爾的眼里竟然閃著隱隱的淚光!“太好了,這樣的詩太好了……”他喃喃說著,掩飾似的轉過臉去。我心里微微一動。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到了讀第二首詩《登樓》的時候,我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位完全可以在杜詩中與我心有靈犀的“解人”,便站起來,一邊念誦,一邊向他忘情地直陳我對這首律詩的起句意境,多年來的癡迷與沉醉。我還沒解釋完,就看見戴爾的眼里已經噙滿熠熠的淚水。“……我讀到了貝多芬!我真的聽到了杜甫詩里響著貝多芬的旋律!”他激動地說。
下一周回來,他用兩種漢語語音為我背誦《登樓》:“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戴爾的聲調變得憂傷起來,他告訴我,杜甫詩歌里對國家和社會的憂慮,很契合他對自己祖國現狀的擔憂,這使他感到一種杜甫式的報國無門的失落與悲哀……窗外落葉飄飄,我心里又是微微一動——這是一個真正把杜甫讀進心里的美國人。他是學音樂的,他用漢語雙音向我吟誦杜甫詩時,似乎真的把杜甫的憂國傷時化進了自己的靈魂與血液之中——這可不就是我在異國異邦聽到的另一闋《梁甫吟》嗎?
下一回課上,我播放著中國古曲,跟他一起讀杜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聽罷二胡曲《江河水》《二泉映月》的傾訴,老杜的《贈衛八處士》讀來更是令人如聞青空鶴唳、高樹悲風。讀到結篇的“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我們——一個中國老師和一個美國學生,一時間竟淚眼相對了!隔著千山千水、千年千歲,杜甫在鞭打我們的心。人生,聚散,生死,浮沉……此刻化作一縷縷連接古今中西的煙云,在我們眼前拍蕩、浮涌。戴爾后來花了兩周的時間,才把《贈衛八處士》完整背了下來;我呢,則因被此詩意境觸動,寫出了《路邊的印第安老太太》一文。于是,戴爾又進而把拙文當作一個中文讀本,杜甫的詩境一時又轉換成對現實人生“在路上”的詠嘆。戴爾向我講起許多他尊敬的玩音樂的友人,常年樂此不疲“在路上”而淡泊名利的故事。因為杜甫,我們一下子發覺彼此有了這么多“心有戚戚焉”的共同話題,每次的“獨立學習”好似成為一場與古人神交、在時光之流中含英咀華的精神盛宴了。
“我的老父親聽說我在跟一位中國老師讀杜甫詩后,對我說,他為我驕傲。”有一回,戴爾這樣對我說。“Proud of me(為我驕傲)”這句英語似乎忽然帶上了詩意,在晴明的秋日泛起酒樣的酣醇。
整個秋天,我為戴爾安排的課程都是在杜詩的吟誦中度過的。冬意漸濃,學期即將結束。讀杜詩上癮的戴爾,要求我最后再給他選一首適宜背誦的短章。那是在初雪之后,我們于窗外零星飄降的雪點子中,一起吟誦杜甫的《旅夜書懷》:“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