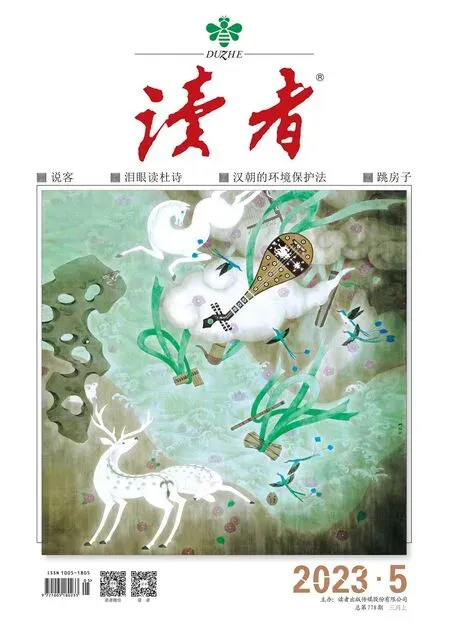記憶之盒
☉〔英〕簡妮·布朗
◎晝 溫譯

丹尼爾站在我的咨詢室門口,牽著他七歲的女兒艾米麗。
“抱歉給你帶來了一個驚喜,簡妮。”他說著,瞥了一眼女兒,“我跟你說話的時候,能讓艾米麗在候診室自己玩會兒嗎?”他看著我,眼下掛著兩個黑眼圈,神色疲憊,“林得了偏頭痛,今天早上得臥床休息。艾米麗堅持要和我一起來,我不忍心拒絕。”
滿足這種小小的愿望是他為數不多能做到的事,他無法彌補女兒們馬上要承受的巨大損失。
“女兒們不知道我的病有多嚴重,”丹尼爾一周前在電話里告訴我,“這樣更好,你不覺得嗎?”
醫生說他的癌癥復發了,很嚴重,可能只剩下幾個月的時間,但他決定不把這個消息告訴她們。丹尼爾擁有兩個女兒——一個七歲、一個九歲,她們是他最驕傲的成就。
艾米麗看著我,臉上帶著燦爛的笑容。她渾身散發著自信,這代表她有堅韌的品格——在悲劇發生后,這種品格有大用處。
“很高興終于見到你了,艾米麗,我聽說過很多關于你的事。”我彎下腰,向她伸出手。她簡單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如果需要我們就敲這扇門,好嗎?”我指著咨詢室的門說,“你爸爸和我會在那兒談話。”
她點點頭。
丹尼爾坐在他的老位子上。他的生命力在逐漸流失,頭發掉光了,臉色愈加蒼白。他穿了一件寬松的運動服,試圖讓自己越來越瘦削的身體看起來不那么單薄。
“我的妻子和岳父岳母都指望我能好起來。我一說病逝的事,他們就告訴我不要那么消極。他們不想談論死亡,認為談論死亡就會讓死亡成真。我當然想活下去,但這已經不可能了,不是嗎?”丹尼爾凝視著我。我慢慢地吸了口氣。
死亡就坐在丹尼爾身邊的沙發上,丹尼爾需要我尊重他直面真相的能力。沒有尊重,人就失去了尊嚴。
我慢慢呼出一口氣:“是的,看起來你撐不了太久了,丹尼爾。”
丹尼爾的聲音很急:“如果我真的要死了,那么我希望林和孩子們能盡量輕松地挺過去。”他一圈又一圈地轉著婚戒。
“丹尼爾,我可以幫你為赴死做好準備,但不是讓你對意外的好運失去希望。”
丹尼爾放松下來,眼里滿是寬慰的淚水。“我只知道假裝自己不會死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他說。
人們總會漸漸明白,死亡避無可避。作為一名專業的醫護人員,就算沒有被邀請參與討論,我也有職責引導人們認識到死亡將近的事實。我見過很多人來不及說再見就走了,這往往會給還在世的人留下無法化解的遺憾。
“讓我們從看得見、摸得著的地方開始吧,”我說,“你想過你會在哪里離開嗎?”
“我無法想象如果我死在家里,死在我們的床上,林和孩子們該怎么挺過去。她們以后會感到恐懼嗎?”他問。
“死亡的記憶并不總是可怕的,它也可以很溫柔。人們常會談起病人在家中離世帶來的安慰。”我說。
丹尼爾的表情更柔和了。“我爺爺就是在自己的床上去世的,奶奶似乎也接受了。但林認為死亡很不吉利,所以我想,如果我在醫院或臨終關懷中心離世,對她來說會更容易接受些。”丹尼爾說。
我向丹尼爾解釋了姑息治療中心和臨終關懷中心的區別。姑息治療中心和臨終關懷中心都有專門從事臨終護理的團隊。病人們可以去姑息治療中心管理癥狀,比如緩解疼痛、抑制惡心。一旦癥狀得到控制,他們就可以回家,或去臨終關懷中心。大多數臨終關懷中心的政策是只接收預后只有三到六個月的病人。
丹尼爾的臉上泛起了血色。實實在在的幫助可能給他帶來一些安慰。
“你家附近就有臨終關懷中心。你可以從家里帶些東西去,比如墻上的裝飾畫,你自己的床上用品。林和孩子們隨時都能去看你,她們甚至可以在那兒過夜。”我說。丹尼爾緊盯著我。
丹尼爾的關注點從現實轉向了感情:“孩子們可以看著我死去嗎?這會不會給她們造成精神創傷?”
“這取決于死亡過程是否平靜。大多數情況下,臨終關懷團隊可以幫你平穩渡過,你在孩子們眼里就像睡著了一樣——會很悲傷,但不會有創傷。”我在改變自己的用詞,從“可能”變成了“會”,引導丹尼爾接受必然的結局。他慢慢地向前傾身,拿起桌上的玻璃杯喝了幾大口水。我一直在耐心等待。
他終于抬起眼睛,我繼續說道:“如果情況特殊,或者突然發生意外,那么最好不要讓孩子們留在那里。這確實會帶來創傷。”
“誰來決定?”丹尼爾問。在如此漫長的談話中,他表現出驚人的毅力。我的思緒短暫地轉移到候診室里的艾米麗身上。我很感激她的獨立自主,讓我可以不受干擾地和她爸爸說話。
“臨終關懷團隊會指導你的,但也希望你能和林談談這件事。”
“我咽氣后怎么辦?能讓孩子們看到那時的我嗎?”丹尼爾問。
我向丹尼爾保證,孩子們往往知道自己想不想看見那個已經去世的人,也知道自己想在房間里待多久。和成年人一樣,孩子們也需要說再見。
“這聽起來可能是個奇怪的問題。”丹尼爾停了一下,然后看著我。
“沒關系,你說。”
“我怎么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會死呢?”
“死亡的最后階段通常會持續幾小時到幾天:身體不再需要吃喝,器官也自然停止運轉;沉睡的時間多,清醒的時間少。你很可能知道自己要死了。”我說。
丹尼爾靠在沙發靠墊上,轉頭望了望窗外。我們在談話間隙休息了一會兒。
他轉過身來,我繼續說:“當林進入生產的最后階段,也就是分娩的時候,你也在場,對吧?不管有多大的決心,她都無法阻止正在發生的事情。是你的女兒們自己選擇誕生到這個世界上的時間的。”
丹尼爾的眼睛因為回憶而閃閃發光:“第一次抱起她們的感覺真是太棒了。”
我告訴他:“就像身體知道如何出生一樣,我相信它也知道如何死去。”丹尼爾露出寬慰的神情。“死亡會在該發生的時候發生。”我補充道。
我等了等,不知道丹尼爾還有沒有別的問題。他可能已經耗盡今天的能量份額。
他的聲音變得低沉了:“我很想活下去,但是癌癥已占了上風。”他停了下來,好像冒出了一個不請自來的念頭,“得癌癥不是我的錯,是不是,簡妮?”
“當然不是你的錯!”我激動地說,“生活帶來挑戰,我們必須面對。面對挑戰的方式不僅影響我們自己的生活,還會影響我們所愛之人的生活。你若能認真對待自己,女兒們就會向你學習,你的豁達和自尊將伴隨她們一生。”
丹尼爾已經振作起來,他坐直身體,好像已經重新定義了希望。與其將希望寄托于茍活,不如與家人一起度過富有意義的時光。
“也許我們該去看看艾米麗?”丹尼爾建議道。我起身打開咨詢室的門,艾米麗微笑著抬起頭。
她走進咨詢室,一屁股坐在父親身邊,睜大了眼睛看著我。“你和爸爸在說什么?”她問。
我看著丹尼爾,想知道他要不要我回答。他向我點了點頭。
“你爸爸和我在談生病的感覺。”
艾米麗抬頭看著爸爸。丹尼爾的眼睛濕潤了。
“你知道爸爸怎么了嗎?”我問。
“知道,他得了癌癥,快要死了。”艾米麗實事求是地說。
我的心碎了,抬眼望向窗外的楓樹,希望得到片刻的安慰。我注意到新生的嫩葉正在四月的微風中顫抖。等我再次看向丹尼爾,他露出求救的神情。
我讀懂了他的暗示,繼續對艾米麗說:“爸爸死后,你和媽媽,還有姐姐,都會很難過,是不是?”
“是的,會的。”她說,“爸爸,我想要你活著。”
她抬頭看著丹尼爾,丹尼爾用雙手把她拉到自己虛弱的身體旁。看著這對父女的親密互動,我想起自己已去世的父親,想到所有不得不過早送走父母的兒女。
丹尼爾對艾米麗耳語道:“我永遠愛你,艾米麗,不管我在不在你身邊。你會記住這一點嗎?”她微微點了下頭。
我傾身靠近她,輕聲說:“說說爸爸去世后,你會想念的東西吧。它們會成為快樂的回憶,在你難過時撫慰你的傷痛。”
艾米麗的眼睛亮了起來:“我想說說這些事。”
“也許你可以和爸爸、姐姐一起做個記憶盒。首先回憶你們都喜歡爸爸什么,然后在家里找一些與之有關的東西放在盒子里,或者做許多個也可以,幫你們留住這些特別的記憶。”
艾米麗熱情地點點頭。
“你喜歡爸爸的哪一點?”我問。她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愛爸爸的吻。”她抬頭朝他微笑。
“當然。”我說,“你覺得我們該怎樣把爸爸的吻放在記憶盒里呢?”
“我知道!”她興奮地說,“我可以給爸爸涂上媽媽的口紅,讓他親吻幾張紙,然后我們就可以把它們放進盒子里了。”她咯咯地笑了。
丹尼爾和我對視一眼,揚起了眉毛。創造力把即將失去的痛苦包裹在喜悅之中,他的吻將在他死后長存。
“下次來的時候,你能帶上記憶盒給我看看嗎?”我問艾米麗。她點了點頭。
孩子們也需要做好準備。
一天,丹尼爾突然疼得厲害,住進了醫院,四十八小時后就去世了,醫生認為他可能死于血栓。林覺得女兒們可能想為父親做些特別的事情,她讓她們自己決定要做什么。
艾米麗問林,她和姐姐克萊爾可不可以摘掉窗臺上花瓶里所有花的花瓣。林同意了。然后女孩們慢慢地摘下每一朵花的花瓣,小心翼翼地堆在床邊的小餐桌上——郁金香、百合、銀蓮、玫瑰,大大小小,顏色各異,留有余香。女孩們小心地用花瓣在蓋著丹尼爾的白色毯子上拼出“爸爸,我們愛你”的字樣。她們一邊擺,一邊和他聊天,告訴他一些她們永遠不會忘懷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