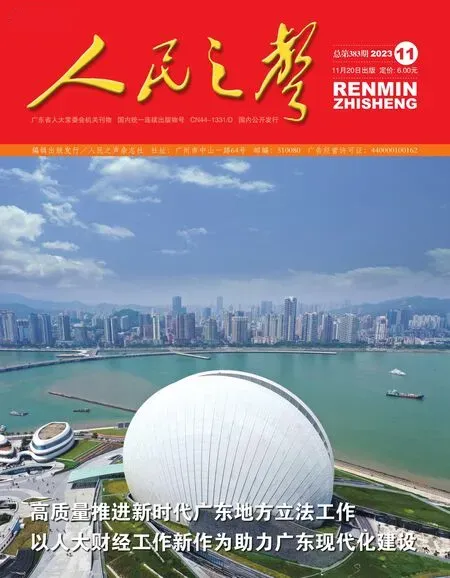智能汽車發展形勢如虹 頂層立法方能助推前行
當前,在深圳南山區的測試路段,一批“蘿卜快跑”無人駕駛汽車在運行;在坪山區,今年已經開始全無人商業化試點,通過手機APP,就可叫來一部“整車無人”的出租車,科幻感十足。隨著深圳智能網聯汽車測試示范路段不斷“擴容”,近期陸續開放南坪快速、水官高速、廣深沿江高速等高快速公路89公里。
在國內首部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法規——《深圳經濟特區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條例》實施滿1年之際,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對全市智能網聯汽車發展情況開展調研。人大代表對于智能網聯汽車發展情況的調研與深度關注,不只是對汽車產業和交通出行的重視,更是對當前時代智能化與網聯化水平的積極推動。
截至今年8月,深圳累計向15家企業、325輛智能網聯汽車發放道路測試及示范應用通知書,車輛較去年8月條例實施之初相比增長170%。累計開放智能網聯汽車測試示范道路771公里,同比增長20%。坪山區更是先行一步,實現全域開放440公里。根據計劃,深圳市有望發放第一張智能網聯汽車正式號牌和核發第一張智能網聯汽車出租車道路運輸許可,在自動駕駛的道路上繼續先行。
經驗喜人,前途光明,如今的智能網聯已經無限接近完全意義的自動駕駛了,政策也在不斷地鼓勵,但是頂層法律規范依然停留在多年之前。當前,各國政府都企圖在智能化時代到來之際拔得頭籌,歐美等多個發達國家已經對自動駕駛汽車進行立法規制,并嘗試推動自動駕駛汽車成為競爭型產業。例如,德國2021年發布的《自動駕駛法》為自動駕駛技術運用于實際場景提供法律依據和監管框架;美國2022年發布的《無人駕駛汽車乘客保護規定》不再要求全自動駕駛汽車配備手動駕駛控制裝置等。
今年全國人代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馮興亞就在建議中指出,自動駕駛相關規定目前多停留在政策層面,立法相對滯后,其中原因不乏是自動駕駛相關頂層設計牽涉眾多法律法規,例如交通安全法規方面的駕駛員與機器的責任劃分就是一個較為棘手的制度設計。然而,自動駕駛企業以運輸經營者身份使用自動駕駛汽車在道路上從事客運、貨物活動的商業化運營模式則可一定程度上避免駕駛員與機器責任劃分問題。因此,盡快推動自動駕駛汽車的商業化運營試點,是其全面量產上路前的有益探索。
2022年8月,交通運輸部發布了《自動駕駛汽車運輸安全服務指南(試行)》(征求意見稿)。但該服務指南還是難以作為自動駕駛汽車商業化運營的法律依據。原因是部分條款與上位法規定存在沖突,例如服務指南明確了自動駕駛汽車上路的合法地位,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卻規定汽車上路必須由人駕駛。由于服務指南僅為部門規章,法律效力位階較低,與上位法沖突時只能讓位于上位法。
即便是地方性法規,也多為原則性規定,在商業化運營方面的具體規定也并不明顯。例如《深圳經濟特區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條例》已經是我國首部規范智能網聯汽車管理的法規,也僅是提及“探索開展商業化運營試點”。至于運行規則,基本上還是各個企業自己在小心謹慎探索,邊試邊改。
正如深圳現在的實踐一樣,我國已有部分企業開始嘗試小規模自動駕駛汽車商業化運營,隨著《關于開展智能網聯汽車準入和上路通行試點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見稿)》的發布,國家也在積極推進自動駕駛汽車商業化運營的嘗試。現階段,還需要國家層面對自動駕駛汽車商業化運營進行立法探索和制度建設,以推進自動駕駛汽車商業化運營依法、有序地整體發展。
自動駕駛的發展背后是狂飆突進的科技發展在驅動,尤其是伴隨人工智能的興起,已經完全改變了當下產業與社會運行規則的方方面面。傳統的法律只是對某個領域的、有可見邊界的行為規范,是具體行業的專家與法律人士就能下定義、定規則的。如今一旦涉及到智能化、自動化的層面,常常都要顛覆曾經的社會形態的邊界,甚至還要做出人與非人、人與機器、現實和虛擬之間的倫理設定與交易準則,需要更加宏觀與前瞻的視野進行制定。
因此正如人大代表建議的那樣,自動駕駛汽車的運行涉及到汽車設計者、汽車生產者、自動駕駛軟件供應商等多個不同主體。這種情形下,它不再是一頭管好產品標準,一頭管好道路交通運行,然后兩套法律就能輕松銜接。人-車-路-云-城,將前所未有成為一個結合體,虛擬與現實,控制者、駕駛員和乘客的關系,都將有別于普通汽車的運行規則,應當在立法的基礎上制訂一套能夠體現自動駕駛汽車特點的、獨立的運營規則。因此在肯定自動駕駛汽車的合法性主體地位的基礎上,還要制定自動駕駛汽車的商業化運營的特殊規則,才能為當下智能網聯汽車企業的商業實踐提供行為指導。在這個過程中,人大更需要結合現實、借鑒國外、更具前瞻地推動立法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