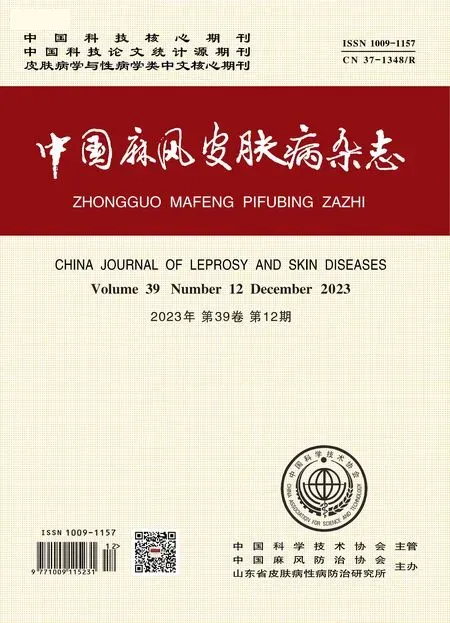界線類偏瘤型麻風伴神經炎和難治性Ⅱ型麻風反應一例
黎 靜 寧 寧 許宗嚴 關 楊 李祥子 李 超 薛浩澤 黃俊新 蔡于茂
1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性病麻風病防控科,廣東深圳,518020;2深圳市皮膚病防治研究所,廣東深圳,518020;3深圳市福田區慢性病防治院皮膚科,廣東深圳,518110;4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皮膚科,廣東深圳,518020
麻風是一種由麻風桿菌引起的慢性傳染病,主要損害皮膚和周圍神經,如治療不及時、不規范,可造成四肢、眼等漸進性、不可逆的畸殘。自WHO推薦使用并免費提供聯合化療方案以來,全球麻風患病率迅速下降,目前我國麻風患病率和發病率都達到歷史上的低水平,深圳市早在1996年就實現了基本消滅麻風,并長期維持低流行狀態[1-3]。麻風尚無有效的疫苗,早期發現和規范治療仍是當前控制麻風流行和預防畸殘發生、發展的基本原則[1]。本報道期望通過對1例界線類偏瘤型麻風伴神經炎和難治性Ⅱ型麻風反應患者發現及診治經過進行分析,為麻風早期發現和治療控制提供經驗。
臨床資料患者,女,40歲,廣西省崇左市人。患者自訴2016年3月無明顯誘因左小腿出現數個疼痛性紅斑,在外院骨科診斷為“血管炎”,用潑尼松治療后好轉,約2個月后雙下肢又出現數十個類似疼痛性結節,自覺肌肉疼痛,無發熱,外院皮膚科診斷為“結節性紅斑”,予潑尼松及其他輔助性藥物(具體不詳)治療后好轉。2016年7月患者曾回原籍皮防機構就診,接診醫生懷疑麻風開具麻風組織液涂片檢查,因查抗酸桿菌結果為陰性,未診斷麻風。之后病情反復發作,先后19次于外院就診,均按“結節性紅斑”給予潑尼松、復方甘草酸苷片、沙利度胺及抗組胺藥物治療,一般治療7天后皮損可消退。2017年起皮損逐漸擴散到上肢和背部。2018年7月因“胸前和腹部出現不痛不癢的環狀紅斑、自覺左足底增厚感”于外院就診,病理檢查結果懷疑麻風,轉診至我院進行專業排查。患者自幼生活在原籍,1999年2月開始定居深圳,否認傳染病史和麻風家族史,同住3人健康狀況良好。
皮膚科查體:面部、耳垂、軀干散在分布大小不等的丘疹、結節和邊緣欠清晰的淡紅斑及半環狀紅斑;四肢散在性分布大小不等、數量較多的紅色及暗紅色結節和色素斑,可觸及較多黃豆至花生米大小深在性結節;雙足底暗紅斑,少量片狀脫屑,左足底干燥及角化過度(圖1)。無毛發脫落;右尺神經粗大,無觸痛及壓痛。雙手掌、右足底觸覺正常,左足跟至第3、4、5足趾區域觸覺遲鈍;運動功能檢查正常。
實驗室檢查:血常規、尿常規、肝腎功能未見明顯異常;皮膚組織液涂片檢查抗酸桿菌:左眶上4+,左耳垂4+,下頜4+,左上肢皮損4+,左腹部皮損4+,左小腿皮損4+,細菌密度指數(BI)為4.0。組織病理示:(右上臂皮損)真皮內見巢片狀分布的細胞,可見纖維分隔,細胞胞漿泡沫樣,含可疑黏液,細胞核形態溫和,散在少量淋巴細胞;(右肘部皮損)表皮鱗狀上皮細胞分化尚好,輕度角化過度,基底層色素沉積,真皮及皮下組織見淋巴細胞、漿細胞、泡沫樣組織細胞浸潤,可見灶狀纖維素樣壞死、抗酸染色局灶見弱陽性的桿菌結構,考慮麻風(圖2)。
診斷:界線類偏瘤形麻風伴神經炎。
治療:患者因HLA-B*13:01檢測陽性,無法接受氯苯吩嗪導致的色沉,主要采用MDT替代方案(利福平600 mg/月,莫西沙星400 mg每日1次)進行治療。患者確診時伴有神經炎,同時給予潑尼松(早上30 mg,下午10 mg)治療。治療1個多月后,手臂出現疼痛的結節性紅斑,考慮發生II型麻風反應,加用沙利度胺50 mg每日2次維持治療。持續治療5個月后,右側尺神經、雙側腓總神經仍粗大,但右側足底麻木癥狀消失,遂停用潑尼松。治療期間,疼痛的結節性紅斑每月發作1次,每次出現1~2個疼痛的結節性紅斑。治療滿4年后,鑒于沙利度胺累計用量超過50 g,為避免發生中毒性神經炎,停用沙利度胺,改用雷公藤10 mg每日3次治療。20天后,雙腿出現數個疼痛的結節性紅斑,并觸及近20個黃豆至花生米大小皮下結節,遂加用潑尼松10 mg/d×10天,因控制效果依然不佳,改為甲潑尼龍晨服16 mg、下午服8 mg,治療3天后改為每日晨服16 mg。本方案治療7天后,結節性紅斑逐漸消退,但停藥后很快復發。遂將方案調整為每當有新疼痛性結節出現時,甲潑尼龍第1天40 mg、第2天30 mg,后20 mg維持治療7天。必要時加服沙利度胺50 mg每日3次,皮疹消退即停藥。療效評估:治療4年后,細菌密度指數降至2.17,確診時皮疹也已基本消退。但四肢仍反復出現疼痛的結節性紅斑。患者停用沙利度胺后,疼痛的結節性紅斑發作頻繁,使用甲潑尼龍能控制,但減量后易復發,仍需長時間維持治療。
討論該患者臨床皮損表現多形性,給麻風的診斷造成混亂,四肢出現麻風性結節性紅斑與皮膚血管炎皮損易混淆,曾被誤診為血管炎,還長期輾轉市內多家醫院被誤診為結節性紅斑。結節性紅斑是界限類偏瘤型麻風常見的臨床表現之一和誤診診斷[4-7]。麻風的延誤診斷被認為是麻風患者畸殘發生發展的重要危險因素,麻風的延誤診斷包括病人就診延誤和醫療機構診斷延誤[8],該患者主要以醫療機構診斷延誤為主。表明相關醫務人員對麻風的臨床表現和麻風癥狀監測“8條疑似癥狀與體征”的核心內容缺乏認識。研究顯示,重視提高患者、社區和相關醫務人員對麻風的認識有助于及時轉診和早期發現[9]。此外,該患者在原籍進行皮膚組織液涂片檢查抗酸桿菌陰性,這可能與取材部位選取以及檢查者的技術有關。本患者最終確診得益于皮膚組織病理檢查,建議對病期長、久治不愈的皮膚病患者及早進行實驗室檢查[10],尤其是皮膚組織病理檢查,以輔助診斷。
氨苯砜是治療麻風感染的首選藥物,但大約有0.5%~3.6%接受過氨苯砜治療的患者會出現氨苯砜過敏綜合征,HLA-B*13:01基因已被國內外研究證實與氨苯砜過敏綜合征發生密切相關[2,11,12]。氯苯吩嗪具有抗麻風桿菌、抗炎及預防麻風反應的作用,但治療過程中會引起皮膚色沉,是阻礙患者使用WHO推薦的聯合化療方案的重要原因[13]。本例患者抗麻風治療使用莫西沙星替代氨苯砜[14]、未同時使用氯苯吩嗪的聯合化療方案,經過4年余的治療,原發皮損基本消退,細菌密度指數有所下降,說明替代治療方案有效。該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出現反復發作的II型麻風反應,這可能與患者未使用氯苯吩嗪有關。目前認為II型麻風反應(麻風性結節性紅斑,ENL)為血管炎型或免疫復合物型變態反應,常見于瘤型麻風和界線類偏瘤型麻風患者,是疾病進程中由于免疫狀態的改變而突然發生的病情加劇,可導致進一步的神經損傷和不可逆的畸殘[15,16]。一項文獻綜述顯示發生麻風反應患者比沒發生麻風反應患者致殘的幾率高2.43倍,及時有效治療可以預防神經病變和殘疾[17]。研究推薦沙利度胺聯合潑尼松作為治療重度II型麻風反應首選藥物[18],該患者使用沙利度胺聯合潑尼松能夠緩解II型麻風反應,但減藥停藥易復發。研究提示還需謹慎考慮沙利度胺使用過量的不良反應[17],該患者停用沙利度胺使用雷公藤聯合甲潑尼龍控制II型麻風反應效果同樣不理想。麻風性結節性紅斑對麻風患者的身心健康產生較大負面影響[19],仍需積極探索可替代的II型麻風反應治療控制策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