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薩的社會加速理論與中國的“躺平”現象
□陶東風
【導 讀】 西方現代知識理論常被中國學者作為發現和診斷中國問題的工具。但若不對具體的歷史情境做考察,則易導致對中國特有經驗的粗暴切割。本文通過對中國學界以社會加速理論分析熱點文化現象“躺平”的冷思考,觀照當下人文社會學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
在學術研究和知識生產日益全球化的時代,東西方知識的跨國旅行在所難免。不但中國傳統知識在西方的介紹與傳播常常可以激活西方思想家對自己社會的創造性思考和發現,西方的現代知識更已成為中國學者發現和診斷中國問題的不可或缺的理論工具箱。這種現象被一些學者稱為中西方文化和理論的“互鑒”。
在思考“互鑒”問題時,人類學家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概念可以給我們以啟發。這個術語與后現代主義對宏大敘事的質疑、后殖民主義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聯袂而行。它產生于吉爾茲本人豐富的民族志研究以及田野作業,以特殊主義、反本質主義的知識論挑戰了普遍主義、本質主義的人類學知識構造。普遍主義人類學的宗旨是發現人類文化的共同結構或普遍規律,而吉爾茲的特殊主義的人類學或詮釋人類學則強調各種不同文化、知識之間的差異性,致力于發現西方知識之外豐富多彩的“地域性”知識。詮釋人類學強調:任何科學共同體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一種局域性的情境之中,帶有歷史的成見。于是,描述知識生產的特定歷史情境,意識到導源于這種情境中的知識效度,就變得非常重要。正是由于知識總是在特定情境之中生成并且得到辯護的,因此我們對知識的考察應該著眼于其得以形成的具體情境條件以及源于這種條件的效度。
當我們援引西方知識來發現和解釋中國問題時,上述警示顯得尤為重要。從晚清、五四時代開始,借助源源不斷進入中國的西方理論來分析中國社會文化的各種問題,已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難以避免的一種潮流和傾向。但這樣做的一個可能后果,是用西方理論特別是以反思現代性為特征的西方批判理論,來強制闡釋乃至粗暴宰割中國的經驗。
我以為,目前學界對于當下社會文化熱點現象“躺平”的討論就存在這樣的問題。
二
在時下分析“躺平”(還有稍稍早于躺平的“佛系”等現象的文章中,使用比較多的理論資源無非兩種:一種是西方的現代性反思/批判理論,比如,形形色色的后現代理論、批判理論、低欲望社會理論(參見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會》)、社會加速與新異化理論(參見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后物質主義理論(英格爾·哈特)、倦怠社會理論(參見韓炳哲的《倦怠社會》)、慢生活理論(參見盧茨·科普尼克的《慢下來:走向當代美學》)、“優績制暴政”/賢能主義暴政(Meritocracy)理論 [見桑德爾的《優績的暴政》(TheTyrannyofMerit),也可翻譯為“賢能的暴政”,英文版2020年9月],等等。這些理論盡管存在內部差異,但其共同點是對現代社會及其發展主義、進步主義、消費主義等價值觀的反思和批判。另一種是中國老莊、禪宗的前現代思想資源(無為而治、淡泊逍遙、出世退隱)。這里我要分析的是前者,我選擇的主要是羅薩的社會加速與新異化理論。

法蘭克福學派第四代主將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在他的《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鄭作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等書中提出了“社會加速理論”。國內不少學者將之運用于對“躺平”現象的分析,認為“躺平”乃是對加速社會的或積極或消極的反抗。認為“躺平”現象是當下中國青年一代對羅薩所描述的加速這一現代社會支配性時間規范的反抗,“躺平的身體是加速社會中忽然停滯與靜止的身體,它似乎以身體化的姿態宣告了對于社會化的拒絕”。
現代社會的重要特點之一確實是加速,從科技創新加速到社會變遷加速,再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節奏加速,加速看起來確乎是當代人十分真切的感受。其中有些加速是具有普遍性的,比如,科技創新的加速可以說將整個現代世界都卷入其中。因此這本書對于我們診斷、分析中國的躺平現象無疑具有啟發性。但同時必須指出:在當下中國,對所謂“時間體制”產生支配性影響的因素不完全與西方相同,支配時間的不只是科技創新邏輯、經濟發展邏輯或資本運轉邏輯,還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邏輯。同樣,中國當代青年選擇躺平的深層原因,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加速”能夠概括的。
首先,就躺平與競爭的關系看,躺平表面看來就是退出競爭、不求發展,從而擺脫加速的邏輯。如果我們不是停留于似是而非的人類天性解釋(喜歡退出競爭是人類的天性,不管東方還是西方,古代還是現在),而是追問當下中國躺平這種人生姿態的具體社會文化原因,我們就必須深入分析一下他們為什么恰恰在這個時候退出競爭,他們退出的到底是什么樣的競爭。在羅薩的分析框架中,西方社會的加速動力中的第一個就是競爭。“一般的社會加速,以及特別是科技加速,是充滿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后果。”[1]31結合上下文可知,羅薩說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中的競爭,顯然是公平正義的自由競爭。羅薩指出,所有社會都有自己分配資源、物產、財富乃至特權、地位、社會身份的標準。在前現代社會和非現代社會,常見的分配模式是“由團體歸屬所預先決定的”。所以,“如果一個人生而為王、為農夫,或為騎士,那么這個人所會獲得的承認,所能夠使用的特權、權力,以及財貨,一出生就或多或少被決定好了”[1]31。這種前現代的等級化分配原則,其實我們一點也不陌生(從20世紀70年代的工農兵大學生到現在的“富二代”,都是由他們的“團體歸屬”預先決定的)。改革開放的進步性標志之一,就是要告別這種以“團體歸屬”定終身的等級制,但這個告別的過程是漫長的。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它扭曲了我們,特別是青年一代的競爭環境,阻礙了中國進入一個符合公平正義之競爭原則的現代社會——因為這種前現代的等級制就是被政治現代化打破的。正如羅薩說的,從現代性的觀點出發,這種前現代的分配方式既沒有效率,更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身份等級制度打破后,才有了自由競爭,“在現代社會的生活當中,幾乎所有領域最主要的分配原則,都是競爭邏輯”[1]32。這里的“競爭”指的顯然是建立在公平正義原則之上的競爭。這個原則不僅適用于經濟領域,也適用于政治(如競選)、科學(如教授職位的晉升和科研項目的獲得)、教育以及日常生活等各個領域,“教育程度、工作地位、收入、炫耀性消費、子女的成就,乃至于婚姻與人脈的獲得和維持,這一切無不是在競爭”[1]32。換言之,“人在現代社會當中所占據的位置,已經不是按照出身來預先決定的,在人的生命歷程當中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永遠的競爭協商”[1]33。很顯然,羅薩筆下作為現代社會加速動力的競爭,在我們這里正是需要爭取而沒有充分實現的制度環境,它當然不可能是中國式躺平的原因。就我所知,很多選擇躺平的中國年輕一代并不反感和拒絕競爭本身,而是反感和拒絕中國式的不公平、不公正“競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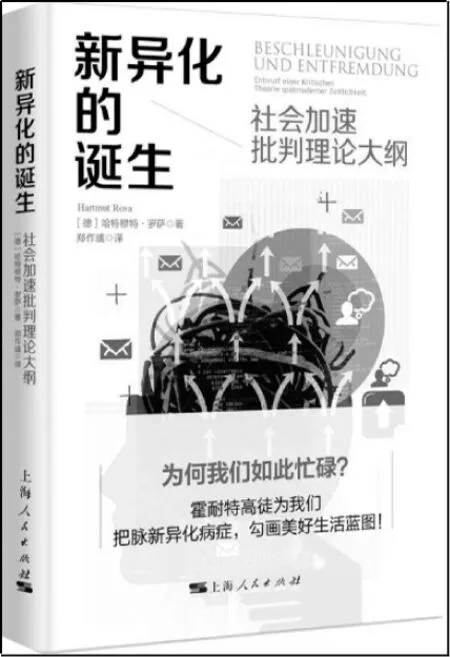
說到這里不得不提及:有人用美國哲學家桑德爾對于“優績制/主義”的批判來分析躺平現象,認為對于躺平主義者來說,躺平是“對今日社會主流體制‘優績制’ 的抵抗”。這個觀點與把競爭不加分辨地視作躺平的原因一樣忽視了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優績制或所謂賢能主義,是與以出身為基礎的前現代等級制不同的社會升遷機制,其核心是讓那些勤奮而又受過良好教育、才華出眾的人獲得升遷的機會。我們長期以來爭取但到現在還沒有充分實現的,不就是它嗎?至于說到優績制也會造成兩極分化,這或許是西方國家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桑德爾《優績的暴政》所要批判的主要問題,但不是我們面對的主要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確實也有大量對于加速社會的反思,對低欲望社會、慢生活或躺平的向往。因為即使在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中,也有一些人不愿意為了獲得地位和財富而過高度緊張的生活,但其原因并不是因為前現代的等級制剝奪了他發展的可能性。
三
羅薩還分析了西方社會發展和變化的無意義、無方向感,一種忙忙碌碌又“原地踏步”的感覺,“無頭蒼蠅般‘狂亂的’ 變化”[1]54,并對其原因進行了分析。羅薩指出,一般講到有方向的動態變遷,是指變遷的各個階段結集成一個成長的、進步的歷史敘事/故事;而“原地踏步”或“無頭蒼蠅般‘狂亂的’ 變化”,則是因為各種變化紛至沓來又沒有意義、方向和相互聯系。這實際上就是當代中國人都能體驗到的所謂“抓狂”。但中國和西方的情況仍然不同:西方社會的“原地踏步”被羅薩稱為“結構惰性”“文化惰性”:(民主自由的歷史已經終結,變化只是表象。“古典”現代性時期確立的那套制度、規范,到了“晚期”現代性階段停止不變了,“人們體驗到文化已經從有目標方向的變遷(進程),轉變成狂亂片段的單純改變”。[1]54-55但我們的情況是:羅薩所謂的“古典現代性”還沒有實現,社會基本結構依然如故,又何來歷史的“終結”?我們不是已經到達了我們的目標,然后陷入了變化無窮又沒有進步的狀態(“疾速的靜止狀態”)。我們的加速變化之所以不再是一個連貫的有意義的“進步敘事”,原因不是這個敘事完成了,而是這個敘事遇到了阻力。我們的變化本來是“有方向感的”,但是這個有方向感的進程中斷了,于是才陷入了無頭蒼蠅般的“疾速的靜止狀態”。某些人感到每天忙得不可開交,但又極度空虛無聊,原因不是他們的目標都已經實現了,而是他們被迫在與他們的目標相反的方向上連滾帶爬、疲于奔命、手忙腳亂。
某些人“抓狂”“無頭蒼蠅”般的感覺,實際上就是源于中國特色的加速。他們的大量時間浪費在大量無謂的瑣事上。事實上,很多領域不但沒有加速,而且在減速。凡權力任性之處,社會發展的速度無不受到嚴重制約甚至停滯不前。這恰恰是羅薩的加速社會理論或其他西方社會批判理論無法解釋的。
四
現代性的承諾本來包含了個體自由和自主性。甚至可以說,自主性觀念是現代性規劃的核心:“我們身為主體,不應讓我們無法控制的政治權威和宗教權威,預先決定了我們該如何過我們的生活:不論是國王還是教會,還是在家庭里,政治領域里,職業生涯里,藝術、文化、宗教里,都不該如此。這一切都應該交回個人手里。”[1]106在羅薩看來,個人獲得自主性的過程與社會加速至少理論上是不矛盾的,甚至是相輔相成的,因為“個體若要實現自主性,必須超越穩固不變的社會秩序,不讓社會階級或社會身份(以及政治權威和宗教權威終身固定下來,也不要讓社會階級或社會身份就這樣一代接著一代地再生產下去”[1]108。只有打破固化的社會等級才能有公平競爭,而后者恰好就是加速社會的動力。但羅薩認為事實不是如此,社會加速發展有助于增強自主性這個信念在西方破滅了,原因是對大多數人而言,工作條件和游戲規則不是自己規定的,人們好像有很多自主性,但其貌似自愿的選擇常常是不由自主的。這就是羅薩所謂的加速社會的異化,這是一種“我們所做的事情(即便是我們自愿做的并不是我們真的想做的事的狀態”[1]127。比如,我想寫我的書,但實際上我沒有寫,我的時間都用來看電視或處理郵件了。這里我不想糾纏到底如何鑒別“真正想之事”和“實際做之事”的差別(我認為無法區分。一個人因為看世界杯而耽誤了寫論文,然后又說自己其實不想看世界杯。我覺得這是十足的矯情),我只想指出:羅薩也承認這種“不得不做”之事盡管不是自己想做的,但畢竟不是被逼的。反觀我們自己,我們根本就沒有“自愿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的奢侈,因為我們的苦惱是我們是被迫去做大量不想做的事情。盡管都是做不想做的事情,但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被迫的。這個差別不可謂不大。以高校青年教師為例。這個被稱為“青椒”的群體或許是中國最為焦慮的群體之一,而這種焦慮很大程度上來自中國特色的科研量化考核制度(把考核、職稱晉升等與論文的數量、刊物的等級、項目的數量與級別、獲獎的數量與級別等緊密而機械地捆綁在一起),我很難想象西方高校的教師會有同樣性質的焦慮。
結語
總之,如果說加速就是單位時間內要處理的事情、發生的事件越來越多,情感和經驗的數量越來越多,其變化的頻率越來越快,那么,在當下中國,導致加速的很多因素是帶有中國特色的,正是這些中國特色的“加速”導致了中國特色的時間焦慮,致使很多人選擇了躺平或者希望躺平而不得(近年來總聽到高校教師抱怨日子過得艱難,有些甚至發出了“退出學術界”的聲明,但他們很少將矛頭對準羅薩意義上的“加速”)。
由于西方的現代性反思有自己的語境,而中國的現代境遇、現代化道路和西方國家又差別很大,所以不加反思地運用羅薩的加速社會理論或其他西方的現代性反思理論,可能忽視中國現代性的特殊性,走向抽象的(脫離中國國情的現代性批判。中國今天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是:所有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包括“佛系”“內卷”“躺平”等網絡流行語及其傳達的重要信息,都必須納入深入的社會分析尤其是制度分析才能抓住要害,準確揭示其內涵,并給出具體而有效的解決方法。但恰恰是這個人文社會科學有效知識生產的基本條件尚待爭取,于是只好王顧左右而言他,或者將整個“現代性”推到審判席上進行審判。有些指責“躺平”者沉溺于幻想的論者振振有詞地寫道:“人有與生俱來的責任和義務,無論你躺或者不躺,它都在那里;每個月的房租、房貸、水電費等,無論你躺或不躺,它也在那里。‘躺平’,并不能消解生活的困難,它所提供的只不過是逃避真實生活時的快意和心靈慰藉。”[2]需要追問的是:造成房租、房貸等“實際問題”的難道僅僅是年輕人奮斗不夠、吃苦耐勞精神不夠嗎?中華民族素以吃苦耐勞著稱,怎么恰恰在這個時候沒有了這種精神?在我看來,回避分析高房價背后的復雜社會原因,而訴諸所謂“人有與生俱來的責任和義務”(這個說法本身就邏輯不通,人的責任和義務并非“與生俱來”的生物屬性,而是歷史和文化建構的社會屬性),是避重就輕,也是根本不能解決問題的。
避實就虛,避重就輕,這樣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當然不會有什么學術意義和實踐意義。
注釋
[1][德]哈特穆特·羅薩.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M].鄭作彧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陳兆平.“內卷”和“躺平”:網絡熱詞的情感表達[N].國家電網報,2021-06-1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