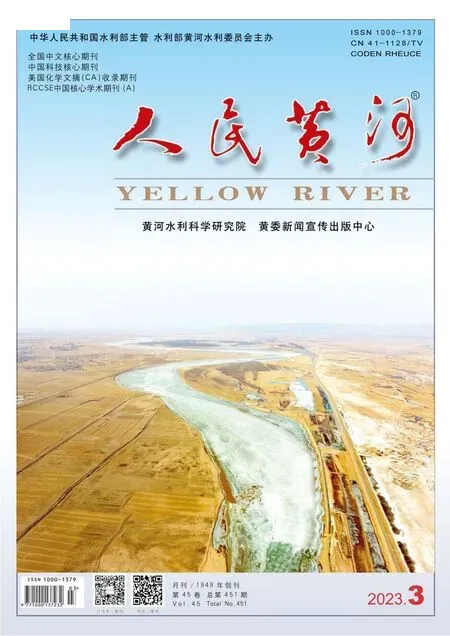黃河流域水貧困評價及時空分異特征研究
牟牧戈,穆 蘭,湯鶴延
(陜西師范大學 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陜西 西安 710119)
2019 年9 月18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1]。2021 年10 月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堅持“量水而行、節水優先”的原則,把水資源作為最大剛性約束,促進黃河流域人水關系和生態環境全面改善。因此,基于水貧困理論合理評估黃河流域水資源短缺現狀及發展趨勢,對于保障黃河安瀾,實現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水貧困已經成為全球繼經濟貧困之后的第二大貧困問題,引起各國政府與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2]。為研究評價水貧困問題,Sullivan[3]、Lawrence 等[4]提出了水貧困指數(WPI)模型。WPI模型作為一種多學科綜合性工具,從多維度對水貧困進行衡量,在實證分析中作為經典理論模型被廣泛使用。筆者借鑒Sullivan的定義,將水貧困視為一種水資源供給不充足、不穩定情況下的社會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社會缺乏可供使用的水,或缺乏獲得水的能力、權利。國內外學者對水貧困問題的研究已有相當豐富的成果,在理論層面,對水貧困的定義與計算不斷發展與完善[5-6],并在水貧困變化趨勢[7]、水貧困評價[8]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在實踐層面,發現水貧困問題對地區農業發展[9]、人民福利[10]等造成顯著影響,改善水貧困問題是區域高質量發展與人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橋梁。學界對中國不同地區的水貧困問題開展了豐富的研究[11-12],從多個角度深入研究了水貧困與其他因素的耦合協調關系[13-14],但現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水貧困指標體系構建、水貧困評估及減緩對策,而對黃河流域水貧困時空分異的研究相對較少。
鑒于此,筆者構建黃河流域水貧困評價指標體系,測算黃河流域水貧困指數,提出水貧困影響因素,同時借助標準差橢圓等方法,從多個角度描述黃河流域水貧困空間分布特征,以期為黃河流域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及水貧困“減貧”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
1 研究方法
1.1 WPI 模型
從資源、設施、能力、使用和環境5 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WPI由各個指標加權計算得出,計算公式為
式中:WPIj為第j個維度的水貧困指數;wi為第i個指標的權重;yij為第j個維度第i個指標的標準化值。
確定合理的指標權重是全面評估水貧困的關鍵。為避免主觀賦權法的隨意性,本文使用熵權法確定指標權重[15]。為了使WPI值的大小能夠代表水貧困的嚴重程度,即值越大水貧困狀況越嚴重,首先采用極差標準化法對指標值進行標準化處理。
1.2 面板Tobit 模型
水貧困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利用水貧困模型計算得到的WPI為取值在0~1 范圍內的受限因變量。為避免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計參數時帶來偏誤[16],本文采用隨機效應面板Tobit 模型對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相對于固定效應面板Tobit 模型,隨機效應面板Tobit 模型可得到一致估計。面板Tobit 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式中:Yi?為第i個指標的潛變量;β為估計參數;Xi為第i個指標的解釋變量;εi為第i個指標的殘差項,服從正態分布;Yi為第i個指標的被解釋變量。
1.3 水貧困評價指標體系
利用WPI模型分析評價黃河流域9 個省(區)的水貧困狀況。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和數據可得性等原則[17],結合黃河流域的實際情況,從資源、設施、能力、使用和環境5 個維度選取17 個指標,構建黃河流域水貧困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水貧困評價指標體系
(1)資源維度包括水資源總量和平均水資源量兩方面內容。由于黃河流域水資源匱乏,地區水資源量主要來源于降水,因此選取年降水量對水資源總量進行評價;由于省(區)間人口及面積存在較大差異,對水資源的可用性造成影響,因此選取人均水資源量和水資源總量模數對平均水資源量進行評價。
(2)設施維度用來考量地區水資源供應量。除最大供水量外,安全生活用水也是衡量地區水資源供應量的重要指標。另外,由于黃河流域是我國重要的糧食產區,因此選取耕地灌溉面積衡量農作物灌溉用水量。
(3)能力維度主要涉及政府支持能力、用水技術及生活用水能力。其中:政府支持能力表現為財政自給率;用水技術選用地方財政科技支持率和高等學校平均在校生數來衡量;生活用水能力為購買安全生活用水的能力,選用恩格爾系數來衡量。
(4)使用維度包括用水效率與用水結構兩方面內容。選用每公頃耕地用水量衡量農業用水效率、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衡量工業用水效率,用水結構采用信息熵進行衡量。
(5)環境維度包括生活環境中可能影響水量或水質的生態因素和人為因素。選取指標為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城市污水日處理量、化肥施用量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積。
2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黃河流域以占全國2.6%的水資源量承載著全國17%的耕地面積,養育了12%的人口,創造了約14%的國內生產總值[18],具有很高的生態和經濟價值。但是受氣候條件和地理位置的影響,黃河流域長期以來干旱缺水,多年平均降水量為451 mm,天然徑流量為490 億m3,并且2001—2019 年水資源開發利用率高達80%[19]。作為我國資源性缺水嚴重的流域之一,黃河水資源無法滿足河道外用水需求,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
本文選取黃河流域9 個省(區)作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2011—2021 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水利統計年鑒》《中國水資源公報》和國家統計局數據。
3 結果與分析
3.1 黃河流域水貧困時間演變特征
黃河流域各省(區)WPI計算結果見表2,可見WPI集中在0.55~0.65 之間,說明水貧困狀況較為嚴重。2010—2020 年黃河流域WPI平均值由0.619 下降到0.573,降低了7.43%,表明黃河流域的水貧困狀況在研究期間得到了改善。

表2 2010—2020 年黃河流域9 個省(區)水貧困指數
為直觀比較黃河流域各省(區)WPI離散程度,使用Stata15 繪制了WPI分布箱形圖(見圖1)。可以看出:黃河流域各省(區)WPI分布離散程度差異較大;四川、甘肅及山東WPI離散程度較高,水貧困狀況變化較大;山西和陜西WPI分布相對較為集中,水貧困狀況相對穩定。

圖1 2010—2020 年黃河流域各省(區)WPI 箱形圖
由黃河流域各省(區)水貧困指數的時序變化(見圖2)可知,2010—2020 年黃河流域各省(區)WPI總體呈現下降趨勢。根據各省(區)水貧困指數變化趨勢,將其劃分成2010—2014 年、2015—2018 年、2019—2020 年3 個階段。①2010—2014 年為波動下降階段,該階段黃河流域各省(區)的WPI變化最大。其中:陜西的WPI由2011 年的0.612 增大到2013 年的0.640,原因是其2013 年降水量較2011 年大幅減少。在2013年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實施之后,2014 年黃河流域9 個省(區)的WPI均有所下降,反映出政策實施效果顯著。②2015—2018 年為平穩下降階段,該階段黃河流域所有省(區)WPI均呈下降趨勢,其中:四川下降5.40%,山東下降4.49%,寧夏下降2.41%,反映出該階段黃河流域各省(區)在水資源管理方面成效顯著。③2019—2020 年為穩定維持階段,該階段各省(區)WPI變化較小。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深入推進,水價水權改革有序進行,使得該階段黃河流域各省(區)水貧困狀況總體穩定。

圖2 2010—2020 年黃河流域各省(區)WPI 變化情況
3.2 黃河流域水貧困空間演變特征
基于2010—2020 年黃河流域水貧困指數的變化情況,使用ArcGIS 的標準差橢圓(SDE)功能,分析黃河流域水貧困空間分布形狀和重心坐標。從黃河流域水貧困重心偏移情況(見圖3)可以看出:黃河流域水貧困總體呈東(偏北)—西(偏南)的空間分布格局,分布在標準差橢圓內部的陜西、山西和寧夏等省(區)是黃河流域水貧困的主要地區。從圖4 可以看出,黃河流域水貧困標準差橢圓重心整體從甘肅東部向東北方向移動,2010—2020 年水貧困重心表現為東南—西北—東南方向傾斜的N 字形。

圖3 黃河流域水貧困重心偏移情況

圖4 黃河流域水貧困重心空間位移情況
利用GIS 自然斷點分級法按WPI大小將水貧困地區分為極低值區、低值區、中值區、較高值區和高值區5 種類型區,對黃河流域水貧困情況進行空間可視化分析(見圖5)。總體來看,黃河流域各省(區)水貧困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以2018 年為例:①較高值區和高值區主要分布在青海、陜西和河南。青海雖然水資源儲量豐富,但水資源分布不均、氣候環境惡劣使得水貧困嚴重[19];陜西和河南水資源稟賦先天不足,河南地下水超采較為嚴重,并且多年來農業灌溉粗放,導致水貧困難以緩解。②中值區主要分布在甘肅和寧夏。甘肅特殊的黃土丘陵溝壑地貌使得水土流失嚴重,水資源利用率低下;寧夏水資源貧瘠,但近年來在水權改革中不斷創新用水模式,并通過建設引黃灌區節水改造工程,節約輸水過程中的水量損失。③極低值區和低值區主要分布在內蒙古、山東、山西和四川。四川水資源較為豐富,不易發生水貧困。山東作為我國的農業大省,農業現代化水平高,水資源利用率較高,不易發生水貧困。山西和內蒙古水資源均較為匱乏,但水貧困指數卻相對較小,原因是山西持續開展水利扶貧,有效提高了當地居民的用水能力,2020 年農村集中供水率達96%[20];內蒙古堅持推進農業、工業和城鎮節水降損,不斷提升各領域水資源利用效率,改善了水貧困狀況。

圖5 黃河流域各省(區)WPI 空間分布
3.3 黃河流域水貧困影響因素評估
為進一步探究黃河流域水貧困的影響因素,基于現有的研究成果及數據的可得性,采用面板Tobit 模型對水貧困指數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已有研究發現,宏觀政策[21]、經濟發展[22]、技術水平[23]均會對資源環境狀況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本文在Tobit 模型中加入環境規制、經濟環境與技術發展3 個維度指標進行研究,見表3。

表3 變量選擇及說明
面板Tobit 模型表達式為
式中:WPIi,t為i地區t年水資源利用效率;β為估計系數;Xk為第k個指標的值;C為常數項;εi,t為隨機誤差。
鑒于影響因素存在比值型變量和數值型變量,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首先對數值型變量數據取對數處理,解決變量間的量綱不一致問題,以確保回歸結果的準確性。借助Stata15 軟件,對黃河流域總體水貧困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并區分上、中、下游分析影響因素的差異,結果見表4。

表4 水貧困影響因素的Tobit 回歸結果
由表4 可知:①環境規制方面,環境治理強度和環境治理效果2 個指標均對黃河流域總體WPI有負向影響,表明環境規制能夠緩解黃河流域水貧困。一方面,環境治理強度對流域總體和下游WPI負向影響顯著,而對中、上游的影響并不顯著;另一方面,環境治理效果對流域總體WPI產生負向影響,且對中游影響最為顯著。環境規制可以減少水污染、提高用水效率[24],環境約束力的提升可促進水污染治理和生態環境保護,產生正向的生態環境效益。②經濟環境方面,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和城鎮化率3 個指標對水貧困的影響并不一致。經濟規模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對流域總體WPI產生正向影響,其對下游的正向影響顯著、對上游的負向影響不顯著,表明經濟規模擴大可能加劇水貧困;產業結構對流域總體WPI有正向影響,但對下游負向影響顯著,這可能是農業種植結構不同導致的,相比于中、上游,下游高耗水作物種植面積小,有助于緩解水貧困;城鎮化率對流域總體WPI和上、中、下游均有負向影響,表明城鎮化率的提高有助于促進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減輕水貧困[25]。③技術發展方面,科研強度和科技使用2 個指標均對流域總體WPI產生負向影響。一方面,科研強度對流域總體WPI有不顯著的負向影響,其中對上、中、下游均有負向影響,但只對中游和下游有顯著影響,研究表明只有當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才會對資源環境表現出顯著的積極影響[26];另一方面,科技使用對流域總體WPI有負向影響,其中對下游負向作用最為顯著,原因是下游的河南、山東兩省農業節水技術的普及推廣使節水效果較為顯著。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 論
(1)黃河流域9 個省(區)的水貧困程度較嚴重,2010—2015 年水貧困指數波動較大,但總體呈下降趨勢。
(2)黃河流域水貧困空間分布呈東(偏北)—西(偏南)的分布格局,陜西、山西和寧夏為流域水貧困主要地區,流域水貧困重心呈傾斜的N 字形從甘肅東部向東北方向移動。流域水貧困指數區域差異明顯,較高值區和高值區主要分布在青海、陜西和河南,中值區主要分布在甘肅和寧夏,低值區和極低值區主要分布在四川、山西、內蒙古和山東。
(3)環境規制和技術發展均對黃河流域水貧困有顯著的減緩影響;經濟環境對流域水貧困的影響不一致,與上、中、下游經濟和產業發展狀況有關。
4.2 建 議
由于黃河流域水資源稟賦先天薄弱且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水貧困很難在較短時期內得以緩解。因此,應強化水貧困意識,推進黃河流域引水調水工程規劃建設,在此基礎上積極探索水權交易的各類方式,以確保流域水資源可持續利用,促進水資源合理配置。
(1)青海、陜西、河南三省水貧困狀況較為嚴重,且水貧困重心呈現向陜西西北部移動的趨勢。因此,這三省應予以重點關注,地方政府應出臺針對性政策因地制宜實施水資源減貧工作。青海應加強水利設施投入,保障水資源充分利用,防止生態環境持續惡化;陜西、河南可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用水結構,解決水資源利用效率低的問題,尋找水資源及產業發展的適宜模式。
(2)環境規制和技術發展均對水貧困有較為明顯的抑制作用,政府應繼續加強環境規制的力度,并不斷推進水利扶貧;加強技術創新,逐步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大力推廣農業節水設備和技術,特別是在河南、山東等農業大省,以噴灌、滴灌等節水灌溉技術取代傳統粗放的灌溉方式,提高農業用水效率,最大限度保障農業用水。
(3)黃河流域水貧困的緩解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首先,黃河流域各省(區)在水資源利用及保護方面應積極交流協作,通過上、中、下游共同努力保障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其次,應積極推進南水北調后續工程建設,利用外調水解決黃河流域水資源稟賦不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