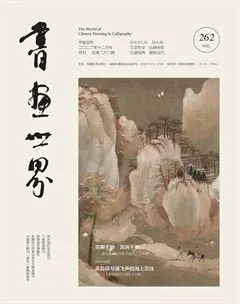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畫勞動人物形象研究
趙怡文
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以來,勞動題材的美術作品成為美術創作中的一個重要板塊,也是主題性美術創作的重要對象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勞動者的形象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影響下被全新構建,在中國畫的革新過程中,藝術家對勞動人物的認識、塑造與表達成為重要的一環。本文從革新的觀念準備與實踐的多種形式兩方面,分析勞動者形象的創新與變遷,總結其新形象特征,并對新時代主題性美術創作中的勞動者形象進行展望。
關鍵詞:勞動題材;勞動人物形象;主題性美術創作
20世紀初葉,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中國畫作為最重要的傳統畫種開始萌發革新思潮。盡管有“造成新一派”的陶冷月、建立“現代國畫”的嶺南畫派“二高一陳”,以及以《新國畫建立之步驟》拉開新中國國畫革新運動序幕的徐悲鴻等中國畫革新派的努力,但在新中國成立前,新派始終未能占據主導地位。同時,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闡述的五個問題為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1959)的文藝政策確定了基調,也為中國畫的革新指明了方向。
新中國成立初期,勞動者的形象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影響下被全新構建,在中國畫的革新過程中,藝術家對勞動人物的認識、塑造與表達成為重要的一環。分析這一時期的中國畫勞動人物形象,對新時代主題性美術創作有著積極意義。時至今日,勞動題材作品仍是美術創作中的重要板塊,也是主題性美術創作的重要對象之一。
一、生成:革新的觀念準備
中國古代典籍中,“勞動”初見于《莊子·讓王》“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1]。西方的“勞動”一詞最早見于古希臘語,后來歐洲各國也出現了與“勞動”有關的詞匯。從它們的含義看,對勞動的認識都局限性地暗含負擔、辛苦甚至是貧困的意思,勞動者更是被賦予“悲慘”“愚”“窮”“弱”等負面含義。
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讓舊中國的勞動者—在此時以農民為主,擁有了積極的新形象。如何描繪這樣的新形象,成了美術界改革須解決的問題之一。
此時的中國美術界面對新的體制、新的社會,對文藝創作有了更加強烈的體制化要求,在20世紀初就尚未解決的一些問題上(例如抗戰前后的“民族形式”之爭)又增添了新的困惑。
最先應時改革的是中國畫。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新中國畫研究會成立”,而后上海、杭州、天津、沈陽、長沙、西安等地也都成立了類似組織。美術家、文藝界領導蔡若虹在1949年5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于國畫改革問題—看了新國畫預展之后》,認為“古風古氣,古意盎然”的國畫,與新時代火熱的革命斗爭和生產勞動不相符。他認為,國畫要跟上時代,必須改革,首先要表現工農業題材和工農兵生活,要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為內容;其次是技法要改變,不要模仿古人、古畫,要注重寫生、注重寫實手法,尤其要重視人物寫生。
1953年9月24日召開的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式上,中國文藝界主要領導人周揚作了代表黨和國家文藝戰略的總綱性的發言,今天看來,這段發言對那個時期的勞動者塑造具有重要的方向性指導。他在題為《為創造更多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的報告中說:“民族畫家正在開始探索如何改進和發展中國古典的繪畫藝術的形式,使之和新的創造任務相適合。這是十分必要的。不解決這個任務,民族繪畫的優秀傳統就不能繼續發展。很顯然,群眾希望在畫中看到的首先是他們同時代的人物的形象,而不盡是那些屬于遙遠的過去的古裝仕女;群眾愛看日常生活中的美麗的花卉、蟲鳥、山水,卻不能欣賞那種遁跡林泉,沒有人間煙火氣的隱士的情調。一切不愿落在時代后面的藝術家都必須懂得并努力地適應群眾的需要和愛好。”
對勞動者認識觀念的轉變以及中國畫改革的要求給以文人審美為主導的中國畫傳統帶來了挑戰,原本服務的“文人士大夫”階層已不存,社會性質的巨變以及明確的“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總方針意味著中國畫的“服務對象”變成了人民大眾,尤其是工農勞動者。
新的塑造對象引發了中國畫改革中的著名案例:基本練習如何正確對待模特兒的問題。這個問題,時至今日仍有討論的必要與意義,特別是在當下國展畫照片成風的基礎上,我們回顧這段批評案例對勞動人物塑造的影響,有著積極意義。

朱丹在《美術》雜志上發表的《在造型藝術中怎樣塑造英雄人物—記蘇聯雕塑家托木斯基院士的談話》記錄了托木斯基的一段話:“過去藝術家手下的英雄,是根據各個不同階級社會的要求予以理想化了的。……但現在我們的英雄,就是平常生活當中的‘人。從外表看,是最平凡,同時又是最真實的人。把這樣的生活在人民中間的‘平凡英雄用現實主義的方法當作偉大的典型人物來表現,這在過去歷史上是沒有的,是破天荒的事,所以也是困難的事。”
朱丹通過托木斯基的話來傳遞對這個時期勞動人物塑造的一種觀念,這是一個前所未有地將普通勞動者作為偉大人物來進行表現的時代,也正因此,他借托木斯基之口反對美術家塑造沒有生活和感情的職業模特兒:“我認為作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藝術工作者,首先應該以最大的嚴肅性對待我們的人物,我們要洞察人們的靈魂的深處,要發現他作為人的最本質的東西。……我們必須重視對人物的選擇,要了解我們的人物,忠實于我們的人物,對他們懷著最高的崇敬和最熾熱的愛情。這樣所塑造出來的形象才是活的典型,才能深切感人,對千百萬的廣大群眾有教育意義。……一個職業的模特兒不僅沒有社會生活,就連他的個人生活也消失了,還談得上什么典型性格呢?所以單單從一個職業的模特兒身上,是表現不出生動的形象也永遠創造不出真正的‘人來的。”[2]
艾中信、倪貽德支持通過對模特兒的寫生表現其性格、思想和感情等本質特征,為創作典型形象打下基礎,但不能將自己設想的勞動人民的某種崇高的思想感情牽強附會在模特兒身上。呂斯百、王式廓等總體上支持基本練習應表達模特兒思想感情的觀點。魯兵等人的反對意見也只是強調基本練習是為現實主義藝術技巧奠定基礎的。
盡管藝術家們在藝術創作的手法與過程上有一定的爭論,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個時期,美術創作方法的主流呈現了從寫實主義到“兩結合”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軌跡。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其核心是藝術為社會主義建設、為新中國的主題服務,同時推動了“新勞動者形象”的形成。
二、重塑:實踐的多種形式
對應不同的改革訴求,畫家們進行了多種形式的實踐。
首先是對英雄人物及重大歷史事件場景中人物的塑造,這在勞動者形象塑造中最為關鍵。徐悲鴻的巨幅中國畫《在世界和平大會上聽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是其中的典型。根據古元的回憶,徐悲鴻在現場畫了速寫,又以著名攝影家石少華的攝影作品為基礎,描繪出了當時的場景。和我們今天許多“復制”照片的作品不同,這幅作品散發出鮮活而熱烈的情緒,與他創作的《巴人汲水》(1937)形成了鮮明對比。1937年,南京淪陷,跟隨中央大學入蜀的徐悲鴻每日坐船去上課,目睹了百姓生活之艱辛困苦,因而有感畫下《巴人汲水》,并題詩:“忍看巴人慣擔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盤中粒粒皆辛苦,辛苦還添血汗熬。”
同樣是逾三米的豎幅狹長畫面,《巴人汲水》中勞動者困苦的形象、嘉陵江百丈懸崖的陡峭,以及所題詩作都讓觀者感到悲苦,而《在世界和平大會上聽到南京解放的消息》一圖則充滿了歡樂與振奮的氣息。他以中國水墨描繪出中國繪畫史上從未有過的眾多人物場景,畫面上中外人物百余位,不但描繪了郭沫若、田漢、馬寅初、鄧初民、翦伯贊、丁玲、肖三、古元等文化名人,還為中國外交事業的精彩開端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寫照。
王盛烈的《八女投江》(圖1)中,江水占了畫面的大半,他巧妙地借鑒了馬遠《十二水圖》中的“層波疊浪”,展現出傳統中國畫的筆墨技巧,而人物則以明暗勾勒出立體感,與水形成鮮明對比。黑色的巖石、暗沉的天空襯托出英雄的悲壯。而八位女戰士仍然都背著槍支,甚至還在不斷反擊,被風吹動揚起的頭發是不屈靈魂的化身。這樣看似絕境中仍然不放棄希望的堅定無畏、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令觀者為之鼓舞,為之振奮,也成就了它在中國畫改革中里程碑式的意義。
普通勞動者的形象塑造主要集中在工農群體。蔡若虹注重寫實的要求,在諸多作品中都有所體現,如葉淺予《夏天》(1953)里的種玉米的老農、周昌谷《兩個羊羔》(1954)里的女牧民、方增先《粒粒皆辛苦》(圖2)里拾麥穗的農民、趙望云《開采礦石》里的工人(1958)、許勇年《群眾的歌手》(1964)里的勞動者群像等,中國畫里的勞動者肖像、群像以及場景都已經脫離了工農舊有的形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些勞動者形象不但有新的面貌,更具備新的品質,反映出他們政治覺悟與勞動熱忱的提高。這些勞動者身上的品質被視為革命最重要、最寶貴的果實,是藝術創作中首先要加以反映的。
特別是為了表現“婦女的解放和整個社會的改革不可分地聯系著,正是在劇烈的社會斗爭中培養了和鍛煉了新的婦女的獨立的勇敢的性格”的現狀,女性勞動者參與社會工作的形象與場景,受到了藝術家們的喜愛。不同職業的女性工作者的獨立肖像得到了藝術家們的高度關注。程十發《歌唱祖國的春天》(1956)將歌唱的農民婦女形象作為畫面的中心與主角,其人物形象在畫面中最為高大突出。單應桂《當代英雄》(1960)更是將女性工人修筑水渠作為主題,畫面展現的高舉錘子鑿石的形象充滿了力量,顛覆了以往的婦女形象,更大膽地將畫面最主要的兩個人物都設置為女性。

少數民族的新生活也是畫家們重點描繪的對象,這種偏好延續到了今天的中國畫創作中。其中一部分與婦女形象結合,如聶南溪的《藏女》(1956)中藏族女性的穿著并沒有傳統藏族貴族女性的華麗,也沒有過多的首飾,衣著顏色樸素,只戴了串珠項鏈,但是神情松弛自然。畫家通過對一位西藏普通婦女閑適狀態的描繪,展現出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當地勞動婦女的新生活。另一部分則主要描繪少數民族群眾幸福生活的場面。以包世學《那達慕的冠軍》(1963)為代表的系列畫作生動地呈現蒙古族傳統賽事的同時,以群像的方式刻畫了蒙古族男女老少的新面貌。他的畫面特別設計了軍民一家其樂融融的場景,他后來的《那達慕組畫》《科學家到草原》也都描繪了這種漢蒙一家親的場景。葉淺予的《中華民族大團結》(1953)則成為思想與技藝皆達到極高水準的、表現各民族勞動人民形象的作品。
勞動人民接受思想教育、提高知識水平不但是勞動者文化生活改善的體現,還是新的人民的文學藝術建立的一種隱喻。朱鳴岡的《憲法草案公布了》(1954)、陸儼少的《毛主席的指示到達了田頭》(1955)、蔣兆和的《讀報》(1956)等作品中均表現了農民自主學習的形象和場景。在后來的近十年間,這個題材被更具象化地展現。方增先的《說紅書》(1964)便是其中的代表。從《粒粒皆辛苦》到《說紅書》,方增先個人作品中勞動者形象的變遷展現了他適應新時代對勞動者主題表達的探索與嘗試。相較于《粒粒皆辛苦》,《說紅書》作為十人群像明顯更加復雜。他卻放棄了明暗,只對人物面部、手部進行簡單渲染,沒有復雜的細節,每一筆都在表現結構。這幅探索中集大成的作品,雖然至發表時他本人還不甚滿意,但仍然被視為浙派人物畫風格最成熟的作品,且在群眾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較為特殊的主題作品,即以古喻今,通過描繪一些古典的故事與場景,將其作為新中國的“故事新畫”。徐燕孫的《兵車行》、任率英的《嫦娥奔月》系列等都改變了舊仕女畫中追求的弱不禁風的病態美,將勞動女性作為參考描摹對象,創造出符合勞動者審美的仕女形象。這也是對勞動者形象再塑造的一種投射。
三、對當代勞動人物創作的啟示
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作品與20世紀30年代、40年代作品進行對比,可以發現,三四十年代的勞動者形象沿襲傳統的認識,仍是表達勞動“辛苦”“負擔”“貧困”的側面,即便是一些較為輕松的場景,也透露著對勞動者的“俯視”。到了探索期,美術家們筆下的勞動人物轉變為“歌頌”對象,不再強調其“苦難”。
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經濟建設百廢待興,勞動者以“工農為主體”,當時的核心價值是“為工農服務”。這一時期的勞動者形象相對比較單一,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勞動生產者知識學習場景的描繪,其中并沒有知識分子形象的參與。這是對“勞動者”這一形象進行“窄化”的現象之一。
事實上,在當下美術作品的勞動者形象塑造中,還存在著以往出現過的問題,如勞動者形象的模式化、創作語言對描繪對象表達缺乏個性、將模特兒作為勞動者原型忽視其精神體現、過度個性化語言不符合描繪對象精神氣質等等,在當下對勞動者形象塑造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時,這些也是美術工作者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促使社會分工日趨細化,科技進步,國際影響力增強,“勞動”的內涵在不斷擴大,“勞動者”的形象更加多樣、豐滿、立體,“勞動場景”則更加豐富。可以說,在當下對勞動者形象的塑造不但呼喚更多元的表現手法,更多樣的場景呈現,也急需更多樣的切入視角。新中國剛成立時,在中國畫改革的浪潮中,對勞動者形象精神的塑造、對傳統筆墨創新性轉化的運用,以及在主題創作中對主題內涵的深入挖掘與理解都是今天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新時代是奮斗者的時代,是“人人都是勞動者”的時代。我們美術工作者也應當積極主動進行學習,更深入理解和發揚新時代的勞動精神,通過作品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為弘揚勞動精神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參考文獻
[1]莊周. 莊子[M]. 陳鼓應,譯.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326.
[2]朱丹. 在造型藝術中怎樣塑造英雄人物:記蘇聯雕塑家托木斯基院士的談話[J]. 美術,1954(2):7.
約稿、責編: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