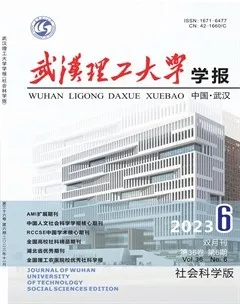國家敘事研究的理論視角、理論困境與實(shí)踐指向
唐欣羽 陳先紅
摘 要: 伴隨著二戰(zhàn)后“民族國家”國際秩序的確立,“國家敘事”作為一種特定的敘事形式逐漸受到多學(xué)科、多國家、跨文化關(guān)注,近年來更是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戰(zhàn)略命題,引發(fā)了學(xué)界的諸多討論。目前的國家敘事研究在理論視角、理論困境和實(shí)踐指向方面均沉淀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就視角而言,存在批判性解構(gòu)與建設(shè)性探索兩大研究脈絡(luò);在理論困境方面,焦點(diǎn)主要是國家敘事中一致性與復(fù)雜性的取舍、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平衡,以及國家敘事的對外傳播困境與對內(nèi)傳播困境何者更為根本的問題;在實(shí)踐方面,目前的國家敘事大致可以分為三大維度:時(shí)間、空間、超越時(shí)空的價(jià)值,每一維度下都有較為清晰的敘事主題,以及相應(yīng)的敘事路徑與策略。基于上述認(rèn)識,本文指出中國國家敘事研究可以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四個(gè)方向?yàn)椋阂皇歉嗟仃P(guān)照與對話既有的批判性學(xué)理傳統(tǒng);二是探究如何調(diào)和國家敘事策略研究中存在的兩組內(nèi)在沖突;三是梳理國家敘事對外困境與對內(nèi)困境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及雙向影響機(jī)制;四是系統(tǒng)地從時(shí)間維度、空間維度與價(jià)值維度構(gòu)建更具整體性與戰(zhàn)略眼光的國家敘事方案。
關(guān)鍵詞: 國家敘事; 國家形象; 中國故事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3.06.005
中國既是一個(gè)沉淀了厚重歷史的文明古國,又是一個(gè)煥發(fā)著旺盛生命力的現(xiàn)代化國家;既是一個(gè)強(qiáng)調(diào)自身制度與文化優(yōu)勢的國家,又是一個(gè)力圖推動全人類共同價(jià)值的國家;既是一個(gè)社會差異化與個(gè)體化程度不斷增強(qiáng)的國家,又是一個(gè)著眼于凝聚社會共識與推進(jìn)一體化進(jìn)程的國家。社會變遷、國家發(fā)展、國際關(guān)系調(diào)整等多重脈絡(luò)相互交織,形塑了當(dāng)今中國所面臨的諸多發(fā)展挑戰(zhàn),國民也在某種程度上經(jīng)歷著認(rèn)同危機(jī)、身份困惑以及價(jià)值觀模糊等困境。因此,在這一時(shí)期面對國內(nèi)受眾和國際受眾建立完整清晰、圓融自洽、豐富厚重的國家敘事,關(guān)系到國家建設(shè)與發(fā)展的成果能否獲得認(rèn)同,進(jìn)而關(guān)系到整個(gè)民族的未來。自2013年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qiáng)調(diào)“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以來,構(gòu)建一種嶄新的國家敘事或中國話語越來越被視作中國特色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的重要使命。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共產(chǎn)黨的奮斗故事、中華民族求解放的故事、改革開放的故事、大國崛起的故事、中華文明連續(xù)演變的故事,是當(dāng)前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需要共同關(guān)注的重要命題,許多國際傳播、戰(zhàn)略傳播、國際關(guān)系、公關(guān)關(guān)系等領(lǐng)域的學(xué)者都投入到這一研究領(lǐng)域之中。大多數(shù)學(xué)者立基于“外宣”與“內(nèi)宣”,探究如何通過“講故事”塑造出能夠獲得國際和國內(nèi)受眾認(rèn)同的國家形象,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shí)力與國際話語權(quán)。這些研究不乏創(chuàng)見,但較少關(guān)注到既有的國家敘事研究傳統(tǒng),也未能與之形成對話。事實(shí)上,“國家敘事”(National Narrative),也叫民族敘事、國族敘事,伴隨著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與二戰(zhàn)后“民族國家”國際秩序的確立而逐漸興起。可以說,在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戰(zhàn)略命題之前,“國家敘事”就已經(jīng)是一個(gè)學(xué)脈深厚的,受到多學(xué)科、多國家、跨文化關(guān)注的研究議題。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積淀與發(fā)展,既有的國家敘事研究在相互交融、相互印證的同時(shí),又呈現(xiàn)出一些根本性的矛盾與張力。相應(yīng)地,實(shí)踐層面的國家敘事在這些理論資源的指引下,也成為多重路徑與策略的集合。
一、 國家敘事的概念界定
作為人類文明的產(chǎn)物,國家在歷史上經(jīng)歷了漫長而復(fù)雜的發(fā)展歷程。不同學(xué)者對這一發(fā)展歷程有不同的闡釋視角,更為學(xué)界所普遍認(rèn)同的論述是:國家形態(tài)經(jīng)歷的是從“王朝國家”到“民族國家”的轉(zhuǎn)變①[1]。民族國家與王朝國家最為根本的區(qū)別在于:王朝國家以君主專制的國家政權(quán)為標(biāo)志,而民族國家的形成往往伴隨著對王朝專制統(tǒng)治的反對和推翻王朝國家的革命實(shí)踐,其重要標(biāo)志是民族共同體的民族意識覺醒以及對民族的認(rèn)同。由這種轉(zhuǎn)變可以看出,國民對國家的認(rèn)同在民族國家的存在和發(fā)展中扮演著至關(guān)重要的角色,為了形塑這種國家認(rèn)同,“國家敘事”應(yīng)運(yùn)而生。
人類天生就是“會講故事的動物”。與“經(jīng)濟(jì)人”假設(shè)不同,“敘事人”假設(shè)認(rèn)為,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源自敘事,包括神話、寓言、史詩、戲劇、漫畫和新聞報(bào)道等各種敘事形式[2]。一般認(rèn)為,敘事指政府、組織或個(gè)人等敘事主體,通過增加可理解的復(fù)合元素,為行為和事件賦予意義,講述一個(gè)由“場景”“角色”“情節(jié)”“因果關(guān)系”共同構(gòu)成的“故事”[3]。當(dāng)敘事主體是擁有影響力的社會參與者,敘事可以成為一種知識性權(quán)力,通過為行為與事件賦予意義并將這一對世界的重新解讀加以推廣,可以重新塑造共識,并服務(wù)于講述者的行動。圍繞同一主題出現(xiàn)不同版本的敘事,就會產(chǎn)生敘事競爭,不同講述者講述有所區(qū)別的情節(jié)與角色,由聽眾進(jìn)行選擇。
在此理解的基礎(chǔ)上,本文延續(xù)翟邁云等人的定義[4],將“國家敘事”界定為:行為體通過對國家歷史、國內(nèi)事件以及角色行為進(jìn)行重新解讀,講述一個(gè)以個(gè)人、黨派、組織為“角色”,以國內(nèi)社會結(jié)構(gòu)為“場景”,以發(fā)生事件為“情節(jié)”的“故事”,主要回答國家有怎樣的歷史與傳統(tǒng),有怎樣的主張與成果,未來將走向何方,從而引起一種“群體性”的感覺,強(qiáng)化個(gè)體作為國民的身份認(rèn)同。
二、 國家敘事的理論視角
(一) 批判性視角
作為政治傳播的主要路徑,國家敘事的本質(zhì)是“通過話語塑造認(rèn)同”。自20世紀(jì)以來,許多重大的政治性災(zāi)難,如戰(zhàn)爭、種族屠殺等,都被直接或間接地視作國家(民族)敘事的產(chǎn)物[5]。伴隨著西方的后現(xiàn)代主義與解構(gòu)主義思潮,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界也掀起了聲討宏大敘事的浪潮。因此,批判導(dǎo)向的研究一度占據(jù)了中西方國家敘事研究的主流。這些研究主要牽涉了兩大理論脈絡(luò):葛蘭西的文化霸權(quán)理論與福柯的批判性話語理論。葛蘭西認(rèn)為,如今西方發(fā)達(dá)國家在實(shí)現(xiàn)“霸權(quán)”時(shí)逐漸淡化其暴力和強(qiáng)制的手段,轉(zhuǎn)而憑借其政治及經(jīng)濟(jì)上的優(yōu)勢將本國的意識形態(tài)或文化價(jià)值觀推行為其他國家所普遍接受的準(zhǔn)則,其影響力并不是透過暴力統(tǒng)治強(qiáng)加于人,而是通過積極的“認(rèn)同”來實(shí)現(xiàn)的。而福柯的批判性話語理論則旨在尋找“限定了知識的可能性條件”,也就是尋找對人們思維方式起到限制作用的一系列話語。這些話語的至高地位往往伴隨著對其他話語的利用和壓制,因此通常與權(quán)力緊密相連,將何為“真理”、何為“正確”的知識深深地嵌入全體社會公民的靈魂。
這兩大理論脈絡(luò)啟發(fā)了豐厚且龐雜的研究成果,在國家敘事領(lǐng)域,最為顯著的是圍繞歷史教科書、主流媒體報(bào)道、法定節(jié)日與儀式等敘事載體所展開的研究。由于歷史教科書是不同社會和政治議程的載體,在不同的國家和國際背景下具有不同的社會和政治需求,因此,每個(gè)國家的歷史教科書都會傳播特定的價(jià)值觀、規(guī)范、行為和意識形態(tài)[6-7],這往往會引發(fā)學(xué)界的質(zhì)疑與挑戰(zhàn)。如詹姆斯·格溫所著的《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的錯(cuò)誤》,基于對美國流行的12本歷史教科書的研究、在課堂上的觀察以及對高中學(xué)生和教師的采訪,揭露了教科書中虛構(gòu)的、不準(zhǔn)確的、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了如“剝削奴役黑人”等被美國教科書忽視的歷史主題[8],“政治驅(qū)動下教科書對事實(shí)存在遮蔽甚至扭曲”的例子也可以在俄羅斯、日本、澳大利亞、法國、希臘和以色列的教科書中找到[9]。從這個(gè)角度看,Elie Podeh將教科書描述為“國家操縱集體記憶的武器”、“最高歷史法院”和“身份政治”的工具[10]。
除了歷史教科書,主流媒體如何完成歷史大事件的書寫與傳播也是研究者重點(diǎn)考察的對象。新聞框架在突出特定價(jià)值和事實(shí)的過程中會塑造人們的態(tài)度和情感,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公眾會在潛意識里形成一種相對穩(wěn)定和固化的價(jià)值判斷和認(rèn)知模式。如周海燕通過在《人民日報(bào)》中檢索大生產(chǎn)運(yùn)動中的核心政治話語——“南泥灣精神”,來探析這一政治話語的流變,以及大生產(chǎn)運(yùn)動的相關(guān)記憶是如何“服務(wù)于現(xiàn)存秩序的合法化”的[11]。
在上述傳統(tǒng)國家敘事載體外,也有學(xué)者循著福柯的路徑,通過在學(xué)術(shù)研究與文學(xué)作品中探尋“知識與權(quán)力”的共謀,闡明國家敘事是如何作為一種潛在的“知識型”,形塑著學(xué)者乃至大眾的知識再生產(chǎn)過程,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薩義德所著的《東方學(xué)》與《文化與帝國主義》,其詳細(xì)地論述了文化與帝國主義是如何達(dá)成共謀的。西方世界中盛行的“東方學(xué)”研究,看似是一門研究東方及東方人的學(xué)科,實(shí)則是西方國家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權(quán)力話語方式,是一套通過對東方的“妖魔化”和“扭曲化”來處理東方的機(jī)制,是服務(wù)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即使是在風(fēng)格各異的小說、詩歌、游記中,也難掩權(quán)力話語所形塑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和意識。
(二) 建構(gòu)性視角
理論的演進(jìn)通常表現(xiàn)為一種建構(gòu)—解構(gòu)—再建構(gòu)的過程,它以否定之否定的辯證形式向前曲折發(fā)展。當(dāng)歷史被諸多“小敘事”肢解成零散碎片、落得一地雞毛時(shí),學(xué)界也逐漸重拾對國家敘事的關(guān)注與認(rèn)識。因此,相當(dāng)一部分學(xué)者是以中性或建設(shè)性的眼光看待國家敘事,認(rèn)為國家敘事本質(zhì)上是以國家為主體,圍繞著“我們是誰”這個(gè)核心命題開展的一系列敘事,既向后看,追索“我們從哪里來”,也向前看,指引“我們向何處去”,其承擔(dān)的功能與作用是其他任何主體敘事無法替代的,因此,沒有任何一個(gè)國家真正摒棄了國家敘事。
具體來說,國家敘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表現(xiàn)在兩個(gè)層面:一是對內(nèi)的層面,國家敘事可以起到凝聚共識和形塑國家認(rèn)同感的作用,通過神話傳說、歷史、文化、文學(xué)藝術(shù)等形式,國家敘事可以幫助國民更好地認(rèn)識本國的價(jià)值體系和文化傳統(tǒng),并理解國家是如何發(fā)展而來的,以及這個(gè)國家為何存在。二是對外的層面,國家敘事可以向其他國家展現(xiàn)本國形象,是國際社會認(rèn)識與了解這個(gè)國家的重要窗口。有效的國家敘事,可以吸引國際關(guān)注,在國際社會中塑造較為正面的國家形象,從而提高國家的文化軟實(shí)力與國際話語權(quán)。
在理論資源方面,建構(gòu)性視角提供了多種國家敘事的分析路徑,其中最主要的分析路徑是工具性話語分析、溝通行動理論以及后結(jié)構(gòu)主義視角,分別指向國家敘事的三種不同功能:話語強(qiáng)制、共識溝通和身份認(rèn)同。通過這些理論視角,可以深入探討國家敘事是如何塑造和影響國家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現(xiàn)實(shí)。
工具性話語分析主要關(guān)注話語在塑造利益關(guān)系中的強(qiáng)制作用。理性主義者認(rèn)為,話語可視為一種影響協(xié)商平衡的利益工具,以協(xié)調(diào)意見和解決分歧為前提。在這種觀點(diǎn)下,話語的有效性在于其是否具備“實(shí)際權(quán)力背書”,基于實(shí)際力量的威脅性言辭可以在談判中施加壓力以實(shí)現(xiàn)既定目標(biāo)。Ronald等揭示了國家A如何通過語言策略來反駁國家B的主張,迫使國家B接受最初不支持的觀點(diǎn)[12]。此外,建構(gòu)主義者從規(guī)范壓力的角度分析了話語的強(qiáng)制力。Finnemore等人指出[13],一旦規(guī)范成為說服工具,它能對態(tài)度與行為產(chǎn)生影響,在合法性規(guī)范壓力下,行動者為了維持其言辭和行為的一致性,會被迫調(diào)整其立場。
溝通行動理論關(guān)注共識溝通的爭論性邏輯。該理論基于尤爾根·哈貝馬斯的觀點(diǎn),假設(shè)互動者共處于一個(gè)“共同的生活世界”之中。在這個(gè)共同生活世界中,敘事者可以通過事實(shí)陳述、邏輯論證,以情感和理性的方式,促使目標(biāo)對象在爭論過程中被說服。從這個(gè)角度看,政治的本質(zhì)不在于競爭,而在于通過溝通與協(xié)商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在理想的話語條件下,敘事者并不希望依靠物質(zhì)條件或支配性的權(quán)力來強(qiáng)制對方,而是試圖憑借理性邏輯說服對方,并承認(rèn)對方有權(quán)反駁。因此,國家敘事并非工具的施加,而是觀點(diǎn)交流和信息溝通的媒介。即便在理性的情況下,當(dāng)行動者發(fā)生利益沖突時(shí),話語使用者可以主動提供新信息并重新構(gòu)建國際議程,以促進(jìn)在特定問題上達(dá)成共識與合作。
最后,后結(jié)構(gòu)主義路徑認(rèn)為話語塑造本體性安全與身份認(rèn)同。激進(jìn)的反思主義者將話語賦予本體性地位,主張沒有話語就沒有構(gòu)建世界的可能。過去及未經(jīng)刻意回憶和認(rèn)知之前的當(dāng)下只是一團(tuán)無秩序的混亂。然而,人類通過敘事的方式將這個(gè)客觀的信息呈現(xiàn)出來,從混亂中提取信息,賦予秩序和意義[14]。這種詮釋和賦予意義是人類理解生命意義的方式之一,當(dāng)今社會,個(gè)人命運(yùn)與民族國家命運(yùn)緊密相連,人們難以脫離國家敘事來構(gòu)建完整的個(gè)體身份。
在21世紀(jì)的國際政治和國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軟實(shí)力的競爭與硬實(shí)力比拼同等重要,各國都將改善國家形象和提升國家聲譽(yù)作為一項(xiàng)重要且緊迫的任務(wù),尤其是在當(dāng)前主要由西方發(fā)達(dá)國家主導(dǎo)國際話語權(quán)的背景下,中國、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大國”都將軟實(shí)力與話語權(quán)建設(shè)提升到國家戰(zhàn)略的地位[15]。而衡量軟實(shí)力與話語權(quán)強(qiáng)弱的一項(xiàng)重要指標(biāo)就是敘事能力的高低,通過國家敘事來幫助人們了解不同文明的根基,勾勒世界的整體圖景,塑造對于群體間利益與沖突的認(rèn)知[16]。能夠更好地傳達(dá)和傳播自己的核心價(jià)值觀和發(fā)展戰(zhàn)略的國家,往往更有可能贏得國際社會的認(rèn)同。對于中國而言,“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等理念主張?jiān)谶~向世界范疇的過程中普遍面臨困境,因此,如何向世界展現(xiàn)“和平崛起”的歷史大國形象,傳遞“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當(dāng)前中國國家敘事研究的核心命題。
三、 國家敘事的理論困境
將目光聚焦到對國家敘事進(jìn)行建設(shè)性探索的研究,會發(fā)現(xiàn)這些研究圍繞多個(gè)核心議題的矛盾與沖突構(gòu)成了國家敘事領(lǐng)域的多重理論困境。
(一) 敘事策略的多重爭議
1.一致性與復(fù)雜性的取舍
在國家敘事研究中,最清晰、最富學(xué)術(shù)張力的軸線就是敘事一致性與復(fù)雜性的爭議,這一爭議在很大程度上是批判性視角與建設(shè)性視角爭議的延續(xù),其本質(zhì)是國家敘事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取舍及平衡。
在傳統(tǒng)的國家敘事研究中,諸多學(xué)者指出國家敘事需要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一致性,同時(shí)保障國家認(rèn)知的連續(xù)性[17-18]。對于中國而言,國家敘事的一致性與連續(xù)性也是一以貫之的:在國際層面,從宣揚(yáng)儒家文化浸染下中華民族非競爭、非對抗和防御性的民族文化,到近代史中被西方列強(qiáng)多番侵略的屈辱經(jīng)歷,都指向中國不同于西方諸國的“和平崛起”的大國形象。而在國內(nèi)層面,以“革命—改革開放—發(fā)展”這一脈絡(luò)為敘事主線,中國共產(chǎn)黨被描繪為唯一能夠廣泛發(fā)動群眾、成功抵抗外國侵略,并逐步帶領(lǐng)中國人民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現(xiàn)代中國政黨,從而為其國家治理權(quán)賦予了無可辯駁的合法性[19]。實(shí)現(xiàn)敘事一致性與連續(xù)性的前提就是,在敘事過程中以高度抽象、高度統(tǒng)一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信仰為內(nèi)核,有選擇地呈現(xiàn)議題及議題間的組接,如圍繞著以“高、大、全”的人物與“偉、光、正”的決策與行動展開,話語內(nèi)部是高度自洽且一致的,不容許出現(xiàn)“矛盾和歧義”。這種政治宣傳式的國家敘事,雖然能夠塑造出清晰的、便于國民理解認(rèn)同的國家形象,但在學(xué)理層面上極易成為上文中批判性研究所劍指的靶子,在現(xiàn)實(shí)層面上的傳播效果也面臨著重重挑戰(zhàn)。
因此,一批學(xué)者主張國家敘事不應(yīng)一味訴諸高度一致的國家共識與團(tuán)結(jié)話語,而是在兩個(gè)維度上延展其“復(fù)雜性”:一是縱向維度,國家敘事應(yīng)更多地重視自下而上的視角,即在宏大官方敘事之外,對個(gè)體的鮮活歷史和深邃感悟予以應(yīng)有的重視;二是橫向維度,國家敘事不應(yīng)是封閉性的、空心化的自我確證,而是需要更多地與他國敘事進(jìn)行對話交流。
在縱向維度上,周曉虹將宏大的國家敘事與以個(gè)人表述為主的口述史進(jìn)行比較,并指出口述史使得國家敘事獲得了個(gè)體體驗(yàn)的具體補(bǔ)充,更為生動可感;同時(shí)使得常常被傳統(tǒng)國家敘事所忽視的下層民眾、婦女和少數(shù)族裔也獲得表達(dá)自己的意見、感受、榮耀甚至不滿的可能[20]。趙新利等認(rèn)為,比起晦澀的政治理念,人們更傾向于接收故事化、趣味化的信息。對國內(nèi)和國外的受眾宣傳時(shí),需要將高度抽象的詞匯具體化,用生動的中國故事對其進(jìn)行闡釋和展現(xiàn),且中國故事應(yīng)是由個(gè)人故事與地方故事匯聚與抽取而成[17]。王昀等也指出建構(gòu)具有全球性的中國故事應(yīng)多關(guān)注圍繞政策話語誕生的具體故事元素[21]。循著這一指引,許多學(xué)者挖掘出了如《山海情》、《國家寶藏》等去除了政治化色彩、見微知著的國家敘事成功案例。
在橫向維度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全燕將美學(xué)與音樂領(lǐng)域的“復(fù)調(diào)”理論運(yùn)用到對外傳播領(lǐng)域,指出對話的本質(zhì)就是復(fù)調(diào)的,是不同話語互不相融的和聲。當(dāng)今中國的對外傳播應(yīng)盡快走出“獨(dú)白”式的、自我重復(fù)的國家敘事,以理性與包容的心態(tài)面對與回應(yīng)質(zhì)疑,在與他國動態(tài)的、持續(xù)的溝通對話中尋找突破點(diǎn),尋找新的中國故事“增長點(diǎn)”[22]。換言之,國家敘事應(yīng)從單向的宣傳和說服模式轉(zhuǎn)向雙向?qū)Φ鹊臏贤▽υ捘J健?/p>
盡管近年來愈來愈多的學(xué)者提出要發(fā)展更具復(fù)雜性與層次感的國家敘事,但也有學(xué)者強(qiáng)調(diào)國家敘事與日常敘事有所不同。日常敘事中通常存在講述者和合敘者,合敘者能夠作為互動成員與講述者進(jìn)行顯性互動,并對事件進(jìn)行解釋、質(zhì)疑、修正,共同確立話語走向,構(gòu)建話語輪廓[18],而國家敘事更多的需要體現(xiàn)權(quán)威性,復(fù)雜化的趨向存在著損害國家敘事清晰度,造成理解障礙與競爭力降級的風(fēng)險(xiǎn)[23]。因此,如何在一致性與復(fù)雜性、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敘事間達(dá)成平衡,也是國家敘事領(lǐng)域?qū)W者需要探究的重點(diǎn)議題。
2.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取舍
國家敘事策略中另一爭論焦點(diǎn)則是特殊性與普遍性間的取舍與平衡。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國家敘事所首要追求的都是體現(xiàn)國家自身的特殊性,即國家品牌研究中所強(qiáng)調(diào)的區(qū)分度與辨識度——開發(fā)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表述和話語體系,在國際社會紛繁的光譜中將國家錨定在一個(gè)具體的位置,幫助本國國民和國際社會了解該國在歷史及現(xiàn)實(shí)中的定位與使命。
但也有很多學(xué)者認(rèn)為國家敘事應(yīng)更多融入普遍性的要素,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在國際層面,一味強(qiáng)調(diào)特殊性在國際社會中的傳播力有限,國家敘事應(yīng)更聚焦世界共享話語。強(qiáng)調(diào)特殊性的對外傳播困境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方面,中國特殊的政治話語一直缺乏世界性的對話基礎(chǔ),話語的離心力明顯大于向心力[24];另一方面,在闡釋政治、外交話語時(shí),頻頻將“大同世界”“仁濟(jì)天下”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理念作為修辭,但又通常不會闡釋這些文化理念的具體意涵及其與政治外交話語之間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導(dǎo)致如果接收者對儒家文化語境缺乏了解,就難以理解中國國家敘事的真正含義[22]。因此,有學(xué)者提出在國際話語場域,中國國家敘事應(yīng)更多地圍繞“文化—發(fā)展—開放”等具有世界共通性的關(guān)鍵性概念展開[23]。
二是在國內(nèi)層面,國民對國家敘事的接受度相對更強(qiáng),甚至將國家敘事作為其看待與解釋事物的唯一框架。這種接受的作用是一體兩面的:國民既會在其生活處于順境時(shí)調(diào)用國家敘事,表達(dá)其自豪感與榮耀感,也會在生活處于逆境時(shí)調(diào)用國家敘事,生發(fā)出對國家的怨懟與不滿。Brooks對一些歐洲國家政策影響者的采訪摘錄表明,歐洲各國高等教育中都出現(xiàn)了相似的趨勢:以就業(yè)為中心、政治冷漠、對學(xué)術(shù)教育而非職業(yè)教育感興趣,但各國的政策影響者都會從各自國家的國家敘事來解釋這一趨勢,并未意識到這一問題是為歐洲地區(qū)學(xué)術(shù)所共有的,也未從全球化壓力與流動跨國教育的視角來對其進(jìn)行解釋[25]。Jarausch在分析德國的國家敘事時(shí)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diǎn):國家敘事的主導(dǎo)地位如何有助于掩蓋各種跨國和全球問題[26]。在國家敘事形塑了社會主流話語的國家,國民傾向于低估民族國家之間的共性和民族國家之外的影響因素。
(二) 對外敘事困境與對內(nèi)敘事困境的關(guān)系
有大量研究表明,中國國家敘事的對外傳播與對內(nèi)傳播都存在一定困境。兩種傳播環(huán)境下的困境存在共通之處,如國家敘事的命題與邏輯的不自洽、傳播土壤的適應(yīng)問題等,但也存在著一種分歧,即對內(nèi)傳播困境與對外傳播困境何者更為根本。
國家敘事的對外傳播困境主要由國際傳播、國際政治、全球公關(guān)等領(lǐng)域的學(xué)者進(jìn)行研究,在他們的研究視域下,中國的國家敘事困境源于一個(gè)相對清晰的他者——掌握了國際話語權(quán)的西方社會,這個(gè)他者既構(gòu)成中國發(fā)展國家敘事的一定參照,同時(shí)給中國國家敘事的傳播帶來了困難與挑戰(zhàn),是中國國家敘事需要形成區(qū)分、警惕被同化的對象。在此背景下,國家形象的“我傳”與“他傳”之間的對比成為近年來研究的熱點(diǎn),大多數(shù)對比研究表明,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敘事主要聚焦于中國社會的陰暗面,緊盯權(quán)力與民眾、中國女性、環(huán)境問題、法制建設(shè)漏洞等問題,而對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進(jìn)步輕描淡寫[24]。這與更多聚焦發(fā)展進(jìn)步面向的國家敘事存在巨大差異,從而導(dǎo)致在現(xiàn)實(shí)世界里,媒體、民眾對國家敘事的信任缺失,破壞甚至瓦解公民對公共體系/部門/機(jī)構(gòu)以及彼此之間的信心,并最終影響到政治效能及社會共識。可以說,在研究國家敘事對外傳播困境的學(xué)者眼中,中國的對外傳播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導(dǎo)致了對內(nèi)傳播困境,因此首要提升的應(yīng)是中國的文化軟實(shí)力與國際傳播力,以賦予國民以認(rèn)同感與信任感,從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國家敘事的對內(nèi)傳播問題。
而研究國家敘事對內(nèi)傳播困境的學(xué)者——主要來自社會學(xué)、政治學(xué)、政治公關(guān)、馬克思主義等學(xué)科,他們的研究視域中缺乏一個(gè)“西方”那樣相對清晰的他者,而是將眼光更多投向自身。巴基斯坦學(xué)者Syed Talat Hussain認(rèn)為,成功的國家敘事應(yīng)是合理且可信的——需要從全國辯論的進(jìn)程中提煉出來的,是大多數(shù)人都贊同的愿景;同時(shí)必須與相應(yīng)的政策和行動相結(jié)合。而巴基斯坦的國家敘事則沉浸在當(dāng)權(quán)者的偏見或需求中,并且與現(xiàn)實(shí)相背離,這樣的國家敘事是難以在國際社會得到認(rèn)可的。“我們在國內(nèi)互相掏出刀子,卻希望呈現(xiàn)一個(gè)統(tǒng)一戰(zhàn)線,向國際社會展示一張愉快的面孔。不要指望當(dāng)管弦樂器壞了時(shí),交響樂會流動。”[27]Laurie也在《官方故事:埃及和阿爾及利亞的政治與國家敘事》中表明,雖然公共外交的學(xué)生和從業(yè)人員都很清楚國家品牌的重要性,以國家軟實(shí)力的視角對國家敘事進(jìn)行了充分的探討,但敘事征服的內(nèi)部風(fēng)險(xiǎn)非常高,有時(shí)甚至是致命的[28]。因此,在研究國家敘事對內(nèi)傳播困境的學(xué)者眼中,是國家敘事的對內(nèi)困境導(dǎo)致了對外傳播困境,首要改變的應(yīng)是國家敘事的話語生產(chǎn)機(jī)制,使其與最廣大人民的意愿相統(tǒng)一,同時(shí)將其付諸實(shí)踐。只有國家敘事在國家內(nèi)部有廣泛的社會基礎(chǔ),才能最大程度上改善其在國際社會的傳播境況。
四、 國家敘事的實(shí)踐指向
(一) 時(shí)間維度的國家敘事:國家歷史與國家傳統(tǒng)
從時(shí)間的維度看,國家敘事主要包含兩個(gè)主題:歷史與文化倫理傳統(tǒng)。這兩個(gè)主題所共享的基本問題就是如何合理連接國家的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關(guān)系,將歷史與文化傳承下來的國家觀念融入到當(dāng)下的生活實(shí)踐之中,建構(gòu)一套可以延續(xù)至未來的心理與文化模板。
在歷史主題下,時(shí)間維度下的國家敘事重要性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兩個(gè)方面:一是為了理解國家從何而來、走向何方,以及國家在當(dāng)下應(yīng)該擔(dān)當(dāng)怎樣的時(shí)代使命;二是為了闡釋國家選擇現(xiàn)有制度的歷史源流與時(shí)代背景。在時(shí)間維度上,既有研究所涉及的國家敘事命題包括對過往歷史的邏輯梳理、對重大事件的態(tài)度、歷史作用和影響的把握等等。國內(nèi)學(xué)者大多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呈現(xiàn)出現(xiàn)代中國,尤其是社會主義中國誕生、成長和發(fā)展的必然性與合理性。這類研究主要遵循歷時(shí)性的線性邏輯,涉及三個(gè)階段:第一個(gè)階段是跨越數(shù)千年歷史的傳統(tǒng)中國,這個(gè)階段的國家敘事幫助受眾建構(gòu)對“文化中國”及其獨(dú)特的國家觀念的認(rèn)同;第二個(gè)階段是鴉片戰(zhàn)爭以來在內(nèi)外交織的困境中坎坷前行的近現(xiàn)代中國,這個(gè)階段的國家敘事幫助受眾建構(gòu)對現(xiàn)代共和國的認(rèn)同;第三個(gè)歷史階段就是1949年以來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實(shí)踐中取得碩果的當(dāng)代中國,這個(gè)階段幫助受眾建構(gòu)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rèn)同。在中國之外,其他國家的歷史敘事也是頗受關(guān)注。美國的國家敘事主要呈現(xiàn)為英雄的國父——拓荒者敘事,這種進(jìn)步主義的神話而后發(fā)展成為主流的自由主義敘事,以羅斯福新政、民權(quán)運(yùn)動、羅納德·里根當(dāng)選總統(tǒng)為標(biāo)志性事件[4]。學(xué)界對日本國家敘事的關(guān)注著重在日本戰(zhàn)后記憶的重建上,指出日本戰(zhàn)后文化記憶錯(cuò)綜復(fù)雜,存在受害者敘事、加害者敘事、英雄主義敘事三種“相互抵觸的創(chuàng)傷敘事分類在爭奪道德優(yōu)越性”,且受害者敘事由于規(guī)避了普通民眾的戰(zhàn)爭責(zé)任,逐漸在日本社會占據(jù)主流地位[29]。
在文化倫理傳統(tǒng)主題下,中國國家敘事的研究主要是闡述中國傳統(tǒng)文化倫理的特質(zhì)性,并挖掘其中正向的部分作為國家的獨(dú)特標(biāo)識。比如,中國的文化內(nèi)核是倫理本位而非宗教本位[30],因此,相對于西方哲學(xué)傳統(tǒng)中“他者-自我”的二元對立視角,中國更傾向于對其他民族、國家都持共存、包容與交融的態(tài)度。林尚立指出,與世界歷史上其他的文化與文明相比,中國人與國家的關(guān)系應(yīng)是最為緊密的,這是由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其一,傳統(tǒng)中國講求“家國天下”,家與國具有同構(gòu)性,國家被視為由家庭擴(kuò)展而成的政治共同體;其二,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制度根植于以“修齊治平”為軸的生活體系,國家權(quán)力深入到人們的生活理念和實(shí)際生活中;其三,中國缺少宗教傳統(tǒng),以世俗生活為主體,國家是組織、協(xié)調(diào)和宰制世俗生活的唯一力量[31]。
(二) 空間維度的國家敘事:制度合理與人民幸福
從空間的維度看,國家敘事需要闡述的是國家在空間維度所設(shè)置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也就是國家是如何組織、安排與協(xié)調(diào)當(dāng)前的種種利益關(guān)系,以及在既有的利益結(jié)構(gòu)體系之中每個(gè)公民的權(quán)益水平、自由空間與發(fā)展資源。據(jù)此,空間維度的國家敘事主要包括兩個(gè)主題:制度合理與人民幸福。
制度合理性的評判需要以人民的自由、發(fā)展與幸福為準(zhǔn)繩,而人民的幸福離不開國家制度的保障。因此,在絕大多數(shù)研究中,這兩個(gè)主題是相互咬合、嵌套的。在制度主題下,近年來國內(nèi)學(xué)界關(guān)注較多的是中國相對于西方“一人一票”制民主所提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從各個(gè)角度闡釋了其理論基礎(chǔ)、制度內(nèi)涵和價(jià)值,構(gòu)建了較為完備的本體論與方法論。此外較多被討論的是政黨、社會與國家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其關(guān)鍵是政黨的角色與功能定位;中央與地方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其關(guān)鍵在于中央與地方的職能分配及互動關(guān)系;民族關(guān)系,其關(guān)鍵是實(shí)現(xiàn)各民族享有平等權(quán)利的制度安排;城鄉(xiāng)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其關(guān)鍵是城鄉(xiāng)一體化;等等。這些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都是國家建設(shè)和發(fā)展階段的重要問題,不僅需要整體的規(guī)劃安排和具體的制度設(shè)計(jì),更需要以敘事的方式將其傳遞給國內(nèi)與國際受眾。
而人民幸福主題下的國家敘事,則更側(cè)重微觀視角下“普通人的日常實(shí)踐和真實(shí)表達(dá)”。為避免國家敘事落入日常敘事過于細(xì)碎的結(jié)構(gòu)劃分與情境解讀,劉子曦提出用“故事形態(tài)學(xué)”的方法關(guān)注不同故事背后敘事結(jié)構(gòu)的同構(gòu)性[32]。這種方法遵循了Vladimir Propp以來的形式主義傳統(tǒng),即認(rèn)為故事中的人物盡管各不相同,但人物的功能卻具有形態(tài)學(xué)上的統(tǒng)一性與穩(wěn)定性。如果將故事看作一個(gè)個(gè)復(fù)雜的工程,研究者可以梳理提取出構(gòu)成工程的多個(gè)功能系統(tǒng)。也就是說,研究者可以在拆解研究大量故事后,創(chuàng)建這類故事的功能總覽,并將這些故事以圖示化的方式呈現(xiàn)。這種對故事要素的提取建立在對大量故事的總結(jié)與理解上,能夠融入制度與歷史層面的思考,捕捉到融會在日常表達(dá)和敘述中的社會心理與普遍感受,從而突破個(gè)人故事不具備推廣性和普適性的局限。
(三) 超越時(shí)空的國家敘事:基本價(jià)值與共享議題
盡管任何國家敘事都根植于特定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脈絡(luò),但在全球經(jīng)濟(jì)一體化的時(shí)代背景下,尋求能被國際社會所共同理解的世界共享話語,從而增強(qiáng)國家敘事的對外傳播信度與效度,也是十分重要而關(guān)鍵的議題。超越時(shí)空限制的國家敘事也有兩個(gè)主題:基本價(jià)值與共享議題。
基本價(jià)值是指人類所公認(rèn)的價(jià)值,包括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互助等。在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由于社會結(jié)構(gòu)和社會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敘事的交流變得復(fù)雜而低效。因此,既有研究多立基于社會學(xué)中的“主體間性”概念和語言學(xué)中的“互文性”概念[32-33],其指出國家敘事需要更多地關(guān)注多個(gè)主體之間、多個(gè)故事文本之間共通的意義空間,簡單來說,就是雙方主體能夠共同理解的事物、共同的價(jià)值追求以及共同的情感訴求——如人類的親情、愛情等,并以此為切入點(diǎn)建構(gòu)國家敘事。例如,電影《流浪地球》就敘述了一個(gè)全人類共同面臨的生存困境,不論國家、種族,全人類天然地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yùn)共同體,團(tuán)結(jié)合作才能尋求生路,這些都是在人類基本價(jià)值的基礎(chǔ)上所進(jìn)行的故事建構(gòu)。國家敘事面臨的最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將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與這些當(dāng)代人類基本價(jià)值相連結(jié),并使其成為國內(nèi)社會遵從、國際社會認(rèn)同的國家核心價(jià)值體系。
共享議題指地球氣候變暖、超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人類共同面對的嚴(yán)峻挑戰(zhàn)。在討論如何應(yīng)對這些挑戰(zhàn)時(shí),全球治理儼然已經(jīng)成為一種基礎(chǔ)性的語境。國家不僅可以通過其獨(dú)特的敘事方式來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還可以在這一過程中持續(xù)發(fā)掘新的敘事資源,調(diào)整或創(chuàng)造敘事框架,以應(yīng)對不斷演變的國際關(guān)系和全球治理需求。這一主題較有代表性的是王昀等人的研究,基于“互文性”的概念系統(tǒng)性地提出了國家敘事在涉及全球共享議題時(shí)的具體建構(gòu)路徑:第一層次是全球治理中的中國擔(dān)當(dāng),在近年來西方保守主義、民粹主義等浪潮推動的反全球化趨勢中,凸顯中國引領(lǐng)全球化進(jìn)程的種種作為;第二層次是一系列對外政策與倡議理念,包括“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新型大國關(guān)系”等內(nèi)容;第三層次是圍繞政策話語所誕生的具體故事元素[21]。
五、 研究結(jié)論
從上述研究回顧來看,國家敘事研究存在批判性解構(gòu)與建設(shè)性探索兩大研究視角,其中批判性研究以揭示國家敘事中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為前提,建設(shè)性研究以論證國家敘事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為前提。然后將目光聚焦于建設(shè)性導(dǎo)向的國家敘事研究,會發(fā)現(xiàn)這些研究存在一定的理論困境:爭論焦點(diǎn)則主要是國家敘事中一致性與復(fù)雜性的取舍、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平衡,以及國家敘事的對內(nèi)傳播困境與對外傳播困境何者更為根本的問題。針對這些困境,目前的國家敘事策略研究大致可以分為時(shí)間維度、空間維度、超越時(shí)空的價(jià)值維度,每一維度下都有較為清晰的敘事主題,以及相應(yīng)的敘事路徑與策略。
基于上述認(rèn)識,本文認(rèn)為可以相應(yīng)地從以下四個(gè)方面進(jìn)一步發(fā)展中國國家敘事的相關(guān)研究:
第一,國家敘事研究要更多地關(guān)照到既有的批判性學(xué)理傳統(tǒng),并與之形成對話。譬如可以將既有的批判性研究理解為學(xué)界對國家敘事扭曲化、偏狹化的一種警告與外部規(guī)制,其內(nèi)在啟示是:如何使國家敘事不僅僅服務(wù)于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而是在最大程度上惠及本國國民乃至世界公民,從而獲得盡可能廣泛的支持與認(rèn)同,這與絕大部分建設(shè)性導(dǎo)向的國家敘事研究實(shí)則是親和的。
第二,國家敘事研究需要更多地調(diào)和敘事一致性與敘事復(fù)雜性、敘事特殊性與敘事普遍性的內(nèi)在沖突。就復(fù)雜性與特殊性這一維度的爭議而言,需要進(jìn)一步討論的議題是如何既能保持塑造清晰的并便于識別、理解、記憶的國家敘事,又不使其失去真實(shí)性、對話性與人文關(guān)懷。就特殊性與普遍性這一維度的爭議而言,需要進(jìn)一步討論的議題是如何使國家敘事既能夠彰顯中華文化的獨(dú)特氣質(zhì),又符合其他國家的文化期待;既能強(qiáng)調(diào)本國獨(dú)特的歷史軌跡與價(jià)值體系,也能關(guān)照到國家隨世界政治經(jīng)濟(jì)格局與文化潮流之變盛衰起伏的真實(shí)圖景。
第三,國家敘事的對外傳播困境與對內(nèi)傳播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連續(xù)一貫、相互作用的。需要貫通性地梳理兩種困境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及雙向影響機(jī)制,為中國國家敘事提出更具整體性與戰(zhàn)略眼光的改善策略。
第四,國家敘事可以在現(xiàn)有研究的指引下,更為系統(tǒng)地涵蓋時(shí)間維度、空間維度與超越時(shí)空的價(jià)值維度,構(gòu)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敘事方案,向世界呈現(xiàn)包容并蓄、海納百川、氣象萬千的新時(shí)代中國話語自信。
注釋:
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中心主義話語下,西歐等區(qū)域在“王朝國家”之前還經(jīng)歷了基于猶太-基督體系的普世國家階段,這一階段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并非本文所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故在此不詳述。
[參考文獻(xiàn)]
[1] ?周平.民族國家與國族建設(shè)[J].政治學(xué)研究,2010(03):85-96.
[2] 曹德軍.大國競爭中的戰(zhàn)略敘事:中美外交話語博弈及其敘事劇本[J].世界經(jīng)濟(jì)與政治,2021(05):51-79,157-158.
[3] Bruner J.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J].Critical Inquiry,1991,18(1):1-21.
[4] 翟邁云,李慶四.為誰講故事:美國兩黨的國家敘事之爭[J].美國研究,2023,37(03):91-114,7.
[5] Berger S.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in Europe:Reflections on the pasts,presents,and future sofa tradition[M]//Jarausch,K.H., Linden berger,T.(eds) Conflicted Memories:Europeanizing contemporary histories.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7:55-68.
[6] Issitt J.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textbooks[J].History of Education,2004,33(6):683-96.
[7] Grever M.,Adriaansen,R.J.Historical culture:A concept revisited[M]//Carretero M.,Berger,S.,Grever,M.(eds) Palgrave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Historical Culture and Educatio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7:73-89.
[8] 詹姆斯·格溫.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的錯(cuò)誤[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9] Grever M.,van der Vlies,T.Why national narratives are perpetuated:A literature review on new insights from history textbook research[J].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2017,21(1):12-34.
[10]Podeh E.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Israeli educational system:The portrayal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history textbooks(1948-2000)[J].History and Memory,2000,12(1):65-100.
[11]周海燕.記憶的政治.[M].北京: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13
[12]Krebs,Ronald R.,Jackson,Patrick,Thaddeus.Twisting tongues and twisting arms:The power of political rhetoric[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7,13(1):35-66.
[13]Finnemore M.,Sikkink,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J].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7:139-174.
[14]V.Wertsch J,白美妃.國家記憶中的敘事工具、事實(shí)與快速思維:以俄羅斯與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記憶僵局為例[J].民族學(xué)刊,2015,6(05):7-14,96-97.
[15]史安斌,廖鰈爾.國際傳播能力提升的路徑重構(gòu)研究[J].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6,38(10):25-30.
[16]常江,楊奇光.國家敘事中的世界圖景:基于對2014年《新聞聯(lián)播》“國際聯(lián)播快訊”的內(nèi)容分析[J].新聞記者,2015(03):48-54.
[17]趙新利,張蓉.國家敘事與中國形象的故事化傳播策略[J].西安交通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14,34(01):97-101.
[18]樊小玲.教科書敘事:自我認(rèn)知、世界圖景與國家形象傳播[J].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8,40(10):160-164.
[19]吳新葉.黨建引領(lǐng)社會治理的中國敘事:兼論國家-社會范式的局限及其超越[J].人文雜志,2020(01):114-122.
[20]周曉虹.口述史、集體記憶與新中國的工業(yè)化敘事:以洛陽工業(yè)基地和貴州“三線建設(shè)”企業(yè)為例[J].學(xué)習(xí)與探索,2020(07):17-25.
[21]王昀,陳先紅.邁向全球治理語境的國家敘事:“講好中國故事”的互文敘事模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26(07):17-32,126.
[22]全燕.從獨(dú)白到復(fù)調(diào):超越國家敘事的對外傳播話語想象[J].社會科學(xué),2020(07):160-167.
[23]陳先紅,秦冬雪.全球公共關(guān)系:提升中國國際傳播能力的理論方法[J].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2,44(06):44-56.
[24]侯洪,董彥君.國家形象敘事的“他者”視域:從《超級中國》說起[J].新聞界,2016(01):31-37.
[25]Brooks,R.Asserting the Nation:The Dominance of National Narratives in Policy Influencers Construc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J].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2020,25(2):273-288.
[26]Jarausch K.H.Beyond the National Narrative:Implications of Reunification for Recent German History[J].German History,2010,28(4):498-514.
[27]Syed Talat Hussain.Ah,the national narrative[EB/OL].(2017-10-23)[2023-05-03].https://www.thenews.com.pk/print/239092-Ah-the-national-narrative.
[28]Laurie Brand.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Narratives[EB/OL]. (2014-09-05)[2023-05-06]]https://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politics-national-narrative.
[29]橋本明子.漫長的戰(zhàn)敗:日本的文化創(chuàng)傷、記憶與認(rèn)同[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1.
[30]陳先紅,宋發(fā)枝.“講好中國故事”:國家立場、話語策略與傳播戰(zhàn)略[J].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0,42(01):40-46,52.
[31]林尚立.現(xiàn)代國家認(rèn)同建構(gòu)的政治邏輯[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3(08):22-46,204-205.
[32]劉子曦.故事與講故事:敘事社會學(xué)何以可能:兼談如何講述中國故事[J].社會學(xué)研究,2018,33(02):164-188,245.
[33]唐華林.跨文化語境下的國家敘事研究[J].中華文化與傳播研究,2021(01):104-114.
[34]劉瑞生,王井.“講好中國故事”的國家敘事范式和語境[J].甘肅社會科學(xué),2019(02):151-159.
(責(zé)任編輯 文 格)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Dilemmas and Practical Directions
in National Narrative Studies
TANG Xin-yu, CHEN Xian-h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China)
Abstract:“National Narrative”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since World War II,and in recent years,it has even become a strategic proposition in China.The current research on national narrative has deposited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theoretical dilemma and practical direction.Firstly,with regard to theoretical perspective,there are two research veins: critical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ve exploration; Secondly,when it comes to theoretical dilemma,the focus is mainly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consistency and complexity,the balance between specificity and universality,and the question of which is more fundamental—the difficulties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r inter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national narrative; Finally,in terms of practice,the current national narrative can be roughly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time,space,and the value beyond time and space,each of which has its narrative themes and strategies.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this paper proposes four direc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narrative: Firstly,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existing critical theories and enter into dialogue with them; Secondly,to explore how to reconcile the two sets of inherent conflicts in the research of national narrative strategies; Thirdly,to sort out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of national narrative and the mechanism of two-way influence; Fourthly,to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a more holistic and strategic national narrative including the time dimension,the spatial dimension,and the value dimension.
Key words:national narrative; national image; Chinas s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