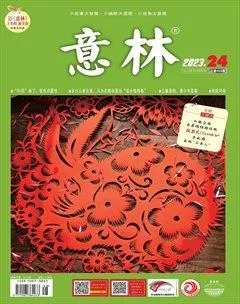會跳舞的頭發(fā)
楊立英

你的頭發(fā)會跳舞嗎?我的會。打記事起,我就有一頭會跳舞的頭發(fā),它們擺出不同的姿勢,或彎或曲,飛揚跋扈,像不守規(guī)矩的舞者,把我折騰得與眾不同,如同異類。
母親總是沒好氣地數(shù)落:“你個瘋丫頭,就不會扎一扎,不知個美丑!”我翻個白眼,小聲嘀咕:“還不是隨你。”
母親亦有一頭同樣的頭發(fā),她的這一特色毫無保留地遺傳給了我,讓我無數(shù)次心生抱怨。
母親整天忙得腳打后腦勺,一刻不得閑,致使她的頭頂常年盤踞著“雞窩”。我非常羨慕小偉娘,穿著干凈的衣褂,頭發(fā)梳理得紋絲不亂,往人前一站,連她身邊矮小的小偉都跟著神氣起來。當然,主要的還因為小偉爹是生產(chǎn)隊長,殷實的日子讓小偉娘有種天生的優(yōu)越感。在小偉娘面前,母親那頭“雞窩”讓我頓覺矮了三分。
一次,母親到學校找我,她的頭發(fā)在微風中跳著雜亂無章的舞蹈,最可笑的是上面還粘著一片樹葉。當母親伸出鋸齒樣的手來理順我飛起的頭發(fā)時,卻被她手上的裂口刮得更亂了。“英子娘的雞窩里快孵出小雞啦!”同學的取笑讓我想找個地縫鉆進去。
回家后,我沒好氣地埋怨母親去學校也不梳梳頭,像個瘋子一樣。忙碌的母親頭也不抬,略有愧疚地回應(yīng):“娘給你丟人了吧?不過頭發(fā)亂了也沒啥,心不亂就成。”
急性子的母親很少有溫情的話語,發(fā)起火來也如她的頭發(fā),張牙舞爪。有一次,我偷吃了爺爺用來壓咳嗽的蘋果,母親反手就是一巴掌,可緊接著,又像漏了氣的皮球,一邊抹著淚一邊摟緊我。
母親再怎么兇我們,也容不得我們被別人欺負。大伯家有五個孩子,個個不是省油的燈,尤以堂姐為甚,下手不分輕重,在我頭上砸出個大包。母親闖進大伯家,激烈爭吵的場景母親沒和我們說起過,但能想象出戰(zhàn)斗力爆表的定是母親的頭發(fā),舞動著節(jié)奏強勁的搖滾。
回家后,母親撓了撓更加蓬亂的頭發(fā),該吃吃該喝喝,像什么都沒發(fā)生過一樣。從那之后,堂兄堂姐再也沒欺負過我們。
父親在縣城上班,家里家外都由母親一個人打理。不服輸?shù)哪赣H干起活來絲毫不輸男人,她的頭發(fā)有時是激情高亢的搖滾,有時是節(jié)奏輕快的恰恰,有時又是平靜舒緩的慢三。一家人在母親情緒的音符里起起落落,感受著她的倔強和堅韌。
父親緣何會看上母親?這是藏在我心底許久的疑問。父親教師出身,舉手投足透著儒雅,而母親大字不識一個。最不可思議的是父親還有些怕母親,小心翼翼地瞅著母親的情緒行事,不時叮囑我們:“你娘不容易,在家拉扯你們姐弟四個,還得照顧瞎眼爺爺,我們都得聽她的。”
日子富足了,母親也老了,越來越溫和。稀疏的頭發(fā)溫順地趴在頭皮上,貧瘠,干枯。即便如此,微風吹來,白發(fā)依舊充滿活力地舞著,像極了母親,從不向困境低頭,總是倔強地頂著亂蓬蓬的頭發(fā),或怒或喜或悲,把貧窮的日子打理得熱氣騰騰。
一頭亂發(fā)是我生命中一道獨特的風景,讓我煩憂,也給我力量。遭遇泥潭時,我一遍遍告誡自己,頭發(fā)亂了,不用怕,只要心不亂。因為,我的頭上長滿了和母親一樣的會跳舞的頭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