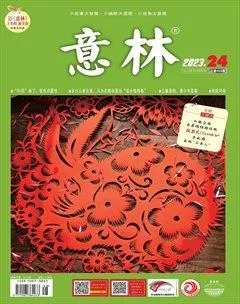又“訓”了父親一頓
結束晨練準備洗澡,父親打來電話:“搭了個順風車到銀行辦點事,是不是還得戴口罩?走得急忘戴了。”末了,還怯怯地“呵呵”一聲,像在掩飾他的“過失”。
距銀行開門還有兩小時,我只得穿戴整齊,騎車趕到城西接他。矮小瘦弱的父親躲在空闊的街角,瑟縮著,雙眼盯著我來的方向。看到他的窘態,我生氣了:“來這么早,也不提前打電話。”
父親不敢看我,喃喃道:“村里你大叔去工地趕早,我就搭他的摩托來了,你工作忙,沒打電話麻煩你。”我自覺言重了:“來了就回家吧,吃早飯。”父親慌了神:“不不不,不餓,辦完就回,我這一身土兩腳泥。”我又生氣了:“我家不是你家呀!”
搓了幾搓鞋底,父親進了電梯,又搓了幾搓鞋底,進了家門。我嗔怪:“哎呀,不用搓啦!”父親只顧搓,不理我。盛了滿滿一碗面條,加一個荷包蛋、兩根油條,父親吃了個精光,又加一碗。我逗他:“必須吃完啊!”父親順從地“嗯”了一聲。待收拾碗筷,我佯裝生氣:“不是說不餓嗎?以后不許說假話!”他說:“好,都吃撐了,剩碗底兒不好!”
父親坐在偌大的沙發里,更顯小,雙手局促地在腿上、沙發上搭來搭去。我遞給他一杯溫開水,手才放定。問我娘,問莊稼,問鄉親,問樹,問雞……我問啥,父親應啥。我慌了:原來那個事事由他拿主意的一家之主哪去了?父親倒是慢慢輕松下來,說著家里村里的情況,可怎么感覺都像是在向我匯報,且眼神躲閃,沒有絲毫他年輕時面對我的厲聲厲色。不再說話,我去洗漱,我邊刷牙邊心慌:此刻坐在沙發里的父親怎么那么像被他訓得貼墻站的兒時的我?
父親從小沒了爹娘,營養跟不上,長得很瘦小。當年為了拉扯我們兄弟仨,下過煤窯,我還一度怨這個家,怨父親沒給我堅強厚實的靠山,可父親又談何容易?
我偷偷瞟了一眼父親,眼前騰起一團霧,我迅速猛洗臉。
收拾完畢,我拿出嶄新的口罩,拉父親起來,給他戴好,又塞了一包放提兜里。上街領他辦業務,買東西,送他回家。其間,又“訓”他過馬路一定跟緊我,一定抄好密碼,有事一定跟我說……
中午有個應酬,我打電話給妻子。女兒接過電話,劈頭一句:“不準喝酒,你酒精過敏不知道嗎?”我“呵呵”一聲:“知道了。”聽到女兒那邊和她媽說:“放心,我又訓了我爸一頓……”
(本文入選2023年四川德陽中考語文試卷,文章有刪減)
張金剛,河北省保定市阜平縣人。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2009年開始寫作,陸續在《人民日報》《中國藝術報》《文藝報》《文學報》《中國城市報》《河北日報》《北京日報》《廣州日報》《西安晚報》《品讀》《當代人》《思維與智慧》等全國各類報刊發表散文隨筆作品。著有散文隨筆集《多年離家已成客》《水盆盛太陽》。多次在河北省、保定市舉辦的主題征文、文學評獎活動中獲獎。
《意林》:父親在您心里是什么樣的形象?
張金剛:父親一生生活在農村老家。山河依舊,草木榮枯,容顏老去,人至遲暮。印象中,父親年輕的模樣,永遠定格在他與母親結婚時照的那張黑白結婚照上。英俊的臉龐、烏黑的頭發、有光的雙眼,二十歲的父親,用“帥”來形容,不過分。僅此,再沒找到別的照片。而他“監護”我成長的路上,我只顧向前,從未用心記住伴我左右的父親從英俊到老邁的模樣。想來,頗是遺憾。
《意林》:文章標題和文章最后被女兒教訓,想要表達什么樣的意義?
張金剛:人生就是一個輪回。在女兒長大的路上,我也正一點點沒了脾氣,沒了鋒芒;斗不過她,妥協于她。對她的“訓”,我也習以為常,或將成為日后的常態。一如,現在我對父親的態度一樣。
又“訓”了父親一頓。是的,是我“訓”了父親,也是女兒“訓”了我;又好像我“訓”了我,“訓”了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