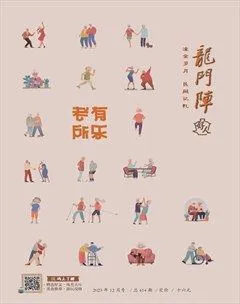東坡肉
曾穎

時隔四十幾年,她仍能記起媽媽眼含淚光微笑的那一瞬,她覺得那是這輩子最溫暖的一刻。
樓上的鄰居在屋頂修了個花園,栽上各色花樹,放上陽傘桌椅,我常常在天色將明之時,上去看朝陽,讀書寫東西。因為是借人家的地方,故將其命名為“借園”。對我而言,東西可以借,但歡樂卻是自己的。這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對自己在物質方面無大創造力的一種精神勝利式的安慰吧。
今天這個故事,就是借園主人朱女士給我講的。她某天上樓澆花,與我偶遇,知道我就是小區鄰居們傳說中的那個作家,她的小園子不僅給花兒和鳥兒們提供了棲所,還“產出”了許多文字,她自然十分高興,就給我講了她父親的故事。
她的父親是個軍人,抗美援朝回來,已是正團職,娶了她的生母,一個能夠用俄文念普希金詩歌的文藝兵,生下哥哥和她。她的家庭,父母郎才女貌,兒女成雙,幸福得羨煞旁人。而20世紀60年代中期,那場眾所周知的劫難鋪天蓋地而來,她的父親也難逃此劫。父親的軍人脾氣,受不了橫空而來的污蔑,他揮拳奮起反擊,被打成抗拒運動的典型。
生母果斷而決絕地和父親劃清了界限,斬斷了包括與兩個兒女在內的所有聯系,以保全她在省歌舞團的工作。她和父親相差15歲,唯一能填補這段差距的,是父親的官職,而一旦這填充物消失了,平衡自然就崩塌了。
在歷經了幾乎脫了一層皮的“挽救教育”之后,父親被發回原籍接受監督改造,唯一的“行李”便是一雙兒女,兒子五歲,女兒三歲。老屋早已不在,生產隊騰出一間保管室,室內除了一個倒扣的拌桶,什么都沒有。但比起有人監視一不小心就可能挨皮帶的土監獄,這間曬壩上空空如也的小房子,也就沒那么恐怖了。
父親早年當過篾匠,求得隊長允許,從后坡拖回幾根竹子,剔枝砍丫,不出半日就拼出一張竹床,一張小桌,三根小凳,把隨身帶的軍被、飯盒、水壺往上一放,勉強就算得是一個家了。三個石頭支上當年從日本鬼子那里繳來的一個長條飯盒,燒上開水兌灰面,就算是一頓飯了。他們那天吃的第一頓飯,是糨糊。
曬壩西邊還有一戶人家,住著母女倆,與保管室相距三四百米,此外周邊半里,再無人家。那兩母女,據說是地主,與村里人沒什么來往。地主婆六十多歲,膝蓋有病,走路一瘸一拐,她的女兒三十好幾了,一直沒有出嫁。
地主家的小姐,通常是令人浮想聯翩的,但這個小姐,卻和想象的不一樣。她沒有白凈的皮膚,也沒有光亮柔順的頭發和纖細柔美的腰肢,更沒有不沾陽春水的纖纖玉指。她面色青黃,頭發發黃而且開叉。小眼睛,大臉盤,一對齙牙破口而出,很不安分地頂在外面,而且還發黃。她年過三十沒有出嫁的原因,大致是因為長相,而地主小姐的身份,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曬壩兩頭,一東一西兩家就成了鄰居,燈火呼應,炊煙融聚,一個地主,一個勞改分子,彼此倒也沒什么嫌棄,雖不敢像正常鄰居那樣,你端著碗來我家擺龍門陣,我拎壺酒去你家打牙祭,但偶爾派娃娃搭個火借個鹽什么的,倒也并不算什么忌諱的事。久而久之,兩家彼此也有了些小小的照應。小姐最怕看到父親給娃娃喂糨糊,經常偷偷把他家的面拿去加點黃豆面炒熟,再下鍋時,滿屋生香;父親編竹蝦筢到竹林背后的小溪里撈到小魚,總是用草穿成兩串,一串掛西屋門口,一串帶回家中,煮得一鍋腥氣。
每當這個時候,地主家那位小姐,現在他們知道她叫蘆花,就會搖頭皺眉,覺得糟踐了東西。父親就自我解嘲,說要是有一碗油,把它們炸得噴香酥脆,再撒上一撮辣椒面和花椒,就美了。
但現實是,這些東西一樣都沒有。
下一次,父親再撈魚的時候,蘆花跑來,把兩串都接了,也不言語,一路小跑就進了竹林子,過小半天后,就端回一碗金黃酥脆的小魚,放到竹桌上,香氣四溢,兩個小孩吃得嘎嘣亂響,父親吃得滿眼淚光。
蘆花做魚,其實用的是“炕”。她把小魚放置在一個瓦片上,瓦片下面燒小火,慢慢炕干,這原本是做貓食的辦法,不同的是擠了內臟加了幾顆鹽和干辣椒面,蘆花稱它為貓貓魚,父親則稱之為蘆花魚。
朱女士說,那時鄉下沒什么玩事,她和哥哥就當了蘆花的小跟班,而蘆花也樂得帶著這兩個孩子,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他們是少有的幾個還會對她笑并把她的話當一回事的人。她說喇叭花的屁股是甜的,兩個小家伙摘下來就啜;她說蜘蛛在唱歌,兩個小家伙就屏住呼吸豎起耳朵聽……
作為家中唯一的勞力,蘆花真正玩的時間并不多,只是兩個孩子覺得她做的事好玩而已。比如抹玉米,她把兩個玉米棒碰在一起揉搓,笸籮里頓時就下起了金黃的雨;比如宰豬草,她把一捆捆苕藤放在刀痕累累的菜板上,咚咚咚的一陣響,苕藤葉青汁四濺,不一會兒就變成一鍋熱氣騰騰的豬食,她常常變戲法一般,從鍋中掏出一個雞蛋或小紅苕,犒勞犒勞身后的小跟班和忙活了半天的自己,煙氣氤氳的灶房里,蘆花總能從壇子里、爐灰里、蒸籠瓦罐里掏出一點土豆玉米胡豆花生什么的,讓他們雀躍歡喜。
他們的童年時期所有的溫暖都與蘆花和她的廚房有關。她總能用最少的油鹽,做出味道完全不同的飯菜,每個月初,她就把不多的菜油和鹽一起,炒得噴香,裝到一個罐子里,每次煮菜的時候,往里放上一勺。她會用泡菜壇子里的酸鹽水加上幾粒小米椒,調出味道極好的蘸水,用來蘸蘿卜。她能在孩子們吃膩了紅苕之后,把紅苕曬干磨細兌水打入開水鍋里做成粉,拌上蒜泥香蔥,吃得人滿身大汗。
后來,父親因為覺得自己做飯實在太難,向隊長申請讓孩子們在蘆花家搭伙。隊長打趣說:要搭干脆全家搭,免得你天天吃糨糊吃壞了我沒法向上面交代。
再后來,某一天早晨,父親讓兒女不再叫蘆花姐姐,而是改口叫媽媽。女兒毫不猶豫地改了口,兒子遲疑了半晌,也改了口。那天,爸爸和蘆花都非常高興,爸爸用鄉里人非常稀罕的舊軍用挎包,換了兩斤豬肉,蘆花不惜血本,拿出過年都舍不得用的幾顆冰糖,一副日子不過了的大手大腳樣,倒出瓶底的菜油,把肉皮炸得酥亮,然后切片墊上黃豆,上鍋蒸了兩個小時,開屜之時,整個曬壩都迷醉在一片香氣之中。
父親說,那是東坡肉,蘇東坡在流放的時候發明的。感謝老天爺,能讓我在最苦最倒霉的時候遇到你!
他的筷子指著碗里的肉,而眼睛卻瞟向蘆花。
蘆花的臉紅得仿佛桌上僅有的二兩酒是她一個人喝了一般。
朱女士說,時隔四十幾年,她仍能記起媽媽眼含淚光微笑的那一瞬,她覺得那是這輩子最溫暖的一刻。
幾年之后,父親平反并落實政策。她們的生母,以當初離開父親的速度,扔下已靠邊站的后夫,沖到鄉下,花枝招展地在父親面前一亮相,用朗誦腔說要與他“重新找回失去的年華”。父親說自己不懂表演藝術,也不想回省城,只想安安靜靜吃一頓東坡肉,你如果會做,就幫我做一份吧!
這場景很像川劇《馬前潑水》,負心的妻子想請重回榮華的丈夫原諒。丈夫在馬前潑了一盆水,說:你將水收回盆中,我便原諒你!
東坡肉就是父親潑出的水。
父親再沒回成都,只是在當地政協謀了個閑職,退休后與蘆花一起,白天讀書釣魚,晚上看五集連播的電視劇,吃吃貓貓魚和東坡肉,至前幾年無疾而終,享年76歲。死前,他無數次給兒女們說過:“你們一定要好好對待你們的媽媽。”
這里,他所說的媽媽,指的是蘆花。
兒女們都回省城工作了,并各自生兒育女。他們前些年也試著去看過親媽,但每一次聽到的,都是她怨念十足地咒罵父親的品味和蘆花的丑,于是就再不去了。
蘆花不習慣城里的生活,一個人在老家生活,她說這里每一片樹葉上都結著以往的日子,令她欣喜快活。兒孫們每月都會回去看她,一到家就嚷嚷著要吃貓貓魚和東坡肉。
我在樓上花園,曾碰到過一個婆婆來澆水,頭發雪白,衣著干凈,兩個牙齒齙在外面,很有卡通感。
我深度懷疑,她就是偶爾來成都看女兒的蘆花,想問問,但害怕太唐突,沒好意思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