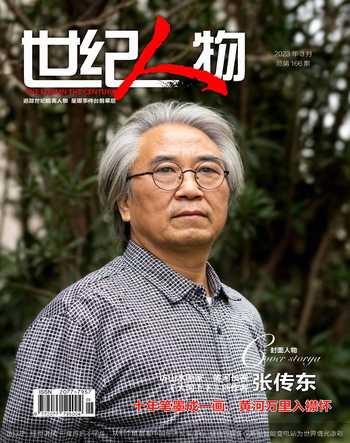“馬上天子”朱棣如何挑選自己的文治團隊?
張磊

“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
刀槍出政權,這是歷代不易的道理。二十多年的時間,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從起兵到登基稱帝,一手造就了明王朝。年號“洪武”,更是推崇武功,彰顯武事之威。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這也是歷代不易的道理,隨著歲月的流逝,文治在與武功此消彼長的競爭中漸漸占據優勢。
開國后,朱元璋承襲了元代相權獨大的中書省制度,國家政務凡事先匯報丞相,然后向皇帝奏聞。相權擴大后對君權的要求是:君主應當是國家元首,宰相應當是行政首腦。而在朱元璋看來“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之能馭不能馭也”,即天下的治亂興衰與君王的駕馭能力是一致的。至于丞相的權力,在他眼里更是“冢宰之職,出納王命”“分理天下之多務”,丞相職在完成君王交代的事務,屬于執行者。可以說,明初的君相矛盾是結構性的,很難化解。
對此,朱元璋曾經也做過一些小的調整,諸如奏事不用給中書省,“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等;按照邏輯,中書省為了適應君權的需要也做過一些調整,不會“獨專省事”。但結構性的沖突遠遠不是進退幾步就能解決的。最后自然是以強勢的一方勝利而告終。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對此進行重大改革,一改歷朝眾建相以分相權的策略,從根本上廢除丞相制度,“特詔天下罷中樞,升六部,使知更定官制”,中書省的權力分歸自身與六部,決策歸己,由是乾綱獨斷,政由己出;行政歸六部,由是彼此頡頏,不敢相壓。
從皇權獨大與皇基穩定來看,這是朱元璋的一大勝利。但“事皆朝廷總之”,皇帝除了國家元首之外,又成了一個事必躬親的政府首腦。廢相后,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詳、處理章奏600余件。龐大的決策量讓他感到“密勿論思,不可無人”,重要國事問題需要幾個參謀助手。在廢相當年的九月份,朱元璋根據古代四輔臣的傳說設立了四輔官。四輔官選拔的標準是對皇帝忠誠,行事公正。但這種老人政治方式本身就預示了它歲命的短促,最后四輔官或致仕,或罷官,或病故,或坐事誅。在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朱元璋仿照宋制設殿閣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
洪武中后期,太子參與處理政務的機會越來越多,不僅得到了政務訓練,也分擔了朱元璋的工作量。當太子死后,議論復相的自然越來越多。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下發一系列詔諭:多次明確廢相的態度。一方面強調自己“起兵至今四十余年,親理天下事務,無不涉歷”,表明自己對處理政務等事有足夠的經驗和能力;另一方面強調自古丞相“多有小人,專政亂權”,并申明現在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最后告誡所有人誰再談立相即處死其全家,并昭示相關講話讓全天下人知曉。
這一系列講話,從制度與法理上杜絕了丞相制恢復的可能,不意間為內閣制的發展開辟了一扇窗。
建文四年(1402)六月,靖難之役終于分出勝負,朱棣奪權成功,榮登寶座。登基后的朱棣發現雖然從龍之臣眾多,但多是龍精虎猛的武將。這存在兩點難處,一是難以適應國家治理的需要,二是難以實現收拾人心的工作,因而必須任用文官。起初朱棣是想用建文舊臣,但方孝孺這樣的名流拒絕與新朝合作,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這年八月,朱棣親自圈選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九月圈選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入直,并參與決策事務。至此,永樂七人內閣形成。
與后世閣臣由外朝大臣推舉不一樣,這次的入閣完全是依照朱棣個人的感情為自己選配的。解縉33歲,才具驚人,渡江后早早歸順;黃淮在御前答問深得皇帝滿意,與解縉一樣,在入閣前在皇帝御榻左右,備顧問;楊榮,31歲,七人中年齡最小,在成祖入京的時候迎謁馬首,請先拜謁祖陵以示正統,故而獲得賞識;其他三人也是名重一時的才學之士。除楊榮、胡廣、解縉三人已在翰林院供職外,其余四人在入閣前都無一例外地先被提擢進翰林院供職。也恰因如此,他們在受到恩寵之后,翰林院身份讓他們順利主掌翰林院事,翰林院漸漸成為內閣下屬部門。
當時朱棣和他們之間的相處頗有上古遺風,深有君臣相知之感。在即位后,朱棣與七人朝夕相與共事,對他們“恭慎不懈”的態度非常滿意,并在宮中常常對皇后談起。后來徐皇后在宮里接見解縉等人的妻子,都賜給五品冠履,享受命婦待遇。
這是一個年輕的秘書班子,因為性格不同,他們的命運也各異。
解縉起初最受賞識,不到半年的時間,就從從九品被破格提拔到了從五品,連升八級。解縉在儲君選立上立下大功,但解縉在征交趾問題上與朱棣意見相異,開始了失寵之路,在永樂十三年(1415)被殺。
楊榮學識深,且深諳事人主之道,“進諫有方”,知道在什么時候說什么樣的話。有記載說楊榮善斷,遇到六部大臣謀議不決,朱棣不高興甚至發怒的時候,只要楊榮一到,幾句話就把緊張氣氛變得緩和了,朱棣也因此化怒為喜。正因為如此,直到朱棣死,楊榮都未曾離開朱棣的左右。
金幼孜整體比較低調,簡易靜默,氣度大,越受榮寵,越謙遜低調。五次扈從北征,其間多有危險,糧乏缺水更是家常便飯,但從無一句怨言,而建言獻策多有幫助。他的這種謙虛謹慎,深受朱棣的嘉許和同僚們的贊賞。
楊士奇每當朱棣離開京師,都是東宮太子監國的輔臣之一。因此永樂十二年、二十年兩度下詔獄。
胡儼不善于領會朱棣的意圖,在永樂二年升任國子監祭酒,沒再預機務。

胡廣謹慎小心,性情縝密,深得朱棣寵幸。
黃淮在朱棣北巡時,輔導皇太子監國,永樂十二年下獄,在獄十年,直到朱棣死后才被釋放出來。
可以發現,七位閣臣的命運與永樂時期的政治結構高度相關,進而對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朱棣在南京登基后,北部邊疆問題始終沒法解決,尤其是永樂七年丘福北征漠北失敗后,整個北部邊防形勢迅速惡化,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使者記載“韃靼軍去北京不遠”,“王師畏韃靼,盡入城堡”,可見形勢之緊張。為此,朱棣率大軍常年駐屯北京,太子以監國身份在南京處理國家政務,形成了“皇帝主軍,太子主政”的格局。其中閣臣楊榮、金幼孜、胡廣常年隨從朱棣,“扈從行營,贊襄軍務”,獲得恩寵獨多,始終受重用,只是胡廣在永樂十六年病逝;楊士奇、黃淮、解縉多隨太子處理政務,黃淮和楊士奇輔佐皇太子監國。君王與太子的矛盾如君相矛盾一樣,也是歷史發展的重要矛盾,因此三人命運多舛。也正是這一結構,無論政局向哪發展,總有閣臣會成為股肱之臣,內閣成了一個基本的制度。
閣臣入直的主要內容是預機務,一是當顧問,了解機務信息,參與核心機密的最初咨詢,做好參謀助手;二是做秘書,作為“代言之司”,代皇帝起草文書材料。有一次,成祖在立春日賜給解縉等與六部尚書一樣的金綺衣。解縉等入謝時,明成祖云:“代言之司,機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故于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云:“若使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共勉之。”從這種情形可以看出,內閣實際上起著一種皇帝智囊團即天子幕僚的作用。

當時內閣事務眾多,楊士奇晚年回憶:初建內閣的時候,機要事務多且緊急,經常從早上工作到晚上,七個人每天早朝后,即入閣處理事務,都沒有時間出來。其中所替皇帝草擬的文稿,多易其稿,凡是詔書命令、禮典庶政、機密事務均參與起草。
楊士奇的敘述大致勾勒出閣臣工作的基本情形與強度,很像皇帝的政策研究室,負責給皇帝草擬材料,充當參謀助手。成祖也是同樣的認識,他對楊榮說:“天下事朕與若等共計之,非若六卿只分理也。”將“共計”與“分理”作為區分內閣與六部職能的重要依據,可謂一語中的。“分理”負責執行天子命令,而“共計”則兼有顧問與輔助決策的功能。
在永樂五年,朱棣要求吏部對考滿的閣臣不派外任,這意味著內閣成為永久性機構。同時內閣有了固定的辦公場所,并有制敕房與誥敕房是從屬于內閣的兩個輔助性機構。由于閣臣受寵獨多,閣臣開始逐步領翰林院事,翰林院漸漸成了內閣的下屬部門,到宣宗時期,翰林院的新辦公地建成,就更脫離核心,對內閣依附更加強化。而且內閣屬于內廷要害部門,很有威嚴性,當時規定凡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內閣,違者治罪。
值得注意的是,內閣受重視的重要體現就是不斷加秩進位,加太子輔導官職,如左右庶子、左右諭德、左右春坊大學士;所受的賞賜與尚書一等。經過永樂一朝的加官與加銜及領事,基本已經在既有框架內發展到極致,剩下的就是加外朝的部院銜。


當然,永樂朝內閣制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皇帝秘書班子的基本屬性還是不可能改變的。內閣沒有管轄政府部門的權限,各部門上奏也是直達御前。且當時“章疏多出宸斷”。時人評價為“永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雖依毗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永樂十七年,楊榮給皇帝建言軍、政、法司諸多部門存在的弊端,朱棣在看后很滿意,評價非常之高,稱贊其抓住了當下的制度弊病。話鋒一轉,“你是我的心腹之臣,如果直接進言,會讓群臣覺得親信政治,猜疑決策,不如秘密讓御史代言,這樣就完善了”。
這個案例生動地描述了閣臣的角色與職能:處理皇帝事務,權力來自皇帝。所以該政府處理的事歸政府,該政府說的話歸政府說,這一隱晦但的確存在的界線還是時刻在提醒著每一個人的。
總之,在永樂時代,閣臣深受榮寵,加銜與位階逐步提高,內閣有固定辦公場所,內閣制度初步形成,剩下的就是首輔、票擬、加政府官銜的演化了。
作為文官化、行政理性化趨向的一面是對文官的重視,另一面就是人才選拔的正規化、制度化。在明初選人有多途,薦舉是其中重要的途徑,科舉的重要性與發展前途并沒有顯露出來,甚至朱元璋一度停了科舉。朱元璋在政府改組廢除丞相之后的兩年才恢復科舉。
因為戰爭的緣故,應天府與浙江等地布政司沒有完成建文四年的鄉試。在永樂元年(1403)二月,朝廷頒詔當年八月應天府即浙江等布政司皆補試;北京附近府縣學校因兵災荒廢的,暫時停止,等永樂三年仍舊鄉試。
永樂二年的會試是朱棣登基后的第一場最高規格的選拔人才考試,朱棣對其非常重視。會試前,禮部奏問會試應錄取多少人?事事以恢復洪武舊例的朱棣反問道:“洪武時期選拔多少?”尚書李志剛回對說“各科不一樣,最多的470人,少的30人”。朱棣說:“我初登大寶,第一次取士,應該多錄取,以后不以此次為準。”并指出“學者成材亦難,當取其大略,其細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語疵而不害理,亦可備數;然科舉是國家取人才第一路,不可濫,且文體毋尚虛浮,唯取樸實。”
可見朱棣首次會試就要在取士人數上與其父太祖看齊,取472人,并明確指示取才要不拘泥于文字細節,要取實際人才。這既反映了他通過“靖難”后急欲籠絡士心的迫切心情;也表現了他敢于和太祖比肩的膽量。當然,這也反映出此時官職空位較多,仕途尚未壅塞。此外,朱棣“科舉是國家取人才第一路”的認識標志著明代最高統治者在洪武、建文兩朝實踐的基礎上,已十分堅定而明確地把科舉考試作為選拔人才的重要渠道。
周忱以善于理財而成名。他是永樂二年的進士,當時朝廷選新進士28人文淵閣學習。周忱向皇帝上奏自己年齡小,希望再學幾年。朱棣非常高興,夸贊其為有志之士,特命增加一人。并命司禮監每月要給筆墨紙;光祿寺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工部擇近第宅居之。并說“不任爾等事,務實得于己,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辜朕期待之意”。
朱棣對下第舉人同樣非常關心,認為“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禮部選取貢士六十人上奏。朱棣召見他們,賜給冠帶,安排在國子監繼續學習,以等待下一次考試。并且勉勵說:“士當立志,志一則工專,工專則業就。后科第一甲人有不在其爾曹乎。”可見朱棣的愛才程度。
永樂一朝,是明代科舉制完善的重要階段,重點在三個方面:
一、規范完善殿試制度。在永樂二年會試后,官方在洪武時期所行的殿試制度基礎上重新厘定、豐富和發展,使其更加嚴密、規范和完備,明代殿試制度由此定型。明確規定讀卷官以閣臣、九卿及詹事府、翰林院堂上官等高級官員充任,閣臣在其中處于核心地位。由此,讀卷官品級大為提高。
二、庶吉士制度確立。永樂二年(1404)殿試結束后,在新科進士中先后選取123人為翰林院庶吉士。此次科考后,庶吉士須考選二、三甲進士之優者為之,標志著進士觀政于近侍衙門者被稱為庶吉士時代的結束。
三、確定考試標準內容。永樂十五年九月,修成《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朱棣親自為其作序,頒布天下,以兩部《大全》統一對《五經》《四書》的訓解,作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和陶冶、牢籠士子思想的工具。
科舉制度的完善也意味著選官制度的變化。由科舉、歲貢、薦舉三途漸漸變成了科舉為主。科舉考試的發展與科舉制度的完善也對社會風氣與社會觀念產生了重大影響。宣德朝進士李賢在回憶錄中寫道:戶部侍郎焦宏的父親曾經是萍鄉縣縣丞,有一天,與幾個朋友、同僚在吃飯作樂時,恰好有在外退休歸鄉的官員,談起了科甲出身問題,焦宏的父親感到非常羞愧。之后對兒子說:“當努力向學,求得科目出身(在科舉上取得一些成就),給你父親爭點氣。”這個故事應該是焦宏和李賢同朝為官的時候給他講的。焦宏是永樂十九年的進士,可見當時社會觀念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明代是一個皇權空前強化和官僚制度高度發達的時代,皇權的影響力和朝廷對社會的控制力已通過各級完全聽命于皇權的官僚而落實到每一個良民身上;與此相應,“民秀”或“秀民”也把能夠出任朝廷官員看作是實現個人價值和光宗耀祖理想的首選甚至唯一途徑,這大大加強了帝國的控制力、流動性與認同感。
朱棣馬上得天下,在得天下之后更多的也是軍事征伐。但在這個“君王主軍,太子主政”的時代,其命運不同的七人內閣使內閣制初步形成,科舉制也漸漸成了選拔人才的主流,科舉觀念深入人心,整個社會逐步形成崇文尚科舉的風氣,帝國的統治基礎空前擴大。(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責任編輯/李雪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