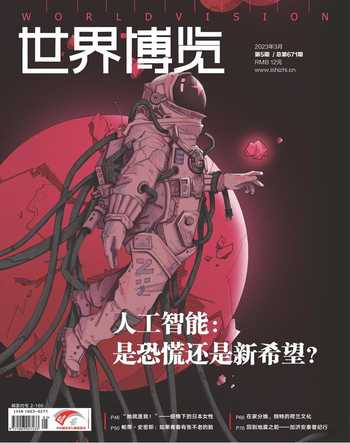在家分娩,獨特的荷蘭文化
Yinanaa

荷蘭每年約有三分之一的新生兒在家誕生。
荷蘭擁有歐洲最高的在家分娩(home birth)率。自1990年以來,荷蘭每年約有三分之一的新生兒在家誕生,這個數字雖逐年波動,卻遠遠高于同等經濟水平的歐洲發達國家——在鄰國比利時、德國、法國,這個數字都不超過2%。來自歐洲國家或其他地區的女性在聽聞或親歷荷蘭女性在家分娩這一“制度”后,往往也會感到不可思議。
我在荷蘭的一位巴西朋友最近便在家里迎來了她的女兒蓋亞。最初,當醫院告知她將在家中分娩時,她完全懵了——“在巴西,沒人會這么做!”但保險條款使她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她直到產前兩周還在工作,直到一個清晨感覺身體開始“發動”。親友從巴西和波蘭趕來陪在她身邊。分娩的漫長和疲憊都超乎她想象,好在家中的環境讓她放松,丈夫和助產士的陪伴讓她感到“安全”。助產士引導她和丈夫象征性地“拉住”女兒的小腳,引領她來到這個世界,那是一個神圣的瞬間,讓她和丈夫感到更加緊密地與彼此連接在一起——她沒想到竟然順利在家中生產了。“我做到了”,她不無驕傲地說,雖然她并沒有因此成為一個“家庭分娩主義者”,卻感受到了一種自信。

一位荷蘭的母親在家分娩后為孩子稱重。
在荷蘭,醫院會為產婦配備免費的助產士協助在家生產。醫療保險只覆蓋因高齡、多胞胎、并發癥(如妊娠期糖尿病)等客觀因素(而不是出于主觀恐懼)被評估為在家分娩會有難產風險的住院分娩。當然,在家分娩過程中遇到困難或危險的產婦也會被緊急轉移至醫院。
荷蘭衛生部門鼓勵荷蘭女性在家分娩,這反映了公共衛生中不將分娩“醫療化”的思路和減輕醫療系統負擔的取向。在荷蘭衛生部門的官方網站上有一篇《你何種情況下不該去見全科醫生》的“勸退”文章,其核心思想是,感冒這類自限性疾病,如果沒有危象,不須求醫。與此同理,荷蘭衛生系統也將分娩視為一個自然的生理過程,如果沒有已知的危險因素,不須醫學干預。正由于“非必要不就醫”的傳統深入人心和醫療系統嚴格的轉介制度(在荷蘭,除急診外,人們不能直接前往醫院就醫。所有醫療需求必須由全科醫生評估后轉診到專科醫生或醫院)。荷蘭醫療保健系統并沒有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的赤字問題。
荷蘭衛生體系為在家分娩提供的系統性支持名為“產婦援助”(Kraamhulp)——醫院會為懷孕早期的產婦安排一位有資質和經驗的護士,在分娩前與產婦保持聯系、建立信任,分娩時擔任助產士協助生產,分娩后提供產后護理,甚至幫助料理家務。在理想狀態下,她們將提供持續的關懷、幫助和支持,而非一過性的醫學干預。
“在家分娩和在醫院分娩一樣安全”,這是關于在家分娩最流行的一句口號。2011年,一項對2000年到2007年間荷蘭近68萬例低風險分娩的比較研究顯示,低風險產婦在家分娩和醫院分娩的新生兒死亡率并無顯著差別。2018年,加拿大一項對英國、荷蘭、挪威、瑞典、新西蘭等國家共計50萬例低風險分娩的研究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但在家分娩的反對者們也有充分的理由。在家分娩首先意味著沒有麻醉。無痛分娩需要專業的麻醉設備和有經驗的麻醉師,這只能由醫院提供。從醫學的角度說,疼痛會造成精神緊張和肌肉痙攣,使產婦無法專注發力,可能延長生產時間。在現代醫學的進步允許減輕疼痛的情況下鼓勵在家分娩和忍受疼痛,被質疑為有違女性福利。
而生產過程的風險和接受及時救治的不確定性則更令人擔憂——反對者們指出,分娩不是一種疾病并不意味著它沒有危險。2021年,一部引起廣泛討論的電影《女人的碎片》正講述了這樣的情形:女主角瑪莎身體健康,孕情良好。她選擇了在丈夫和一位訓練有素的助產士的陪伴下在家分娩。由浴缸到床上,瑪莎遲遲無法娩出胎兒,胎心驟降。盡管助產士打電話叫了救護車,瑪莎的胎兒還是因缺氧而死。
也有不少荷蘭女性在社交網絡抱怨“產婦援助”制度所承諾的持續性支持并不完備。每當她們反映不適和疼痛,都會被助產護士以一句“正常情況”打發回去,更別提見到產科醫生。“非必要不就醫”仿佛成了將一切人攔在醫療資源之外的合理借口。當在家分娩的倡導者為選擇權吶喊時,產婦自由選擇在醫療機構分娩的權利似乎已被漠視——經濟闊綽的人可以隨時憑私人保險就診于私人醫院,依賴公共保險的人則被迫在家分娩。盡管荷蘭人并無分娩等于“鬼門關走一遭”的觀念,但準媽媽們也同樣擔憂分娩時的種種風險,以及在這些風險出現時,她們與醫療資源的距離。
荷蘭之外,在英國、美國和北歐國家,“在家分娩”運動正在悄然復興。然而,只要稍一觀察,便會發現,在家分娩是一種發達國家的特權——信任自己的身體,首先意味著信任隨時都會提供支持的醫療資源。在這些資源中,最重要的便是護理資源。在家分娩的核心理念是分娩的“去醫療化”。在操作層面,這意味著醫療責任由產科醫生轉移至產婦和助產士在內的護理人員。目前,發達國家往往已發展出專業的產科護理人員培養體系,但熟練的產科護理人員依然供不應求。
能請得起一位有經驗的助產士,本身就是一種特權。而這種特權,在一些發達國家被體系化為女性的福利。一個反例則是,在同樣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的瑞典,由于地方議會拒絕將助產士的工資納入公共開支,在家分娩者只能自費聘請助產士和護理人員,這極大打擊了瑞典女性在家分娩的積極性。或許更有廣泛性的反例是,在某些低收入國家,婦女因為醫療資源的極度匱乏而被迫在無幫助無保護的情況下在家分娩。
關于在家分娩的爭論還在繼續。來自不同社群和文化的人也在多重因素的塑造中做出選擇。在這個意義上,荷蘭的在家分娩浪潮對于他國所能提供的經驗或許是:分娩并不只是一個生理過程。在家分娩有其醫學價值和文化價值。但在這些價值之外,分娩自由的傳統必須由完善的助產及護理系統和涵蓋更廣的福利體系保駕護航。
在家分娩的流行也與荷蘭發達的女性權利思潮和運動有關——人們認為,醫院分娩是一種高度標準化、集中化甚至產業化的過程。產婦如流水線作業般被推進產房,生產,然后“出廠”。而在家分娩則允許“個性化”的主宰和創造。在家分娩過程中,產婦在十月懷胎過程中與助產士等護理人員建立的情感聯結,也比產科醫生短暫的“職業”聯系更具真實性,更能幫助產婦以信任、放松的心態生產。

荷蘭阿姆斯特丹,“準父母“們在上課學習分娩姿勢。
在醫院分娩的產婦要犧牲掉一部分隱私。在家分娩則為產婦及其伴侶保留了充分的自主權——產婦無須在得到醫院允許后匆匆趕往醫院,匆匆生完孩子,匆匆洗澡,然后匆匆出院(在荷蘭,生產后若母子均無問題,稍事休息便會被“趕出”醫院),而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在熟悉的地方生產。她們可以將家里布置成喜歡的樣子迎接新生命的到來,可以和家人及朋友交流,可以在疲憊時休息一陣兒再“發動”……支持者們認為,在家分娩減輕了產婦和伴侶的心理負擔,從醫學的角度而言有助于順利分娩。
在家分娩的支持者們往往指出,在現代醫學出現前,人類幾千年的漫長歷史中,女性一直在無醫學干預的條件下分娩。甚至到20世紀70年代,四分之三的女性依然在家分娩。“分娩的醫療化”是一個極為晚近的觀念,它反映了人們在后工業革命時代對“最小化風險”和“控制一切”的迷戀,而現代醫學的進步為此提供了技術支撐。
還有一些支持者認為,這一獨特的荷蘭文化在現代觀念的變化和分娩的“醫療化”的沖擊下,甚至有消失的可能。因此,他們成立了在家分娩團體,撰寫科普文章,向學校和社區提供培訓課程,以期消除人們對在家分娩的恐懼。
自然、自主、自由,這些無形的文化價值是在家分娩的吸引力所在,也是擁躉者們的立場。但荷蘭的在家分娩文化也始終伴隨爭議。
(責編:劉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