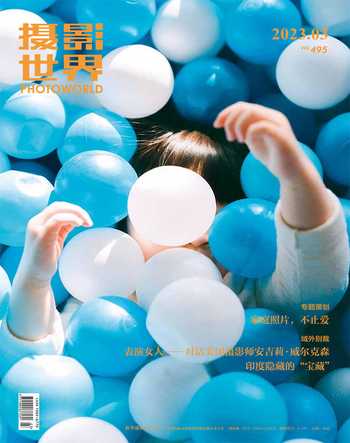風景的動態存在
姜緯
攝影大師李·弗里德蘭德以社會題材聞名于世,但他于1990 年代至21 世紀初在公路旅程中拍攝的風景照片,卻少為人知。他這些照片展示了美國西部景象,均使用大底片和廣角鏡頭從非常規的位置進行拍攝,在呈現地質地貌狀況的同時,也扭轉著人們對宏偉壯觀的習慣性期望。
盡管李·弗里德蘭德的風景照片包括了一些具有美國西部鮮明特征的區域,比如優勝美地、死亡谷、大提頓和大本德國家公園等,但其視角與形成這些經典風景名勝的國家概念的理想化表達方式截然不同。
李·弗里德蘭德的風景攝影匯集了一系列自然形態:陡峭的山脊、如鏡的湖泊、蜿蜒的樹林和叢生的草坡。即使在白天,他也經常使用閃光燈來達成將前景和背景融合在一起的密集分層效果。
在閱讀觀賞這些照片的過程中,引起了我關于風景攝影的一些想法。
德國當代哲學家、美學家漢斯- 格奧爾格·伽達默爾有個著名的觀點:“傳統,不是我們要繼承的現成遺產,而是靠我們今天的創新來參與并規定的動態存在。”在風景攝影的傳統和脈絡中,李·弗里德蘭德的實踐,就是這樣的動態存在。去美國西部拍攝,顯然是要力圖突破前輩們建立起來的先驗的背景與架構。在他鏡頭里,達意高于狀物,也就是說,表達意味的興趣要大于描摹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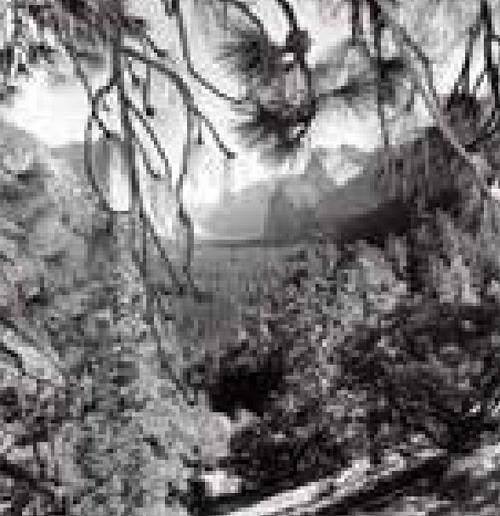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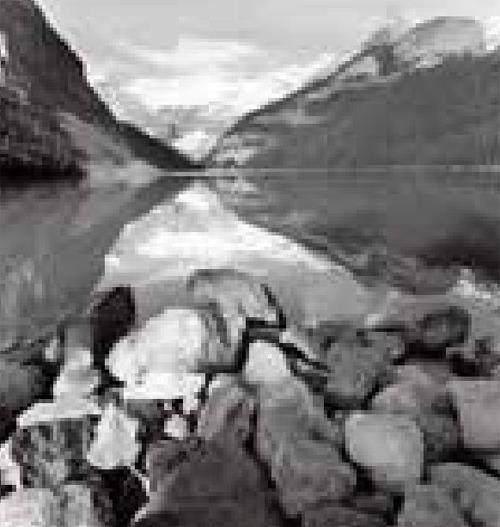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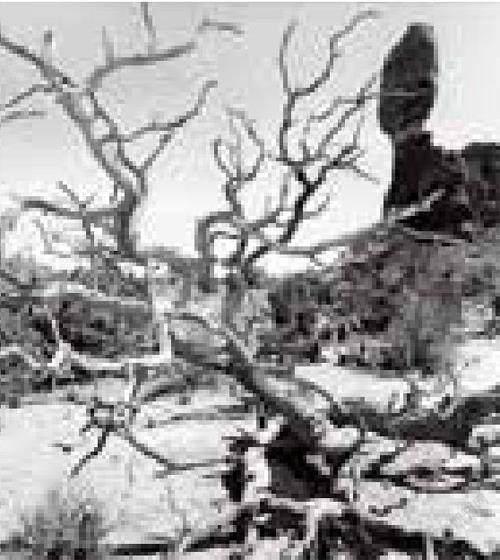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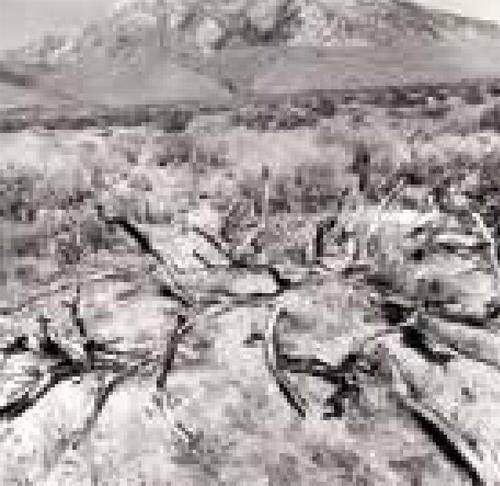
動態存在自有其意義。亦步亦趨,傳統就仿佛一潭死水,逐漸失去其應有價值,變成孤立的標本。正由于動態存在,傳統和脈絡才不至于枯竭、寂滅,才有可能作為參考和基礎,也能起到發動機的作用。
所謂風景,其含義都是人賦予的。我們看到、領略到、品析到的每一處景觀,它呈現給我們的含義,都來自其背后交織在一起的話語。對此的觀察與思索之所以值得留意,是因為所有的景觀必然涉及人,必然涉及控制、利用、表征、再現、改造,等等。我們任何人生活在其中的空間都是雙重的:風景既是地理空間,又是意義系統編織起來的空間,而后者至少和前者一樣重要。
根據環境心理學的觀點,風景可以理解為地表某一空間的綜合特征,包括其功能與結構特征,以及表現為各因素相互作用的關系,是一個多層次的生活空間。風景的質量取決于兩個特性:“可解性”和“可索性”。前者體現了人對于安全的需求,后者反映了人對于未來的求知欲,人期待運用種種信息去預測、探索未來的生活格局。而之所以總有些風景照片被人詬病,是因為它們缺乏動態存在。一百年前的攝影師看到什么,如今的攝影師也只看到幾乎同樣的。眼里只有風景,沒有風景中的自己,于是了無生氣。
傳統和經典的歷久彌新,取決于重新開啟的歷史語境。我們對線性史觀和自然之道的反思,展現的是人與世界相互關聯的具體性。新風景之“新”,就是要深入探討“風景”所提供的美學和表達方式能否演繹與衍化出新的境界,對我們當下洶涌而至的感官體驗進行有效的整理和構建。也就是說,新風景之“新”,在于傳統風景攝影要經過“轉化”,合理改造其內在語法,使得它向復雜的當代生活完全開放。這注定不易,但非常值得我們去努力追索。
在我看來,風景攝影固有之精神,主要有兩方面。
一是美學。無論何時何地,一旦離開了美學思維,人們將很難找到更好的出路。審美蘊蓄著自由和創造,其強烈持久的內驅動因的作用與滲透,使得審美成為理性與感性的交叉點和結合點,并承擔起與社會存在不斷加劇的異化現象相對立的職責,就如同理查德·舒斯特曼在其《生活即審美》中深刻指出的:“在一個其他各個方面都是冷冰冰的物質主義和法則規定的世界里,審美成了一個自由、美和理想意義的孤島,它不但是最高愉快的唯一所在,而且是精神皈依和超越的一種方式。”因此,風景攝影的美學訴求,尤其置于中國語境,是否完全時過境遷,我看不見得。
二是借鑒。一部攝影史,從不乏有志者把攝影作為獨立的視覺藝術加以看待和實踐,對此我非常贊同。但同時,一部攝影史,也是不斷借鑒、不斷學習從而不斷發展壯大的進程。我曾經寫過:“攝影短短兩百年不到,并不足以向時間攫取更高更多的價值來供我們用度,故而,它有繼續創造的動因。”換個視角看,方興未艾的當代藝術,博采眾長,跨越邊界,攝影在其中風生水起,而攝影本身,更沒有理由畫地為牢。所謂繼續創造,至少一部分表達方法有賴于此。
風景攝影固有的精神,我們要發揚光大。值得注意的是,說到風景攝影,大可不必拘泥一時一地一人一招一式。相較于郎靜山先生的年代,如今資訊發達繁盛,眼界闊大,能利用的古今中外資源豐富多樣,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已成事實而不是愿望。美學和借鑒,不能僵硬,其外延和內涵,均應擴展、周轉、延伸,甚至脫胎換骨,我們要抱持開放的態度。
我們欣喜地看到,一些有想法的中國攝影師,已經在實踐方面走出了值得鼓勵和贊賞的堅實步伐。中國新風景攝影在數字化、互聯網的新時代的演繹與衍化,歸根結底,是考驗、檢視攝影師如何把重點放在對周遭景致的觀看理念上。被考驗、檢視的不僅關于景致,更是我們的身心觸動和感受。攝影師既是觀察者,也是被觀察者;既是影像的主體,同時又是客體。
我們樂見攝影師扭轉固有的影像風格,讓我們可以不單關注拍攝題材,也留意題材究竟以怎樣的方法來呈現;不僅看見山川,還能夠目及城市;或者日復一日行走四方,追尋影像的成果,經由反復的觀察和考量,使作品成為關于文化的視覺評論,而非只是描述一種單獨特殊狀態;又或者嘗試從復雜的景致里提煉純粹的經驗,以審慎但又直覺的表達來做出回應,引發觀眾內在的聯想與對話。
新風景之“新”,也是提醒我們,應當看到表相背后的重心,即如何理解、勘察歷史洪流中人的自然屬性和文化屬性,如何保持對當下生活的情感和警覺,同時又能通過照相機使這樣的生活獲得妥帖的形式感,進而重新使攝影的敘事觀念成為一個議題。
無論如何,中國當代社會畢竟提供了紛繁豐富的環境基礎,不斷產生著符號和意味。作為視覺的反饋,攝影已經出現多元的形態,關于“風景”的觀看、拍攝、呈現和議論,也成了繁復無盡的表述與想象的循環再生產。
在巨變時代,多數現成的模式已然或正在失效,既往的理念和經驗正在接受檢視,這是探究歷史的必要性,也可以說,這種探究就是理解和造就我們自己。無論傳統和歷史多么重要,都不可能永久地套在它們的軀殼里面凝固不動。如果沒有引入共時的橫向坐標,歷時的縱向坐標遠遠不夠。進入新時代意味的是,傳統和歷史將與當下多元文化廣泛地對話,這是風景攝影自我校正和修訂的前提。另一方面,風景攝影的精神以及意義,只能在與當下多元文化的對話之中得到充分的闡釋或驗證。因此,新風景攝影不是保存傳統和歷史的孤立標本,而應當以互動的方式活躍于我們的當代視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