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太空系統網絡作戰力量建設研究
張兆春 張皓陽
(1 西安衛星測控中心 2 四川大學)

近年來,美國將太空和網絡劃為作戰域,并納入其追求全方位優勢地位的戰略規劃中,在理論指導、力量編成、裝備建設、演習演練等方面全方位加強建設,積極搶占大國博弈的新高地。
1 太空系統面臨多重網絡威脅
太空系統所面臨的網絡威脅包括國家間的軍事行動和日常攻防、希望尋求經濟利益且掌握大量資源的有組織犯罪分子、計劃利用衛星碰撞等災難事件實現訴求的恐怖組織,乃至希望展示個人技術水平的黑客。
針對太空指控系統的網絡攻擊
當前,主要國家的太空作戰指揮控制中心既是太空態勢感知信息匯聚中心,又是太空資源調度與任務分派中心。敵方利用計算機成像、電子顯示、語音識別與合成、傳感、虛擬現實等技術制造各類假消息、假命令以及虛擬現實信息,并綜合運用網絡空間攻擊手段將其發布和傳播至對方太空態勢感知與指揮控制網絡,誘使對方太空作戰指揮系統做出錯誤判斷,使其采取利于己方的行動,進而達成影響和削弱對手指揮控制能力的目的,取得戰略戰術上的有利態勢。
針對衛星等航天器系統的網絡攻擊
敵方利用接收途徑和各種軟硬件所存在的“后門”漏洞,通過欺騙手段將網絡病毒和分布式拒絕服務工具等網絡空間武器遠程植入或無線侵入到對方的衛星等航天器測控網絡,注入惡意上傳指令,或對其星載計算機進行滲透、篡改、竊密和潛伏遙控,使星載工作設備陷入間歇性或全面性癱瘓,或誘騙星載計算機非正常操縱衛星姿軌,甚至誘使衛星熱管理系統失效,從而引發星載電子設備燒毀甚至爆炸,造成永久性物理破壞。
針對地面基礎設施和天基信息鏈路的網絡攻擊
對手可以針對地面基礎設施進行網絡攻擊,如對衛星控制中心、相關的網絡和數據中心實施攻擊,可導致直接重大安全危險和潛在的全球性影響。對手可結合電子戰、信息戰實施網絡電磁頻譜干擾,阻斷星上、星下遙測遙控信號,干擾對方的天基信息系統數據分發鏈路。
針對空基系統的網絡攻擊
包括對通信和導航網絡的干擾、欺騙或劫持,瞄準或劫持控制系統或用于執行任務的特定電子裝備,還可以直接拒止空基系統對天基信息系統的使用,在太空域中切斷空基系統數據采集、處理、傳輸所依賴的鏈路和節點。
2 美太空系統網絡安全的戰略理論條令
國家戰略—指明威脅確立原則要求
2020 年6 月,美國新頒布的《國防太空戰略》將網絡戰與電子戰列為太空對抗的主要手段,明確提出“國防部正將其太空方式從支援職能轉變為作戰領域,以應對動能打擊、電子戰、網絡攻擊等威脅和挑戰。”充分說明,美軍在備戰太空的同時高度重視太空系統所面臨的網絡威脅以及這兩大作戰域之間的交織和滲透。
基于對太空領域網絡安全重要性的認識,2020年9 月,美國發布了首份針對太空領域網絡安全的政策文件——“航天政策5 號令”(SPD-5),確立太空領域網絡安全的原則,要求太空系統在設計、開發與運行階段都要充分考慮網絡安全問題,通過跨部門、跨聯盟、軍民商一體的合作,制定嚴密的安全策略并預留保底手段,管理好供應鏈風險,確保太空系統的網絡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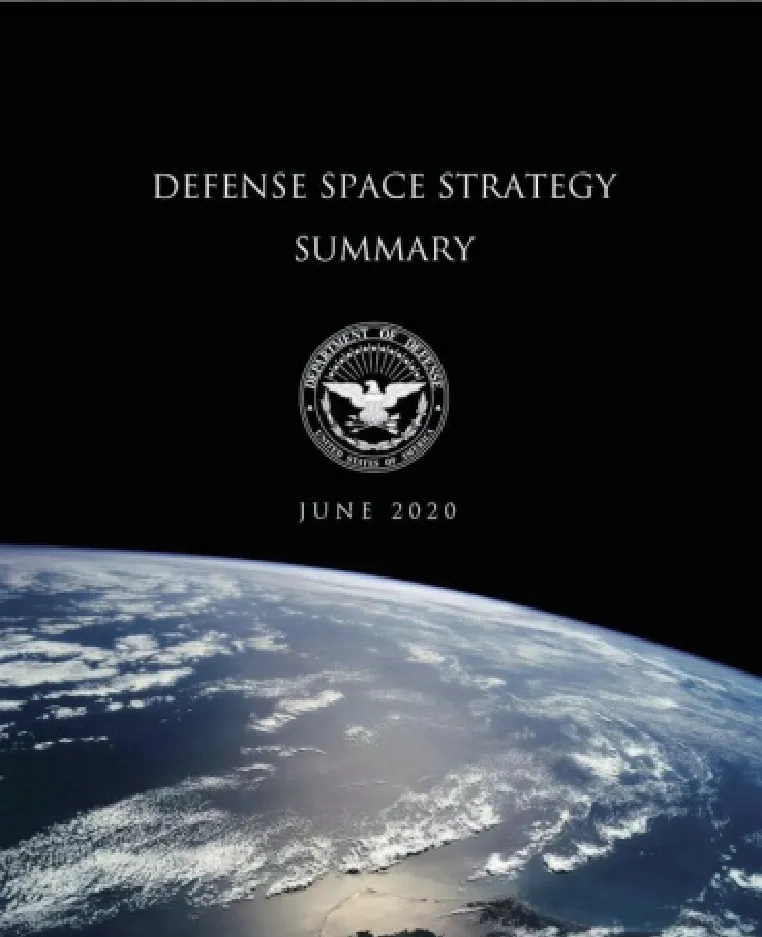
美國2020 版《國防太空戰略》
2020 年12 月,美國又推出新版《國家太空政策》,新增了單獨的“太空系統網絡安全”“電磁頻譜保護”兩小節,更加強調了網絡電磁空間安全對于太空系統的重要性。在專門針對天基定位、導航與授時系統的政策文件——“航天政策7 號令”(SPD-7)中,特別要求提升GPS 及其增強系統和設備的網絡安全性能。
“天權”理論—闡釋太空作戰的網絡維度
2020 年8 月,美國天軍(USSF)正式發布頂層作戰條令《天權》(Spacepower,又譯作“太空力量”),提出“天權”理論:改變了過去從“感知、利用、控制、進出”等任務領域維度去研究理解太空作戰的理論框架,提出從物理維度、網絡維度和認知維度描述太空作戰問題。“天權”理論將網絡維度提高到空前的高度,認為網絡空間作戰是太空作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空間是指揮控制太空作戰力量,利用太空支援聯合作戰的重要依托,同時也為對手實施太空攻防提供了更低成本和更低技術門檻的手段。《天權》將太空作戰理論區分為軌道戰、電磁戰、網絡戰等七個專業領域,掌握這些專業領域技能是成為太空戰專家的必備條件。
作戰條令—明確力量統籌運用的方法要領
2018 版《太空作戰條令》(編號JP3-14)明確指出:太空與網絡電磁空間具有特殊的相關性,幾乎所有的太空作戰行動都依賴于網絡電磁空間,網絡電磁空間的部分重要行動只能依托太空系統;將網絡攻擊列為太空領域的主要威脅之一,要求情報部門重點預警網絡攻擊太空系統的相關事件,加強太空系統鏈路段、地面段的網絡安全防護。
2018 版空軍的《太空對抗作戰條令》(編號ANNEX3-14)在描述指揮關系時特別指出,聯合部隊空中組成司令部司令通常被授予“太空協調權”,該司令部匯聚了空中、太空與網絡空間三大領域的專家,其獨特的多層視角對于更好地協調太空作戰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從中可以看出太空與網絡空間的融合在指揮控制層面的重要性。
2019 版陸軍的《太空作戰條令》(編號FM3-14)將太空作戰與網絡空間作戰、電子戰有效集成融合視為陸軍太空核心能力的重要支撐,賦予了陸軍網絡中心在太空作戰中的具體職責。同時,要求執行太空作戰規劃時必須配備網絡電磁空間專業人員,一體設計太空與網絡電磁空間的作戰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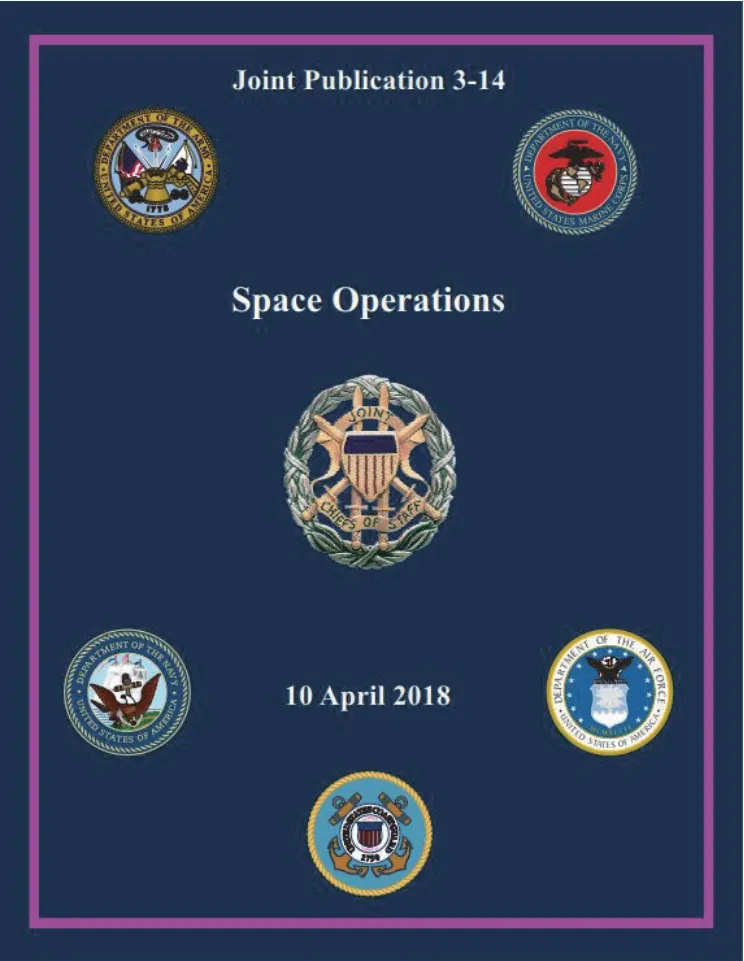
美國2018 版《太空作戰條令》
3 美太空系統網絡作戰力量編成
天軍謀求獨立作戰能力
2020 年7 月,美國天軍宣布重整原空軍太空作戰力量,隸屬于原空軍太空司令部的14 航空隊的主戰力量改建為太空作戰司令部,就地重組8 支德爾塔部隊(DEL),其中承擔太空網絡系統作戰的主要是德爾塔部隊第6 分隊。
德爾塔部隊第6 分隊專司測控網運行和網絡防御作戰,總部駐科羅拉多州施里弗空軍基地,前身為原第50 太空聯隊第50 網絡作戰大隊,下設第21、22、23 太空作戰中隊,第61、62 賽博中隊,5 個分遣隊及12 個位于不同地點的操作點位,共操作管理空軍衛星控制網(AFSCN)7 個跟蹤站15 套測控天線,以及6個GPS 專用地面站/監測站,承擔空軍衛星控制網運行管理、GPS 專用地面設備及整個測控系統的網絡防御任務。其中,第61 賽博中隊負責測控網網絡防御,第62 賽博中隊配屬給第4 德爾塔部隊(導彈預警),為其提供導彈預警系統網絡防御。第22 中隊是空軍衛星控制網的控制中心,第21 中隊為備份節點。
此外,彼得森-施里弗兵營第50 任務支持大隊第50 太空通信中隊負責操作運營空軍空間網絡防御相關單元(CDCC-S)并執行防御性網絡空間操作,保護關鍵的空間任務系統。

2020 年5 月15 日,美國太空部隊旗幟亮相
其他軍種基本實現一體化運用
美海軍將太空力量與網絡空間力量一體建設管理與運用是基本規律。美海軍艦隊網絡司令部/第十艦隊通過被指派到海軍網絡空間作戰司令部太空作戰局的人員擬定海軍太空計劃,反饋太空需求,管理和維護海軍窄帶衛星系統,支持海上聯合作戰。美海軍陸戰隊于2020 年11 月成立了“海軍陸戰隊太空司令部”(MARFORSPACE),“將有機會在信息環境中創造協同效應,太空和網絡能力兩者結合可以提供競爭優勢。”
此外,美空軍、海軍部隊電子戰機作戰力量,可向太空網電作戰提供支援,通過“舒特”等武器系統對地面設備、星地鏈路等實施網電攻擊。
網絡空間司令部的支援力量
美軍網絡作戰力量主要由網絡空間司令部管理運用,當太空網電作戰需要額外的網絡作戰力量支援時,網絡空間司令部可向其提供兵力支援。網絡空間司令部下轄133 支具有全面作戰能力的網絡部隊,其中25 支為國家任務部隊和作戰任務部隊提供專業支援的“直接支援部隊”。
4 美太空系統網絡戰典型裝備
空軍衛星控制網鏈路防護系統
空軍衛星控制網鏈路防護系統(ALPS)部署于全球各站點的每1 套天線設備,通過可遠程操控的頻譜儀,操控中心實時偵測射頻干擾(RFI)行為,監測衛星測控下行S 頻段鏈路狀態。ALPS 后續將升級為射頻干擾監控系統(ARMS),對上行、下行鏈路均可實時監控,擴大鏈路態勢感知能力。空軍衛星控制網從2016 年起在第22 中隊增加防御性太空對抗崗位,用于監視衛星下行鏈路信號情況,偵測電磁干擾和射頻干擾行為。
防御性網絡空間作戰項目
防御性網絡空間作戰項目(DCO-S)是美軍針對空軍衛星控制網實施的防御性網絡空間作戰項目,旨在推進威脅偵測、防護、識別與響應工具開發部署。其中“蝎尾獅”(Manticore)偵測工具開展端點與網絡數據收集、數據提取與融合分析工具開發、集成與測試部署;“飛馬”(Pegasus)防護工具開展軟硬件供應鏈管理、信息加密和網絡加固;“羊身蛇尾獅”(Chimera)識別工具通過系統分析、漏洞映射和網絡/情報集成開展威脅識別;挪威海怪-1(Kraken-1)響應工具負責事件管理、調查和精準響應工具開發。
“賞金獵人”
“賞金獵人”(Bounty Hunter)系統為高度保密項目,主要能力是在特定作戰區域提供防御性太空控制支援,阻止對手指揮信息系統的有效使用。美軍在夏威夷、新加坡、土耳其、伊拉克和卡塔爾烏代德空軍基地等地均部署過Bounty Hunter 系統。
“舒特”系統
“舒特”(Suter)系統以電子干擾電磁波、敵方防空雷達探測電磁波等為載體實施入侵攻擊,取得系統控制權限后,通過修改作戰參數,或者利用“木馬”病毒癱瘓敵方防空雷達系統,達到突襲目的。目前,該系統已在美軍部署使用。
網絡飛行器
網絡飛行器實質上是一種特殊軟件,可安裝于美空軍任何電子介質,通過任意網絡空間入口注入,能根據需要實施網絡空間偵察和網絡空間攻擊任務。實施網絡空間偵察任務時,該飛行器既可主動識別己方網絡空間的潛在威脅,也可自主探測敵方網絡空間的情報信息;實施網絡空間攻擊任務時,該飛行器可作為惡意代碼的載體,攜帶病毒、木馬、蠕蟲等傳統意義上的惡意代碼,對敵方網絡空間實施破壞。
新一代干擾機
新一代干擾機除了實施電子進攻外,還可實施網絡空間攻擊,其關鍵技術是使用多用途有源電掃相控陣(AESA)產生用于網絡空間攻擊的數據流或惡意代碼,然后用專業波形和算法將數據流打包成無線電波束,通過敵電子探測設備天線進入敵防空系統、指揮控制網絡。美國海軍于2018 年正式裝備新一代“咆哮者”(EA-18G)電子戰飛機,能夠對敵方的雷達和通信網絡進行有效的電子攻擊。
計算機病毒
迄今為止,美軍已經研制出3000 多種計算機病毒武器。其中,“震網”病毒是首個利用網絡空間來控制真實世界的惡意代碼,“火焰”病毒是迄今發現的代碼量最大、設計最復雜的病毒,“勒索”病毒主要以程序木馬、郵件、網頁掛馬等形式傳播。
5 美太空系統網絡戰演習演練
構建專業化對抗靶場為演習演練提供技術支撐
2020 年5 月,美國防信息安全技術服務提供商美泰科技正式推出可重復使用的“太空靶場”(Space Range)虛擬作戰體系,通過模擬真實網絡環境,查明隱藏漏洞、不當配置和軟件缺陷,達到預防和挫敗網絡攻擊的目的。太空靶場可以提供現實網絡安全訓練,參訓人員“足不出戶”即可提升保護關鍵太空資源的能力水平。
此外,“太空旗”(Space Flag)演習主要依托波音公司的網絡化虛擬對抗系統,蘭德公司(RAND)的太空對抗推演也有太空防御分析工具(DSPAT)的支撐。
在戰略戰役演習層面探索天網一體化運用的指揮控制與方法要領
“施里弗”(SW)系列演習是美軍探索戰略戰役層級太空力量建設與運用的重大演訓活動。早在2009 年“施里弗-5”演習中就曾預測太空與網絡電磁空間將在多個層面交織在一起,并設想美軍及其盟友的多處太空和網絡電磁空間設施遭到攻擊。“施里弗-2010”演習進一步就天網威懾的協同增效,一體運用的戰術、技術與程序展開研究。在“施里弗-2014”至“施里弗-2020”的7 次演習中,均設置了一個與美實力相當的大國,在太空與網絡空間組織實施作戰行動來達成其戰略目標的設想背景,以檢驗聯盟太空和網絡空間威懾與作戰能力及體系彈性,探索聯盟、軍民商太空與網絡空間力量一體運用的指揮控制體系等內容。
在戰役戰術演習層面重點檢驗太空系統網安能力錘煉網絡進攻能力
從“太空旗”演習紅藍對抗的扮演方分析,網絡與電磁空間的進攻與防御是其演習的重要主題。藍方主要是空軍原14 航空隊的第50、460 等擔負聯合作戰太空信息支援的聯隊,紅方是第527 太空侵略者中隊和第26 太空侵略者中隊。紅方運用衛星通信干擾、GPS 干擾等手段攻擊藍方太空系統,以錘煉藍方對抗條件下的抗毀頑存能力。
2017 年6 月,美空軍在國家安全局網絡防御演習中舉行了首次“太空網絡挑戰賽”,旨在幫助“增強對太空網絡安全挑戰及安全理念的認識”,驗證網絡技能,測試了構建、強化太空任務網絡并防護其免受網絡攻擊的能力,以獲得新型解決方案并更好地在全球共享信息。
在黑客挑戰層面重點測試并強化太空系統網絡防護能力
在首次舉辦的“太空安全挑戰2020”研討會上,美軍首次組織了名為“黑掉衛星”(Hack-A-Sat)的黑客攻擊衛星挑戰賽。2021 年6 ~8 月,美空軍與天軍舉辦第二屆“黑一顆衛星”太空系統網絡安全挑戰賽,全球1000 多個太空系統安全研究團隊參與其中。參加年度決賽的8 個團隊在24 小時內針對模擬太空系統(包括虛擬地面站、通信子系統、“平衛星”物理衛星硬件,以及用于模擬和測試命令的數字孿生軟件),實施黑客攻擊,查找安全漏洞,開展太空系統網絡攻防對抗,各團隊被要求同時操作和防御自己擁有的脆弱性的系統,同時攻擊對手相同的系統來得分。活動旨在激勵世界頂級網絡安全人才發展必要的技能,以幫助減少漏洞并建立更安全的太空系統。
6 結束語
太空實力是美國霸權的堅實技術和軍事基礎,太空領域出現重大漏洞與安全風險,無疑會動搖美國霸權。美國借助強化太空系統的網絡安全,意在構筑應對他國的反太空能力,從而贏得大國競爭背景下的戰略戰役與戰術層面的軍事勝利,并希望借著強化太空系統網絡安全的機會,謀取制定太空規則的主導權。
美國依賴太空系統與網絡空間的程度遠超其他任何一國,高度依賴就意味著承擔巨大的安全風險。近年來,美軍將網絡和太空劃為作戰域,成立網絡空間司令部、太空作戰司令部和天軍,從戰略條令、組織機構、作戰力量、態勢感知、作戰演習等層面持續推進太空實戰化建設,形成了世界領先的太空網絡作戰力量和太空攻防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