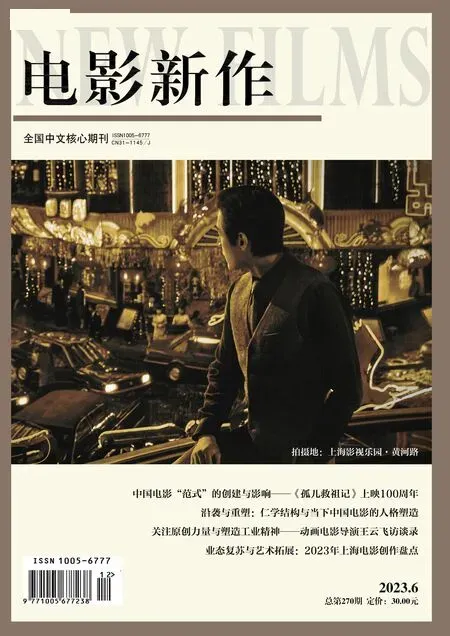“十七年”時期上海電影制片廠歷史題材影片中的“英雄”形象塑造
馮 果 高殿銀
回望1949年之前的上海電影創作,其經歷過20世紀20年代好萊塢電影的沖擊、20世紀30年代左翼電影的現實主義創作,以及20世紀40年代電影審美多元化等幾個歷史階段,上海電影人始終堅持電影創作表現民族精神的藝術探索道路。正如學者萬傳法所說,縱觀上海電影創作,其“形成了以1949年前的上海電影為中心的‘上海電影傳統’”。1反映到影片的具體創作中,以表現市民生活為主的市民電影作為上海電影的主要類型,從現實生活出發塑造出具備抵抗精神的角色。在塑造角色過程中,一是關注人物命運,體現出普通人尤其是勞苦大眾的生命力;二是注重對人物日常生活的展示;三是以“家”為中心構建人物關系,包含鄰里關系。新中國成立后,“延安電影傳統的進入,與上海電影傳統形成互補和互相的滲透模式,又影響了‘十七年’電影”2,而老上海電影人“試圖融合‘上海電影傳統’與‘延安電影傳統’”3。重新審視這一時期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攝的歷史片,能夠明確地察覺出是兩種電影傳統特質相互融合與闡發的過程。
20世紀50年代,上海電影制片廠創作了歷史題材影片《宋景詩》(1955)。影片將這位在19世紀60年代帶領農民起義的領袖塑造為英雄人物,既是上海電影在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新政策時做出的改變,又體現出以鄭君里為代表的老上海電影人在這一時期的創作傾向。直至1960年,上海電影制片廠陸續創作了一批歷史題材影片,塑造了李時珍、林則徐、魯班、聶耳等經典的歷史人物形象。這一類人物形象既是作為榜樣的英雄,又兼具著普通人的特點,通過榜樣特質與人民精神互通的方式,使歷史人物充滿時代的現實價值。與同時期“長影”的《甲午風云》(1962)、“北影”的《青年魯班》(1964)等同類影片塑造的歷史人物形象相比,上海電影制片廠的創作,既顯示出延安傳統中的革命性,又融合了上海電影傳統。因此,基于電影塑造歷史人物形象的真實與虛構限度,圍繞英雄的雙重身份構建、特質書寫以及日常生活捕捉等方面,探究上海電影制片廠這一類影片中的英雄形象為何兼具榜樣與普通人特質的雙面性,以及這種雙面性在影片中的呈現方式,可以管窺上海電影制片廠歷史片創作的獨特性。
一、構建人物的雙重身份:榜樣和普通人的關系置換

圖1.電影《宋景詩》劇照
根據《1954—1957年電影故事片主題、題材提示草案(節錄)》中“關于歷史與歷史人物傳記方面的主題、題材提示”,歷史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用這些由歷代中國人民的乳汁培養出來的偉大人物、進步戰士和創造者的思想與感情教育觀眾,用他們的熱烈的愛國主義英勇精神和捍衛祖國、造福人民、反抗壓迫的高尚品質教育觀眾,以豐富正在參加建設新的生活的人民大眾的思想,在人民身上培育優秀的品質,號召人民為更加美好的未來而斗爭”。4這個“提示”目的是讓電影人在創作中提取人物的“生平事跡”“思想與情感”“愛國主義的英雄精神”“高尚品質”等特點,使之對大眾起到豐富思想、提升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時代語境決定著歷史片中需要塑造的典型形象首先是作為“榜樣”的真實英雄,如宋景詩、李時珍、林則徐、魯班和聶耳等,重點講述其在中國歷史進程中堅守信念、勇于反抗的行為和精神。另一方面,這種以榜樣存在的英雄形象,身上還需具備人民群眾的普遍性特征。于是上海電影制片廠力圖要達到的,是通過將主要人物的品質特點、具體行為與普通人互為補充以構建英雄的雙重身份,實現英雄和人民相互成就、精神互換的效果。
在《宋景詩》的準備工作中,攝制組曾去魯西體驗生活,是為了在真實的環境中,熟悉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習慣。既然此時的環境已經不再是當時的環境,但為何還要去體驗生活?據鄭君里留下的材料顯示,去魯西的體驗要明確《宋景詩》的任務是“創造英武的農民形象,而不是別的”5,因為魯西的民風依舊還在,去當地體會的實際是一種精神。很明顯在此片中,雖然主要人物是宋景詩,但作為農民領袖的“英雄”才是值得歌頌的人物,將榜樣與農民形象并置,是要通過宋景詩這個英雄的誕生來突出農民形象的品質。《宋景詩》是上海電影制片廠此類歷史題材影片的開端。此后的幾部影片也是通過構建英雄和普通人之間的關系,將英雄從神化中人化,強調英雄和普通人并無區別,使英雄和普通人等同,完成普通人只要通過勞動、具備堅毅的品質也可成為英雄的轉換。可以說,英雄所具備的是榜樣和普通人的雙重身份。《李時珍》(1956)在塑造李時珍的人物形象時,創作者考慮到如果“光是李時珍和賣草藥的,一紅一白,色彩單調”6,因此增加了徒弟小溜的形象。小溜作為李時珍幫助過的對象,一方面可以體現出李時珍的品質,另一方面小溜成長于李時珍的信念之中,被師父的堅守之心所感染。比如,拜師一場戲的表演實際就是對以李時珍這個人物為代表的榜樣的高度認可,并通過使小溜成為徒弟來實現李時珍精神的延續。《魯班的傳說》(1958)中,選取的魯班的“造橋”“造廟”和“造角樓”三個主要事件,其中都不僅只講述魯班的智慧,還同時多次展現群眾做手工、搬運等勞動的動作,表現出勞動人民勤奮、努力的品質。影片中更是將魯班與正在勞動的人們放在同一畫面中,如“造橋”事件中,魯班在打槽時,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鏡頭,魯班位于畫面左下角,一部分工人站立于他身后觀看并延伸至畫面最右邊,更遠處是正在勞動的另一部分工人,雖然處于畫面最遠處,但群演的動作依舊可見。在這里群演不再是背景的展示,而是通過與魯班在同個畫面中的勞動,體現出榜樣等同于勞動人民的一面。勞動人民才是真正歌頌的英雄。還有片中三個掌墨師相似的表演,他們在面對阻礙會通過沮喪的動作和語氣表現出失意、苦惱,但是當問題解決,并且知道為自己解決問題的人是魯班之后,他們的動作、語速會加快,這種相似的反應,實際是為塑造魯班的榜樣形象而服務的。同樣地,由群眾之口重復說出的“仙師”“仙人”的臺詞也是將魯班塑造為榜樣時的重要口號。但由魯班說出的“和凡人一樣”的臺詞,又將英雄人化,使之與人民群眾進行置換。
與之相似的,《林則徐》(1959)中眾人仰望阿寬爬旗桿掛帽的表演,實際是人民英雄行為的展演,而林則徐多次看著人民齊力拉炮、努力工作的畫面,也是為了突出三元里抗英斗爭的人民群眾。《聶耳》(1959)中以“鄭雷電”(張瑞芳飾)為代表的革命者,將其塑造為普通人中的英雄,同時通過與主人公之間的關系,完成真正的英雄是勞動者、農民、清醒的革命者等的話語表達。如果說作為《林則徐》和《聶耳》的導演,鄭君里在《宋景詩》之后的電影創作都“采取了雙線并進的敘事架構”,他的影片“多有著‘雙主體’,或者賦予人物以雙重身份,試圖以此兼顧政治和藝術的雙重要求:一條滿足自我表達訴求,另一條滿足主流政策需求;一條延續中國電影的優良傳統及藝術規律,另一條符合新中國的新時勢,宣傳革命思想,贊頌人民群眾等”7,那么實際沈浮、孫瑜等創作者也在英雄形象的塑造過程中,呈現出這樣的傾向性,即上海電影人也需通過“英雄的誕生”來完成自我的改造。
這樣的關系置換,不僅符合當時的主流話語,也延續著早期上海電影創作中的傳統——對普通人生命力的突顯。不論是孫瑜《大路》(1934)中反復被描繪的工人修路的場景,還是許幸之《風云兒女》(1935)中結尾片段人民拾起工具奮起反抗的畫面,都是對普通人所具有的抵抗精神的呈現。這樣的場景也持續重現在這幾部歷史片中,那些多次出現的不分主次人物的勞動、斗爭的畫面,由于圍繞著英雄的行為和人物關系而展開,使英雄兼具的榜樣和普通人的雙重身份得以自然呈現。
二、從人物特質出發:關注英雄作為“人”的復雜性
作為典型人物,上海電影制片廠這一系列歷史片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既具有英雄的普遍性,又充滿個性化的特征。為何上海電影制片廠創作的這類人物形象,與臉譜化、概念化的英雄人物之間拉開了距離?從演員塑造人物形象的方面,“從人物的個性出發”8無疑是重要的原因,即將重點放置于英雄形象的個性之處,把握人物形象中“精神所聚注的地方”9,這正是蘇軾所說的一個人的“意思所在”。蘇軾認為,“一個人的生活情調、個性、精神風貌并不是在這個人外在形體的一切方面都能充分表現的,它往往突出地表現在某一個方面”。10這種“意思所在”與顧愷之所提出的創作人物畫的主張“四體妍蚩,本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相似,都表示通過人物的某個關鍵部位,找到人物的個性和精神所在,使人物傳神。而“寫照的價值,是由所傳之神來決定”11,那么英雄形象所具有的雙重身份的特點決定了其特質既要表現榜樣的一面,又要突顯“人”的復雜性。在上海電影制片廠歷史片的創作中,首先通過與傳統美學的結合來彰顯英雄的文人精神氣質;其次演員通過動作、表情將人物的堅定信念融于普通人特點和情感的自然涌現中,突出英雄的精神所在;最后通過人物關系豐富英雄的人性和人情味。
正如趙丹在塑造林則徐角色時所總結的,“英雄人物所以成為英雄人物,首先是他對社會歷史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他的英雄行為(具體的行動)”12,這是在塑造英雄人物時首先需要掌握的。上海電影制片廠的這一系列歷史題材電影在呈現英雄行為時,雖然都選取了人物勇于抗爭、奮斗的主要事件進行敘述,但特別之處在于通過將人物的行動放置于自然之中,形成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互動關系,以電影化的手法突出人物勤勞、堅毅的品格,使英雄的榜樣特性融于文人精神氣質中。如《魯班的傳說》中,在魯班出場部分,使用了三個鏡頭組接,內容為魯班和山、魯班和松、魯班和瀑布,從開端就將人物如山般堅毅、如松般高潔不屈、如瀑布般生生不息的特點以隱喻的方式鋪墊,使他的精神有了“一種高處流動的境界”13,并通過影像語言較為流暢地為此后魯班在游歷中親傳手藝、淡泊名利、謙遜助人的形象提前布局。這幾部影片中,表現自然與人之間關系的場景并不少見。如《李時珍》中,導演將人物置于水和山之間,多使用全景表現人物游于山水間,同時搭配人物近景,顯示出李時珍所經歷的困苦與堅定的決心,使人物“至死不怕難”的精神在與自然的融合中顯現。再如林則徐送別鄧廷楨的鏡頭組接,魯班為修角樓時站立于天地之間的思考和探索,聶耳在飄雪的冬日拉琴以及與朋友們一起走到天明迎來日出等鏡頭,都將人物特質融于自然,在中國美學傳統中突顯人物精神。
落實到演員的表演層面,人物特質的呈現需要深入角色,在歷史和生活中找到英雄的精神所在,這就不僅只是熟悉英雄的典型事件,也要注意對普通人的特點進行捕捉。如趙丹對聶耳形象特質的提取——“聶耳是個‘風云兒女’,他是一個偉大的音樂家,但首先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14,聶耳的性格“天真活潑、樂觀、諧趣、喜說好動”,并且由于對“革命事業發展前途的堅定的信心”,顯現出“樂觀主義的精神”。15因此趙丹在影片中對聶耳的塑造,會有些調皮的動作設計,如影片開頭拉小玩具、勾梯子、敬禮道謝等,都是從聶耳的精神出發表現,不追求形似,而是從人物作為普通人的特點出發,在神似中自然傳遞英雄精神。孫瑜認為,“魯班的性格具有勞動人民典型的代表性,同時洋溢民族的色彩:勤勞勇敢,聰明智慧,健康樂觀,謙虛樸素。”16魏鶴齡在塑造魯班形象時,身背褡褳,時常微低的身體姿態,與普通人無異的神態、動作,都體現出他和勞動人民的同一性。片中經常出現的他走路的鏡頭、他流著汗水勞作的連續性剪輯畫面,即是對他作為勞動人民勤勞這一特質的“特寫”。
演員還通過細微的表情來表現人物堅定的決心、堅毅的性格,將作為榜樣的英雄性格特征凝結于人體最能傳遞深情的地方。如在表現李時珍對學醫堅定的決心時,畫面搭配著纖夫的號子聲與配樂的歌聲,趙丹在一個停留時間較長的鏡頭中,通過持續凝視遠方的眼神,表現出李時珍如纖夫般逆流而上,面對困難不退縮的心境。到了結尾處,年邁的李時珍仿佛再次聽到纖夫的號子,踉蹌著尋聲奔走,依舊通過眼神傳遞幾層意思:先是回憶起當年的初心,接著是在徒弟哭泣中回神,最終表現出他刻書的決心。此時李時珍身上所凝聚的不僅是他個人的情感與精神,同時也是中國人不怕萬難也要堅守的信念。在林則徐形象塑造時,趙丹通過遠望江面和炮臺的眼神,表現出林則徐守護祖國的堅毅之心,以及表達出剛強的一面。在送別鄧廷楨時也是有多個鏡頭以眼神為表現重點,而在摘帽一場戲中,通過逐漸推近的林則徐面部的鏡頭,觀眾也得以沉浸在人物一絲不偏的眼神中。在這樣突出眼神的鏡頭中,創作者多會使用近景或特寫,規避人物的肢體動作,從而將重點集中于人物的眼神,從眼神抵達英雄情感涌現之處。
上海電影制片廠的這幾部作品,都為人物構建了家庭、鄰里和朋友的人倫關系,在塑造英雄形象的過程中為其增加普通人的特點,豐富其人性的色彩。《李時珍》通過增強李時珍與老魏、徒弟小溜之間的人物互動,在兩個次要人物的配合與襯托中,使李時珍的形象更加豐富飽滿。在三人一起歷經千辛找到花田的那場戲中,趙丹需要表演出李時珍護花的狀態,先是趙丹飾演的李時珍將拐杖扔掉表現出興奮,接著老魏想要伸手碰花,但被李時珍打掉了手,這一串護花的動作和臺詞,單靠個人的表演達不到如此生動的效果,因此需要在與對手的互動和交流中將李時珍的至純至樸的性情傳達出來。趙丹在對李時珍形象的創作中,還曾與康泰、錢千里兩位演員一起研究戲,這就使得片中的師徒關系、好友關系都在生活中進行了自然排演。日常生活中的關系通過體驗的方式融入對角色關系的把握中,使得片中的人物關系更顯自然。《聶耳》中,也通過聶耳和鄰居小紅等人、歌舞班演員們的關系呈現,為聶耳的樂于助人以及由自身的樂觀積極的精神影響他人的特質增加了色彩。在進行林則徐的人物形象塑造時,趙丹曾和飾演鄧廷楨的李鏞以及飾演關天培的鄧楠一起研究這組人物關系和角色的基調,如他們從“群英會”中的“黃蓋”和《三國演義》中的張飛身上尋找到關天培的性格特征。在關天培、鄧廷楨與林則徐關系中,三人通過民族文化的來源挖掘了人物的民族性格,使得林則徐與好友、戰友之間的情感顯露,增加了林則徐形象的情味,使之與臉譜化的英雄拉開了一定的距離。
三、深入生活:在兩種不同時代節奏中統一英雄氣質

圖2.電影《林則徐》劇照
鄭君里在《宋景詩》的拍攝準備中,表示“歷史傳記片的演員體驗生活的方法,在過去并未積累經驗”。17這其實反映出兩個問題,在上海電影制片廠的歷史片創作中,為何需要體驗生活?體驗生活對于英雄形象的塑造有何幫助?鄭君里認為,演員創造角色必須要“站在進步的思想立足點去認識角色”和“站在角色的立足點去感受角色所感受的”,并將這兩個對立的方面在實踐中達到統一,“也就是演員的認識與性格(角色)的體驗的對立的統一”。18新中國成立初期,伴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系統引進,演員們全面學習其“體驗”的演劇方法。“斯氏體系”中的“體驗”主要要求演員“在舞臺上時,在角色的生活條件下,與角色完全一樣正確地、充滿邏輯地、按照順序地、像人那樣思考、希望、追求、行動”19,即演員要“生活于角色之中”。在具體創造人物形象時,演員根據“最初為劇作者所提供,經過導演所豐富,最后在演員的創作想象中成熟和具體化的”“虛擬的‘社會條件’”,“才能體驗到與角色相符的思想、感情和行動”20,在“規定情景”中真實生活。由于英雄角色兼具榜樣和普通人的雙重特點,是故這一時期體驗生活需包含兩個層次的內容:一是在準備過程中,摒棄依靠史料的單一方法,進入英雄的生活環境,感受英雄的精神;二是演員要真實地生活在為英雄設定的戲劇情境中,抓住生活細節,注重拉近英雄和普通人間的距離,從而在塑造英雄時“拋掉英雄的概念”,使得古今、虛實“兩種不同的時代節奏在人物氣質上”21達到統一。
由于塑造的是歷史片中的英雄形象,因此演員首先要從史料中對人物性格、經歷事件、采取的行動方面作基本了解。趙丹在對李時珍形象的準備過程中,“讀明史,讀《本草綱目》,懂得幾味藥草的性能,豐富了一些歷史知識,獲得一些理性的東西”。22據資料顯示,在《林則徐》的拍攝準備中,創作者對清廷儀注及服裝、清廷制度、人物品級年齡等進行嚴苛的考據,力圖完善一個真實的歷史情境。但依靠史料的梳理,不足以獲得英雄形象當代塑造的材料,因此鄭君里在《宋景詩》的準備工作中,提出需要通過體驗魯西生活,“觀察地方色彩反映在人物造型上的一些跡象,收集造型設計的原始資料”。23趙丹也曾在塑造李時珍形象的準備中,學習如何從動作上來還原中醫行醫時的姿態,并在生活中穿上劇中服裝。他在林則徐形象的準備中亦如此,在適應服裝的過程中“體味古人的生活習慣與風尚”24,這是通過深入生活從而生活于角色中的一部分表現。但這些還只是通過從生活中汲取英雄形象外部表現的材料,對于演員扮演歷史人物來說,在生活中還原人物,“既以生活為依據,又以歷史的具體為依據”25的統一才能擺脫從概念上塑造榜樣,使英雄在古今中達到平衡。

圖3.電影《聶耳》劇照
塑造英雄形象的“體驗”最終要達到的是演員從自身出發,進入英雄的“規定情境”,按照時代的邏輯生活,養成在形象創造中的“一種我只是在生活著的自我感”。26趙丹同《李時珍》攝制組一起在天姥山腳下齊家村原始大森林生活,找到通向角色內心之處:首先感受到李時珍質樸、純真的本性,其次找到與百姓們相處的方式。反映在片中,趙丹對李時珍修《本草》堅持到底的精神、為百姓們看病時的用心、傳遞知識時的毫無保留等表演,不僅立足于李時珍這一人物所處的歷史語境,還加強對他的當代解讀。與此同時,趙丹根據規定情境,“體驗到與角色相符的思想、感情和行動”27,在與包鄉紳的爭論、修成《本草》、草稿被毀、發現老魏尸體、結尾處堅定的信念等片段時的表演,“有根據地、合理地和有成效地實現行為”28,使得李時珍的榜樣特質得以自然涌現,豐富了人物形象。很明顯,他“在塑造這個人物時,不是從概念而是從生活出發”。29隨后,在電影《聶耳》的創作方面,處理聶耳在北平紀念“九·一八”公演,遭到反動當局禁演的片段時,趙丹他們將曾經在上海演戲時被禁的生活實感移植到本場戲中,把聶耳的動作和演員的動作概括成一個,“構成了這場戲的戲劇情景、人物情緒、語言和動作”30,達到按照英雄的邏輯去體驗生活的效果。
這一時期拍攝歷史片“體驗”生活的經驗,對演員表演觀念的變革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演員在塑造人物階段,既能從歷史和生活獲得依據,又能在現實的氛圍中尋得歷史人物的理性材料和感性材料,并轉化為表演的素材。他們不是僵化地模擬英雄的動作,也不是像文明戲時期生硬地演講和教化,而是試圖在自我與角色之間找到共通之處,依靠生活依據,在體驗中“充分地獲得角色自我感,忘掉歷史劇的概念”31,從而呈現出英雄人物的自然狀態,使英雄人物越是進入規定情景越深,反而越流于平易自然32,這也是上海電影制片廠創作歷史英雄的獨特之處。
從中國電影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上海電影制片廠在這一時期的歷史片中重視對日常生活細節的呈現并不是偶然,在此前的市民電影中,編導者仔細描繪的普通人生活的圖景使角色生動、鮮活起來。由此在英雄的形象塑造中,通過生活細節的捕捉突出人物特性中的人性和情味的一面,豐富了英雄形象,拉近了英雄和普通人之間的距離,這也正是上海電影傳統中突出人物日常生活的延續。如在電影《李時珍》中,趙丹在表演李時珍通宵為小溜母親看病這場戲時,是如何表現人物的感受的?當清晨感受到從窗戶照進屋內的陽光時,趙丹將手伸進光中;接著在一個側拍的近景中,趙丹將雙手翻動,這是一個如烤火一般的動作,通過如此自然生活的動作、姿態為李時珍的形象增添了情味。趙丹曾說這個動作將他帶入了童年的生活意境中。實際上,這也是演員通過體驗與想象,達到了在此時此地與角色的共情之處。那么這個動作從演員在鏡頭前的表演,就變成了由生活細節帶來的李時珍奉獻、忘我精神的生動體現。之后穿針的片段,年邁的李時珍無法在夜晚將針穿上,趙丹通過幾個連續穿針的動作表現人物的倔強,并由縫衣服時想到妻子后失落的神情,再配合放下衣物和捏手的動作,前后的對比細膩地傳遞出英雄“作為一個人”的豐富情感。與此前在陽光中翻動雙手的動作相似,都通過自然的生活細節,突出李時珍作為“普通人”的特點,并加強其純真、質樸的性格體現。
之后,在電影《林則徐》中,趙丹通過摔茶杯的動作表現人物性格中的“剛”,這是林則徐形象的主要一面。但當仆人拿來毛巾準備收拾時,他接過毛巾動手收拾并使用溫和的語氣,這里的中景鏡頭既全面又相對集中地使觀眾看到他仔細收拾的動作,體現出人物“柔”的一面,由此,剛柔結合的表達將其心情變化、個性、特質都呈現出來。當表現林則徐熬夜工作時,趙丹通過生活化的表演設計,如戴眼鏡、剝橘子、看地圖、打太極,中和了人物的距離感,讓人物在自然的表演中鮮活起來。從演員和攝影機配合的這些細微處的動作、表情,使得上海電影制片廠在這一時期塑造的英雄形象有了獨特的面貌。演員并不是簡單從形似的角度出發來塑造人物,而是通過形神結合的方式來傳遞人物的民族精神。此外,在這些影片中,不僅是主要人物,還是次要人物的塑造如《魯班的傳說》中翠兒水中照鏡、河邊打水、羞澀時低頭垂眉的動作,以及《聶耳》中小紅被打時通過肢體動作表現出的惹人憐愛的姿態,聶耳在船上合演《鐵蹄下的歌女》時眾人打牌、看書、縫衣服等鏡頭,都以人物的民族精神為底色,通過生活細節的捕捉,使圍繞英雄而構建的人物關系有了豐富的呈現。

圖4.電影《林則徐》劇照
結語
1950年代中期,在中共中央的批示下,北京電影學院開設了演員專修班,來自“上影”“北影”“長影”的一眾演員參加了此次培訓。在教學中,演員們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學習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驗”表演的訓練方法。上海電影制片廠演員沙莉、凌之浩等人在回憶起此次培訓時,都認為演員需要從生活出發去塑造角色,“深入的生活體驗之后”33對演員是有幫助的。這一時期在上海電影制片廠的歷史片創作中,演員塑造英雄形象時深入生活體驗的方法,盡管深受“斯氏體系”的影響,但他們“沒有完全照搬,而是融入民族表演的質素”。34在“十七年”時期的文藝創作語境中,這些歷史片中的英雄形象既符合主流話語的表達,上海電影制片廠的創作者又“把握住中國人民的生活和性格”35,不僅從中國傳統美學中汲取創作靈感,還從生活細節的捕捉中描繪出英雄生活的情境。在對英雄人物特質的展現中,演員實現了自我與角色的統一,既呈現出英雄的榜樣精神,又使英雄作為普通人的個性特點得以自然、生活、真實地涌現,這既是“十七年”時期電影“內心表演”和“人情表演”36的實踐,又延續了上海電影傳統中的現實主義關懷和文人精神氣質。
【注釋】
1 萬傳法.上海電影、上海電影傳統與中國電影學派[J].當代電影,2018(09):100.
2 萬傳法語.對話與商榷:中國電影學派的界定、主體建構與發展策略[J].當代電影,2018(05):14.
3 鮮佳.新中國成立后影人鄭君里創作轉型研究[A].厲震林,萬傳法主編.上海電影與中國電影學派:理論與批評文集[C].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20:199.
4 1954-1957年電影故事片主題、題材提示草案(節錄),原載《電影劇作通訊》,1953年10月1日。引自吳迪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1949-1979(上)[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360.
5 李鎮主編.鄭君里全集(第六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119.
6 趙丹.銀幕形象創造[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81.
7 同3,206.
8 同6,119.
9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沈陽:遼寧出版社,2019:177.
10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06.
11同9,152.
12同8.
13 林年同.中國電影美學[M].臺北:允晨文化,1991:128.
14中國電影出版社編輯.聶耳——從劇本到影片[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275.
15同14,280.
16孫瑜.銀海泛舟[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236.
17同5.
18 鄭君里.角色的誕生[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80.
19[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演員自我修養 第1部[M].楊衍春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21.
20同18,30.
21同6,116.
22同6,91.
23同5.
24同22.
25同6,92.
26同6,88.
27同20.
28同19,44.
29桑仁.趙丹與李時珍[J].中國電影,1957(04):15.
30同14,330.
31同25,92.
32同6,75.
33沙莉.懷念蘇聯老師鮑·瑪·卡贊斯基[J].中國電影,1957(Z1):105.
34厲震林.20世紀60年代初期表演民族化的中國電影實踐和理論[J].未來傳播,2022(04):103.
35以群.建立中國電影風格[N].大公報(上海),1949-5-19.
36 厲震林.“十七年”電影表演美學論綱[J].當代電影,2014(01):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