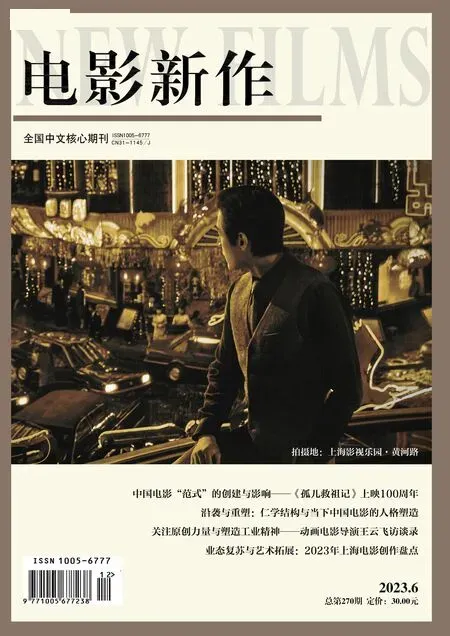文化反思與家國同構(gòu):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的國際突圍
常 江 狄豐琳
近年來,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出品的電影頻繁在各類國際電影節(jié)中斬獲獎項(xiàng),并在評論界引發(fā)了有關(guān)哈薩克斯坦“新浪潮后”或“國家新浪潮”的熱議。1值得一提的是,絕大多數(shù)獲得國際關(guān)注和認(rèn)可的哈薩克斯坦影片均為藝術(shù)電影或先鋒電影。盡管截至2021年年初,藝術(shù)電影在哈薩克斯坦全國電影總產(chǎn)量中的占比只有7%2,但它們卻贏得了與此不成比例的能見度和美譽(yù)度,成為這個古老而常新的國家最重要的形象名片。哈薩克斯坦作為中國最主要的鄰國之一,以及“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其藝術(shù)電影的成功為我們以電影業(yè)為切入口審視、反思本國當(dāng)代文化生產(chǎn)與對外傳播之間的關(guān)系提供了鏡鑒。一方面,源自國家意圖的、相對寬容且開放的“頂層設(shè)計(jì)”在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的進(jìn)步和繁榮中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哈薩克斯坦新銳電影人意圖明確的“國族敘述”顯著強(qiáng)化了這些作品的文化主體性,在哈薩克斯坦人民的“自我界定”和國家的“認(rèn)同凝聚”中扮演了積極角色,突破性地挖掘了藝術(shù)電影所具有的文化政治潛能。
本文立足于“一帶一路”倡議的文明互鑒視角,首先,描述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近年來以電影節(jié)展為路徑實(shí)現(xiàn)文化突破的情況,探析其“國際路線”的規(guī)劃方式和現(xiàn)有成果;接著深入創(chuàng)作主題,專注對哈薩克斯坦最重要的藝術(shù)電影創(chuàng)作者群體——“獨(dú)立一代”導(dǎo)演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進(jìn)行考察,嘗試在美學(xué)和敘事等層面歸納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成功的經(jīng)驗(yàn);最后,立足于經(jīng)典文化理論,在這一時期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文本與該國國族身份和民族文化構(gòu)建之間建立邏輯關(guān)聯(lián),剖析藝術(shù)電影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相糅合的社會語境中所具有的文化政治潛能。
一、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的節(jié)展之路
目前,依照發(fā)行網(wǎng)絡(luò)的不同,哈薩克斯坦電影主要存在三種類型:依靠市場盈利的商業(yè)電影,政府下令或資助拍攝的國家電影,以及主要依托國際電影節(jié)展贏取知名度的藝術(shù)電影。3在哈薩克斯坦國內(nèi)的院線和發(fā)行市場上,藝術(shù)電影極少出現(xiàn),它們被創(chuàng)作出來的主要目標(biāo)就是角逐各類國際電影節(jié)的重要獎項(xiàng),再實(shí)現(xiàn)自外而內(nèi)的“美學(xué)回流”。近年來,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在重要國際性節(jié)展上取得的成績,包括《卡拉塔斯的瘟疫》(The Plague at the Karatas Village,2016)在鹿特丹國際電影節(jié)獲NETPAC獎(The 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Asian Cinema);《小家伙》(My LittleOne,2018)入圍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jié)主競賽單元,主演薩梅爾·葉斯利亞莫娃(Samal Yeslyamova)憑借這部電影獲得最佳女演員獎;《領(lǐng)導(dǎo)的秘訣》(The Secret of a Leader,2018)獲2019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jié)最佳影片獎;《黃貓》(Yellow Cat,2020)入選第77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jié)地平線單元獎最佳影片的提名,并獲得第68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jié)開放電影大獎的提名等。

圖1.電影《黃貓》劇照
哈薩克斯坦當(dāng)前的電影創(chuàng)作者群體既有拉希德·努格馬諾夫(Rashid Nugmanov)、阿爾達(dá)克·阿穆爾庫羅夫(Ardak Amirkulov)、塞里克·阿普里莫夫(Serik Aprymov)等“50后”與“60后”的“哈薩克斯坦新浪潮”(Kazakh New Wave)一代,又有納里曼·圖雷巴耶夫(Nariman Turebaev)、埃爾蘭·努爾穆漢貝托夫(Erlan Nurmukhambetov)、阿坎·薩塔耶夫(Akan Sataev)等“70后”的“后浪潮一代”(the generation of the post-Wave),也有阿迪爾汗·葉爾江諾夫(Adilkhan Yerzhanov)、塞里克·阿比舍夫(Serik Abishev)等“80后”的“獨(dú)立之子”(Children of Independence)一代。其中,“哈薩克斯坦新浪潮”在20世紀(jì)80年代末崛起后又迅速消沉,盡管時間短暫,卻成為哈薩克斯坦電影吸引國際社會注意力的起點(diǎn),其“低成本預(yù)算+實(shí)驗(yàn)性語言”的生產(chǎn)思路為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后續(xù)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4隨之而來的“后浪潮一代”形成于20世紀(jì)90年代末至21世紀(jì)初,這一代電影人在堅(jiān)持美學(xué)創(chuàng)新的同時,也致力于提高哈薩克斯坦電影制作的總體技術(shù)水平,提升電影盈利能力,提速電影業(yè)的商業(yè)化進(jìn)程。5而最新銳的“獨(dú)立之子”一代電影人則活躍于21世紀(jì)的第一個十年,他們較少依賴政府扶持,堅(jiān)持走國際化的“節(jié)展路線”,并有著直面社會問題且尖銳表達(dá)的勇氣。
事實(shí)上,在哈薩克斯坦,這種通過選送藝術(shù)電影參加影視節(jié)展以提升本國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美譽(yù)度的策略早在20世紀(jì)80年代中后期便已初具雛形,成為該國在那一時期追求民族獨(dú)立的社會運(yùn)動在文化藝術(shù)領(lǐng)域的投影。比如,“哈薩克斯坦新浪潮”運(yùn)動的代表影片《針》(The Needle,1988)最初就選擇在敖德薩金公爵電影節(jié)(Golden Duke Festival)上首映,并獲得“一種關(guān)注獎”,次年在蘇聯(lián)全國上映后旋即成為票房冠軍。但是,像這樣票房與口碑雙豐收的藝術(shù)電影數(shù)量極少,大部分藝術(shù)電影處境較為艱難。哈薩克斯坦電影產(chǎn)量較低,每年出品長片僅15部左右,預(yù)留給藝術(shù)電影的產(chǎn)業(yè)空間較為狹小。從放映市場看,絕大多數(shù)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面臨的困境與其他國家和地區(qū)沒有什么不同:影院排片量小、制片價(jià)值低、觀眾數(shù)量少。即使是一些藝術(shù)品質(zhì)上乘、得到國際評論界廣泛認(rèn)可的藝術(shù)電影,在哈薩克斯坦國內(nèi)也往往無緣院線;哪怕能夠獲得院線給予的排片機(jī)會,也極易在其他兩類影片的擠壓下淪為票房“炮灰”。比如,“新浪潮”一代國際知名度最高的導(dǎo)演之一達(dá)赫讓·奧米爾巴耶夫(Darezhan Omirbaev)的電影《卡依哈》(Kairat,1992)和《心電》(Cardiogram,1995)盡管在全球多個電影節(jié)展獲獎,但在哈薩克斯坦國內(nèi)的關(guān)注度則始終不高。此外,在20世紀(jì)90年代,由于藝術(shù)電影融資缺乏法制環(huán)境的支持,哈薩克斯坦電影產(chǎn)業(yè)投資者在相當(dāng)長的時間里需要繳納高額稅款,國內(nèi)外的潛在投資方對電影制片業(yè)望而卻步。獲得國家獨(dú)立的哈薩克斯坦,其藝術(shù)電影反而自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開始陷入蕭條。
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在獨(dú)立后的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導(dǎo)演不得不回歸80年代中后期的“傳統(tǒng)”,忍痛“舍棄”國內(nèi)市場,將主要注意力轉(zhuǎn)向節(jié)展以吸引國際觀眾,并通過國際聯(lián)合制片或?qū)で筚Y金贊助的方式繼續(xù)他們的創(chuàng)作之路。依循這一路徑,大量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的制作與宣推工作迅速國際化。比如,阿迪爾汗·葉爾江諾夫?qū)а莸摹镀降卦煳荨罚⊿troiteli,2013)由哈薩克斯坦的索羅斯基金會(The Soros-Foundation Kazakhstan)出資拍攝。當(dāng)時該基金會組織了一場面向全社會的短片劇本創(chuàng)作比賽,邀請哈國青年表達(dá)他們對社會問題的看法,鼓勵年輕人以藝術(shù)創(chuàng)作為手段回應(yīng)社會問題。片長不足10分鐘的《平地造屋》從70個作品中脫穎而出,為阿迪爾汗·葉爾江諾夫贏得了6000美元的獎金。他隨即用這筆錢制作了一部長片電影。不止《平地造屋》,阿迪爾汗·葉爾江諾夫?qū)а莸牧硪徊侩娪啊犊ɡ沟奈烈摺贰⒅x里克·阿比舍夫(Serik Abishev)導(dǎo)演的《第6號案件的證人》(Witness of Case No 6,2016)、穆拉特·馬漢(Murat Makhan)導(dǎo)演的《法院執(zhí)行人》(The Court Executor,2016)等均獲得哈薩克斯坦索羅斯基金會6000美元的獎金。這些獎金隨后成為他們啟動長片項(xiàng)目的初始資金。埃米爾·拜加津(Emir Baigazin)導(dǎo)演的《和諧課程》(Uroki garmonii,2013) 則從世界電影基金會(World Cinema Found)獲得制作資金,由哈薩克斯坦JSC Kazakhfilm公司、法國Arizona Films公司、德國的Rohfilm公司和The Post Republic公司聯(lián)袂出品并制作,時任哈薩克斯坦國家電影中心(Kazakhstan's National Cinema Center)首席顧問的安娜·卡奇克(Anna Kachko)擔(dān)任制片人。這種由哈薩克斯坦電影人主導(dǎo)的國際合作模式,逐漸改寫了享有盛譽(yù)但又呈半封閉狀態(tài)的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生態(tài)。
進(jìn)入2 1 世紀(jì)以來,哈薩克斯坦政府逐漸意識到藝術(shù)電影對國家形象塑造和本國文化傳播的重要作用,遂開始在頂層設(shè)計(jì)上持續(xù)發(fā)力,通過一系列舉措為本國藝術(shù)電影國際可見度和關(guān)注度的提升提供引領(lǐng)和保障。比如,修訂后的哈薩克斯坦《文化法》第二十八條明確規(guī)定:政府支持舉辦電影節(jié)等活動、鼓勵參加電影節(jié)和比賽,相關(guān)章程自2010年起施行。6哈薩克斯坦電影工作者聯(lián)盟也于2016年提出影片扶持計(jì)劃,包括加強(qiáng)國際聯(lián)合制片、降低國產(chǎn)電影產(chǎn)品稅和外國人在哈拍攝電影的稅收等一系列設(shè)想。7同年《電影制作法》出臺,其有助于各種類型的電影公司定期享受國家補(bǔ)貼,并吸引外國電影制作公司。2016年至2018年,哈薩克斯坦文化研究所組織了超過10次公開聽證會,邀請哈薩克斯坦最重要的電影制作人、制片人和發(fā)行商,以及來自法國、美國和俄羅斯的專家對擬出臺的《電影法》的法律草案進(jìn)行了討論。同時,其還研究了英國、意大利、德國、韓國、中國等國家的經(jīng)驗(yàn),以便進(jìn)行比較。2019年,《電影法》正式出臺,明確表示支持哈薩克斯坦電影向世界市場發(fā)行,鼓勵本國電影制作者與世界主要電影公司聯(lián)合制作電影。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在創(chuàng)作者自身努力和國家法律環(huán)境的支持下,自此走出低迷。
二、“獨(dú)立之子”與“游擊隊(duì)電影”運(yùn)動
如果說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的上述“國際化”生產(chǎn)與制作實(shí)踐在2010年之前尚處于起步與摸索時期,那么從21世紀(jì)第二個十年開始便屬于它的“優(yōu)化”與成熟時期。這一時期正是最新銳的“獨(dú)立之子”一代創(chuàng)作最為活躍之時,代表人物包括阿迪爾汗·葉爾江諾夫、法爾哈特·沙里波夫(Farkhat Sharipov)、塔爾加特·貝克圖爾西諾夫(Talgat Bektursynov)、阿斯卡爾·烏扎巴耶夫(Askar Uzabaev)、扎蘇蘭·波沙諾夫(Zhasulan Poshanov)、葉爾蘭·努爾穆漢別托夫(Yerlan Nurmukhambetov)、沙麗帕·烏拉茲巴耶娃(Sharipa Urazbayeva)等,他們已經(jīng)成為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的中堅(jiān)力量。“獨(dú)立之子”的稱謂不僅源于這些年輕影人的理念與實(shí)踐大致成形于1991年哈薩克斯坦獨(dú)立之后,也與他們敢于挑戰(zhàn)傳統(tǒng)、密切關(guān)注社會熱點(diǎn)問題、努力平衡作品的社會責(zé)任與藝術(shù)價(jià)值的集體創(chuàng)作理念密切相關(guān)。
“獨(dú)立之子”一代主張通過電影創(chuàng)作來實(shí)現(xiàn)“社會介入”,據(jù)此掀起了廣受國際關(guān)注的哈薩克斯坦“游擊隊(duì)電影”(partisan cinema)運(yùn)動。阿迪爾汗·葉爾江諾夫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哈薩克斯坦電影長期以來就像是一只鴕鳥,把頭藏在沙子里,為了不被卷入熱潮不敢表達(dá)任何意見,并回避任何當(dāng)代主題。8作為“游擊隊(duì)電影”的發(fā)起者之一,阿迪爾汗·葉爾江諾夫呼吁藝術(shù)電影導(dǎo)演在籌資困難之時,更應(yīng)團(tuán)結(jié)一致,在直擊社會現(xiàn)實(shí)的同時,不斷探索新的電影語言來贏取生存空間。同年發(fā)布的“游擊隊(duì)電影”運(yùn)動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將阿迪爾汗·葉爾江諾夫的上述觀點(diǎn)具體化: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應(yīng)探索建立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導(dǎo)向的低預(yù)算電影生產(chǎn)機(jī)制,從而在創(chuàng)作環(huán)境逼仄、經(jīng)費(fèi)稀缺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產(chǎn)出文化效應(yīng)。
緊扣“游擊隊(duì)電影”運(yùn)動宣言的第一部電影是扎蘇蘭·波沙諾夫擔(dān)任導(dǎo)演、編劇,阿迪爾汗·葉爾江諾夫擔(dān)任共同編劇的《收費(fèi)站》(Toll Bar,2015)。影片借助“收費(fèi)站”劃分了兩個世界,一邊是屬于富商兒子艾達(dá)爾的“紙醉金迷”,另一邊則是屬于窮人勞安的“顛簸窮困”,兩級對立的現(xiàn)象既映照哈薩克斯坦社會的分裂狀態(tài),也折射出當(dāng)代都市生活的普遍性孤獨(dú)。此外,對于某些“前現(xiàn)代”價(jià)值觀的批判也是“游擊隊(duì)電影”運(yùn)動的核心訴求,代表影片是《卡拉塔斯的瘟疫》。在一個名為卡拉塔斯的村莊爆發(fā)了一場瘟疫,多數(shù)村民被感染,地方當(dāng)局宣稱這只是一場流感,他們下放了補(bǔ)貼,而補(bǔ)貼中的90%是用于治療流感的藥物。實(shí)際上這是一場腐敗騙局,官員從中收取回扣。新來的年輕市長銳意改革,卻處處受挫,被告知這種腐敗計(jì)劃是“國家傳統(tǒng)”,就像人們正在死亡的事實(shí)一樣。影片通過大量風(fēng)格化的明暗對比表現(xiàn)手法,讓觀眾沉浸在一個充斥著圖像符號和隱喻思維的世界,視覺隱喻背后折射出阿迪爾汗·葉爾江諾夫?qū)Α皞鹘y(tǒng)”的批判性檢視。
鑒于“游擊隊(duì)電影”運(yùn)動在選材和表達(dá)上有批判現(xiàn)實(shí)的傾向,因此它們在哈薩克斯坦國內(nèi)的生存空間仍然狹小,但這反而堅(jiān)定了“獨(dú)立一代”導(dǎo)演積極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的決心。他們在這過程中也探索出一套低成本的、“為電影節(jié)制作電影”的生產(chǎn)經(jīng)驗(yàn):一方面,一個好的創(chuàng)意或者明確的拍攝動機(jī)對于此類電影的創(chuàng)作是至關(guān)重要的;另一方面,在拍攝過程中,盡可能縮短拍攝周期并時刻把控節(jié)奏,最大限度減少重復(fù)鏡頭的拍攝和一些不必要道具的花銷。隨著越來越多低預(yù)算、高話題性的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在國際節(jié)展上斬獲重要獎項(xiàng),“游擊隊(duì)電影”運(yùn)動開始受到外國影迷、媒體和電影人的關(guān)注與歡迎,這反過來又促使一大批電影創(chuàng)作者加入“游擊隊(duì)電影”運(yùn)動,或至少在自己作品中體現(xiàn)一些“游擊隊(duì)電影”的創(chuàng)作理念。此外,“游擊隊(duì)電影”運(yùn)動的理念甚至擴(kuò)散至音樂、戲劇等周邊藝術(shù)創(chuàng)作領(lǐng)域。例如,哈薩克斯坦知名樂團(tuán)Irina Kairatovna的MV制作就被認(rèn)為具有“游擊隊(duì)電影”的風(fēng)格9;而強(qiáng)調(diào)以表演為手段揭示社會問題的“游擊隊(duì)劇院”(partisan theatre)運(yùn)動近年來也頻繁見諸報(bào)端。這些引人注目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實(shí)驗(yàn)表明“游擊隊(duì)電影”正在逐漸從一種旨在維系生存的權(quán)宜策略演變成一種一般性的美學(xué)風(fēng)格。
近年來受到廣泛關(guān)注的非“獨(dú)立一代”導(dǎo)演制作的藝術(shù)電影作品莫過于2018年獲哈薩克斯坦最佳劇本評論家選擇獎的電影《城市污垢》(City Filth,2017)。這是“后浪潮一代”導(dǎo)演納里曼·圖雷巴耶夫踐行“游擊隊(duì)電影”運(yùn)動理念的第一部作品。影片采用準(zhǔn)紀(jì)錄片的拍攝方式,通過樸實(shí)無華的美學(xué)特征,揭示特權(quán)現(xiàn)象的存在和肆虐,指出這將導(dǎo)致國家秩序失衡的結(jié)果。圖雷巴耶夫嚴(yán)格遵守“游擊隊(duì)電影”運(yùn)動的規(guī)則,即用最低預(yù)算拍好一部電影。首先,所有演員均在沒有報(bào)酬的情況下義務(wù)出演,工作人員也沒有報(bào)酬;其次,為展現(xiàn)真實(shí)的生活情境,電影沒有使用特效,連影片中夾雜著對普通哈薩克斯坦人就社會和道德問題進(jìn)行訪談的錄音片段,也是取自幕后制作團(tuán)隊(duì)在現(xiàn)實(shí)中進(jìn)行的真實(shí)采訪;最后,沒有聘請專業(yè)剪輯師,而是導(dǎo)演本人親自操刀影片剪輯工作。在影片中,一個“特權(quán)青年”觸犯法律卻依然逍遙法外,主人公(被害者的男友)決心用正義手段讓特權(quán)青年受到公正的懲罰,但最后卻因種種原因以私刑處置特權(quán)青年,結(jié)尾——本應(yīng)是公平正義原則的捍衛(wèi)者,反而成為冷血?dú)⑹帧F卜懦隽撕芏嗍茉L者對于“將正義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動用私刑”這種行為的看法,在觀眾中產(chǎn)生強(qiáng)烈共鳴。銀幕上,多數(shù)叫好與血腥私刑的鏡頭組接形成強(qiáng)烈的反差,不僅使觀眾從陰暗殘酷與溫情繾綣交織的畫面中生發(fā)心靈震撼,還能在無形之中審視自己的觀看行為。這樣看來,“游擊隊(duì)電影”運(yùn)動不僅能將具有反思精神的電影人集結(jié)起來,還能通過他們所制作的電影引發(fā)觀眾的反思行為,既給了電影人、觀眾自主選擇符合其精神需求的影片的一個機(jī)會,也為哈薩克斯坦現(xiàn)存的種種社會問題建立了公共檔案。

圖2.電影《卡依哈》劇照
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在21世紀(jì)的第二個十年,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領(lǐng)域其實(shí)是“獨(dú)立之子”“哈薩克斯坦新浪潮”“后浪潮一代”三代共存的局面。或者說,“獨(dú)立之子”只是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的制作者集體的一部分。但這一群體所體現(xiàn)出的社會批判意識和文化反思精神將當(dāng)代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置于全球聚光燈下,使之成為一場正在“進(jìn)行中”的媒介與美學(xué)運(yùn)動。以“獨(dú)立之子”作品為代表的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也依托其在國際節(jié)展上的耀眼表現(xiàn),有力地對外傳遞了哈薩克斯坦的國家文化與身份認(rèn)同。
三、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中的國家文化與身份認(rèn)同
縱觀2 1 世紀(jì)第二個十年的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會發(fā)現(xiàn)這些作品無論采取何種敘事框架和美學(xué)風(fēng)格,都格外重視對哈薩克斯坦國家文化與國族身份認(rèn)同的摹刻。它的主要表現(xiàn)手段包括:借助草原這種象征性的文化符碼,關(guān)注哈薩克斯坦傳統(tǒng)生活方式的艱辛、混亂和迷茫;構(gòu)建“家國同構(gòu)”的內(nèi)在話語邏輯,通過對普通人遭遇的講述,在個體經(jīng)歷與國族歷史之間建立緊密關(guān)聯(lián)。依托電影媒介強(qiáng)大的文化滲透力,藝術(shù)電影在哈薩克斯坦當(dāng)下的社會語境中成為國家文化和身份認(rèn)同得以形成和傳承的重要資源。
哈薩克斯坦知名電影導(dǎo)演、編劇、演員巴爾迪·納林貝托夫(Satybaldy Narymbetov)在論及哈薩克斯坦電影與其他國家的電影的區(qū)別時,認(rèn)為“景觀”(landscape)是最重要的維度。文化理論認(rèn)為,作為一種文化隱喻,電影中以視覺和文化意象出現(xiàn)的種種景觀,往往是承載創(chuàng)作者意圖的最主要的象征性符碼(code),而觀眾則通過對景觀的體認(rèn)與解讀獲得民族身份認(rèn)同。10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主要通過刻意打破附著在景觀符號體系上的傳統(tǒng)意義方式,來制造觀眾審美接受上的陌生感,進(jìn)而促使其形成“反思性認(rèn)同”。這是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在文化上的一個顯著特點(diǎn)。
比如,作為中亞地區(qū)的標(biāo)志性景觀,遼闊無際的草原在傳統(tǒng)觀念中通常被隱喻為生命的源泉;然而在許多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中,草原卻被賦予了荒蕪、孤獨(dú)的意涵,其創(chuàng)作意圖則指向?qū)ΡJ亍?nèi)向的傳統(tǒng)文化身份的反思。在影片《和諧課程》中,荒涼的草原不僅被反復(fù)用于烘托青少年阿斯蘭在面對校園霸凌時內(nèi)心的心理掙扎,也被用來強(qiáng)化那些在后蘇聯(lián)時代的社會轉(zhuǎn)型中被拋棄的人的困境;《平地造屋》中的草原雖然美麗壯闊,但卻荒涼、不宜居住。片中兄弟兩人為在阿拉木圖郊區(qū)建造一個家,決定趁天黑從附近的建筑工地偷取材料。可是草原并未給他們二人提供庇護(hù),導(dǎo)演借此反思為何獨(dú)立后的哈薩克斯坦未能給無產(chǎn)者、貧困者和失敗者提供適宜棲居的家園。此外,廣袤無垠的草原也經(jīng)常被藝術(shù)電影用來表現(xiàn)個體在文化認(rèn)知上的迷茫或“誤入歧途”,這在阿迪爾汗·葉爾江諾夫2011年的電影《房產(chǎn)經(jīng)紀(jì)人》(Realtor,2011)中得到了明顯的體現(xiàn)。11在這部電影中,主人公因意外“穿越”到一千年前的哈薩克斯坦,醒來時發(fā)現(xiàn)自己抵達(dá)的是一片無情、暴力和血腥的草原;而他們在古代哈薩克草原上的迷失,顯然是其在當(dāng)代哈薩克斯坦現(xiàn)實(shí)生活中迷失的隱喻。影片期望通過重建對歷史的認(rèn)同感與歸屬感的方式來追求當(dāng)下的文化認(rèn)同,這也意味著哈薩克斯坦人只有與過去重新建立聯(lián)系才能實(shí)現(xiàn)對個人身份乃至整個國族文化的救贖。
近年來,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中的文化認(rèn)同日益顯著地融于“家庭”意象中。通過對普通哈薩克斯坦家庭模式變遷的描摹,這些電影嘗試令其觀眾形成一種建立在私人情感結(jié)構(gòu)基礎(chǔ)上的國族文化認(rèn)同。在對“家庭”這個意象的表現(xiàn)上,電影創(chuàng)作者往往同時體現(xiàn)出兩方面的創(chuàng)作意圖:家庭在健康、有機(jī)的國家文化中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傳統(tǒng)家庭結(jié)構(gòu)瓦解、更具現(xiàn)代氣質(zhì)的家庭模式誕生的不可逆轉(zhuǎn)性。阿迪爾汗·葉爾江諾夫的三部電影作品《平地造屋》《房產(chǎn)經(jīng)紀(jì)人》《擁有者》都致力于表現(xiàn)人如何屬于一個“領(lǐng)地”,并通過個體努力的方式捍衛(wèi)這一“領(lǐng)地”——也就是“家”。具體而言,影片《平地造屋》的主旨是為被剝奪權(quán)利的家庭建造一個家園:房屋建設(shè)是哈薩克斯坦正在進(jìn)行的國家建設(shè)的“微縮景觀”,將哈薩克斯坦作為強(qiáng)大游牧民族和建立哈薩克汗國的輝煌歷史與1991年獨(dú)立后該國普通民眾的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直接聯(lián)系起來;在影片《房產(chǎn)經(jīng)紀(jì)人》中,房產(chǎn)經(jīng)紀(jì)人達(dá)里克本打算出售祖屋以盡快還清負(fù)債,而在回到過去后,他才真正領(lǐng)悟到祖屋的價(jià)值所在,并決心保衛(wèi)自己的“家”,因?yàn)樗J(rèn)識到個體、家庭、家族的命運(yùn)實(shí)際上是與整個國家的命運(yùn)休戚相關(guān)的;至于影片《擁有者》(The Owners,2014)表現(xiàn)的則是傳統(tǒng)家庭崩潰與瓦解過程,通過描摹個體對房產(chǎn)和土地歸屬權(quán)的爭搶,來隱喻哈薩克斯坦在文化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所遭遇的結(jié)構(gòu)性困境。
整體來看,在21世紀(jì)第二個十年,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的國家文化與個體身份敘事,顯然有別于政府直接投資拍攝的主流歷史片——前者致力于營造一種建立在文化反思基礎(chǔ)上的國族認(rèn)同,并將“現(xiàn)代性/現(xiàn)代化”作為“后獨(dú)立”時期哈薩克斯坦國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塑造。在這些作品中,草原既是美麗遼闊的,也是荒涼貧瘠的,成為上述文化反思所依托的主要景觀。而普通哈薩克斯坦人在傳統(tǒng)家庭結(jié)構(gòu)瓦解的過程中對“家園”的渴望、追尋和重建則為走出歷史陰霾、在現(xiàn)代世界煥發(fā)生機(jī)的哈薩克斯坦國家文化的“新生”注入了希望。在這個意義上,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找到了一條兼容美學(xué)與文化政治價(jià)值的發(fā)展道路,其成功證明了國族敘事在藝術(shù)電影生產(chǎn)與傳播中擁有巨大空間和無窮潛能。
結(jié)語
作為“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哈薩克斯坦當(dāng)代媒介、藝術(shù)和文化的發(fā)展為我們從文明互鑒的視角體察外部世界、思索本土價(jià)值觀的跨文化交流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一方面,出于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復(fù)雜原因,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因其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主題選擇、(因低成本而)樸實(shí)無華的美學(xué)、對道德灰色地帶的大膽探索而在本國電影業(yè)的版圖中處于邊緣位置,但這些影片卻并未選擇消極避世或犬儒主義,反而是通過積極、持續(xù)與社會現(xiàn)實(shí)對話的方式,為觀眾營造了文化反思和身份認(rèn)同的空間,這體現(xiàn)了電影媒介與電影藝術(shù)在面臨結(jié)構(gòu)性壓力時所具有的強(qiáng)大彈性。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在記錄民族歷史、構(gòu)建現(xiàn)代國家文化、塑造國族身份認(rèn)同方面所體現(xiàn)出的巨大潛能,值得中國電影事業(yè)管理者和創(chuàng)作者群體借鑒。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雖然在哈薩克斯坦國內(nèi)存在彼此甚少交集的“三重發(fā)行體系”,但是在國家立法與制度環(huán)境建設(shè)層面,還是為帶有一定偏離色彩的藝術(shù)電影——尤其是“獨(dú)立之子”一代的“游擊隊(duì)電影”——預(yù)留了寬容的空間。國家通過一系列手段支持這些電影代表哈薩克斯坦去參與各大國際電影節(jié)展,使之成為外部世界破除關(guān)于哈薩克斯坦封閉、保守的傳統(tǒng)刻板印象的重要中介。畢竟,文明互鑒的前提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文化公約數(shù)”,而非那些不可調(diào)和的文化獨(dú)特性。哈薩克斯坦藝術(shù)電影的成功,為我們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探索講好中國故事、打造中國文化名片的實(shí)踐提供了有價(jià)值的啟發(fā)。
【注釋】
1 張玉霞, 迪努爾·哈力江.哈薩克斯坦獨(dú)立以來的電影發(fā)展之路[J].當(dāng)代電影, 2018(08):51-57.
2 [哈薩克斯坦]古爾娜拉·阿比凱耶娃.中亞電影十年(2010—2020)[J].王垚譯.北京電影學(xué)院學(xué)報(bào), 2021(01):87-102.
3 Gulnara Abikeyeva.Three trends in Kazakh cinema[EB/OL].https://rus.azattyq.org/a/kazakhstan-kino-itogigoda/27454848.html.2015-12-29.
4 Beumers B.Waves,old and new,in Kazakh cinema[J].Studies in Russian and Soviet Cinema,2010(02):203-209.
5 Abishev S,Lumpov E,Smailova I.The phenomenon of Partisan Cinema: alternative film production in Kazakhstan(Appendix: A Manifesto)[J].Studies in Russian and Soviet Cinema,2022(01):61-78.
6 Lawon Culture of Kazakhstan[EB/OL].https://wipolexres.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kz/kz083en.pdf.2006-12-15.
7 哈通社.哈薩克斯坦制定電影業(yè)發(fā)展至2050年理念[EB/OL].http://www.inform.kz/cn/2050_a2950713.2016-09-19.
8 Olga Kasyanova.Adilkhan Yerzhanov:“Cinema is us as astraus”[EB/OL].https://seance.ru/articles/kino_kak_straus/.2014-09-01.
9 Alimana Zhanmukanova.Irina Kairatovna and Political Art in Kazakhstan [EB/OL].https://oxussociety.org/irinakairatovna-and-political-art-inkazakhstan/.2021-06-03.
10Martin Lefebvre.Landscape and Film[M].New York:Routledge,2006.
11 Abishev S E,Taldybayeva A S,Bekkozhin M K,et al.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urban cinema environment as a search for identity[J].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Reviews,2019(05):474-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