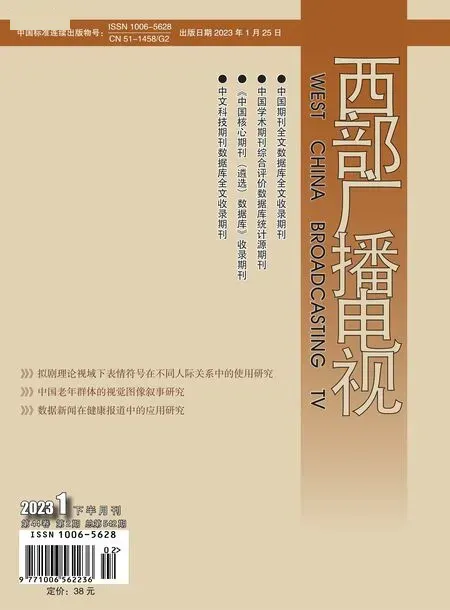擬劇理論視域下表情符號在不同人際關系中的使用研究
——以微信平臺為例
倪慧敏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
在傳統的面對面交際中,交流雙方可以憑借語言之外的表情、神態、動作等非語言符號獲得額外的交流信息,從而建立起情感聯系,使交流順暢有效地進行。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普及,依靠手機網絡的即時通信社交逐漸流行。與面對面交際不同,網絡人際傳播存在共同在場缺失和表情隱匿等特點[1]。為了彌補網絡人際傳播中的不足,表情符號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關于表情符號的概念學界至今沒有明確的標準,筆者通過分析表情符號的發展時間和呈現特點將其劃分成四類:字符表情(以美國信息交換標準代碼表情和日本顏文字為代表)、臉譜表情(各類即時通信軟件默認的黃臉表情)、卡通貼圖表情(以韓國即時通信軟件推出的主題貼圖表情為代表)、自制表情包(包括圖像表情、動態表情和圖文互動表情等)。自制表情包的出現和盛行使得大眾正式開啟了網絡表情的“狂歡”。
1 研究問題的提出和研究方法
表情符號流行至今,相關的研究不在少數。語言學視角下,余光武、秦云提出了表情符號在網絡交流中的輔助交際作用[2];在傳播學角度,李菲、匡文波、邱水梅、劉麗群、劉璽辰基于使用與滿足理論,歸納了表情符號在人際傳播中的使用動機,并發現性別、愛好、互動對象、社會文化等均會影響人們使用表情符號的行為[3-5]。
現有的研究雖然歸納了人們使用表情符號的動機及影響因素,但不同的即時通信軟件所連接的人際關系也不盡相同。特別是近幾年,隨著微信用戶群體的擴大,微信用戶的好友數也不斷上升,人們在微信中處理的人際關系開始從熟人社交轉變為泛社交,從前的私密性、封閉式微信社交模式逐漸淡化,使得表情符號的受眾不再局限于年輕人,使用模式也呈現出更加多元的形態。基于此,本研究重新解構戈夫曼的擬劇理論,將人際關系網絡以強關系、弱關系進行區分,探討微信一對一交際與社群交際語境下,人們使用表情符號的行為規律。
結合訪談法,以年齡在20~35歲,不同性別、職業的15人為研究對象,進行20分鐘的訪談,并對訪談內容進行分析歸納。
2 一對一交際下的表情表演
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皆大歡喜》中有這樣一句話:“世界是一個舞臺,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一些演員,他們都有下場的時候,也有上場的時候。”社會學家戈夫曼也將戲劇比擬人生,認為表演者就是個體或群體;觀眾既可以是特定情境中的人,也可以是表演者本身;在日常生活的舞臺中,表演者通過樣貌、身份、言談等裝備,努力設計前臺表演,又將與之相反的另一面藏匿在私密后臺[6]25。
2.1 弱關系的前臺表演
前臺與后臺是擬劇理論最為經典的概念之一,前臺指表演者有意(向特定的人群)進行特定表演的地方,后臺指在前臺被竭力抑制的行為或與表情促成的印象不相一致的行為發生的地方。在微信的一對一交際中,人們在每一個聊天窗口搭建的“舞臺”上,努力調整自身的角色進行表演。
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把人際關系分為強關系和弱關系。呂露[7]48指出,在不同的人際關系中,人們在與家人、好友等具有強關系的對象進行交流時使用表情符號的頻率最高,與具有弱關系的對象交流時使用表情符號的頻率要低于具有強關系的對象。在不同的人際關系和不同的語境中,人們使用表情符號的動機也存在差異。
通過訪談發現,在與弱關系對象聊天時,由于網絡交際的非臨場特性,表演者時常會使用表情符號策略性地進行自我呈現,營造符合觀眾和自我預期的個人形象。這種通過表情符號的自我呈現就是前臺的表演。
2.1.1 表演者的“理想化”
擬劇理論中“理想化”表演表現為當個人在他人面前進行自我呈現時,總是傾向于迎合并得到對方承認的價值,而實際上他的全部行為并不一定具備這種特質。這種表演的“理想化”也同樣體現在微信交際中。部分受訪者表示,會通過使用表情符號選擇性地展現自己想要在他人面前塑造的形象,并掩飾與自己的理想不一致的行為。當面對地位較高的人時,表演者試圖使用表情符號展現聽從、禮貌的自我形象;面對普通朋友時,則通過使用不同風格的表情來塑造理想的自我形象。例如,通過可愛的卡通表情符號呈現“呆萌”的少女形象,通過有趣搞怪的表情符號打造風趣幽默的個人形象。正如威廉·詹姆士所言,使用者面對每個不同的對象都會表現出自我中某個特殊的“理想化”特征[8]。
2.1.2 觀眾的“乖巧”
戈夫曼認為觀眾既可以是特定的人,也可以是表演者本身[6]197。觀眾的“乖巧”行為是出于對表演者的直接認同,或是出于想避免鬧劇,或是出于某種目的而討好表演者。有受訪者表示,與地位較高的人或是想要尊重的人聊天時,會在表情符號的使用風格和方式上使用“乖巧”手段,如采用對方能夠理解的表情符號實現禮貌需求,或積極使用傳遞正向情感的表情符號避免誤解;與普通朋友聊天時,也會根據對方的表情符號使用情況來調整自己是否使用表情和使用什么風格的表情,從而實現印象管理,例如,選擇與表演者所使用的表情相似的表情符號類型,拉近心理距離,提升彼此的親切感和信任度;使用可愛、調皮的表情符號輔助信息的表達,營造良好的聊天氛圍,避免尷尬的局面。
2.2 強關系的后臺“狂歡”
擬劇理論下的“劇班”表示在進行表演時相互協同配合的任何一個個體或一組人。在弱關系中,表演者通過使用表情符號來進行前臺的表演,以期實現自我呈現和印象管理。與之相對,戈夫曼指出,在后臺區域最重要的并不是要努力營造良好的交往氛圍。在微信社交中,強關系可以看作是表演者的后臺區域,強關系對象間更像是“劇班”伙伴,通過通力合作、共謀秘密來獲得后臺松弛和“狂歡”。劉麗群和劉璽辰認為,在不同的人際關系中,傳遞信息是與弱關系使用表情符號的主要動機,而與強關系交流時實現娛樂則為主要動機[5]。呂露進一步提出,情侶關系間使用的表情符號最為多樣化,好友間使用的表情符號更個性化,與家人和其他弱關系間使用的表情符號較為單一[7]。由此可見,當表演對象為強關系時,不僅人們表情符號的使用頻率會隨之加強,使用動機和方式都會隨之發生改變。
通過訪談發現,受訪者與好友聊天時,除了滿足基本的情感表達之外,還會使用彼此熟知的或同款表情符號,實現共謀的默契,或是通過表情分享、“斗圖”來實現表情“狂歡”。此外,在前臺表演中不允許出現的有可能會冒犯他人的一些舉動,在后臺區域也常有出現,并會被當作是成員間親昵的表現。例如,在與好友聊天時常使用一些“惡搞”表情,這在后臺被視為是調節氣氛、實現娛樂的行為。在與家人的聊天中,表情符號的言語反饋作用則體現得尤為明顯。例如,“好的”“是的”“知道了”“我在忙”等聊天反饋語,通過使用表情符號可以最大限度形象生動地還原面對面的會話。但在與弱關系對象聊天時,單獨使用表情符號常會被視作態度敷衍、不禮貌。因此,與強關系對象聊天中大量使用表情符號不但增加了聊天的娛樂性和效率化,也體現了劇班成員間的合作和共謀。
2.3 前臺與后臺的相互轉換
在傳統的社會交際中,前后臺的分界線相對嚴格。戈夫曼指出,人們有時通過營造一種后臺氛圍也能夠把任何區域變成后臺。這種前后臺的轉換在微信社交中也時有發生。在部分網絡人際關系中,使用表情符號的前后臺行為會發生轉變。
2.3.1 異性間的表演模式切換
戈夫曼指出,無論男女兩性成員的關系多么密切,在對方面前都需要維持某種形象。這種兩性關系間的交往模式無論是在傳統社交還是在網絡社交平臺都是適用的,尤其體現在強關系的戀人關系中。相比其他關系,戀人之間會有傾向性地使用更多的非語言符號來展示內心情感、維持親密關系。因此,戀人關系間表情符號的使用也會更頻繁和多樣化[7]。但通過訪談發現,在兩性關系中,無論男女都會避免使用過于惡俗、粗暴的不雅表情;男生會傾向性地使用調皮、可愛的表情符號迎合女生的喜好,避免誤會的產生。
2.3.2 局外區域下的表演模式
擬劇理論將既非給定表演的前臺又非與之相對應的后臺區域定義為“局外區域”。在前臺區域中,表演者往往想要給予觀眾某種印象,或是避免與給予的印象相抵觸,也就是說,他們在前臺區域扮演的角色是他們最重要的角色,但在局外區域,表演者可以認為這并不是很重要的表演或只是一場預備的演出。
微商、群好友、搖一搖好友等從未謀面的微信好友,人們會很自然地將其定義為弱關系對象。根據以往的理論驗證,在弱關系中人們通常會使用前臺表演策略來進行自我印象的管理。但通過訪談發現,針對局外人群,表演者通常不會有意地進行前臺表演,也不會主動發起后臺合作實現放松娛樂。
在日本的人際關系中,中根千枝根據關系的親疏,將人際關系劃分為“內、外、他所”[9]。“內”指家人、好友等強關系人群,針對這一人群,一般無須客套且不使用敬語;“外”指同事、熟人等弱關系人群,針對這一人群,需要使用敬語來表示敬意;“他所”指和自己無直接關系的人,針對這一人群,日本人多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態度,不使用敬語。隨著微信的泛好友化,網絡社交也呈現出與之相似的關系網絡。這些無須進行前臺表演的微信好友,就近似于日本人際關系中的“他所”。在局外區域的語境下,前臺的自我印象管理被忽略,表情符號的主要功能變為表達意圖、提高溝通效率,最終達成共識。
3 社群交際下的表情表演
一個人的劇班由于沒有其他劇班成員的干擾,表演者能迅速決定應采取何種可行的立場。當由一個人的劇班轉向大劇班時,劇班所擁護的現實特點就不同了。微信中的社群就像是一個大劇班,劇班內的每一個成員通過相互合作來維持共同的目的。根據社群構建的目標、社群交際頻率和社群成員的不同,表情符號的使用動機和行為也隨之發生變化。例如,以強關系搭建的家庭群、好友群等,劇班成員間表情符號的使用傾向于后臺區域的“狂歡”。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同類型的社群,由于成員人數和成員關系的差異,社群內表情符號表演的前后臺界定也會變得十分模糊。例如,以父母和孩子為主的核心家庭群內,表情符號的后臺“狂歡”較為明顯;以親戚、親屬為主的大家庭群內,為了避免代際間的理解偏差,晚輩更傾向于使用正向、可愛的表情符號進行前臺表演策略。
與強關系構建的社群不同,以同學群、工作群、家長群為代表的弱關系社群內,表情符號的使用功能多呈現出與前臺表演相似的策略。在此類社群內表演,要求劇班里的演員有一定的忠誠度,依附于選派的角色,謹慎地按照約定俗成的規則進行表演。例如,地位高的人會直接影響戲劇行為的進程,他們的表情使用偏好會被優先得到滿足。此外,成員內部常會保持基本的一致性,對于地位高的人發表的意見、觀點,其他劇班成員需要通過使用積極、正向的表情符號表明立場態度,否則會被認為是不合群及對擔任角色的認知模糊。
4 結語
微信的網絡交際模式既是基于現實生活的社交又有別于傳統的社交模式。本文從表情符號的使用切入,對戈夫曼的擬劇理論進行了重新解讀,明確了在不同的網絡人際關系中,表演者通過調整表情符號的使用方式,進行前臺和后臺的切換,實現了不同的交際目標。在弱關系社交中,人們傾向于通過表情符號進行前臺的印象管理;在強關系社交中,人們偏向通過表情符號進行后臺的娛樂“狂歡”;但在戀人、非現實好友等特殊關系中,人們使用表情符號的策略也會發生轉變。在社群交際中,由于關系結構的復雜性,即使是同類型的社群,由于成員人數和成員關系的差異,社群內表情表演的前后臺策略也會有所不同。
本研究的分析和結論僅基于與15位受訪者的訪談,樣本數據較為單薄,尚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此外,社群交際呈現出比一對一交際更為復雜的人際關系,僅僅基于強弱關系理論尚無法支撐。在社群交際中,由于不同人員關系的交融,促使表情符號的使用呈現出一種集體表演的模式,對社群交際中人際關系的研究還需不斷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