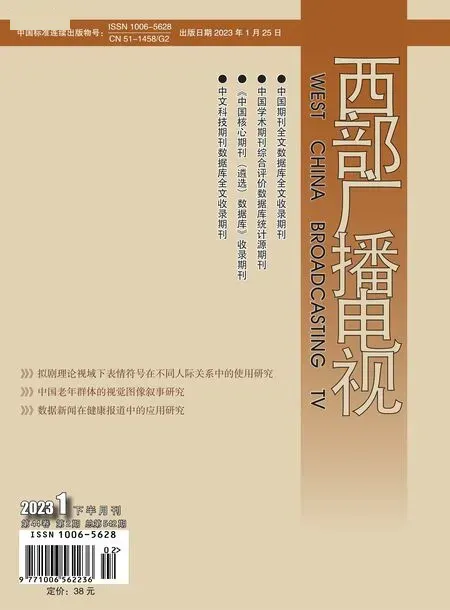妥協(xié)與抗?fàn)帲壕穹治鲆暯窍码娪啊赌倪钢凳馈返娜宋镄蜗蠼庾x
范紅銳
(作者單位:寧夏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院)
《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簡稱《哪吒》)的核心主題是人與命運(yùn)的抗?fàn)帯S捌v述了本應(yīng)是靈珠降世的哪吒卻在陰差陽錯(cuò)下變成了魔丸,而靈珠卻與龍王之子敖丙相融合。魔丸暴虐,因此被施下了天劫咒語,三年后將被摧毀。但哪吒并沒有妥協(xié),身為“魔童”,面對(duì)眾人的偏見,他毅然決然地向命運(yùn)發(fā)起了抗?fàn)帲⒆罱K與敖丙共抗天劫,拯救了陳塘關(guān)的百姓。本文基于精神分析的研究視角,通過潛意識(shí)分析、人格結(jié)構(gòu)理論及心理防御機(jī)制來解讀電影中哪吒和敖丙的精神世界,并進(jìn)一步分析人物的形象內(nèi)涵。
1 理論背景
精神分析的創(chuàng)始人是弗洛伊德,他原本是奧地利維也納執(zhí)業(yè)的精神病醫(yī)生,在治療患者的過程中他認(rèn)識(shí)到了催眠療法的局限性,從而改用自己的精神分析法,以此去挖掘患者遺忘的欲望。1895年,弗洛伊德與布洛伊爾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出版,該書可以說是精神分析的理論奠基之作。此后,他于1900年發(fā)表了《夢的解析》,標(biāo)志著精神分析理論的初步形成。直到1910年召開第二次國際精神分析大會(huì)時(shí)成立了國際精神分析協(xié)會(huì),精神分析才最終形成。精神分析對(duì)電影的介入首先得益于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hào)學(xué)的發(fā)展,通過符號(hào)學(xué)理論,電影內(nèi)容被“文本化”,電影的構(gòu)成要素被“符號(hào)化”,這些“文本”和“符號(hào)”成為精神分析學(xué)介入電影的質(zhì)料[1]。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在電影中的應(yīng)用非常廣泛,主要用到的是弗洛伊德的無意識(shí)理論、人格理論、釋夢理論及心理防御機(jī)制等,對(duì)于電影文本中角色的心理分析較多。
2 “自由”的剝奪:潛意識(shí)與自我
弗洛伊德將人的心理結(jié)構(gòu)分為三個(gè)部分:意識(shí)、前意識(shí)、潛意識(shí)。如果將人的心理活動(dòng)比喻成一座漂浮著的冰山,那么露出水面的部分就是意識(shí),意識(shí)與外部環(huán)境相聯(lián)系,是人有目的、有約束的心理活動(dòng),符合外部環(huán)境的限制;介于水面上下部分的是前意識(shí),它處于意識(shí)和潛意識(shí)之間,有著防守、把關(guān)的作用,它不在意識(shí)之中,但是能經(jīng)過自己的掌控或他人的提醒而進(jìn)入意識(shí);在水面以下的、大部分人看不到的就是潛意識(shí),它處于人的心理結(jié)構(gòu)的最底層,與性本能緊密相連,它是非理性的,涉及的內(nèi)容可能是違背社會(huì)道德等方面的,因此潛意識(shí)是被人們壓抑或隱藏起來的,雖不為人們所注意,但可以影響人們的行為。弗洛伊德認(rèn)為,潛意識(shí)與兒童發(fā)育階段中的創(chuàng)傷記憶息息相關(guān),這些回憶會(huì)讓人產(chǎn)生一種羞恥感,因此人們往往十分排斥。但是,潛意識(shí)的內(nèi)容通常會(huì)趁前意識(shí)松懈時(shí)進(jìn)入意識(shí)。這就是弗洛伊德學(xué)說的核心——無意識(shí)理論。
潛意識(shí)有著很多刺激源。電影《哪吒》中,哪吒的潛意識(shí)情節(jié)在影片中多次體現(xiàn),主要受父母和陳塘關(guān)百姓的影響。哪吒從小就是“魔童”,父母擔(dān)心哪吒闖禍,只能將他約束在總兵府的后院中。由于工作繁忙,他們也無暇陪伴哪吒玩耍,而百姓出于對(duì)“魔丸”的恐懼,人人疏遠(yuǎn)他、憎惡他,甚至同齡的小朋友也不敢與他玩耍。可見,哪吒一直以來都受到現(xiàn)實(shí)的約束,失去了自由。久而久之,哪吒潛意識(shí)下認(rèn)為自己就是百姓所懼怕的“妖怪”,他也逐漸認(rèn)同了這個(gè)定位。人的行為受潛意識(shí)控制,在這一心理下,他對(duì)母親的陪伴表示滿不在乎,對(duì)百姓能接納自己也不抱任何希望。生長在這種成長環(huán)境中,哪吒開始不信任任何人,他變得沒有安全感,內(nèi)心非常的孤獨(dú)和委屈。這些心理創(chuàng)傷也刺激了哪吒潛意識(shí)的形成。但是在現(xiàn)實(shí)的種種“約束”下,哪吒的潛意識(shí)依舊有著對(duì)自由的向往,他期望得到他人的認(rèn)同,因此他三番五次地逃出結(jié)界,并試圖去融入社會(huì)。
而影片中的另一角色敖丙和哪吒有著相似的成長經(jīng)歷。他有著妖怪的身份,不被世俗所接納,從小就只能孤獨(dú)地生活在黑暗中,因此他最渴望的就是獲得自由。敖丙的潛意識(shí)多來自父親和師傅對(duì)他的言語教導(dǎo)。為了改變龍族的悲慘命運(yùn),父親對(duì)敖丙寄予厚望,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振龍族。而他的師傅申公豹一直向他灌輸人的成見不可跨越的思想,并告訴敖丙魔丸是他一生的宿敵。出于對(duì)父親和師傅的認(rèn)同,這種潛意識(shí)在不停地影響著敖丙。他過著傀儡般的生活,不但失去了自由,也隱藏了真實(shí)的自我。在龍王和申公豹的嚴(yán)苛要求下,敖丙壓抑了自我最真實(shí)的需求,他善良的天性被剝奪,對(duì)人類抱有成見,潛意識(shí)下對(duì)父親和師傅的教導(dǎo)深信不疑。
3 對(duì)抗與游離:角色的三重人格
弗洛伊德在心理結(jié)構(gòu)的基礎(chǔ)上又提出了人格結(jié)構(gòu)理論,該理論與心理結(jié)構(gòu)有一定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也分為三個(gè)層次: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位于人格結(jié)構(gòu)的最底層,是最原始的部分,它是非理性的,是人生存所需要的欲望和沖動(dòng),不受社會(huì)道德、倫理的約束,只遵循快樂的原則。自我位于人格結(jié)構(gòu)的中間層,是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所呈現(xiàn)出的我,它在本我和超我之間調(diào)節(jié)矛盾。自我是理性的,它可以壓抑本我的沖動(dòng),使之不會(huì)突破自我的“防線”。而超我則以至善為原則,它位于人格的最高層,是遵守道德規(guī)范的我,根據(jù)道德規(guī)范來約束本我。在這三個(gè)層次中,自我有著強(qiáng)力的調(diào)節(jié)作用。當(dāng)本我處于一種非理性的狀態(tài)時(shí),自我會(huì)壓抑、轉(zhuǎn)移本我的沖動(dòng),這就是防御機(jī)制。在影視中,本我多體現(xiàn)在壞人的貪婪、邪惡、暴力、欺騙等方面;超我則體現(xiàn)在那些完美之人的身上,他們正義、勇敢、善良,大多有著崇高的精神;而亦正亦邪之人,就是自我,自我是本我與超我沖突協(xié)調(diào)的結(jié)果,既要約束本我的沖突,也要按照理想原則去構(gòu)造自己[2]。在影片《哪吒》中,角色的人格結(jié)構(gòu)主要體現(xiàn)在哪吒和敖丙二人的身上。
3.1 哪吒的三重人格分析
本應(yīng)是靈珠轉(zhuǎn)世的哪吒卻在陰差陽錯(cuò)下變成了“魔童”,因此哪吒的身上呈現(xiàn)出“神性”與“魔性”的二元對(duì)立,這使得他經(jīng)常游離在本我和自我之間并產(chǎn)生激烈的對(duì)抗[3]。本我是人格結(jié)構(gòu)中最原始的部分,是非理性的。誕生之初受魔丸控制的哪吒就是他無意識(shí)人格下的本我,有著最原始的欲望,會(huì)盡情釋放自己的本能,這一狀態(tài)下的哪吒擁有毀天滅地的恐怖實(shí)力。同時(shí),本我人格下“魔化”的哪吒不受任何社會(huì)道德、倫理的約束,因此在后期失去控制時(shí)他會(huì)變得六親不認(rèn),無差別地攻擊身邊的每一個(gè)人,甚至難有人是他的對(duì)手。
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間徘徊,常用來調(diào)節(jié)本我和超我之間的矛盾。同時(shí),自我會(huì)受到外部環(huán)境的影響而發(fā)生變化。與無拘無束的“本我”不同,“自我”是受到限制的。影片開始,哪吒失去控制,太乙真人給他戴上了象征“約束”的乾坤圈。哪吒的魔化狀態(tài)也由此被壓制,同時(shí)他還受到了來自父母、師傅及百姓的“約束”。可以說,戴上乾坤圈的哪吒就是他自我的體現(xiàn),在自我人格下,哪吒的行為會(huì)受到種種限制。生而為魔的哪吒從小就缺乏陪伴,他渴望融入社會(huì),被大家認(rèn)可。但是,哪吒自出生以來就一直受到來自現(xiàn)實(shí)的種種限制和約束,因此他的“自我”一直處在被壓抑的狀態(tài)之中,當(dāng)自我被過度壓抑時(shí)便會(huì)引發(fā)內(nèi)心沖突,進(jìn)而不斷和本我進(jìn)行抗?fàn)帯.?dāng)申公豹揭開了哪吒真實(shí)的身世后,哪吒的自我將再也無法壓抑本我,本我終究會(huì)爆發(fā)。這也是哪吒最終魔化從而掙脫乾坤圈的原因。
超我遵循至善原則。影片的前期,哪吒經(jīng)常向超我靠近。當(dāng)李靖欺騙哪吒是靈珠轉(zhuǎn)世,未來要靠他斬妖除魔保護(hù)百姓時(shí),渴望受到百姓認(rèn)可的哪吒在修煉結(jié)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擊敗了一只夜叉,并從他手里救下了被擄走的小女孩。在影片結(jié)尾,李靖為了拯救哪吒使用了可以轉(zhuǎn)移天劫的一命抵一命的血親符,當(dāng)?shù)弥赣H的良苦用心后,哪吒幡然醒悟,他回到父母和師父的身邊一起對(duì)付申公豹,最終他不僅拯救了陳塘關(guān)百姓,還得到了他們的認(rèn)可。此時(shí)的哪吒至善至上,實(shí)現(xiàn)了向超我的轉(zhuǎn)變。
3.2 敖丙的三重人格分析
作為靈珠,敖丙一直在懲惡揚(yáng)善,他本身有著超我的一面,這從他一開始和哪吒聯(lián)手擊敗夜叉并救人的舉動(dòng)就可以看出。但是敖丙的內(nèi)心卻時(shí)常游離在本我和自我之間,一方面,他不敢違抗父親交給他的使命;另一方面,他又時(shí)常懷疑申公豹對(duì)他的教導(dǎo)。敖丙所在的龍族一直被世人視為妖,就算歸順天庭也只能世世代代鎮(zhèn)守在深海下,不為世俗所認(rèn)可。龍王和申公豹將重振龍族的使命都寄托在敖丙的身上,久而久之,敖丙壓抑了最真實(shí)的自我,他將魔丸視為對(duì)手,對(duì)于龍族不公的命運(yùn)感到十分憤怒。在經(jīng)歷內(nèi)心激烈的對(duì)抗后他的本我終將被激發(fā)出來。同時(shí),敖丙一直生活在海底,因?yàn)槭廊藢?duì)龍族的偏見,他從來都不敢正大光明地行走在世間。再加上長期受龍族和申公豹的集體心理暗示,他來自本我中殘暴自私的一面被釋放了出來。此時(shí)的敖丙有著最原始的欲望,在本我的驅(qū)動(dòng)下,他不僅渴望自由,渴望世人接受龍族,還想著可以封神登天,重振龍族。他的超我不再壓抑自我,本我也沖破防線得到了釋放,為了自己的欲望開始傷害無辜之人。
自我遵循現(xiàn)實(shí)原則。隨著外部環(huán)境的發(fā)展,敖丙的自我在不斷完善。作為靈珠,他和身為魔丸的哪吒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而偏偏二人的命運(yùn)又是如此相似。當(dāng)敖丙在海灘結(jié)識(shí)哪吒后,他從哪吒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過往,仿佛哪吒就是鏡像中的另一個(gè)自己。兩人也在斬妖除魔之時(shí)成為彼此唯一的朋友,受哪吒的影響,敖丙開始逐漸認(rèn)識(shí)到真實(shí)的自我。在哪吒生辰宴上,敖丙與哪吒之間的戰(zhàn)斗更像是他的本我與自我之間的沖突。向命運(yùn)妥協(xié)的敖丙聽到和他有著相似命運(yùn)的哪吒說出“我命由我不由天”這句話時(shí),他的內(nèi)心動(dòng)搖了。此時(shí)的敖丙決定抗?fàn)帲龌卣嬲淖约海?dāng)他與自己達(dá)成和解時(shí),他的自我也變得完整了。
在敖丙幡然醒悟后,他開始拋卻內(nèi)心的欲望并放下世人對(duì)他的成見,轉(zhuǎn)而救下了哪吒和陳塘關(guān)百姓,選擇與哪吒共抗天劫。這時(shí)敖丙的內(nèi)心高尚又無私,他超我的人格占據(jù)上風(fēng),在這一過程中敖丙也完成了至善至美的道德升華。
4 哪吒與敖丙的心理防御機(jī)制
防御機(jī)制是自我用來對(duì)抗本我和超我的。當(dāng)本我威脅到自我并使人產(chǎn)生焦慮時(shí),自我就會(huì)采用一系列的防御機(jī)制來對(duì)抗本我。弗洛伊德給出了很多種防御機(jī)制,常見的有否認(rèn)、投射、退化、隔離、抵消、轉(zhuǎn)化、合理化、升華、幽默、反向形成等各種形式。防御機(jī)制是一種常見的心理行為,當(dāng)個(gè)體遭受影響或產(chǎn)生消極情緒時(shí),會(huì)自然地產(chǎn)生防御機(jī)制,并依靠這些防御行為來調(diào)節(jié)內(nèi)心的平衡。人們?cè)谌粘I钪薪?jīng)常會(huì)使用心理防御機(jī)制來保護(hù)自己,但若長期使用,便會(huì)導(dǎo)致超我與本我失衡,損害心理健康。影片中哪吒從童年起就經(jīng)歷了很多心理創(chuàng)傷,因此他的內(nèi)心積存了各種負(fù)面情緒,為了壓制這些負(fù)面情緒,從而產(chǎn)生了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機(jī)制。
壓抑是心理防御機(jī)制中最基本的一種,是指把令人感到痛苦的經(jīng)歷或不被接受的欲望壓制到潛意識(shí)中,并不為自己所覺察。影片中,哪吒從出生就被貼上“標(biāo)簽”,他飽受百姓的偏見。而李靖夫婦和太乙真人也一直約束著哪吒的行為,并教哪吒如何通過幫助別人使百姓接納他。由于長期的孤獨(dú)和過多的規(guī)矩約束,哪吒不僅把他的負(fù)面情緒壓抑到潛意識(shí)之中,還壓抑了更多的憤恨。雖然表面上遺忘了,但這些負(fù)面情緒仍會(huì)影響著哪吒。同樣,影片中敖丙自出生以來也有著太多的規(guī)則束縛。師傅的教導(dǎo)、父王的期望都?jí)旱盟贿^氣來,在世人面前為隱藏龍族身份的敖丙也一直是孤身一人。長期的孤獨(dú)與壓力導(dǎo)致敖丙也將這些負(fù)面情緒壓抑到潛意識(shí)中,表面上他是遺忘了,但是這些痛苦經(jīng)歷卻時(shí)時(shí)刻刻影響著敖丙,這也是他最終內(nèi)心產(chǎn)生動(dòng)搖的原因。
反向形成是指個(gè)體表現(xiàn)的外在行為與其內(nèi)在動(dòng)機(jī)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哪吒屢次惡作劇,實(shí)則是他渴望融入社會(huì)并希望眾人接納他的表現(xiàn)。但是,在經(jīng)歷了百姓的偏見、父母和師父的約束以及好朋友敖丙的背叛后,哪吒發(fā)現(xiàn)他的正面努力不被接納,這導(dǎo)致他采取了反向形成的防御機(jī)制,即哪吒的心里其實(shí)非常孤獨(dú),他渴望被愛和陪伴,希望眾人可以接納、認(rèn)同他,但實(shí)際表現(xiàn)出的卻是一副冷漠、無所謂的態(tài)度[4]。
此外,陳塘關(guān)的百姓視哪吒為“魔童”,出于恐懼的心理,百姓心中形成了一個(gè)妖怪的形象并投射給哪吒,而哪吒也逐漸認(rèn)同了這一認(rèn)知。認(rèn)同是把某人的特征加到自己身上以某人自居[5],因此哪吒經(jīng)常哼唱“我是小妖怪,逍遙又自在”。而相似的命運(yùn)與成長經(jīng)歷也使哪吒成為敖丙鏡像中的另一個(gè)自我,他將自己投射到哪吒的身上。在與哪吒的最終決戰(zhàn)中敖丙本已屈服于命運(yùn)的安排,但是當(dāng)他看到作為其鏡像的哪吒向命運(yùn)發(fā)出挑戰(zhàn)時(shí),敖丙的內(nèi)心產(chǎn)生了前所未有的動(dòng)搖。他開始認(rèn)同哪吒的行為實(shí)際上就是相信自己也可以打破命運(yùn)的不公。最終,敖丙選擇與哪吒聯(lián)手共抗天劫。
5 結(jié)語
本文通過精神分析理論,對(duì)影片《哪吒》中哪吒和敖丙的一系列行為進(jìn)行解讀,深入挖掘其背后隱藏的心理原因、人格沖突和防御機(jī)制,并進(jìn)一步認(rèn)識(shí)到人物的形象內(nèi)涵和精神世界。此外,在新的時(shí)代背景下,將精神分析理論運(yùn)用于電影研究,可以擴(kuò)大其在影視和學(xué)術(shù)研究領(lǐng)域內(nèi)的影響,進(jìn)一步深化和豐富電影的文化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