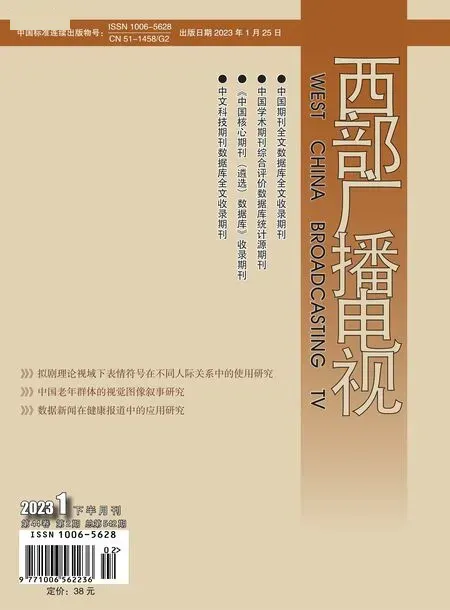從前文本看《霸王別姬》與《蝴蝶君》的表達異同
王瀟悅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
《霸王別姬》與《蝴蝶君》兩部影片分別由中國導演陳凱歌和加拿大導演大衛·柯南伯格執導。前者的故事跨越50年之久,改編自李碧華的同名小說;而后者根據美國華裔劇作家黃哲倫同名戲劇改編。它們同將故事背景放置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并總體強調了動蕩時期理想與現實間、舞臺與生活間、生存與死亡間的情感糾葛。盡管由東西方文化理解差異所帶來的場景再現略有不同,但二者皆通過使用前文本敘事策略達成了極高的共通性和可比較性。
作為互動文本的一部分,前文本通常可以為劇本提供更完整的敘事基礎,增進電影在表達深刻立意時的可被理解程度,同時也幫助歷史文化實現再傳播。歐尼爾將前文本歸類為啟動戲劇性行動的場合。她在研究教育領域的過程劇(Process Drama)時寫道:“前文本將激活、啟動過程劇文本的編織。除了表明它不僅存在于文本之前,而且還與文本相關,這個術語很有價值,因為它承載著文本語境中更深層次的含義,可成為一個解釋性的理由或是借口。”[1]
中國學者趙毅衡認為“狹義的前文本包含文本中的各種引文、典故、戲仿、剽竊、暗示等,廣義的前文本還會包括這個文本產生之前的全部文化史”[2]。顯然,《霸王別姬》和《蝴蝶君》將戲曲文本《霸王別姬》和歌劇文本《蝴蝶夫人》作為解釋片中文化語境、增強文化底蘊的引文、典故、戲仿、暗示,無疑起到了前文本的作用。此外,從詞義上看,戲曲與歌劇在英文中皆可寫為“opera”,雖然二者來自不同的文化體系,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但都屬于以音樂為主體的舞臺表演藝術,共通性和可比較性也由此達成。
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在共同運用前文本敘事方法時,所使用的悲劇性策略仍在層次和程度上不盡相同,由此所產生的悲劇性效果將在敘事結構、人物塑造、主題表達等方面形成差異化體現。
1 電影對前文本的衍生與重構
戲曲與歌劇作為這兩部電影的前文本,其無論是在情感基調還是故事走向上都對電影有著暗示和引導作用,而這種作用會直接影響整部電影的最終情感表達。因此,兩部電影在創作時都不約而同地對戲曲、歌劇進行了內容衍生和重構,但它們在衍生與重構的過程中所采用的方式和達成的效果都是不同的。
電影《霸王別姬》以京劇《霸王別姬》為前文本進行內容再創作。京劇以秦朝覆滅、楚漢相爭為歷史背景,講述了西楚霸王項羽被困于垓下,在營中與虞姬飲酒作別,虞姬自刎,項羽殺出重圍,迷路,至烏江,因感覺愧對江東父老在江邊自刎的故事。而電影《霸王別姬》以1924—1977年的北京為背景,講述了程蝶衣與段小樓之間的復雜情感糾葛。在電影中的這一時期,中國經歷了外國入侵、政權變更和復興重建等大事,社會長期處于一種不穩定狀態,這與戲曲中的社會狀態是高度吻合的。與此同時,影片中程蝶衣與段小樓作為京劇演員,兩人分別飾演了戲曲中的虞姬和項羽,這樣的方式讓影片中的人物與戲曲中的人物形成緊密聯系,達成人戲合一的狀態。此外,影片中,程蝶衣遭到段小樓的殘忍背叛,于11年后自刎于戲臺的悲劇性結局也與京劇如出一轍。不過在這里,導演對戲曲文本進行了意義上的重構,將一場愛情悲劇轉變為了人性斗爭,將戲曲中對虞姬和項羽二人至死不渝的愛情的歌頌轉化為對人性扭曲的控訴和諷刺。
電影《蝴蝶君》僅保留了歌劇《蝴蝶夫人》中的悲劇性結局,但對影片中所呈現出來的社會狀態、性別符號以及情感關系均進行了倒置般的解構與重構——即以一種完全相反的形式構建故事,使電影與戲曲之間形成明顯反差。歌劇《蝴蝶夫人》敘述了女主人公巧巧桑在與美國海軍軍官平克爾頓結婚后慘遭背棄,最終以自殺了結生命的純粹愛情故事,是以1900年尚處于明治天皇時期的日本作為故事發生地,整體社會狀態呈現穩定局面。而電影中所呈現出的社會狀態卻與戲曲中完全相反,動蕩與紛亂的氣息充斥著整個社會,為整體的感情基調渲染了不穩定的氛圍,具有暗示效果。與此同時,片中宋麗玲與伽里瑪之間的愛情性質也與歌劇不同,影片中兩人的愛情是國家斗爭下的產物,是以情報竊取為最初目的而產生的不純粹感情。另外,影片對情感在性別上的主被動關系也進行了對調,宋麗玲作為影片的“女主角”在結尾處返回中國,離開了伽里瑪,而伽里瑪在獄中自殺。多方面的敘事倒置,將愛情的立意從普通的個人層面擴展到了具有反思意義的群體層面,意在以迥異的社會背景、人物特點和關系構建來演繹相似的悲劇,表達了創作者對于愛情的思考。
2 戲曲/歌劇人物的表象與意象傳達
無論是在京劇《霸王別姬》里還是歌劇《蝴蝶夫人》中,人物形象都相對單薄,觀眾無法單純從一場戲里了解到人物的各方面特征和成長經歷所帶來的人物弧光。因此,戲曲/歌劇往往是對現實的抽象化和片面化表現,而電影《霸王別姬》和《蝴蝶君》卻恰恰借用了這種抽象且片面的表達特征來增強人物之間的戲劇沖突。
在京劇中,虞姬為愛赴死,忠勇癡情;項羽威風霸氣,乃忠義之士。此二者鮮明的身份符號被賦予片中人物身上,或為表,或為里,助推主角人物的情感外露。在電影《霸王別姬》中虞姬這個角色承載著名與利,小四對于虞姬這個角色的渴望僅是對飾演虞姬所帶來的江湖地位的垂涎。而程蝶衣對于虞姬的追求則深入內核,是不甘心妥協現實,對美好的無力幻想和渴望,更是癡情的象征。影片最后程蝶衣舉劍自戕,更是人戲合一,與虞姬徹底融為一體,兩個人物身上承載的悲情效果在此刻達到極致,共存永生。
反觀飾演西楚霸王項羽的段小樓,他雖憑借著扎實的功底,將這一角色表演得爐火純青,出神入化,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出賣程蝶衣、背棄菊仙,與西楚霸王的人物內核截然相反。他得到的僅是角色的表象,反倒是他的妻子菊仙,雖沒能飾演虞姬,甚至是與高雅的表演藝術完全背離,但她用實際行動演繹了現實生活中有情有義的虞姬。她的自盡結局更是與京劇中的結局有著目的上的相似性,即以自己的死亡來警醒、成全所愛之人。此二人不同于程蝶衣,沒有與戲曲人物達成表里的共同一致。但電影通過拆解戲曲人物的內在與外在,達成的對比效果,更具備諷刺和現實意義。人物的復雜性、角色的立體感和飽滿度也就在這內外表里的矛盾沖突中得以表現。
相比之下,電影《蝴蝶君》對于歌劇人物的使用,則多停留在表象。一是由于該片所構建的社會背景、人物特點、情感關系都與歌劇所呈現的截然不同,因此原劇中的人物無法為影片創作提供參考和借鑒。二是由于人物表象在此歌劇當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以一男一“女”在愛情中的關系和地位,即愛與被愛,拋棄與被拋棄,主動與被動為敘事基礎來呈現一出悲劇。因此,對蝴蝶夫人表象的呈現實則也蘊含了愛情地位的象征意義。電影中,戲曲演員宋麗玲一開場就通過對蝴蝶夫人角色的飾演被賦予了蝴蝶夫人的外殼,獲得蝴蝶夫人的表象和被動的愛情地位。而之后隨著故事的推進,到尾聲伽里瑪在獄中扮演起了蝴蝶夫人,于是蝴蝶夫人的表象隨之轉移到了他的身上。表象的轉移過程意味著兩人在愛情中的主導地位發生了改變,從之前的宋麗玲盼望伽里瑪的到來,變為伽里瑪對宋麗玲的渴望和期盼。這種依靠表象的轉變來達成的人物關系構建,不僅沒有影響片中人物弧光的展現,更利用歌劇表象外化了影片人物的內心情感需求。宋麗玲從被動到主動的轉變,是其擺脫了外界給予的束縛和干涉之后,所實現的思想上的解放和為愛情義無反顧的態度;而伽里瑪從主動變為被動也是后期的社會經歷所致,長年獨居的生活和得而復失的經歷讓他無法接受自己所愛之人的離去,也無法正視宋麗玲是男人的真相。
3 戲曲/歌劇結構的線性表達
《霸王別姬》和《蝴蝶君》這兩部電影均采用了線性敘事的方式來呈現故事,并將人物對戲曲和歌劇的表演片段放置于影片的開頭和結尾兩處,前后呼應,增添了故事的懸疑氛圍。但這兩部作品在分割戲曲和歌劇結構時卻有著不同的處理方式。
在電影《霸王別姬》中,導演陳凱歌將一段完整的京劇表演拆分成兩節,一節放于開頭,一節置于末尾。開頭處,程蝶衣與段小樓穿著戲服來到黑漆漆的舞臺中央做準備,寒暄中提及過去那段殘酷的時光。緊接著,一小斯聲音入畫張羅著要給他們打開舞臺的燈,二人站在從門口透進來唯一的光里等待著舞臺亮起,戲曲開場。就此,該片段戛然而止,隨之開始的是程蝶衣與段小樓從小時候講起的舊事。導演將這場京劇表演的前半部分以倒敘的方式提前展現給觀眾,使中間的敘事情節既像是在講述虞姬與項羽的人生,又像是描述程蝶衣與段小樓的人生。這種戲中戲的嵌套方式構建起了一種戲如人生、曲終人散的敘事視點,使電影中的現實故事與戲曲故事形成緊密的交織,達成預示、影射效果。影片的最后3分鐘,“十一年后”字幕出現于畫面中心,一段黑場過渡后,京劇表演片段再現,成為全片的高潮——程蝶衣伏劍自刎宣告這段亂世情以悲劇收場,也標志著這個紛亂無序時代的落幕,情感的復歸也就在這場戲中得以達成。
再看電影《蝴蝶君》,其歌劇結構相對獨立。雖然歌劇《蝴蝶夫人》的結局表演出現在了電影的開頭和結尾,卻是作為兩個單獨的片段來進行不同的內容呈現和情感表達。在開頭處,歌劇里的女主人公由宋麗玲扮演,是男女主人翁相遇的一個契機,同時也為由這次契機所產生的感情做了悲劇性的結局鋪墊。而在影片的末尾處,歌劇的情景演繹是由男主人公伽里瑪來完成的。前后兩處角色的互換,暗示了兩人在情感中所處位置的轉變,意在展現與原劇不同的愛情關系。同時,歌劇《蝴蝶夫人》作為一種意象的指引,其所要傳達的并不是劇中的具體社會環境或者人物特征,而僅是一種對悲劇愛情的思考。
4 戲曲/歌劇主題的轉變和升華
作為互文性文本,電影《霸王別姬》在主題上更側重于揭示人性的復雜和對時代社會的批判,而不是單純地呈現愛情和戲曲內容。這也是陳凱歌導演將電影的結局改為自刎的意義——在特殊的年代,揭開表象,異化的人心與人性皆浮出水面,程蝶衣的自刎正是對表象的窺破,也是人生與戲無法撕扯開的注定結局。而其自刎時所用的劍也被賦予了三重含義:一是虞姬忠勇癡情精神的象征符號,二是程蝶衣和段小樓情感的具象載體,三是程蝶衣和段小樓背棄菊仙的見證。《霸王別姬》電影正是通過與戲曲的相互指涉,將京劇中理想且正面的人物形象進行解構,并將拆解后的表象和內在特點投射在多個電影人物形象中,重塑出復雜多樣的真實人物。
電影《蝴蝶君》則遵循了歌劇《蝴蝶夫人》的愛情悲劇主題。在對人物形象和關系進行倒置重構的過程中,派生出影片對浮于表象的愛情的批判。歌劇中的主角之間的地位關系是固定的,愛與被愛、拋棄與被拋棄,始終如一;而電影中的人物關系隨著情節的發展產生反轉。在電影結尾,扮演成蝴蝶夫人自盡的伽里瑪,用生命演繹了角色。歌劇成為困住他的囚籠,象征著一場愛情假象。鏡子作為伽里瑪自殺的兇器成為打破假象的工具,是一個幫助人物徹底看清事物本質的意象道具,隨著鏡碎人去,徒留的只有看透愛情表象的無奈與悲憤。
戲曲與歌劇所形成的前文本與電影相輔并敘的方式,能有效增強人物的感染力和故事的感召力,是將一個已具有藝術價值和思想內涵的作品進行再創作的過程。此時的電影,其本身便已經具備了與前文本比較時所衍生出的戲劇效果,這種戲劇效果是影片主題表達的有力推手。
5 結語
法國符號學家茱莉亞·克利斯蒂娃(Julia Christeva)在1969年出版的《符號學》一書中首次提出了互文性這一術語[3],并認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轉化[4]。根據其語言邏輯,互文性應該是“在一個或多個語篇之間建立關系的語篇特征”,或“語篇之間的相互關系或相互作用”[5]。這意味著一個文本只有與前文本進行比較才能被理解,它要求我們不把文本理解為一個獨立的系統,而是把它理解為一種差異和歷史的痕跡。重寫、重構是“閱讀行為”發生后的結果,它不同于對前文本的質疑或是抄襲,而是在肯定了前文本的基礎上實現再創作。基于此,前文本的作品價值和閱讀者的感知能力都能得到很好的驗證。通過文本間重復顯現的符號關系以及差異性表達,二者意義的獨特性都能得到實現[6]。正如電影《霸王別姬》和《蝴蝶君》,它們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對戲曲和歌劇元素進行了解構和重構,塑造了與前文本不同但又相互共存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它們很好地保留了前文本的藝術本質和文化語境,并在此基礎上注入了新的思考和表達,這對藝術作品之間,特別是不同形式的作品之間的融合和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這種互動不僅用于電影制作,還用于編碼和解碼其他文本,如小說和戲劇。托妮·莫里森的小說《爵士樂》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使用即興爵士樂的風格來講述故事,讓讀者仿佛置身于20世紀20年代爵士音樂家哈萊姆即興演奏的節奏中。爵士樂不僅作為一種情節驅動力,還象征著一種文化內涵。它為小說《爵士樂》提供了不再需要刻意用語言來表述,便可完成社會背景建構和文化價值傳達的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