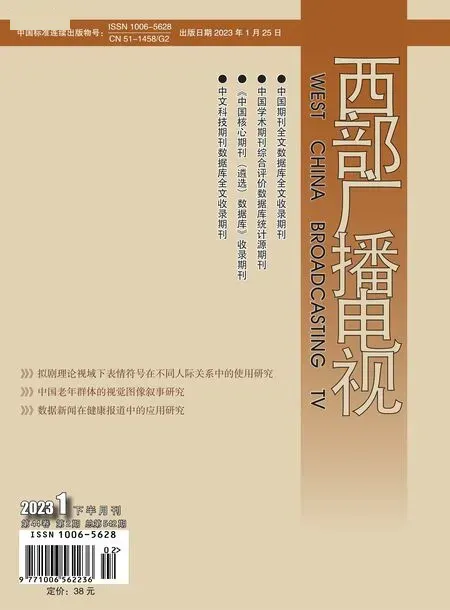結構主義符號學視角下孫悟空形象建構研究
——以《大話西游》為例
同曉雨
(作者單位:河北傳媒學院)
20世紀60年代起,后現代主義思潮席卷西方社會,這一思想涉及建筑、藝術、文學、歷史、哲學等諸多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既是對現代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又是對現代主義的批判與解構。黑色喜劇就是后現代主義思潮在影視界的主要表現形式,其內核依然是悲劇,它的外延是一種哭笑不得的幽默。它將悲劇內容與喜劇的形式交織混雜,以此表現世界的荒誕、社會對人的異化、理性原則破滅后人的惶惑或者是人類徒勞的自我掙扎。其中以對傳統文化的調侃與批判表現得最為突出。
《大話西游》便是這樣的代表作品,其將周星馳對普通人物的理解與體會展現得淋漓盡致。從“斗戰勝佛”到“至尊寶”,不僅是孫悟空從神到人的轉變,更是神性消解的體現。
“頭戴金冠,手持金箍”的孫悟空威風凜凜,是高高在上的斗戰勝佛,與普通人民頗有距離。每一部優秀的影視作品背后都蘊含著深刻的時代內涵,“至尊寶”的創作也與時代同頻。從孫悟空到至尊寶,不僅僅是斗戰勝佛的神性消解,更是觀眾自我多元化需求覺醒的間接體現。“至尊寶”就是這個時代承認平凡卻又不甘于平凡的蕓蕓眾生,每個擁有“英雄夢”的平凡人都可以從“至尊寶”的身上瞥見自己的影子。作為一部源于生活卻高于生活的影視藝術作品,《大話西游》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
1 研究背景和意義
1.1 研究背景
《西游記》作為我國四大名著之一,對數代中國人尤其是文人墨客都有著深遠的影響。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西游記:“故雖述變幻恍忽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1]中國文藝界也由此創作了無數以《西游記》為主要題材的文學與影視作品,而其中具有復雜性人格的大師兄孫悟空更是眾多影視劇的男主角。也是由于孫悟空形象的復雜性,創作者塑造了許許多多同一原型人物的不同影視形象,而不同的形象具有各自特殊的符號含義,這與作品背后的傳播語境、受眾心理和媒介技巧都密切相關。
1926年上映的《孫行者大戰金錢豹》,是我國電影電視史上的第一部以孫悟空為主要影視形象的影片。從這部影片誕生至今,共有50余部相關影片誕生,從戲劇到電影,從動畫片到愛情片,種類繁多,其中每一個孫悟空都具有自己獨特的角色形象與特點。《大話西游》作為一個分水嶺式的作品,將孫悟空的形象塑造得更加人化,其開始擁有感情線,此后作品中的情節也不拘泥于唐僧師徒四人的取經之路,更多是從取經路上的某一節點而衍生出來劇情,且大多帶有戲說與改編色彩,在人物設置上也更加擬人化。
1.2 研究意義
從理論角度來講,雖然有較多的學者都從多個角度研究了孫悟空的影視形象及其演變,但是很少有學者從結構主義符號學的角度入手,而從這個角度研究它的演變并進行對比分析的學者更是少之又少。本研究從結構主義符號學的角度出發,分析孫悟空在關鍵節點的影視形象,并對節點前后的形象進行簡單對比,這對于孫悟空影視形象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參考價值。
另外,孫悟空的影視形象在不同的影視作品中是如何塑造的,是否有變化,有何變化,這種變化又承載著怎樣的社會傳播環境與受眾心理變遷,同樣值得研究。
2 結構主義符號學的概念界定和引用
本文基于傳統符號學理論,結合羅蘭·巴特的結構主義原理,最終形成本文核心理論——結構主義符號學理論。本文將從“話語層”和“意識形態層”兩個層面,研究孫悟空影視作品中形象符號的能指和所指,并結合具有代表性的關于孫悟空的影視作品,進行更具說服力的研究。
2.1 符號的能指和所指
在本研究中,孫悟空將被視作一個具有特殊含義的符號,即兩者間具有任意關系的能指與所指的辯證統一體,因此能指就是符號的物質載體,它的表現形式為符號的聲音和形象;所指就是符號的精神內涵,它的深層含義是符號所代表的“精神概念或心理意義”[2]4。阿瑟·阿薩·伯格在其所著的《媒介分析技巧》一書中,解釋了如何理解符號的能指與所指:能指是詞語或符號的字面意義或外在含義;所指是其象征的、歷史的或情感的內容[3]。在界定清楚符號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后,我們就可以把孫悟空影視形象看作是辯證統一的特定影視作品中的能指和所指的符號含義。
2.2 分層結構下孫悟空形象的結構主義符號學
2.2.1 話語層
在影視作品中,導演、編劇往往傾向于通過角色選擇、服裝道具、臺詞動作、視聽語言等來傳遞自己的創作意圖,以引發觀眾共鳴。因此,本文中話語層的符號內容,即在以孫悟空為主角的影視作品中具有特定含義的內容。孫悟空形象在話語層的能指構成就是那些具有特殊含義的細節,所指就是這些細節的特殊內涵[4]。
2.2.2 意識形態層
本文所進行的意識形態層面的符號分析,是在充分分析話語層中孫悟空符號的能指與所指的前提下,再次結合藝術創作的時代背景、社會背景及視聽語言表達等因素,從而剖析作者創作時的文化內涵。而意識形態層的符號,它的能指就是作品創作時的社會背景、創作者和受眾的價值思想等,它的所指就需要聯系更為廣泛的社會現實來探討[2]6。
3 孫悟空影視形象的能指與所指
以下筆者將從結構符號學的角度出發,以由劉鎮偉導演,周星馳、朱茵等主演,于1995年上映的電影《大話西游》為例,來研究這部影片中孫悟空的影視形象。
3.1 話語層的孫悟空
3.1.1 形象建構
《大話西游》中的孫悟空顛覆了以往所有的影視劇及觀眾固有的刻板形象。在《西游記》中,孫悟空是一個懲惡揚善、武藝高強、一心護送師傅去西天取經的大師兄,是許多人心目中的大英雄。經典的孫悟空形象是“身穿金甲亮堂堂,頭戴金冠光映映。手舉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稱。一雙怪眼似明星,兩耳過肩查又硬。挺挺身才變化多,聲音響亮如鐘磬”[5]。然而,在《大話西游》中,孫悟空80%的戲份以其前身至尊寶示人。至尊寶有著雜亂、沒有打理過的毛發,樣子十分粗鄙。在影片的最開始,至尊寶是一個黑店的土匪頭子,而且還中了昆侖三圣的七傷拳,絲毫沒有一點威風凜凜的樣子,這與《西游記》中戰無不勝的大師兄有著很大的差別。并且,因為七傷拳,至尊寶在后面的形象也有多處丑化。例如,在和現出原形的蜘蛛精春三十娘打斗時,受七傷拳所害,至尊寶只能倒著用手走路。甚至由于夜色太黑,被其他人當作逃走的蜘蛛精而被火燒、毆打,雖然小弟們后面聽到聲音停止了毆打,但至尊寶也被燒傷,整個畫面極其慘烈。
至尊寶雖然是五岳山的大當家,手下有一眾小弟,但是每一次在危難關頭,他都會遭到兄弟們的背叛,甚至出賣。比如在第一次對戰春三十娘時,至尊寶被春三十娘打落進水池里,但他爬上來之后卻信誓旦旦地說:“想殺我哪有那么容易,問過我兄弟們先。”可一回頭,他的兄弟們都跑完了。這種情況還有很多,而至尊寶也早已坦然接受。所以,至尊寶并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大當家,他的組織也只是一盤散沙。
在《西游記》中,大師兄孫悟空雖然不會像唐僧一樣只說佛語,但也不會滿口臟話,他的本質還是一個被唐僧教化了的佛門弟子。但在《大話西游》中,至尊寶卻滿口臟話,甚至在一開始還是孫悟空時,便對他的師父唐僧和觀世音菩薩不敬,甚至還要聯合牛魔王吃掉唐僧。例如,在至尊寶變成孫悟空后,只因十分不耐煩唐僧的啰唆就想殺死他,甚至還向觀世音菩薩抱怨,說唐僧就像一只蒼蠅,雖然從孫悟空嘴里說出的這段話看似無厘頭又搞笑,不過他對唐僧的厭惡之情卻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出來。
3.1.2 能指分析
一開始,至尊寶只是一個身受重傷、邋里邋遢又完全沒有威嚴的土匪頭子,在春三十娘和白晶晶到來之后,其形象雖然略有改變,但本質還是沒有太大的區別。隨著故事的推進,至尊寶從一開始只是為了救他的娘子白晶晶,到愛上紫霞仙子,再到最后為了唐僧及其他人不得不接受緊箍咒,放下心中的愛與俗世塵緣,成為齊天大圣,去拯救蒼生。但他卻沒有辦法救紫霞仙子,不斷加緊的金箍更是讓他在最后一刻放開了紫霞仙子的手,這也代表著齊天大圣在凡間的塵緣徹底了斷。在故事的最后,即使已經要和唐僧去西天取經,他還是幫助轉世的至尊寶和紫霞仙子喜獲姻緣。孫悟空拯救了蒼生,成全了有情人,卻還是被自己的轉世及所愛嘲笑:“你看,那個人他好像一條狗啊!”
3.2 意識形態層的孫悟空
3.2.1 社會環境變遷
至尊寶與大師兄孫悟空最本質的區別:大師兄是一個英雄,而至尊寶只是一個平凡的人物。這也是《大話西游》與其他孫悟空影視作品最為不同的一點。當然,這與至尊寶的扮演者周星馳也有很大的關系。1962年周星馳在中國香港出生,將李小龍當作偶像的他,對李小龍的電影與表演風格十分感興趣。受此影響,他也夢想成為一名電影演員。“小人物”“無厘頭”是周星馳電影的標簽與特有風格。在周星馳的電影中,很少能見到一開局就是“大英雄”式的人物,很多主角一開始都只是普通甚至有些卑微、可憐的普通人物,但是他們都會有一些不同尋常的經歷,在歷盡磨難、完成一些驚天動地的大事后,又都會化作過眼云煙,主角又成為蕓蕓眾生中的一員,過著平凡卻又不普通的生活。《大話西游》中的至尊寶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代表。
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經濟開啟了騰飛式的發展模式,人們的價值觀和文化理念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我國社會也逐漸進入現代化。而現代化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往往伴隨著世俗化。所謂世俗化,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神性的消解與人性的多元化需求。神性的消解,就是說社會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會逐漸擺脫宗教思維,作為社會的客觀主體,人類會以更加多樣化的視角和思維來理解或看待事物的矛盾及本質,以此來更好地認識世界、了解世界。基于此,自然而然就會出現眾多從個人視角出發的、極具個性化且多樣化的需求。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極具代表性的“無厘頭文化”也得以被受眾接受。在新時代,受眾更容易對有趣的內容產生興趣,而帶有濃重教科書氛圍的作品,若不進行創新,則難以吸引受眾的注意力。雖然這一變化有利于多樣化藝術的產生,但也容易讓人們忽略真正的時代精神。
3.2.2 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
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創作的《大話西游》,成功地將孫悟空這一英雄拉下神壇,使其成為一個擁有七情六欲的凡人。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進一步加快,中國人民在解決了基礎的溫飽問題后,逐漸開始重視并追求精神世界的滿足與享受。因此,在此期間的影視作品更加注重滿足觀眾的這一需求,“孫悟空”也從神壇上走了下來成為“至尊寶”。這一時期的受眾包容性更強,他們可以接受不完美但有著非凡經歷的人成為電影主角,并且會認為這樣的主角與自己的距離更近,甚至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但不可忽略的是,至尊寶也是孫悟空的一部分,《大話西游》也是對《西游記》進行解構之后又進行了二次建構。盡管至尊寶與孫悟空不同,但他是孫悟空的轉世,所以到了最后,孫悟空和至尊寶在大是大非上的選擇是相同的,他們都愿意為了拯救蒼生而奉獻自己,都愿意放棄自己的自由,不顧取經路上的艱難險阻,堅定地護送唐僧去西天,取來經書,普度眾生。
至尊寶的種種經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從側面映射出當時社會普通人的艱難與困苦。“所有偉大喜劇的內核,其實都是悲劇”這句話,恰如其分地總結了周星馳的電影。在《大話西游》上映的當時那個年代,雖然改革開放的進程已經加快,但當時的受眾主要追求的依然是物質水平的提升,再加上1986年版的《西游記》在受眾心目中有著不可動搖的地位,這就使得《大話西游》在上映最初兩年的票房十分慘淡,也不被各類專家看好。直到1997年以后,這部“偏娛樂化”的喜劇電影才在思想更加新潮的大學生中傳播開來,得到了真正的發展,開啟了“無厘頭年代”。
4 結語
《大話西游》的成功更重要的一點是它的分水嶺作用。從只知降妖除魔、護送師父取經的“斗戰勝佛”到為情癡纏的“至尊寶”,《大話西游》成為我國電影史上有關《西游記》影視作品的分隔線。在此之前的有關孫悟空的20多部作品,都將關注點聚焦在唐僧師徒四人取經路上發生的故事,但自《大話西游》之后的30多部作品,卻更多將鏡頭放在大師兄孫悟空身上,其個性更加鮮明,形象更加豐滿、突出,也逐漸獨自作為主角出場。這種變化及創作思路,對于整個影視市場都具有非常積極的影響,不僅拓展了導演與編劇選題的范圍,也使得他們制作出來的影片更加符合社會的發展,能滿足廣大觀眾的多樣化需求。只有創作出符合時代特征,與社會及人民同頻的作品,才能讓觀眾產生情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