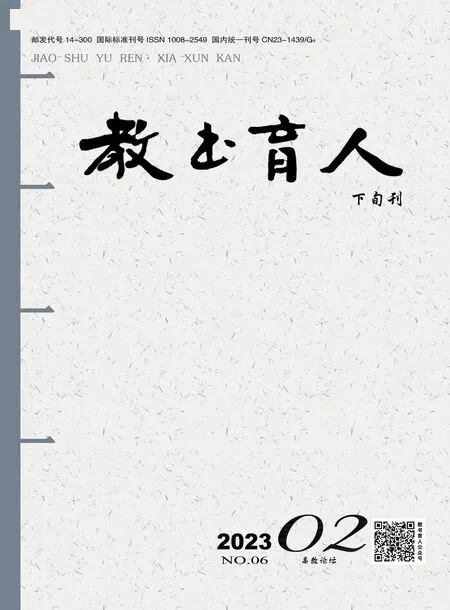“巨機器”批判視域下大學生信息工具依賴綜合征研究*
戴理達 (徐州工程學院金融學院)
一、問題的提出
教育信息化是一場技術打底、素養引領、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主旨的時代變革。2018 年教育部頒布的《教育信息化2.0 行動計劃》,倡導將教育信息化作為教育系統性變革的內生變量,引領教育現代化發展。現實生活中,有部分大學生對信息工具過度依賴,導致其學術功能隱抑、實踐主體性喪失,這成為當前教育界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為人才成長提供系統培養體系”,這也就意味著隨著技術變革與社會變遷,高等教育應將人才培養置于更為寬廣的系統環境之中,并且在教學實踐中,將技術因素定位于實現創新型國家戰略的引擎方面,而非學生心智與行動的“桎梏”。
近年來,“數智技術”與信息工具的融合顯著地拓展了學習場域,提升了學習的便捷性與效率性。但是大學生對信息工具的過度依賴,將導致“數字權利主義”的蔓延,信息依賴綜合征深度干擾著個體的成長路徑。長此以往,那些只能通過工具邏輯和數據思維去思考的學生可能降格為“數據(工具)原住民”。[1]由于較低的獲取成本與運用風險,導致那些“碎片化”信息在不知不覺中褪去了人的主體性與有機性。[2]當個體生命持續被動地接受算法的“反向馴化”時,學生作為生命個體應然的認知規律與學習節奏被屏蔽掉了,進而喪失對鮮活有機世界的深度感知與積極響應,這與教育信息化、智能化的社會意蘊相悖。教育承載的是人類的文明與理性,而非單純滿足社會“器物”之需;教育旨在響應有機世界人類心智的多元訴求,而非“構造”整齊劃一的、機械式的生存秩序與行動規制——“巨機器”。[3]誠然,一味地封閉或對抗信息技術無異于消極逃避,而通過“技術悅納”與“技術降噪”進行雙向調節,是疏解這一困境的理性選擇。本研究秉承大學教育的“行為指向觀”和“社會實踐觀”,借鑒芒福德的“巨機器”批判思想,緊扣學生作為生命個體在終身學習、職業成長中應然與必然的規律,探索“以生命尺度為邊界”的信息工具運用方式,以期通過技術馴化素養培育實踐,解蔽技術與工具對“人”的圈囿,重申信息工具的育人旨趣。[4]
二、相關文獻回顧
目前,關于信息技術變革與工具運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1)宏觀層面數智技術與信息工具的交融對高等教育全局的影響。信息工具的智能程度將保持持續性增長,高等教育應樹立終身教育的觀念,在專業調整、院系結構、辦學理念等方面及時變革,應對人工智能浪潮的巨大影響(劉愛生,2019);[5](2)微觀層面“數智技術”與信息工具的交融對高等教育局部的影響及其整合機制。高校教師應充分利用立體教材、數據分析、移動課堂等新型教學形式,重塑教學過程(施俊龍,2019);[6]丁玉祥(2020)結合智能時代在線教學質量評估標準的特點,從在線教學質量評價標準研制的現狀入手,以“信息協會版”為例,探尋了在線教學質量評價標準研制的背景、過程,并解析了標準的內容構架。[7](3)技術訓化素養視域下的數字規訓與消解策略。張家軍(2021)從身體、時間、空間、權力的四個維度探討了信息工具對教育的規訓景觀,并提出未來的教育應打破數字權力,重構新型學習空間,喚醒學生身體智慧,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超越虛擬依賴;[8]Sherry T(2017)指出,當前工具載體化的數字權利幾乎可以丈量一切,遮蔽了教育領域人文倫理關懷,因而應統合內外感官,回歸到“身心合一”的全人培養模式;[9]Gardner H(2013)指出,信息工具與應用程序支撐的電子幻象文化塑造了一代“數字原居民”,因此應在合理必要界限內使用工具,在“非虛假性”需求下規避因工具“惡意”使用而為教育場域帶來的隱性規訓。[10]
總之,從研究思路來看,既有的研究多側重單線模式,即技術及工具對高等教育的影響,而對雙向作用機理探索不夠深入;從研究方法而言,規范研究占據主流,基于大樣本數據的量化研究涉及較少;從研究內容而言,多是信息工具反馴化效應的規約,鮮有將其與受教育者“崗位人”與“社會人”雙重角色相貫通;對“技術悅納”與“技術降噪”雙向調節的作用機理探究不夠深入。
三、“巨機器”批判視域下信息技術與工具的育人旨趣
美國技術思想家芒福德(L·Mumford,1934)認為,現代技術的一個突出問題即“對有機世界的系統性背離”,整齊劃一、高度組織的“巨機器”泯滅了實踐主體的有機特征。這里的“巨機器”并非是對技術及技術體(工具)規模上的界定,而是旨在刻畫以“控制”或“權力”為特質的一元化技術秩序。這種秩序建立在整齊劃一的效率追逐基礎上,背離了人作為實踐主體的有機性與能動性。因此,芒福德指出,技術開發與工具運用應遵循心靈優先和環境均衡之原則,重申人的實踐主體性與人類需求的合理規定性,將人從冰冷的技術中解放出來,回歸到鮮活的生活世界中來。教育實踐若把技術與工具視為人的基本規定,那么依然沒有跳出“大機器”時代的思維禁錮。人的發展與幸福是教育信息技術(工具)的價值尺度,信息技術及其工具在教育領域的應用,應通過廣域開發教育資源、豐富教育呈現樣態、提升教育質量,來培養信息社會所需的創新型人才,使其能自覺屏蔽“社會分工性隔膜”和“自我封閉式”的職業意象,在積極融入生態化的群體交往中實現自身價值。在教學實踐中,應堅守立德樹人目標,厚植“以生命尺度為邊界”的工具運用觀,尊重生命個體的合理訴求,使學生獲得更為深刻的生命體驗與更為全面的個人發展。
當前,智能技術裹挾著信息工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以封閉的硬性方式追求效率目標,以“狡黠”而隱蔽的手段褪去人的有機性與主體性。[11]為了遏制技術的“蠻性”,有必要對其進行規訓,這就要求我們與技術互動的所有行動都要圍繞積極的生命需要。將信息工具的使用置于人與環境之間開放、持續的調適中,幫助學生跳出“知識閾值”,在新舊知識經驗的沖突中重構認知體系;幫助學生打破單純的效率目標“藩籬”,使其能憑借自身的興趣愛好主動喚起探究未知世界的欲望,激活知識更新、能力遷移與情感交互的潛質。此外,全球語境下職業競爭的權變特征日趨凸顯,技術馴化素養有助于勞動者在與外部環境演進相匹配的格局中,借助智能技術迅速而敏銳地捕捉各種信息,對職業環境的動態變遷做出及時響應;借助于網絡使信息作為跨越時空“零距離”交往與協作的媒介,使之成為延伸個體職業價值鏈的紐帶;通過信息工具同外界建立多維和諧的網絡關系,以豐盈生命有機體社會交互行為的內涵。
四、大學生信息工具依賴的表征與歸因
(一)大學生信息工具依賴的表征
第一,就空間維度而言,大學生在虛擬網絡世界被賦予了一種新的身份——“在線工具人”。指尖觸屏式的學習模式極大地節省了感知、表象、推理、歸納、演繹、分析等思維活動的精力成本與時間成本,使學生獲得了一種“在線比在場更具效率”的心理慰藉和思維定勢。教育場域各類隨手可及的極具視覺、聽覺、觸覺沖擊力的信息工具,極大地刺激了學生大腦對聲音、符號、圖像的感知,但弱化了對客觀世界的真實體驗,尤其是阻滯了高階思維能力的發展,使其逐步喪失了批判性思維,僵化了人與社會的互動。久而久之,信息工具在提升學生具象思維的同時,卻束縛了抽象思維的發展。大學生的身體陷入被“物化”與“數字化”的境地,算法所提供的大數據畫像成為價值取向乃至生命意義的主流評價尺度。
第二,就時間維度而言,“泛屏化”的學習過程使得那些不斷閃現的電子界面和觸屏操作,使學生陷入注意力持續跳轉之中,認知的穩定性遭遇破壞,人類固有的深度專注力和主動思維習慣被逐漸邊緣化。[12]移動微學習平臺在幫助使用者充分利用“碎片化”時間的同時,與持續的在線信息“聯手”,割裂了學生學習固有的生命節律。學生在線學習的任何一項活動都被賦予了整齊劃一的時間節點;一旦超過這一節點,在線評價系統便將其判定為超時任務或無效任務。這使得大學生不得不在數據時間所框定的學習場域內,“趕場”似的疲于奔命在各項學習任務之中;進而,學習演變為一種以機械時間指揮的、對教學資源“量”的追求。至于學習任務本身的達成度,此任務與彼任務之間的邏輯關系,任務達成過程中學生心智付出(投入)與認知升級(產出)的關聯性,均被屏蔽于學業考評體系之外。
(二)大學生信息工具依賴的歸因
第一,在當前的教育實踐中,信息工具運用導向出現一定程度的偏航。學校單純囿于學科發展或課程教學之需,將信息工具的運用固化為完成特定學習任務的一項技能。實質上,這種學習工具的定位混淆了“社會人”與“崗位人”的區別,漠視了信息工具對大學生終身發展的社會意蘊。“崗位人”教育理念側重于針對特定市場需求的“專才”培養。盡管在短時間內能實現學校——人才——市場的對接,但具有明顯的時空單一性,極不利于開放式競爭環境中知識與技能的動態升級;“社會人”教育理念從系統的角度出發,聚焦于人才的可持續發展。大學生在專業課程學習中,為了完成信息搜集、數據處理、流程設計、項目展示等任務,不得不沉浸于由數字構筑的世界。身陷于“虛擬實踐陷阱”的大學生將逐漸喪失與真實世界中實踐主體“人”的交流與互動;一旦走出校園,這些能運用數智工具完成特定崗位任務的“崗位人”,卻難以實現多維社會角色的適應、整合與轉換。
第二,從技術哲學的視角來看,信息工具自身的意向結構使其對教育數據的生成、采集、追蹤、評價與反饋具有“野蠻控制”與“智能束縛”,促逼學生在技術限定的關系中學習、生存,使其在被“去主體化”的同時形成了一種無形的精神依賴。這種極具隱蔽性和誘惑性的異化導致那些過度依賴工具規則的學生,只會用數據思維去思考問題,用符號式語言進行溝通交流,用程序性思維構建自己的認知體系,用格式化流程與世界打交道。久而久之,則逐步喪失了作為實踐主體的“人”對客觀物質世界應然的情緒感知與理性思辨。正是由于那些脫嵌于真實客觀世界的認知體驗便捷了基于數字游戲規則的學習過程,信息工具的使用逐漸演變為一種具有路徑依賴性的行動選擇,無形中給學生設置了一個“數字鎖定陷阱”。
第三, 當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升級轉型面臨著育人體系“特色化”與“標準化”的博弈,智能技術的運用激增了二者平衡的挑戰度。那些高度標準化、程式化、整齊劃一的教學評價體系為信息工具的“泛化”間接地提供了土壤。在數字鏡像的世界里,運算智能與感知智能將學生在線學習的過程數據與結果數據以標準化的方式實時呈現出來。每一項學習行動均被抽象為以“0”和“1”為代碼的信息進行存儲和傳輸,而那些無法進行標準化編碼的因素,如學生個體的心理資本,生生之間、師生之間有益的社會關系等,被排除在考評范圍之外。這種評價機制最大限度地規避了主觀隨意性,便捷了教學評價,滿足了當下教育評價的標準化、統一化與可視化要求,但不過是“巨機器”思維在新型技術環境下的一個“復生”。
五、“技術悅納”與“技術降噪”協調視角下信息工具依賴的疏解
從技術哲學的視角而言,對“巨機器”的克服并非意味著徹底打破舊有的技術秩序,也不是生硬地改變傳統工具的運用規則,而是在堅守技術作為“人構建自身與世界的中介”這一理念的基礎上,實現人與技術及技術體(工具)的共生。信息技術為人構建自身與世界提供了一種可能,作為實踐主體的“人”負責實現這種可能性,即技術的更新迭代與人類需求的滿足呈現出互惠共生的樣態——這一點與“技術可供性”異曲同工。“技術悅納”與“技術降噪”的相互調適,是人與技術共生的一個基本前提,尤其是在教育實踐中,這既是“人”生存體驗的開放性對技術目標達成封閉性的統籌,也是“人”生命樣態的多樣性對技術秩序單一性的補充。[13]結合當前大學生對信息工具的盲目依賴,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適度規約。
(一)尊重生命節律,通過學習與放空(Unlearning)促進認知躍遷
當海量信息充斥著教育場域時,“學習”與“放空”的適時切換,對于幫助大學生跳出“數字”成長空間、重塑高等教育內隱的人文空間有著積極現實意義。放空,既不是被動地接受與消極地放棄,也不是在既有的經驗與認知框架內固步自封,而是以空杯狀態接納數字化學習環境的“可供性”,通過心智放松、經驗修復、虛心向道,有效降低無效信息或負面信息對認知體系的干擾。
具體而言,首先高校應厚植“人本發展觀”,尊重生命節律,以學生生命感悟與社會體驗為切入點,引導他們正視當下非理性“內卷”潮。在教學過程中,適度放松學習任務的固有程序與評價模式,提供基于學習任務的彈性時間節點,將學生從持續而機械的屏幕跳轉中解放出來,使其獲得更多的靜心體驗、深度思索與愉悅交往的“內在時間”;其次,由于那些基于算法的學業評價體系窄化了“時”的變化、割裂了“時”的延展性、遮蔽了“時”的創造性,[14]因此高校應摒棄狹隘的教學效率觀和短視行為,打破機械時間對學生自主學習的圈囿,使其在“以身體之、以心驗之、以情感之、以文化之”的過程中汲取源于獨立思考的知識養分,提升自主探究能力。[15]
放空,不等同于放棄主動探索而只是被動接受信息。但現實情況是,信息工具的泛在使用極大地便捷了學生對所謂標準答案的搜尋,使其知識儲備演變成了智能技術的“函數”,諸如歸納、演繹、對比、推理等高階思維似乎喪失了用武之地。因此,為了幫助學生打破“被告知”的心理惰性,教師應有意識地拓展學習任務價值鏈,將上游的“動因探究、脈絡勾勒、路徑演進、關聯構建”,與下游的“存疑質疑、反饋評價、效應分析、趨勢預測”等環節充分融入任務體系,使學生能自主屏蔽海量信息對意義構建先入為主的干擾,在“信息放空——噪聲降低——信息甄選與重拾——意義構建”中實現信息技術的“可供性”。
(二)以勞動教育為契機,引導學生通過社會實踐重拾獲得感
由于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勞動的育人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勞動教育正被弱化。2020 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指出,高等學校應圍繞“雙創”教育,結合學科特色積極開展實習實訓、專業服務、社會實踐,使學生增強誠實勞動與公共服務的意識。“信息依賴綜合征”之所以頑固難愈,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數字構筑的虛擬世界里,人們不必過于擔心由于認知不足、情緒宣泄甚至言語攻擊所引發的社會評價風險;或者說,正是由于“泛屏”環境阻隔了人與人的直接交互,因此他們能夠獲得比真實物質世界中更豐盈的“存在感”與“獲得感”。
承襲芒福德的“心靈首位論”思想,可依托勞動教育這一載體,重申勞動的時代意蘊,引導大學生重新審視自身的社會角色與責任當擔。一方面,由于勞動是一種社會性的實踐活動,其過程與結果是實踐主體與真實世界互動的產物。因此,應將信息技術與工具嵌入高校的實踐教學體系中,優化“產—學—研—創”實習基地與業界的信息交互機制,使學生能夠感悟到勞動創造價值這一過程帶來的真實“獲得感”,避免虛擬學習空間造成的生命體驗與存在價值的抽離;另一方面,由于在線學習與真實物質世界的實踐通常出現一定程度的“脫嵌入”,因此高校可借助于勞動教育來推進二者的對接。勞動實踐并不為學生提供標準劃一的解決方案,也不提供隨手可及的搜索引擎,更不設定由算法“指揮”的評價體系,而側重于搭建一道幫助學生體驗客觀物質世界的橋梁。這就意味著,學生在實習實訓中必須通過自身的動手動腦“摸爬滾打”,獲得感性認識,通過既有的“舊識”構建“新知”,從而實現理性認識與感性認識的有機統一,實現身體真實體驗與心智成長的雙重優化。
(三)整合“崗位人”與“社會人”雙重角色,提升大學生技術訓化素養
“社會人”最初是作為“經濟人”的對稱而出現在人際關系學術中(E· Mayo, 1932),其內涵是自然人在自覺適應社會環境、遵守社會規范、參與社會實踐、履行社會角色的過程中,獲得社會的認可、情感上的滿足與精神上的愉悅;而“經濟人”則假定動機與目標的物質性是人發生社會行為的出發點。在此意義上,那些以特定的稟賦和固化的技能去滿足崗位之需,從而獲得物質回饋的行動者,被稱之為“崗位人”。“崗位人”與“社會人”都是通過社會實踐滿足自身的需求,只不過前者僅限于物質層面需求,而后者更傾向于精神與情感的滿足。從技術可供性來看,前者實現的是封閉狀態下預設目標技術的功能,抹殺了人類思維固有的批判性;而后者體現為在開放環境中對非預設目標技術功能的追求。
誠然,信息技術與工具固然能有效地活化人的實踐潛能,但若割裂了精神與物質的關系,純粹為了經濟收益而履行崗位職責,則有悖于職業生態的和諧共生。因此,高校應將技術馴化素養培育深度融入信息化教學全過程,利用數字技術與信息工具,構建時空邊界相對柔性的有助于學生獨立思考與知識遷移的學習場域,促進學生批判性、創造性思維的養成;打破專業學習與職業生態之間的屏障,以規避信息工具使用泛濫對實踐主體所帶來的諸如信息窄化、認知固化、學術功能隱抑等“反向馴化”的弊病,引導學生以積極開放、樂觀向上的姿態應對職業價值鏈的不確定性。通過虛實結合、空間重塑,將充滿真、善、美的存在價值教育融入學習空間,以避免虛擬學習空間導致的存在價值被剝奪;將基于信息場域的深度學習能力培育融入學生終身發展與職業規劃體系之中,拓展信息技術的育人場域,豐富專業人才終身學習、知識更新、能力遷移等素養之內涵,以實現信息技術與工具對人才培養“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辯證統一。